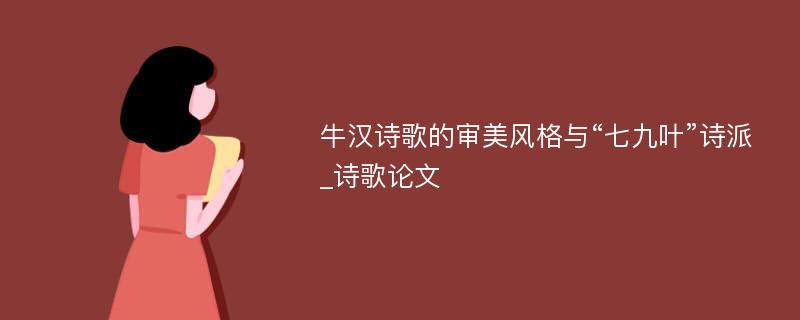
牛汉诗歌的美学风格与“七月”、“九叶”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诗歌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3-0089-06
“风格即人”,法国诗人布封说得好,诗的风格就是诗人的性格与风采形象地凸显。 风格的形成除受到作家主体的创造性改进等主观因素影响外,“还受更多的外在的指示 物,如社会的和地理的起源性因素的决定,而这种外在的指示物又可以重新被解释成风 格在一个场的内部所占据的位置。与所有这些不同的位置相对应的是它们在表达模式的 空间、在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空间、主体的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1](P89)牛汉诗歌 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多方面因素有关。牛汉生长在荒凉的大西北,残酷的社会境况和恶劣 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他身上流淌着蒙古族人的血液,这些因素造就了诗人硬朗刚烈、坚 忍不拔的个性,那雄强奔腾的美学风格,与现实搏击的魄力,真挚浓烈的情感贯穿其诗 歌创作始终。总体看来,他的诗歌充盈着阳刚之气、蕴涵着生命的力度美。
不过,牛汉是一个不喜欢受约束和被固定的人,他从未受制于某一种表现模式或审美 品格。牛汉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创新和自我改进,他的创作风格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与完 善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因此,他并不十分赞同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固守在某 一个流派的旗帜之下。长期以来,文学史家(以及政治家)将牛汉归属为“七月派”诗人 ,对此,他欣然认同,即使在最可能说“不”的时期,他都挺直脊梁。牛汉用几近半个 世纪的切身遭遇体会出“七月派”作为一个流派的真正含义。对于“七月派”,牛汉认 为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文学流派”,“ 不是自觉的组织联系,更谈不上‘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而是在“一个特定历 史条件下,在世界观、美学观、创作方法上互相吸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渐渐形成 艺术志趣大体上相近的一个作家群,客观上形成为一个流派。”诚然,作为“七月派” 成员,他本人从未有过什么“宗派意识”,晚年的他也很少强调自己属于哪一个流派, 在艺术追求上,他更未拘囿于此。对于自己的作品始终被冠以“七月”诗派之作,牛汉 保留着独到的见解,从他对“九叶派”诗人的评价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他的有关思想。 借此,笔者试图从“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的比较中探究牛汉创作风格的特点,以 及形成的文化因由。
1951年,《彩色的生活》被选入“七月诗丛”第2辑,此次是牛汉作为“七月派”作家 出现最为正式的一回。而十年前正是牛汉初涉诗坛之际,对于一个就读偏远山区的中学 生而言,诗歌仅仅是极为单纯的精神需要,促使牛汉很快走近“七月”派的,除诗人主 观情感的认同和“世界观、美学观、创作方法等方面”的吸引外,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1942年,牛汉报考的复旦和西南联大同时准备录取他,诗人回忆说:“两所学校都通 知我了,当时报西南联大就是奔着闻一多、冯至、朱自清他们去的,可惜没有路费去不 成,只有去西北大学。如果当时不在西北而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我很可能会成为‘九叶 派’诗人。”(注:根据笔者2001年9月30日采访牛汉的录音整理。)我们当然可以质疑 诗人的这种假设,却绝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牛汉在西北大学读书时,西南联大 有一个刊物叫《冬青》,负责人之一刘北汜经常向牛汉约稿,牛汉的诗歌也发表在西南 联大的壁报上,而且,牛汉经常投稿的《黄河》月刊[2]、《诗星》和《诗创作》也常 常刊发“九叶派”诗人的作品。从诗人主体情感方面看,牛汉虽然与“七月派”更为亲 近,然而,他从未否定或排斥过“九叶派”诗人。即使在40年代末,阿垅等“七月派” 诗人对“九叶派”诗人进行口诛笔伐时,牛汉也并未持有相同意见。在这里需要阐明一 点:“九叶派”是后人追加的流派,随着80年代诗集《九叶集》的问世,向世人展示了 当年的诗歌实绩,才有“九叶诗派”之称,它与那些一开始就明确打出旗号、有宣言、 有核心指导思想的社团流派有所不同。与“七月派”形成过程较为相近的是,“九叶派 ”诗人是在《中国新诗》、《诗创造》等非纯粹“九叶派”专刊上发表作品时,因互相 吸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走到一处。当然,他们有各自的经历和创作个性,但在客 观上确实存在诗风相近的作品,有相同的艺术观点。
作为40年代的两大流派,“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虽然分属不同的流派,但他们 之间却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40年代最富有活力的诗歌群体,他们的诗歌都凝结了 时代的感受,他们对现实和生命的关注都没有游离于时代风云。同样强调主体对客观世 界的感受,同样是关注生命,在“七月派”诗人那里体现为“主观战斗精神”,“九叶 派”诗人则发出“拥抱历史”的呼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出发点是强调作家的 热情和创造力,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 表现了主体观客体的主观态度,他用“肉搏”、“突进”、“相生相克”、“拥抱”等 紧张性的词语加以说明。胡风始终都坚信:文艺虽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又是用来进行社 会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但它必然是作者的内心矛盾斗争的产物,文艺作品不能离开 个人的灵魂与血肉,这就是他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其他“七月派”诗人一样, 牛汉在创作中自觉地实践着诗是诗人“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这一艺术观,他注重自体 生命本能的冲动,钟情于那些宏阔、富有冲突性的自然事物,对时代的关注则集中表现 为强烈的责任心和拯救意识——拯救苦难、拯救现状、拯救整个民族。
与“七月派”诗人相同的是,“九叶派”诗人也是一群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步青 年,他们置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里,用诗歌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传达 时代与人民的呼声。他们也重视反映现实,无非是不拘泥于再现现实的表层,他们主张 对现实要有一定的透视和距离,要深入到现实的里面去,反映现实的本质(这一点常常 被研究者忽视甚至遭到扭曲)。较之“七月诗派”,他们更重视诗的独立价值和艺术生 命,他们在坚持诗人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强调诗歌的艺术规律、独立 地位与价值以及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性、独特性与创造性,重视诗人的艺术个性。 正像21世纪之初,袁可嘉回顾“九叶诗人”的创作时所说:“九叶派”诗人认为“文艺 确有反映生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和表达作者个人情志的表现功能,重要处于在反映 者必须有自己的深切体验和独特艺术,不可概念化或标语口号化,表现者必须有真情实 感和艺术手法,不可陷于滥情或感伤。九叶特别强调个人心绪和人民心志的沟通,表现 方法的多彩多姿。”[3]40年代,“九叶派”诗人在尝试着用现代手法反映当时尖锐的 政治现实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他们使一度超脱尘世的现代诗充满了时代的喧嚣 ,很多“九叶派”诗人选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就足以证明 这一点。《诗创造》是一个政治倾向鲜明的进步诗刊,它正视现实并有一定的政治与艺 术影响,它要求诗作的大的政治方向一致,要求进步诗人们的大团结,反映出当时整个 国统区渐渐涌向高潮的现实斗争。《诗创造》月刊具体的主持人是诗人杭约赫,他本人 创作过不少辛辣的政治讽刺诗,也得到许多革命作家与进步诗人的支持;他与唐祈曾指 出:“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与这 艰苦而辉煌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来试验我们对于新诗的写作。”在诗 的对象领域方面,“九叶派”诗人不是单纯的面向内心世界,而是在写出时代的精神和 实质的同时力求个人情感与人民情感的沟通。为了更准确深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与 政治斗争,他们尝试着用现代的构思与技巧写出了一些具有深度的好作品,如:杜运燮 的长诗《复活的土地》,是一幅巨大的政治意象画,几乎勾画了当时世界与中国政治斗 争的整体面貌,其概括力之强,涵盖面之广当时还没有第二首长诗可比;另有唐祈的《 时间与旗》、辛笛的《垂死的城》、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等;从穆旦的诗中,我们也 容易感受到个人经验和时代内容的血肉交融、难扯难分,不仅是那些写战时一个民族共 同经历的艰难困苦生活的诗作,而且在另外一些他特别擅长表现的以知识者个人精神历 程的变化和内心挣扎为核心的诗作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可见,“九叶派”诗人对社会和 现实的关注与“七月派”诗人有极为相近的地方。
虽然如此,两个流派的诗人在创作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如果说“九叶派 ”诗人寻求的是诗与现实的平衡、追求社会性与个性的平衡[4](P26),那么,“七月派 ”诗人则注重人对诗、诗对现实生活的强力突入的美学风格,这一点尤为鲜明地体现在 牛汉早期的诗歌创作中。40年代初期是黑暗与光明、民族的苦难与民族的希望形成鲜明 对比的时代,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与同时期其他“七月派”诗人一样,牛汉的创作风格 呈现出明朗浑朴与抑郁忧患的强烈反差。诗人一方面以史诗般宏阔辽远的气势感怀民族 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命运,在历史的纵横交错中展现人民生活的苦难进程,以壮年的 豪情写下扬厉奔腾的诗篇,以激越的情怀展望民族的新生;另一方面,面对悲哀的北方 、逃难的人流、残破的土地和理想的阻遏,诗人郁愤满怀,他在诗中抒发着沉重的忧患 感伤。这一时期,牛汉诗歌的节奏变化与其美学风格彼此对应,舒缓的节奏和急促的节 奏各得其所,那强烈跳荡的节奏感,蕴涵着一种动态的诗美,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 里需要特别指明一点:无论是牛汉刚跻身诗坛,还是40年代中后期,他本人都未曾明确 意识到自己正在或即将与“七月派”发生什么样的联系。事实上,自从他在情感上向“ 七月派”靠拢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自觉实践着“七月派”作家的创作观,他以个体的 生命体验和情感价值观作为创作原点,从自我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艺术的原创力和雄厚 的生命强力,读他的诗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诗人主观情感的跃动以及主体个性的 张扬与舒展,这些都奠定了其诗歌审美风格的基调。
但是,“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创作上的分歧不仅仅是美学风格方面的迥异,相 对于“七月派”诗人对艺术生命与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紧密融合的创作观念,“九叶 派”诗人则更强调诗的艺术生命的独立价值,强调艺术性。“九叶派”诗人虽然关注现 实,认为现代人与现代政治密切关联,作为人的深沉经验呈示的诗,自然也不可能脱离 政治生活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现实和政治的关注是以诗要有其独立的品格为前提的, 是以诗人的个体本位为前提的,他们认为诗歌与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没有任何从属关系 ,诗的政治化和写作主体狭隘的“阶级分析”视角,都不可取。“九叶派”诗人是以个 人化的抒情步入诗坛的,他们追求的是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传统。然而,除朱健和 徐放以外,牛汉和大部分“七月派”诗人一样,他们都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无家可归 ”的胡风,参加过闸北战斗的阿垅,在“苦暗的雨中长大”的孙钿,曾经“长途跋涉” 的彭燕郊,绿原的童年的“痛感”和邹荻帆的“乡村的忧郁”等等。童年的不幸和初涉 人生的艰辛,深刻而痛苦地沉积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流浪与漂泊剥夺了他们求知的机 会,却给予他们书本上没有的血肉相搏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革命体验。苦难 带给他们生活与精神上双重的紧张感和反抗意识,他们的诗歌充溢着坚韧的战斗精神。 所以我们说,“七月派”诗人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更重视个人向社会整体的融合,强 调诗歌的社会性和战斗意义,他们强调做人与做诗人不能两分,是合二为一的。如同胡 风在给王晨牧的信中指出:“艺术第一呢,人生第一呢?这应该是早已不成问题的问题 ,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但不幸的是,对于许多诗人,这还 是一个常常被颠倒了的致命的问题,他们常常忘记了去掉人生就等于去掉了艺术。”[5 ](P76)较之艺术个性和创作手法,对现实和政治的关注被“七月派”诗人放在首要位置 上,他们作品中流露出坚定的现实主义的战斗情怀,这在牛汉40年代后期的创作中鲜明 地体现出来。
40年代后期,牛汉在艺术的经营和形式的约束方面深受“七月派”的影响,他有意识 地克制激情的自然流露,注重通过内在情感的充实弥补其诗歌缺乏凝练和细致的不足, 从而改变了以往奔泻无遗却内蕴不足的倾向,坚韧的战斗精神以一种内在的力量爆发出 来,呈现出厚重沉实的美学风格。同时,诗人开始注重把握生活的思想性并努力从个人 狭小的格局中跳出,将苦斗精神指向革命战斗和复杂的现实生活,与现实的人生并进, 与革命一同成长,历史情境与情境中人的相互渗透在他的诗歌中,几近水乳交融,诗歌 的表现力也有所增强[6](P26)。
“文革”时期,两个流派的诗人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被整肃打击的对象,他们失去言说 这一最基本的话语权力,创作转向地下,在“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流 露出忧患意识。牛汉等“七月派”诗人主要从主观精神、人格发展的层面表达非常时期 他们对生存状态的忧患意识,而穆旦等“九叶派”诗人则更侧重从诗学的层面感受人生 ,探索生命的忧患。在此,只要我们对他们的文化背景略加分析,就可以理解其差别所 在。就文化背景比较,“七月派”的很多作家都受到过俄罗斯文艺的影响,对牛汉文化 性格影响至深的也是俄罗斯文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诗人为自由、为祖 国、为人民而战斗的精神影响牛汉毕生。同时,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的用心写作而不是 “用脑写作”的艺术观促使牛汉苦苦追溯艺术的本源。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的“用心” 其实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看到的东西并不就是真的东西,真的 东西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的。潜移默化间,牛汉自觉实践着 “七月派”的创作理念。“文革”后期,牛汉的创作被笼罩在现实悲剧的氛围中,苦难 催生了他的人格力量,诗人从残败的意象中体认生命的本性,探索生命的真谛,构筑一 方独特的情感艺术空间。此时,诗人受难的悲剧感与俄罗斯作家自我流放的悲剧意识不 能说没有精神层面的关联。在失语的文学场、在失落的历史空间,在极度痛苦和寂寞中 ,牛汉重新找回诗性、找回自我。他在“文革”后期的“潜在写作”再次强化并提升了 “七月派”诗人崇尚苦难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的悲剧美,从某种意义上讲,牛汉已然成为 “七月派”精神的当代延续。而且,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询促使他走向更为高远的人 生境界和艺术意境。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九叶派”诗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素养,他们走上诗坛前 就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化底蕴。谈及40年代读穆旦的诗歌,牛汉说:“穆旦的诗我要读三 遍才能看懂,而别人的诗我却一目了然。第一次读他的诗歌是发表在《大公报》上的《 旗》,我认真看了。那时,我身边的朋友中也有人写这种诗歌,所以我不觉得陌生,也 不排斥,但我明显觉得穆旦的诗比他们的好。”不同的诗味,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 作手法,仅此一句就道出“七月派”与“九叶派”创作中存在的根本差异。从思想和文 化渊源看,“九叶派”诗人显然受到他们所热爱的英美现代诗歌和文论的影响,他们以 “非中国”的形式和品质,表达了中国人自身的现实和痛苦,他们对生命、对个体的呈 现是高雅的思悟,是睿智而理性的把握,并最终上升到哲理层面,具有学院派的风格, 但较之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们又多少显得不够纯粹。“九叶派”诗人善于熔铸中国传统 的文采与欧美现代的诗风于一炉,他们的作品是古典色彩与现代诗思相互交融的结晶, 即使是在荒蛮的年代,穆旦“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依然延续着其40年代就已经形 成的平衡与内敛的美学风格。
从文化根底、艺术视野方面看,40年代,牛汉及其“七月派”同仁的确无法与“九叶 派”诗人抗衡,他们的起点不同,但这一点丝毫不能影响牛汉及其同仁的作品在文学史 上所占据的地位,更不会影响其代表作品的经典性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牛汉真正 在诗坛上脱颖而出并奠定其在诗坛中的地位,并非因为他是“七月派”成员,也不仅仅 因为他在40年代创作了《鄂尔多斯草原》和《彩色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其“文革” 后期所创作的富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如《半棵树》、《梦游》、《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汗血马》、《空旷在远方》等。这些作品从思想深度、情感内涵、美学风格和艺 术表现等多方面体现出牛汉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诗人在思想、人格与诗艺上的超越,它 们已经超越于“七月”诗派曾经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作为研究者,我们无法苛求诗人 在40年代就完成这种内在的超越,当时,诗人正主动倾心于由个体走向和接近群体—— “七月”诗派。与诗派自觉的投入和融合的过程中,他尚且无暇顾及或根本没有考虑到 超越群体、超越自我,从其所谓的个性化的创作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烙印着“七月”诗派 这个诗歌群体的共性特征。
牛汉的超越诞生于“文革”时期内外挤压的精神困扰和生存境遇的艰难,苦难催生了 他的诗性意识的觉醒和新生,强化了诗人自我诘问、自我反驳和自我超越的主动心态, 他不再追求向群体靠拢,而是沉潜于对生命的深层巡视、哲理思考,尽量不让自己的创 作受到太多的外界约束。80年代以来,牛汉逐渐由放射性地表达情感转向深入博大的心 灵境界和神秘深邃的哲理境界,深入到生命自体的律动中,突出地表现情感内部发生的 冲动和运动,反复实践着具象与抽象、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等多元融合,这使得他 的不少作品都富有哲理性,蕴涵和放射着生命的活力、人格的光辉,其创作的美学风格 也呈现多元发展的走向,其中,超拔的美学风格尤为突出。
纵览牛汉半个多世纪的美学风格,我们看到,作为“七月”诗派的一员,就创作风格 而言,牛汉与该流派的关系几经变化:从40年代初的游离到40年代中后期的进入,由“ 文革”时期的创造性的发扬到80年代以降的彻底超越。晚年,诗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 考、对生存处境的关注、对自我否定和超越的尝试、对生活的哲理性探索、对理性统摄 感性的熟谙等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超现实主义精神、狡黠的魔幻色彩、深奥的象征内 涵和繁复的现代性意义,并在艺术手法、创作观念上与“九叶派”诗人彼有应和。
收稿日期:2003-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