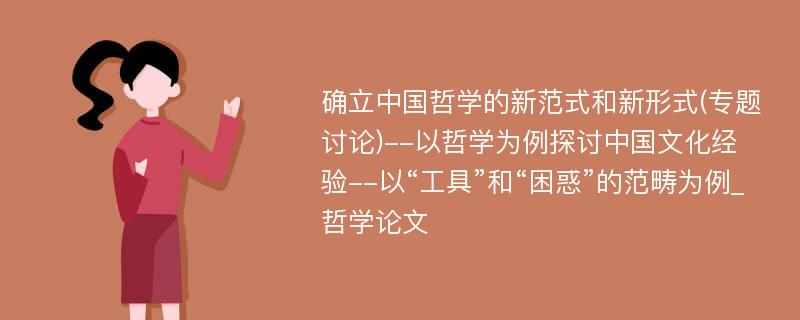
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专题讨论)——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为例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46-15
中国是否有哲学史与能否发展中国哲学研究,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问中国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同西方的哲学相类似的学术形态,后者思考能否进行体现中国文化经验的哲学创作。在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讨论中,这两者经常被混同起来,且前者往往被用来代替后者。其实,之所以质疑“中国哲学史”,不仅出于对古典思想认识的偏颇,也同对“中国哲学”现状的不满意有关。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确不尽如人意,表现为一种尴尬的局面。极而言之,要么是“哲学”而不“中国”,要么是“中国”而不“哲学”。哲学而不中国,指用很确定的西方哲学范畴与思路裁剪中国资料,削足适履,使固有的思想变得面目全非;中国而不哲学,则是局限于中国哲学的资料研究 (特别是出土文献研究),虽然这对古典文献学或思想史研究都有意义,但与哲学不在一个研究层次上。整个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对哲学的理解上。
我的见解是,要走出困境,必须改变习惯的思路,把焦点转到中国哲学研究上来,即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
哲学不仅要思考现成的理论,更要面对经验。经验有很多层次,有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经验,也有某种文化传统中的经验。反思前者的哲学是一般哲学,而探究后者如中国文化经验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当代中国,这两种哲学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但本文关心的是后者。经验有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而最重要的间接经验,自然是记述在各种伟大的文化经典中的历史文化经验。这种记述在体裁上分两类,一种是论说的,另一种是叙事的。哲学属于论说,而历史则是叙事。叙事与论说相比,其内容更经验化。读者可以以其文字为中介,重新想象、体验文本所记述的生活图景,所以更能激起道德与情感的力量。在中国经典中,叙事是主体。经典世界中的基本结构也与其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一样。按现象分类,我们则可分别以人、事、物为主题,对其人格理想与生活方式作多方面的探讨。因此,反思中国文化经验,必须注意其说故事的传统①。
哲学地反思经典思想世界的生活经验,不是对过去的故事作简单复述或者再创作。古典哲学是古代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故事的重新讲述也曾是古代思想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即使上述情况在现代社会文化中仍有存在的可能,这也不是哲学的主要形态。同时,尽管我们对照搬西方哲学理论编撰中国哲学史有异议,但得承认现代意义的哲学论说是西学的产物,它在论述西方文化的经验上有卓越的成就,中国哲学研究需要学习或借鉴其基本的哲学分析,包括概念分析与现象分析两种方法。
哲学论说的基本单位是范畴,它可以是传统固有的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对象,也可以是今日对传统文化经验重新所作的、具有原创性的提炼。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在范畴分析的层次上,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结对涉及宇宙、人生的概念,诸如天人、性命、善恶、是非、有无、物我、本末、体用、言意、形神、理气、心性、知行、道器等等,这些称为哲学范畴并不过分。问题在于,它们并非西式哲学范畴的对应物,但时下的哲学史学者却很容易往这一方向联想。最典型的莫过于把“道”与“器”看成是本体与现象的中式表达。虽然《易传》的确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界定道器关系,而且玄学、宋学也都有重道轻器的倾向,但它与把现象看成本体的副本或影子的西式世界观仍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易传》对“器”的内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有着丰富的论述与适当的强调。它甚至把三代的文明史描述为上古圣贤观象制器的过程。如果扣紧经典本文的脉络,综合《易·系辞》、《尔雅·释器》、《礼记·礼运》等文献中与器相关的论述,把器理解成文化哲学的范畴,或许比将其当作一般本体论范畴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基本经验。
器是人工制造物,其中部分是直接从自然物中选择而来的。器可分实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三种类型:实用性的器指生活与劳动用具;功能性的器是社会交换的辅助物,如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象征性的器主要是礼器或饰物。对器的这种分类不仅使认识具体化,而且有助于理解儒、墨、道三家对文化的不同层次的认识与态度。儒家重诗、书、礼、乐。孔子重礼,自然重器,主要是礼器之器,特别是祭祀用的器皿。《左传》成公二年记有他“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政治观点。孔子甚至把行为是否守礼或者说器的使用是否正当,提高到划分政治有道或无道的高度:“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孔子还以器喻人,批评管仲器小,说子贡是“瑚琏”,鼓励弟子成大器。作为对比,墨家也重器,不过不是礼器而是工器。《史记》说墨子“善守御,为节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是指会操器,包括一般工具与武器,以及重视节约资源。《墨子》中还有一组文章,专门介绍如何通过城械的建设及布阵进行城镇防卫的知识,其中相当部分即是如何制器的知识。一般来说,工器的使用者就不大可能是礼器的享用者。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会对工器和礼器两者采取相反的态度,因此墨家要“非乐”、“非葬”。道家是第三者,既不重礼器,也不重工器。如庄子拒受相位时,把“衣以文绣”的牺牛当作无意义的牺牲品,其实是对祭礼之器的亵渎;同时又借圃者之口,称“有机物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庄子·天地篇》),以为借机器追求效率的生活方式会影响道德的纯洁。而《庖丁解牛》的故事则显示,技比器更重要。儒、墨、道三家器观的不同,实质是各家对文明立场的差别或对立。
器的观念不仅同器的制作与应用相联系,同时由于儒家对器的象征意义的重视及其观器论人的方法,使器的概念超越了经验描述的范围。但是,只有到了《易·系辞》才将器与道相提并论,把可见的东西与不可见的思想对象配对成双。如此言器,才是哲学上的突破。虽然,玄学、理学都有重道轻器的倾向,但是从王夫之的“天下惟器”,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器”展开的却是相反的思路。王夫之一反传统的“道不变器变”或“道变才器变”的说法,提出“器变而道变”的观点,很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依循上述三大器类的划分来观察,就会发现器与道关系的变与不变,不能一概而论,而各有各的规则。简言之,实用之器是器道互变,功能之器是器变道不变,而象征之器是器不变而道变。因此,把器当作一般的现象,特别是理解为物,其实是把文明压缩成单一的层次,缺乏深度感的表现②。
这样的尝试,突破越抽象越哲学的成见,不是把器局限于本体论的框架中论述,而是放在观念史的视野中,当作探讨中国文化形成及古圣先贤对这一伟大经验反思的历程,其成果是文化哲学的收获。器是用以表达固有文化经验的传统哲学范畴,但是,重读传统的经史之学,不难发现仍有大量的、重要的文化(或生活)经验并未在对器的一般论说中被分析,因而它仍是有待挖掘的思想矿藏。
下面的例子,是关于“惑”的精神现象的讨论。
惑不是哲学的专业词汇,而是古已有之的日常语言。但它也有不平常之处:孔子有“四十而不惑”之说,韩愈的《师说》则把传道、授业与解惑界定为为师的基本使命。夫子自道是把不惑当作自己人生境界向上展开的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在此之前“惑”是其存在的问题。而韩愈的“解惑”是针对求学者而言的。依儒家传统,“学”的目的首先是学做人,去惑便是成人必经的重要历程。由此可见,在中国(尤其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惑是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对什么是“惑”,《论语》没有加以定义。但从孔子为学生解惑的种种例子看,宋儒认为解惑就是达“权”。“权”,即是权衡、取舍。这意味着,所谓惑,就是面对多种可能性、不确定然而又互相矛盾的局面,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的心理状态。它与无知及怀疑的心理现象有牵联,然而却不能与它们混同起来。惑不是无知。无知是对对象一无所知,一片茫然;惑是与固有的信息多少有联系,但出现矛盾,不能确定,因而引起混乱。惑与疑有时相连,但怀疑之疑与疑惑之疑也有很大区别:惑者感到困惑、不确定,也就是不自信;疑者则是不相信或质疑某些特定的意见或成说,而这种质疑一般是建立在另外的信念之上的,其实很自信,如疑古派之疑古。
“惑”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经验,不仅指它存在于不同的人身上,而且指它覆盖在精神的不同层次上,其问题包括认知与价值两大领域。认知有知觉与理智问题,价值则有情感及道德问题。儒家尤其是孔子所关切的问题不在认知,而在价值特别是道德方面,包括道德评价与道德抉择上。如对不守礼但成大事的管仲如何评价;对偷了羊的父亲该不该告发;遇到子不子父不父情形时应站在哪一边;等等。“四十而不惑”,不是指孔子变得神通广大,而是表明他以坚定的精神信念为前提,有了更丰富的处理复杂道德难题的经验。但是,经验是无限的,小到个人的情感危机,大到政治冲突的困局,孔子未曾面对过或者没法解决的“惑”总是存在的。有些“惑”是个人的性格引发的,有些“惑”则是时代性的。从王国维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集个性(情与知的矛盾)与时代(古与今的冲突)之“惑”于一体的例子。
从孔子、韩愈对“惑”的关注,导向对这种普遍的精神经验现象的描述与分析,其内容是一种中国文化经验的表达,其结论的有效性则并不局限于中国人身上。这种经验是历史上本然的存在,但只有纳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它才能在文化转型之际成为现代人的经验,或者与现代经验融会贯通起来。
“道”与“惑”是两个不同的例证。“道”是古老的哲学范畴,对它的讨论是通过观念史的分析,把其所依托或承载的经验内容揭示出来,让它洋溢着文化的力量。“惑”则本是一个普通名词,但是对它所标示的经验作进一步的描述分析后,我们可以打开观察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视角,或者深入到人性的某一区域。中国哲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思路或形态:像现代新儒家那样,建立宏大的体系是一种;从局部经验出发,对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切片分析,也可以很哲学。前者从具体到抽象,后者则从抽象到具体。其实,哲学就是具体与抽象或者观念与经验的双向通道。明乎此,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就能找到自己的本与源。
(附记: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
注释:
①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5)。
②参见陈少明:《说器》,载《哲学研究》,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