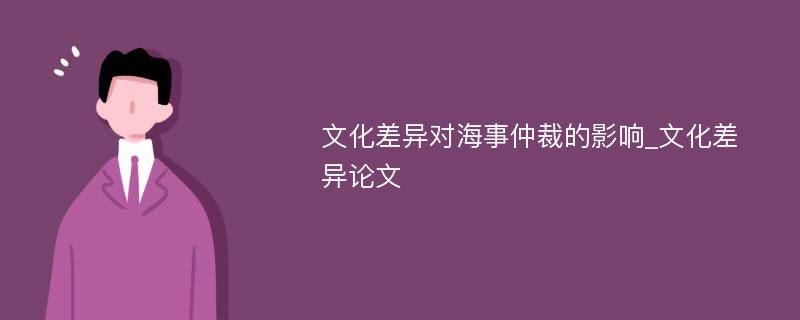
文化差异对海事仲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海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59-(2012)04-0106-05
几乎可以肯定,文化差异仍旧是国际仲裁中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而海事仲裁又是国际仲裁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其结果在最近大量的伦敦仲裁案件中有所体现。受此影响,在近期大量的涉及中国船厂与欧洲买方(或船东)的伦敦仲裁案件中,中国船厂几乎完全败诉。事实上,笔者从未听说任何一宗中国船厂胜诉的案件。虽然每个案件事实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众多败诉案件仍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许多伦敦仲裁案件都涉及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的船舶建造合同。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一,在大约一年半以前由马来西亚最高法院组织的吉隆坡研讨会上,受邀的演讲人之一英国的克拉克勋爵说,近年来伦敦出现的大量中国造船案件对于仲裁员或律师等是“一生的幸运”。其二,许多在英国主要的海事、商事大律师行工作的大律师朋友都告诉笔者,他们随时都在处理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案子,要么是作为大律师,要么是作为仲裁员。就笔者本人而言,过去三年中也在大约在三四十个案件中担任仲裁员。
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的船厂(当然也包括比较少的其他亚洲船厂,如越南船厂)遭遇如此惨痛失败的原因。从表面来看,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中国或亚洲船厂有利。因为,第一,依照英国法(通常是造船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当事人(造船案件中的买方)若想将对其不利的“市场风险”转嫁给卖方或船厂以从合同中脱身是非常困难的。第二,由于案件性质(译者注:即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船东往往想从合同中脱身),人们一般认为经验丰富且熟悉英国法律规则的仲裁员应当在事实或合理性判断方面同情中国或亚洲船厂。第三,几乎所有的造船合同都是根据以偏向船厂著称的日本造船协会格式(SAJ Form)拟定的。这也是BIMCO起草新造船格式(NEWBUILDCON)以平衡船东和船厂利益的原因。所以,显然不能认为中国船厂的大量败诉案件是签订自杀合同所导致的。
笔者曾听说中国船厂中存在一个共同看法,觉得伦敦仲裁法庭不公正。这也是在仲裁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普遍会有的感觉,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船厂所遭遇的如此众多的败诉应当有更深层的原因。
2012年5月在温哥华召开的国际海事仲裁员大会上,笔者就曾提过这个问题。许多重要的伦敦海事仲裁员参加了那次会议,但笔者并未从他们那里得到直接答复。只有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的秘书长Ian Gaunt先生公开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许多中国船厂“吃了过于宽容的亏”(victims of their own generosity)。
有些仲裁员说明了一些其他的原因,例如仲裁代理人的水平有限,各种形式的证据缺乏或缺陷,等等。这些情况也和笔者的自身经历相一致。据笔者总结,中国船厂败诉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差异”有关。
例如,在口头证据的质量问题上,中国的事实证人很少有能够在交叉质证(cross-examination)中表现良好并取得英国仲裁员信任的。作为一名经常与英国仲裁员组庭审理造船争议的仲裁员,笔者认为双方都存在问题。与笔者共同组成仲裁庭的一些外国仲裁员同样缺少对中国事实证人的了解,例如他们说话、撰写文件、(对另一方的行动)做出反应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局限性等。有几次笔者采信了中国或亚洲事实证人提供的证据,但是同样的证据却得不到同一仲裁庭的其他西方仲裁员的认可。笔者坚信自己的结论是公正做出的。不相信中国事实证人提供的证据这一问题应当是双方缺乏理解或互不信任造成的。所以除非双方(亚洲当事人和欧洲仲裁员)的文化差异能够消除或者变小,海事仲裁跟投资仲裁一样,也难以消除对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偏见。
一、文化差异在仲裁中的主要影响
在任何仲裁(包括海事仲裁)中,双方通常都有两方面的争论焦点。即:法律上的争议和事实上的争议。
(一)法律上的争议
海事合同通常采用英语书写。至于准据法,如果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中经过讨论,或者采用通行的标准合同(例如BIMCO合同),那么一般会选择英国法。这背后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根据英国法订立和解释合同具有含义明确、权利与义务清楚、解释准则确定等优点,因此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些反过来又使英国海事和商业法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准确性、合理性和公正性。此种美誉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司法机构可能都无缘获得,因为花费数百年时间确立并不断完善法律系统的机会已经不再有了。
当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时,文化影响通常不起什么作用。在很少的场合中,中国当事人会坚持在伦敦仲裁,但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香港,也存在这样的仲裁(和法律适用)约定:“在香港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笔者怀疑背后动机与人们认为的好处有关:当涉及文化差别时,中国法律会倾向中国当事人。但这不过是种错误观念。
(二)事实上的争议
文化差异对事实争议(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的影响是最深的。在实践中,许多案件主要涉及事实争议(例如造船纠纷),而仲裁结果主要甚至完全依赖于事实认定。仲裁员调查发现的事实必须有证据支持。事实证据表现为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如果当事人能够充分和准确地保管并提交书面证据的话,这样的证据当然是比较理想和可信的。此外,这种书面证据在仲裁中一般不易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许多只做文件审理的海事仲裁案件中,文化差异对案件结构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幸运的是许多海事仲裁(主要是租船合同纠纷)仅仅通过审查书面证据的方式进行。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协会完全成员(full member)2011年做出的裁决总数为592个,其中只有143个裁决是经过开庭做出。因此,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约75%的裁决仅仅根据书面证据的审理做出。
二、仲裁中证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书面证据的问题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文化中,采用书面形式记录事实是不受欢迎的。在中国,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在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也不例外。举个例子,在几年前吉隆坡举行的一次国际仲裁大会上,一名著名的马来西亚律师向Mustill勋爵提出了一个问题(准确说应该是投诉)。他说,在马来西亚将事情记录下来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说,如果你给政府部门写信,你将永远无法得到答复。最近笔者在报纸上读到,许多日本公司努力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公司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公司内部很少保留书面证据。
笔者认为,除非亚洲文化向好的方向发展,即学会习惯保留下完整、合理,甚至能够自证其权利(self-serving)的书面记录,否则亚洲公司将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保留书面记录不仅能在未来出现纠纷时作为证据,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对仲裁员而言,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因为他们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依照英国法律做出事实认定。而且,文化差异也会对亚洲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如果一位亚洲当事人无法提供一份详细的文件,就需要向一位西方仲裁员请求反向推断,习惯于西方公司做法的西方仲裁员就可能不会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证据没有被保留下来,从而对其做出不利的推定。
在亚洲当事人披露或者提供了详细的书面材料情况下,文化差异对于文件效力的认定仍然会产生影响。亚洲人的写作方式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仲裁员是否了解这一点将直接影响裁决结果。例如,即使面对对其不利的主张,亚洲人也不愿做出十分直接或直率的书面回应。所以,如果亚洲当事人对西方当事人的主张做出书面回复时,仲裁员将会发现这种答复往往是谦和有礼、迂回婉转的,甚至有推脱矫饰的嫌疑,这时仲裁员应当十分小心,不能轻易将之当做其论据软弱无力的表现,更不能将其作为直接承认错误的证据。
(二)口头证据的问题
在书面证据缺乏或者不充分情况下,亚洲当事人通常需要提供口头证据。这是此种情况下唯一能支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如果提供口头证据,开庭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应的程序通常是:先提交主证据(通常由提前交换的证人的书面证词代替),之后由对方律师对证人交叉质证(目的是使仲裁员对证人证词失去信任),之后由本方律师再次询问。开庭会是仲裁中十分重要(也十分昂贵)的一步,仲裁员在开庭中调查发现的事实通常决定案子的结果。这也是文化影响(或文化差异)最易产生问题的阶段。
事实证人说话和反应都有不同方式,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仲裁员听取或接受证据的方式也会因为文化背景有细微或巨大的差别。举例来说,众所周知,如果自家孩子和邻居的孩子打架,妈妈会倾向于相信自家孩子的“证据”,尽管这位妈妈也许熟知法定诉讼程序和自然公正原则,也决心在两个孩子间保持公正,但她肯定无法成为仲裁人,因为她存在先入偏见。
将以上情况扩展到国际仲裁,很明显,仲裁员不能和任何一方当事人存在金钱或其他非金钱(家庭、工作)关系。在实际情况中往往更为复杂。按常理,仅仅注意“关系”对于防止先入偏见的产生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还有当事人或者事实证人与仲裁员有同样的背景、基因、行为方式和/或共同的目标利益(goal interest)①。这些因素在仲裁中很少受到关注,例如,大多数标准仲裁条款或制度原则并不涉及此因素(除了国籍问题,这个问题笔者之后会提及),仅在很少出现的一次性使用的仲裁条款中涉及②。
三、仲裁中文化差异的实例
实践中存在大量文化差异的实例,以下举出几例说明。
例一:克里斯托弗先生提过一个例子,香港德普律师事务所的诉讼合作伙伴在《亚洲争端评述》(Asian Dispute Review)杂志2012年4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场对亚洲证人的交叉质证,证人与律师之间的对话如下。
律师:“你是否了解依照协议,如果你不能在最后期限前提供融资证明,我方客户有权终止合同?”
证人:“合同中是那样写的。但是据我了解,对此类大型合同而言,日期的微小变动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律师:“到7月1日我的客户有权终止合同,是这样吗?”
证人:“在商业交易中,法律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
Tahbaz先生说,问题就在于,从西方观点来看,法律确实可以适用于任何事情。如果仲裁员是西方人(这种几率比较大),亚洲证人就有麻烦了。如果仲裁员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呢?仲裁员仍旧会恪守西方的准则“法律适用于一切”,但多少会关注证人的错误观念,因为知道这是中国人当中十分普遍的一种看法(例如法律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即使要基于记录实际发生情况的证据做出判断,仲裁员也很可能会更重视其他的问题,例如:亚洲当事人是否提供过融资证明?这些证明是否充分?是否涉及弃权、禁止反言和排除原则等问题?如是,这些原则是否得到证明?等等。
例二:笔者同两位已退休的伦敦法官一起参加过一起伦敦仲裁,其中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位中国代表前往某欧洲国家,在停留期间签署了一份文件(形式合同)。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当事人是否就6艘新建散货船的销售达成一致。此行之后,船价大幅上涨。欧洲当事人坚持认为双方签署了文件,已经达成一致。而按照常理,欧洲当事人一定是对的。在交叉质证中,中国证人的解释是:“我必须签署一个文件,向上级和国家机关证明欧洲之行是有正当理由的。”仲裁庭的另两位仲裁员完全不能理解这个说法,但是笔者能够理解。中国证人进一步解释他的签字是有限制条件的,尽管这种限制令人难以理解。其他两位仲裁员同样不能理解,而笔者能够理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证人宣称双方经会议决定签署的形式合同不能代表最终协议,中国代表仍要就几个突出问题进行谈判,完成获取领导同意等手续。
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欧洲之行过后的通信和当时的文件非常可信。例如,文件清楚记录了几个突出问题的谈判内容。欧洲证人称,中国当事人意图在协议达成后重新开始谈判。但是看文件的内容和时间安排笔者却不这样认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起草的裁决书裁定中国当事人(或船厂)败诉。然而经过反复思考,三位仲裁员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中国当事人获胜,协议没有成立。
四、仲裁员的国籍
为克服文化影响所做的努力很多,其中很著名的一项就是国籍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多数仲裁条款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6条第4款规定:
“在指定仲裁员时,任命机构(指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应考虑所任命的仲裁员的国籍不同于当事人的国籍的可行性。”
国际商会仲裁院的《2011年仲裁和争议解决规则》第13条第5款规定:
“独任仲裁员或者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的国籍应不同于当事人的国籍。”
伦敦国际仲裁庭的《1998年仲裁规则》第6条对这个问题有十分全面的规定:
“6.1如果双方国籍不同,那么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应具有不同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国籍。
6.2当事人国籍应包括其控权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国籍。
6.3在本条中,若某人是两国或多国公民,其应被视为拥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机构仲裁规则》第11条第2款规定:
“若当事人双方国籍不同,独任仲裁员或三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不能与任意一方国籍相同。”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很多问题,确保任命的仲裁员拥有适当国籍。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注意容易误导他人。仲裁员和当事人的国籍根本不是问题核心所在。例如,由于笔者在殖民时代的香港长大,笔者长期持有英国护照,而一直没有中国护照。事实上,笔者连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都没有。笔者不认为任何仲裁机构会在有中国当事人或中国公司参与的仲裁中任命笔者做仲裁员,尽管笔者可以声称笔者和中国当事人具有不同的国籍。因此,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实质性而非表面上的国籍。
五、当事人对文化差异的应对措施
由于知名的仲裁机构难以采取有效方法减少文化差异问题,当事人自身采取一些个别的做法也许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其中一种做法是笔者之前提及的,就是坚持约定英国法以外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以规避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笔者曾说过这种想法其实是误解,因为法律不会被文化差异所影响。但笔者曾经听一位中国当事人提及,“香港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条款有较高的几率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一名懂得中国文化的仲裁员,因为适用的法律是中国法。
另一种比较类似的做法是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仲裁语言应为英语和汉语。从表面来看,这可以降低翻译成本。但这条规定使任命掌握这两种语言的仲裁员的几率加大了,而懂这两种语言自然可能了解这两种文化。
一种有争议的说法是,近年来仲裁地点的不断增多也与文化差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当事人希望在本国进行仲裁,避开传统的西方仲裁地点。例如,许多中国船厂决定将来在中国大陆进行仲裁,仲裁地点的第二选择是新加坡或香港。他们能否在现今的航运市场中达成所愿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在中国开庭比在伦敦开庭对他们有利。
六、文化差异与律师
如果了解双方当事人文化背景的理想的仲裁员很难找到,律师,尤其是为亚洲当事人辩护的律师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一位好的律师要为亚洲当事人辩护,必须懂得亚洲和西方文化。如果仲裁员是西方人,当律师为亚洲当事人准备开庭时,文化差异就要在很大程度上被考虑。有效的辩论是一种给适当的观众(即仲裁员)呈现完整、令人信服的故事的能力。
对大多数的亚洲或中国事实证人来说,第一次经历对抗式交叉质证绝对是相当艰难的。如果证人事先没有接受过训练,很难有出色表现。有时,一个看似有利的案子能因表现不佳的证人变得不利。例如,在交叉质证过程中溜之大吉、突发心脏病、和对方律师或者仲裁员发生争执等。甚至某案件中愤怒的中国证人对对方当事人和律师大打出手,连警察都出动了。
所以,如果一个案子有多个证人,律师最好挑选一名愿意并有时间接受培训,而且能够进行良好交流(英文水平并不重要,因为翻译人员在场)的证人。这个人可以不是职位最高的人,因为职位高低对作证并不重要。
为事实证人提供培训准备,可以有不同形式。可以是讲座的形式,也可以是模拟仲裁,让亚洲或中国证人在仲裁开始前熟悉作证。
模拟仲裁在国际仲裁中已并不罕见。当案件涉及巨大利益时,模拟仲裁可能会与真正的仲裁一样进行上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将从一群和真正的仲裁员有相似经历,相同专业领域,共同性格、态度和文化的人当中选拔出一个“影子仲裁庭”。仲裁双方都由来自同一律师所的律师代表。事实证人将像在真正的听证会上一样被传唤,并被交叉质询许多困难的问题。鼓励仲裁庭对事实证人的表现苛刻一些。整个训练包括许多工作,并且十分昂贵,但是成果也很显著。
模拟仲裁在美国很常见。美国律师和证人之间的接触也十分普遍。美国律师当然会遵守地域的限制,例如,《美国律师协会的专业操守准则》就涉及了证人的虚假证词问题。该准则第3条第4款b项规定,律师不可伪造证据,或帮助证人做假证,或对证人做法律禁止的诱导。但是引导事实证人熟悉仲裁流程,指导证人正确回答问题则是美国法律所允许的。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行为准则》似乎更严厉些,规定“严禁律师排练、联系和指导证人使用证据”。英国律师依照要求只能“使证人熟悉流程”。但是这是对法庭诉讼来说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仲裁,尤其是国际仲裁就难以确定了。
法国和瑞士法律则禁止律师和证人间的任何形式的联系。
总而言之,不同的法律体系做法大为不同,并且这在国际仲裁中也是个未解的难题。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很难或基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③。应该鼓励对亚洲或中国的事实证人在开庭前进行培训和模拟仲裁,以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
七、结语
总之,文化差异或文化影响的问题在仲裁案件中必须被合理解决或使其对仲裁公正性的影响最小化。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无法创造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国际仲裁系统。
注释:
①参见Exparte Pinochet Ugarte(No.2)[1999]1 All ER 577。
②参见Jivraj v.Hashwani(2011)UKSC 40。
③参见LCIA Arbitration Rules 1998第20条第6款,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0第4条第3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