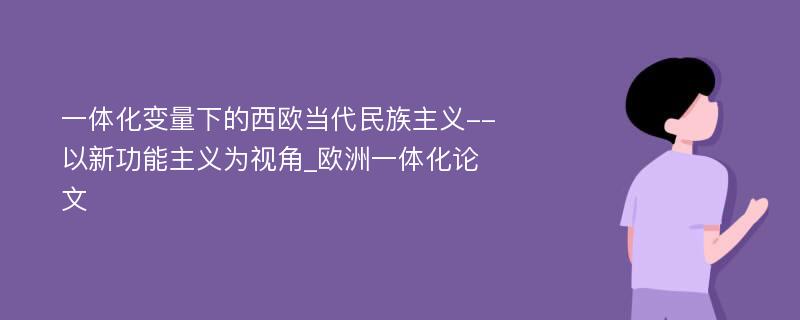
一体化变量下的当代西欧民族主义——新功能主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变量论文,新功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现代民族主义的真实基础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而主权民族国家构成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不断扩展与深入,无论是作为政治管治主体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构成及其权能形式,还是与民族国家密切关联的公众的民族主义认同与情感,都在发生着深刻而重大的改变。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假设是:欧洲一体化或广义上的区域一体化与民族主义演进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笔者已在他文中阐述了当代西欧民族主义的产生以及主要表征,即笔者所指称的西欧“后民族主义”。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究竟如何改变着西欧传统类型的民族主义或导致一种新型的“后民族主义”呢?其中的内部促动机制和内在逻辑线索又是什么呢?本文拟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就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一、民族、民族主义和“后民族主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族的传统定义大致包括种族特性、宗教传统、语言文化和地理方位等要素。或者说,这几个要素的某种结合成为对一个民族的主要判定尺度。由此而言,民族属性或个体的民族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先天既得的属性,很难实现后天习得意义上的改变,即所谓“一个德意志人无论他或她的英语说得如何纯真地道,也无论他或她在伦敦生活得如何长久(当然不是在其子孙后代的意义上),都不会因此而成为英格兰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nation)更多地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ethnicity),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概念(people),尽管不能简化为人种或种群意义上的概念(race)”。① 但这绝不是说,语言文化及其属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重要,而是说某一种族体往往拥有属于自身的独特语言文化。相应地,一个民族对上述方面的自我认同意识(我们)和与外界分离开来的自主意识(我们不是你们),就是民族的感知、情感和认同。
民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多地是一种近、现代意义上的概念,集中表现为某一民族创建或拥有自己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政治意愿与追求。② 从“理想”的角度讲,满足世界各民族上述意愿的最好方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直接性含义,也是所谓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表层含义。但是,近、现代社会条件下民族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实践,却导致了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与扩展:一方面是民族国家成为世界各国主体民族实现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特别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体间存在的事实上不平等,进而促发甚至激化这些少数族体的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要求。就世界范围而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近、现代社会中凭借其经济与军事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与掠夺,从而直接促动了这些弱小民族建立自己强大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政治愿望与斗争。因此,现代民族主义至少关涉到三个层面上的重要关系: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主权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强大主权民族国家与弱小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于近、现代欧洲国家特别是多为单一民族国家的西欧国家来说,一方面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及其意识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主权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甚至战争的频发。但欧共体乃至欧盟的实践表明,正是这些饱尝民族国家间战争之苦或狭隘民族主义之痛的西欧各民族,最先开启了超越主权民族国家间限制的欧洲一体化或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就长期性的制度化结果而言,欧共体乃至欧盟政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西欧国家政治管治权力重新分配或构建的过程,突出体现为主权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拥有的绝对统治或管辖权的终结。但是,“欧洲一体化”的完整意蕴不仅包括一个拥有管治权、自主权的民族国家向超国家层面集中的过程,还包括着一个拥有管治权、自主权的民族国家向次国家层面下放的过程。③ 也就是说,“侵蚀”主权民族国家传统管治权的不只是超国家的欧共体乃至欧盟,还有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管治主体。同时,至少从动力机制的视角看,“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如何更好地满足作为主权民族国家的欧共体乃至欧盟成员国的更广泛利益诉求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超国家权力对各成员国权力的赤裸裸的剥夺或集中。否则,人们将很难解释主权民族国家向形成中的超国家体的职权甚至主权让渡,以及围绕超国家体的创建和法律授权过程中的理性合作精神。换句话说,欧共体乃至欧盟各成员国之所以创建或加入欧共体乃至欧盟而投身于区域一体化合作,首先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基点的、试图调节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关系的过程,为此目标,它们愿意在自愿基础上不断地向欧共体乃至欧盟机构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透过这一过程,亦使人们看到当代西欧国家中一种“后民族主义”的产生。
概括地说,“后民族主义”是一种后主权民族国家时代的新型民族主义。一方面,经济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欧洲所提供的多重管治框架,不仅在政体制度层面上而且在更为普通的经济社会生活层面上削弱着西欧公众与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传统性联系。其结果是,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认同具有更多的理性精神与反思意识,与此相应,现代民族主义中隐含着的主权民族国家崇拜和传统民族意识中隐含着的种族优越性偏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内在性约束。另一方面,机构及其职权在不断扩张的欧共体乃至欧盟,同时为西欧各主权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少数族体提供认可并满足其利益追求的制度化渠道。这同时从诱惑(拉动)和迫使(推动)的意义上,使各主权民族国家和少数族体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采取一种更为理性合作的立场。与此同时,作为自主性的制度性主体,欧盟机构也在不断地通过其有效管治的政绩以及民主合法性的积累,赢得欧洲公众日益增加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为区域共同体意识或欧洲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基础。
当然,西欧国家的这种“后民族主义”仍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并与传统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对“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做出一种量化的描述,而只能更多地从对比的意义上来界定它,比如通过阐明现代民族主义的弱化来论证“后民族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即通过“一反一正、一弱一强”来归纳概括。“一反”是指它与传统民族主义方向的背离,“一正”是指与后民族国家时代相对应的民族主义的理性化发展趋向;“一弱”是指传统民族主义的诉求对象、手段与目标等所表现出来的弱化趋势,“一强”则是指在一体化背景下民众的欧洲认同不断强化。
二、欧洲一体化与西欧民族主义的演变
对于当代西欧民族主义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理应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加以分析。但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它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三个历时性的阶段:民族国家主权的转移、传统民族主义认同的弱化和新型民族意识的构建。
(一)民族国家主权的转移
即使站在人类21世纪初的立场上看,西欧民族国家间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能具有那样深刻的国家主权让渡的内涵,仍然是一件多少让人感到惊异的事情。时至今日,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论它们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有多高,都还依然很难触及关键性领域的超国家机构管治,比如在东南亚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笔者认为,欧洲的这种高起点的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启动,大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欧洲特性”得到解释。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使和平问题凸显和导致主权民族国家的声誉受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给人类社会的是灾难,这使和平理念进一步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作为战争策源地和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对战争的反思是更深层次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争之源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遭到了欧洲政治精英和广大公众的普遍质疑。这一方面使得人们更容易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虑和平问题,④ 通过寻求对主权民族国家的一种超国家制度性约束来消除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将这种超国家思维嫁接到至少与安全相关的领域,而这构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创议的源起。⑤
其次,欧洲精英们创制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或新功能主义的“欧洲一体化模式”。至少从“事后智慧”的角度说,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启动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欧洲之父”们所创制的渐进主义的或新功能主义的“欧洲一体化模式”。尽管有许多政治家像温斯顿·丘吉尔和阿尔蒂罗·斯皮奈利(Altiero Spunelli)等关于“欧洲联邦”的热情鼓动,⑥ 但政治家们最终采纳的是一种部门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路。事实证明,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共体”乃至“欧盟”,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并逐渐从“低政治”领域过渡到“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过程。很难假设,如果欧洲精英们当年选择了一个更加联邦化的一体化方案,随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呈现出怎样的情景。但是,1954年《欧洲防御共同体条约》被否决和半个世纪后《欧洲宪法条约》再次被否决,所表明的显然不只是主权民族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依然享有的重要权力。
当然,对于现实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它何以能够顺利启动,而在于它一旦启动后就具有不可逆转的前进动力,并且这种部门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思路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渐进性职权让渡以后,已经明显地产生了一种主权转移的后果。共同的煤钢联营政策、共同的农业政策、共同的原子能政策,也许都不足以对共同体内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构成实质性的侵蚀,但当它们结合成为整体并由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体系甚至货币制度来实施管理时,性质就几乎肯定会发生改变。同样,当超国家层面上的欧盟制度体系不仅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普通性国家政体,而且的确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机器那样运作并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民族国家主权的分割与让渡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实中还包括向次国家层面上的主权转移)。⑦
(二)传统民族主义认同的弱化
对起始于经济领域的民族国家主权转移的后果,以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的阐释,即经济部门的功能性需求“外溢”(spill- over)将会导致公众政治与文化认同向超国家层面制度机构的转移。⑧ 事实证明,就像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诸因素渗透其中的曲折过程一样,公众政治与文化认同向超国家层面的转移也是非常复杂而艰难的,但一个的确发生着的现象是传统民族主义认同的弱化。那么,欧洲一体化如何促动传统民族主义认同的弱化在西欧国家中逐渐发生呢?
首先,欧共体乃至欧盟制度框架下所彰显的共同利益、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弱化着人们源于某些先天性自然特征的民族意识。在民族国家的管治框架下,人们的民族意识更多地是通过某些先天性的属性来确定和维系,比如一个人所属的种族、血统、出生地和语系等。欧洲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交往、人员流动,并使人们日益认识并接受民族起源之外的其他集体性身份向度,比如共同的物质利益追求、政治与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就是说,在当今的欧洲社会,不同民族起源的人们完全可以成为同一个生活共同体中的成员,而民族身份之外的其他认同也可以促使人们结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结果,基于人们先天继承性自然特征的民族意识逐渐走向弱化。
其次,欧共体乃至欧盟制度框架所创建的多重交往性联系,冲击着基于主权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民族主义情感。建立在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无一例外地创建了民众间基于公民身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并依据公民权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利。应该说,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公民权随着民族国家的制度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而不断扩大,结果是公众对民族国家日益强烈的归属感乃至崇拜。尽管民族国家层面仍然存在,但欧洲一体化及其所创建的多重性制度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多维交往空间,各种区域性和地区性交往层面为欧洲一体化所激活。在这样一个多维交往空间里,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众相联系,由此基于一种排他性公民权的极端依赖(迷恋)性民族主义的基础就被大大削弱了。随着这种联系的事实性弱化,政治家们也就很难诉诸极端民族主义情感(种族优越主义和极端排外主义)的政治动员。
上述事实显然不足以说明,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情感本身的消失或被替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渐趋活跃的新极右翼主义政治和大部分国家的联邦化与分权化的政体改革,都是明显的反证。更进一步地说,欧洲一体化本身可能会成为刺激区域性、地方性文化身份复活的直接动力。⑨ 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甚至生活方式会消失在一个日益一体化欧洲之中的担心,许多少数族体希望形成更加具有政治色彩的区域共同体,直至主权民族国家。比如,巴斯克人、伦巴第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等,就是希望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来维持其民族文化认同。但从整体上而言,可以确信西欧国家公众的民族主义认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那种将民族意识与种族自然特征相等同、将民族主义情感与主权民族国家相等同的绝对性联系已经终结。这既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渐积性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条件。
(三)新型民族意识的构建
对传统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理性态度与反思精神,构成了欧盟层面上形成一种新型民族意识的前提,但如果把这种新型民族意识界定为一种(准)欧洲民族意识和对欧盟政体的认同,那么人们会发现,这方面的进展仍然相当迟缓。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大型民意调查《欧洲晴雨表》的数据表明,欧洲公众总体上说依然更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区域性共同体身份,对欧盟及其机构的认同度最低。⑩ 这既可以用欧盟层面上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认同之形成的滞后性来加以解释,也与欧洲一体化所选择的路径或者说欧盟所选择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认同的培育方式相关。
部门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路决定了欧共体乃至欧盟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直接面对政治文化认同这样敏感的话题,因而只能采用一种“绩效”与“示范”的制度认同培育方式。换言之,欧共体乃至欧盟只能通过促进经济一体化给成员国及其公民带来经济收益与社会福利,以赢得来自后者的不断扩大的管治授权与心理认可。在这方面,欧共体乃至欧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始于统一市场建设的欧共体,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括27个成员国、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10万亿欧元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1993年随着欧盟的建立而实现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标志着欧洲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1999年开始流通的欧元,则标志着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创建。在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经济交往日益便捷的欧洲空间中,欧盟公众可以更好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现在,欧盟成员国及其公众已经日益接受了欧盟这一超国家层面管治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欧盟的建立使得自身可以更多地从政体设计与政治文化认同培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如欧元样式的设计、欧盟徽旗、欧盟盟歌、欧盟日、欧盟统一护照、欧盟统一牌照、欧洲文化首都等。但是,欧盟在寻求公众政治文化上的超国家认同与归属感时也遇到了难题。一个例子是1992年发生的《欧洲联盟条约》批准危机,丹麦公众在第一轮全民公决中否决了该条约;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欧洲宪法条约》遭到了法国和荷兰公众的否决。这两个事件虽然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但也表明一个经济共同体在向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甚至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内在困难。(11)
作为经济共同体的欧盟,虽然需要来自成员国政府的管治授权,但完全可以采取一种“专家管治”的方式,只要这种管治的成效能够为公众主体所认可与接受;但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欧盟,首要的是公众的充分知情与民主参与,因而其很难凭借管治者的专家性质而进行自我辩护。这就涉及欧盟所采取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认同培育方式的特殊性问题。一方面,欧盟从成立之初就坚持把如何更好地满足成员国及其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这一“附属性”原则体现在欧盟的制度框架设计上就是把欧盟置于成员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在一个由理事会、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组成的“权力三角”中,代表成员国利益的理事会始终处于政治权力核心的地位,而更多地从欧盟层面考虑问题(特别是政体设计等长远性方面)的委员会与议会则处于从属性地位。(12) 不仅如此,这种制度框架结构很容易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成员国政府及大国首脑才是欧盟的真正领导者,欧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国际性组织而已。这样也就很难凝聚公众对欧盟权威的接受与认同。另一方面,欧盟还积极支持区域性、地方性共同体的民族自治要求。通过其制度框架下的区域委员会和区域政策,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型地区民族主义的促动者。正如克耶尔·古德曼所说:“欧洲联盟为欧洲人提出了一个新的选择,即由各个地区组成的欧洲取代由各个国家或各个民族组成的欧洲。在欧盟框架下,德国的联邦州、西班牙的自治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地区,获得了一种新的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它们可以通过区域委员会实现制度化。在国家权力上移的同时,地区的自觉性也在加强。”(13) 无论是英国20世纪90年代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相继设立,(14) 还是法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行政体制改革,(15) 都可以发现欧共体乃至欧盟政策影响的影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对区域性、地方性共同体的民族自治要求的鼓励甚至制度性支持,在弱化成员国公众对本国政府及其制度的传统性认同的同时,也对公众在超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文化认同抑或新民族意识产生了一种内在性抑制。
三、西欧“后民族主义”初露端倪
在西欧的一体化背景下,西欧的民族主义如何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族主义的“后民族主义”呢?考察西欧传统民族主义的新动向是验证“后民族主义”的第一步。
欧洲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民族时代。欧洲步入后民族时代是欧洲整合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一体化进程能够激励不同国家的政治角色认同并转向新的政治机构,以寻求采取共同决策或者是把决策委托给更高一层的超国家机构。这种超国家机构不仅代表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协调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有利于政治精英把他们的忠诚从国家层面上升到欧洲层面上去。因此,虽然霍夫曼曾经预言,欧洲的民族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固执的,不易击败”的特征,绝不是过时的角色,(16) 但就欧洲一体化近50年的历史看,欧洲原有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欧洲知识分子对一个统一的欧洲也越来越认同。“后民族主义”的精妙之处在于突破单一的民族认同,通过非政治化的文化整合机制实现了泛政治化的利益追求。
西欧一体化进程并非一路顺风,而是不断跨越障碍。在这一过程中,西欧种类繁多的民族主义正在逐步演化为西欧区域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并非已经形成,而是处在发生阶段。目前还不能说西欧已经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即:高度的欧洲认同、统一的文字、共同的一致对外以及整体民族的统一政治诉求。但西欧区域民族主义的演进与区域一体化是同步的。如果将西欧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做个比喻的话,那么,新型民族主义具备更多的理性与适应过程中不断增长的生存智慧,其宽容、平和、兼容并蓄的特色恰似大海;主体民族(法兰西、德意志、盎格鲁-撒克逊三者之间即法德、英法、英德)之间恰似来势汹汹的河水;边缘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则犹如江水,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矛盾一目了然;移民对单一民族认同的冲击犹如溪水,水流平缓,支流分散;比利时的两大民族之间和意大利的南北之间恰似湖水,表面平静,深处暗藏潜流。西欧的传统民主义将在一体化大势的推动下,汇入宽容、平和、兼容并蓄的后民族主义的大海。
四、新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理论思考
依据新功能主义理论的阐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民族主义演变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传统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弱化,二是一种新型的(准)欧洲民族意识和对超国家机构欧盟认同的形成。从西欧当代民族主义演变的现实来看,可以说,前者已经得到了较为明确的验证;而后者最多只是处于一种萌生性的阶段,并且依然有着不确定的前景。
对西欧当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性概括是它对传统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偏离或超越。对此,可以称之为欧洲一体化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否定性解构,而这种解构显然是一种与欧洲一体化相伴生的渐进性过程。但无论从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还是从它的目标设计来看,传统民族主义的解构都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产生一种超国家层面上的新型民族主义或“欧洲民族主义”。至少从核心理念和基本制度设计的视角来说,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由成员国发动并掌控着的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过程,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成员国及其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权的超国家政体。此外,欧盟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类似主权民族国家的准欧洲政体,对于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因此,欧洲一体化似乎不会轻易导致一个欧盟层面上的新型民族主义的主动建构。依此而言,起草并通过一部欧洲宪法对于欧盟的政体化发展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但正是这一点却很难得到成员国公众的理解与认可。
总之,现实中的西欧当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混合形态或过渡形态的民族主义,新功能主义理论可以对其中的一个层面即传统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弱化提供较好的解释,但似乎很难对另外一个层面即超国家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构建提供充分的说明。不仅如此,如果仅仅遵循一种新功能主义或渐进主义的思路,我们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一种欧盟从量变到质变的前景。那么,这种对西欧当代民族主义的“后民族主义”概括意义何在呢?在笔者看来,其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欧洲社会经过数百年的主权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发展后实现超越自身的可能性。
注释:
① Jurg Steiner,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Longman,1998,pp.257-258.
② Tim Bale,European Politics :Art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5,pp.4-6.
③ 郇庆治:《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④ Miles Kahler,"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i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Charles S.Maicr (ed.),Changing Bounderies of the Politica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⑤ 胡瑾、郇庆治、宋全成:《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49页。
⑥ 李巍、王学玉主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 Tim Bale,European Politics :An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pp.57-58.
⑧ Ernst Haas,Beyond the Nation- 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⑨ [英]戴维莫科、凯文罗宾斯著,司燕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⑩ "European Commission",http://ee,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12) 郇庆治:《欧洲绿党的欧洲化》,载《欧洲》,2006年第6期。
(11) Thomas Banchoff and Mitchell Smith(eds.)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London:Routledge,1999,pp.11-15.
(13) Kjell Goldmann,Transforming the European Nation- State,London :Sage,2001,p.78.
(14) 郇庆治:《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第316页。
(15) 胡康大:《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4—254页。
(16) Alain Dieck Hoffma(ed.),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Nationalism,Liberalism,and Pluralism,Lexington Books,2004,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