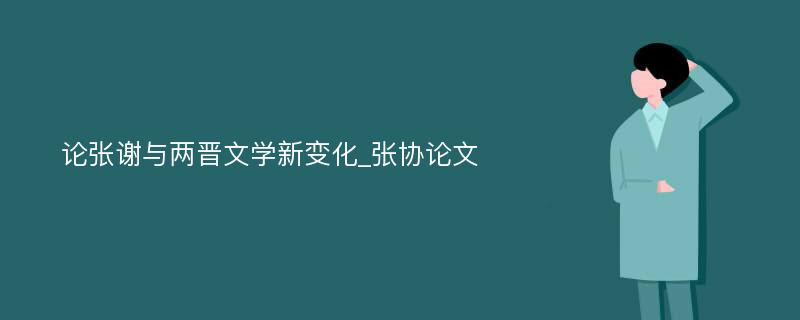
论张协与两晋之际文学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晋论文,论张协论文,文学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5-0162-05 张协是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南北朝时期的文论著作对其评价甚高。钟嵘《诗品》将张协列入上品,并评价为“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刘勰《文心雕龙》则曰:“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文选》共收录张协作品十二篇,分别为卷二十一《咏史诗》、卷二十九《杂诗》十首、卷三十五《七命》。然而,目前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显然和张协的文学史地位不相匹配。《文选》所录张协作品作于何时,其思想主旨如何,其文风特点及影响如何,张协作品与两晋之际文学演变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张协后期作品及其史事背景考索 《晋书·张协传》曰:“协字景阳,少有俊才,与载齐名。辟公府掾,转秘书郎,补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讬疾不就,终于家。”[1]西晋八王之乱至光熙元年(306年)结束,此前两年,诸王混战愈演愈烈,又有匈奴首领刘渊叛晋独立,氐人李雄据蜀自称成都王。其时百姓饥馑,生灵涂炭,可谓“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张协在永兴元年(304年)左右,“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大约在永嘉年间卒于家中。 厘清张协归隐的大体时期后,再来细读《文选》所录张协作品,根据相关史事,推断其写作年代。张协《咏史诗》李善注:“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故咏此诗以刺之。”李善注揭示出《咏史诗》的写作背景。西晋末年政治动荡不安,但仍有不少士人迷恋仕途,结果在政治斗争中无辜丧生。元康时期,惠帝愚痴,贾后专权,出现了“权在群下,政出多门”之类政权旁落的局面。永康元年(300年),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相继被杀,左思退居。太安元年(301年),齐王冏不朝,颍川处士庾兖发出“晋室卑矣,祸乱将兴”的慨叹。太安二年(303年),陆机、陆云兄弟被杀。张协目睹当时贪慕禄位者的不幸遭遇,表达出“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的归隐心声。因此,此诗当作于永兴元年(304年)张协隐居前后。 张协《杂诗》十首并非一时之作,但通过所写内容推测,大多作于晚年。其中有些诗篇直接写隐逸生活,可知作于屏居时期。如其三“高尚遗王侯,道积自成基”,其九“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其十“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真”。此类描写与《晋书》本传所载“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的生活状况颇为一致。有些诗作从写作心境上看,也当作于晚年隐居前后。如其二“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其四“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这两首诗皆感叹时光流逝,当作于晚年。其五“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旨在抨击晋末政治,和其《咏史诗》颇为相似,也当作于后期。其一“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以及其六“感物多思情,在险易常心”,二诗写作年代虽难以断定,但从表达出的忧患意识看,很可能也作于惠帝末年。《杂诗》其七、其八描写战事。其七“常惧羽檄飞,神武一朝征。长铗鸣鞘中,烽火列边亭”描写边境战乱,其中“舍我衡门衣,更被缦胡缨”表达出张协试图告别隐居生活,为国效力的志向,由此可推知该诗当作于惠帝末年至永嘉初年胡族乱华之际。其八“述职投边城,羁束戎旅间”,描写漂泊军旅生涯,当作于张协任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时,约在永宁元年(301年)左右。张协《杂诗》十首非作于一时一地,当为张协后期不同诗歌选编汇集而成,并非作者有意创作的组诗。但是,因大多作于晋末动乱时代,其内容主旨具有一定连贯性,因此可以当作特定时期的一组诗歌来加以研究。 关于《七命》作于前期还是后期的问题,学界也有争议。但从《七命》所写内容上看,《七命》当作于张协晚年,反映出他对西晋士风及晋末动乱的反思与批判。《七命》第七事着力描写“时圣道醇”的盛世景象,此段颂美之辞与西晋最鼎盛的太康时期并不相符,当是张协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永康元年(300年)以后,“天下荒馑,百姓饿死”,西晋社会呈现出丧乱之象。惠帝末年,屏居草泽的张协反思西晋社会的浮华风气以及晋末社会动荡不安,此时唯有开明盛世的出现才能够吸引张协再次出仕,《七命》恰好反衬出张协对于晋末社会的心灰意冷。因此,正如《晋书》本传所载,《七命》当作于张协隐居之后。归隐几年后,看透世事的张协并未再次步入仕途。 综上所考,《文选》所录张协作品大多作于其隐居前后的晚年时期。可以看出,张协《七命》与前期所作宴游赋《洛禊赋》、体物赋《安石榴赋》相比,思想内涵更加丰富深厚。其《杂诗》十首与其前期一些游仙诗残句相比,艺术境界也更趋成熟。张协作品前后产生较大变化,使其突破了西晋太康文学的束缚,引领着东晋南朝文学发展的新趋向。 二、张协作品主旨新变及其成因探析 太康文学重视作品的形式美而忽视内容主旨的表达,因此,刘勰《文心雕龙》评曰:“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身处两晋之际的张协对社会及人生进行反思,其作品主旨有了新的面貌,思想内涵愈发深厚。面对动荡的现实、突变的政治,批判现实与讽刺时事成为张协作品的重要主题。张协有感于西晋社会贪吝成风、进而谋荣的不良状况,对当时贪禄位者予以批判。张协《咏史诗》李善注曰:“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故咏此诗以刺之。”与左思《咏史诗》直接抨击门阀制度不同,张协采用汉代二疏“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的典故,表达出“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的隐逸情怀。张协通过二疏功成身退的正面事迹,试图劝诫“纳身于狂荡凶狡之中”的士人,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弃世遗荣的人生态度。张协作品能够批判流俗,抨击贤愚倒置的社会现象,此种思想在《杂诗》其五中尤为显著。该诗以《庄子·逍遥游》中“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的典故,隐喻西晋社会贤愚倒置。对于有德之士,西晋社会像越人不懂冠帽一样弃而不用。“穷年非所用,此货将安设?”向曰:“冠不用于越,将何所设之,此疾时君不用贤之甚也”。联系西晋社会,贾后专权,外戚受宠。八王乱起,一批小人得势,贤人因此受到打压与迫害。最后一句“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翰曰:“人皆不识贤愚之甚殊也”。张协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更是直指西晋政治的混乱局面,批判当权者昏庸不堪。此外,张协还对西晋浮华腐朽的社会风气进行批判与讽刺。在《七命》中,西晋社会的浮华风气被层层展现。“徇华大夫”试图通过“荣子以天人之大宝,悦子以纵性之至娱”劝说“冲漠公子”出山。其中所铺写的富贵荣华、声色滋味,正是西晋士人浮华之风的写照。“任情极性,穷欢尽娱”的风气弥漫士林,导致士无操守,游走权门,奢靡无度。张协通过“冲漠公子”之口对西晋浮华之风予以彻底否定:“服腐肠之药,御亡国之器。虽子大夫之所荣,故亦吾人之所畏。”浮华风尚令人生畏,奢侈无度,必将亡国。张协作品所表达的批评意识与两晋之交葛洪等人对于社会的反思情结有相似之处,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乱世的反省、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以及些许无奈情绪。只不过张协更能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通过间接的隐喻彰显其对社会的思考,因此表达相对含蓄,情感也较为真切。 反思现实之余,张协对于未来充满不安,其作品表达出浓郁的感物怀忧之情,这在《杂诗》十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杂诗》其一以“秋夜凉风起”发端,抒发“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之愁绪。李善注:“古诗曰:‘感物怀所思’,曹子建《杂诗》曰:‘沉忧令人老’”。良曰:“此时物忧气结之于心也”。时光迁逝之悲,对于汉末士人而言,是建功无门之慨叹;对于曹子建而言,则是年华老去之悲哀。而张协则将难以言说之忧气郁结于心,无法排遣。《杂诗》其二:“弱条不重结,芳蕤岂再馥。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济曰:“九州岛外有瀛海以绕人国,言人居于此中死生之疾如鸟飞于目前也。”昔日繁华不在,生命如飞鸟般流逝,失落之情油然而生。《杂诗》其四:“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氏卜。”向曰:“畴昔,少时叹岁时来迟。晚节,衰暮悲年华促也。”张协通过今昔对比,更凸显出暮年之阮。“将从季氏卜”采用《史记》典故,贾谊曾从司马季主占卜。张协用此典故,寓意自己也像贾谊一样前路未卜。“岁暮怀百忧”,有对生命不永之忧,有对西晋政局之忧,也有对百姓罹乱之忧……众忧交集,于是发诸斯篇。《杂诗》其六通过描写路途艰险,暗喻世道艰辛。“感物多思情,在险易常心”,翰曰:“感此山薮之物,思情多在此,险阻复有所惧,故易恒常之心。”张协告诫自己:世道艰险,要常怀戒备之心。此种心态在陆机诗文中也时常浮现,只不过陆机未能知足而止,最终被害。感物怀忧,像乐曲的主旋律,萦绕在张协心田,挥之不去。张协内心的迁逝之悲、无常之叹,不同于建安士人建功立业的迫切渴望,不同于正始名士的苦闷焦虑,也不同于太康文士的钟情适性。张协笔下流露的是看透繁华后的一丝悲怆,是身处乱世的些许忧虑,更是历经艰险后的无所适从。 现实动荡不安,未来飘忽不定,将何去何从?明哲保身或为最佳出路。《晋书》本传曰:“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在其《杂诗》中,张协或是寄托遗世独立的人生情怀,或是抒写无为养真的遁世之志,或是彰显固穷守节的道德操守,诸如此类皆是张协隐逸心态的真实写照。《杂诗》其三“高尚遗王侯,道积自成基”。李善注:“《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积道德者,天与之,地助之。’《庄子》曰:‘无为无治,谓之道基。’”张协离群索居,无案牍之劳顿,不为世俗所累,体现其逍遥物外的人格追求。《杂诗》其九真实反映出张协隐逸生活状态,其隐居之地较为偏僻且荒芜。“结宇穷冈曲,耦耕幽薮阴。荒庭寂以间,幽岫峭且深”之类的描述与史载“屏居草泽”的隐居生活颇为一致。就在此人迹罕至的荒野之中,张协“以吟咏自娱”,写出“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沈。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的诗句,表达其顺应自然、养性无为的隐逸之志。 《文选》所录张协作品篇目虽不算多,但内蕴较为丰富。张协作品主旨的新变,究其原因,首先与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导致的士风及士人心态的显著变化有关。西晋元康年间贾后专权,不少士人贪恋权位,躁进不安。永康以后,诸王争斗愈演愈烈,仍有一些士人游走权门,投身暗流。张华、潘岳、二陆兄弟等士人追名逐利,最终在政治风云中丧生。太康时期的“身名俱泰”,元康时期的“放达不羁”随之消逝,晋末士人从反思中走向清醒,由愤世嫉俗走向远离世俗。身处乱世,张协等人的作品更加关注现实,具有忧患意识。这是对汉魏风骨的回归,但不同的是建功立业之心泯灭,遁世避祸之志滋生,因此作品相对较为内敛含蓄,同时具有清新真切之美。其次,和玄学思潮的发展有所关联。“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是玄学思潮重要的命题。正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以嵇康的悲剧告终。太康时期,张华提出“柔顺文明”的玄学人格,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然而在晋末动乱的社会,此种尝试也徒然无功。“任自然”则过于放达,唯有顺应自然,方可在乱世中生存。张协作品中体现出批判社会、明哲保身的思想,更多的是受玄学思潮中庄子的影响。郭象《逍遥游》注盛行于东晋朝野,其“适性以为逍遥”的思想影响当时士人,张协思想与其颇有相似之处,可谓两晋之际的思想先锋。最后,和张协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张协前期身处西晋相对中兴的太康时期,生活安定、仕途平稳,其作品也顺应了“繁缛力柔”的太康文学主流。张协后期作品有对社会的反思,有时光迁逝的忧虑,有归隐情志的抒写,也有军旅生涯的追忆等。这些作品都是张协人生经历的实录,透露其历经繁华、忧患无依、遗世避祸的真实心境。 “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叙写时代之悲哀。“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可谓诗人之自况。“闲居玩万物,离群恋所思”,正是人格之写照。反思乱世、寄情物色、玄化人格,共同铸就了张协后期作品的文学主题与思想内涵。随着作品思想内涵的变化,张协的艺术及审美等发生变化,对两晋之际文学新变产生了诸多影响。 三、张协诗风新变之表现 提及西晋后期诗歌,论者多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之类玄言诗风为代表,实际并非如此。西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突变,百姓困苦不堪,乱离世事致使士人人生追求及文学创作发展变化。当时文士人格模式由太康时期的柔顺文明变为高蹈避世,他们摆脱幻想,更加现实,无法仕进、继而退守。表现在文学上,左思批判现实的咏史诗、郭璞寄托坎坷的游仙诗、刘琨慷慨悲壮的赠答诗,此类创作突破了采缛力柔的太康诗风的束缚,为西晋文学平添了张力与厚度。张协《杂诗》十首在晋末诗风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也颇值得重视,其华净清新的诗风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诸多影响。张协作品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回归汉魏文学传统、艺术上注重“巧构形似”、审美上趋向奇崛诡异等方面,具体如下。 1.张协作品秉承了汉魏诗歌艺术传统,在内容上关注现实,叙写人生,为西晋文学增添了力度。钟嵘《诗品》曰:“其源出于王粲”。张协继承了王粲关注现实、凄怨悲情的诗风。张协《杂诗》十首中有些诗篇直接描写社会动乱,通过写景状物抒发忧患情怀,这与王粲《七哀诗》有相似之处。相比而言,张协诗歌情感上不及王粲沉痛悲怆,但其内在无法排遣的忧思,反而使得张协诗歌作品更加隽永有味。除了继承王粲诗风,张协诗歌受《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以及阮籍等诗歌影响较为明显。迁逝之悲为汉末士人重要的文学主题,在《古诗十九首》中多有表现。张协《杂诗》十首中前四首皆以时节转换发端,其中内蕴与《古诗十九首》有相似之处,更有一些诗句直接化用之。曹植《杂诗》七首意悲而远,充满忧患。张协《杂诗》十首亦承此余绪,情韵悲凉。“离思故难任”、“沉忧令人老”、“俯仰岁将暮”、“忧戚与我并”,此类无法排遣的忧思穿过时间界限,在张协诗歌中再次呈现,汉魏时期的慷慨悲凉转变为晋末乱世的忧虑无助,同样凄楚动人。阮籍《咏怀诗》善用隐喻及象征手法,表达其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张协《杂诗》十首对此也有学习借鉴。张协《杂诗》其五“昔我资章甫”借诸越以喻流俗,其六“朝登鲁阳关”借行路艰难暗喻人世艰辛,此类作品将汉魏诗歌注重比兴寄托的艺术风格发扬光大。张协诗歌摒弃了西晋太康诗歌模拟、柔弱、繁缛之风,继而回归汉魏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传统。其作品将写实与寄托结合,融工巧于悲凉之诗境,对东晋南朝诗风的发展走向颇具影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景阳诗挥洒匠心,纵横尽情。尽情而不拙,匠心而不乱,其手笔固高,熟于古法也。”[2]正因张协充分吸收汉魏诗歌艺术传统滋养,更能将身处乱世的人生体会灌注其中,故其诗歌才能纵横尽情,打动人心。 2.张协诗歌在艺术技巧上注重“巧构形似”,为西晋繁缛诗风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东晋南朝山水诗创作也有所影响。所谓“巧构”指构思精巧、文笔工整,“形似”指描形状物、形象逼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3]可见,南朝时期“文贵形似”已经蔚然成风,但其发端者,当从张协开始。张协“巧构形似之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描写场景,动态多变。张协写景善于动态描摹,并将多种景物先后铺排呈现,有如蒙太奇般布景运镜。大段写景之后,再加以情语或玄思,使得诗歌情景交融,隽永有味。如《杂诗》第一首,该诗首句写时序,“凉风起”三字为全诗定下萧索情调。随后,张协充分捕捉动态场景,将视角在不同空间中互相切换。室外,蟋蟀在台阶下吟唱;屋内,飞蛾于灯下扑火,一派凄清孤苦之象。秋意渐浓,君子远役,而佳人孤独已久。思妇数年的执着等待,转变为不经意间的刹那凝眸:那充满期盼的屋前,并不见君子的足迹;唯有庭前的茂草,发出了新绿,更添了些许哀愁。环视室外,青苔早已布满空墙;放眼屋内,蛛网挂满屋角。“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孤苦之景充斥眼帘,无法散去;深层忧思藏于心田,难以言说。全诗通过思妇的视角转换,渲染出凄清孤寂的氛围,生动传神地烘托出一位思绪游离、心神不定、孤苦无依的思妇形象。 二是体物精微,形象逼真。张协观察细致,善于因物赋形,捕捉景物之内在特性,传达出物色之神韵。张协描写雨景,各不雷同。或是随风飘洒之急雨:“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或是密如抽丝之细雨:“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或是阴云密布之暴雨:“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或是绵绵不断之苦雨:“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此类工笔细摹,把握住不同状态下雨景特点,更将景语和情语融合,清新旷逸的艺术形象与诗人超迈情志巧妙契合,达到情景交汇的艺术境界。张协还擅长描写秋景,能够对声音、光影、色彩等方面展开细致描摹,刻画出生动逼真的自然景象。“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蟋蟀凄清的吟唱声与烛光下飞蛾扑腾的影像交织,共同营造出秋夜里孤寂幽冷的氛围。“寒花发黄采,秋草含绿滋”,秋雨过后,菊花焕发出鲜黄色的光彩,秋草蕴含着绿色的韵律,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观察力。“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旸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殷红的霞光与阴暗的浓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作随后极写秋物之凋零,暗喻生命之短促。王夫之评价曰:“佳句得之象外”[4]。张协描写景物形象逼真,更能将人生感悟融会其中,因此具有象外之趣。 三是炼字琢句,富于词采。张协描写景物,能够使用清新优美的语句,并锤炼出关键字眼,物色因此更加生动可感。“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诗句对仗工整、清新雅致。“洒”字将飞雨之动态美展现无遗,“栖”字则衬托出菊花之幽静。“龙蛰暄气凝,天高万物肃”,夏秋之际,节气转换,物色颇殊。一个“凝”字,暑热的夏季因此定格;而一个“肃”字,秋季萧索之气跃然纸上,令人如临其境。“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涌烟”及“散丝”设喻形象生动,将习以为常的“腾云”、“密雨”等物象描摹得富有动感和生命力。 陈祚明评价张协诗歌曰:“风气微开康乐。写景生动,而语苍蔚,自魏以来,未有是也。”张协写景之作在山水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值得重视。张协写景之作状物工巧,词采清新脱俗,用字生动传神。张协作品不同于单纯的比兴感物,更能体物缘情,通过景物描写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玄思,自然物色逐渐成为独立审美对象而存在。张协诗歌在表现手法、写作模式等方面对后世山水诗创作颇有影响,可谓东晋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之先行者。谢灵运山水诗体物之精微、字句之工巧颇似张协诗歌。如谢灵运名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此类景句通过光线的明暗对比以及时间的流转,刻画出变幻之物色,体现诗人对于自然美独到的捕捉能力,这正是在继承张协“巧构形似”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成。张协诗歌也有一些结尾表达出“高尚遗王侯,道积自成基”之类的玄学旨趣,此种由自然物色的工笔描摹再到体悟玄思的写作模式对后世颇有影响。如谢灵运山水诗写景之余,就多以玄思收尾。张协较早使用此类创作模式,只不过其“以玄对山水”的主观意识并不强烈,与东晋诗歌玄冥观照、物我合一之境相差较远,但张协诗歌注重从自然物色中悟道,其“道”多为老庄玄退思想,这在西晋写景诗至东晋山水玄言诗发展中起到了过渡作用。南朝时期,张协“巧构形似”之诗风余波回荡。钟嵘《诗品》评价谢灵运诗曰:“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5]201钟嵘评价鲍照曰:“其源出于二张。善写形状物之词。”[5]381《颜氏家训·文章》曰:“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6]张协一派诗歌以写形状物之工巧著称,其继轨者对此有所发展。谢灵运诗歌巧构而能放逸,放逸之余常有狷介不平之气;鲍照长于写形而能险俗,正因险俗故多奇警之语;何逊巧于经营而出之清新,风格清简而有俊逸之美。此皆“极貌写物”之余而又有“穷力追新”之意。 3.张协作品还扩大了西晋诗歌的审美境界,其“諔诡”诗风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张协诗歌不仅有自然清新的一面,而且有“諔诡”的一面。钟嵘《诗品》评价鲍照曰:“得景阳之諔诡”。所谓“諔诡”,是指奇崛诡异的审美风格。此种美学特质在《庄子》、《楚辞》等作品中有所体现,阮籍诗歌中也有一些此类风格作品。西晋太康诗人写景喜用优美的意象,营造出柔和典丽的氛围,彰显采缛力柔的美学追求。张协诗歌突破了时代审美特点,其《杂诗》其九、其十,多用奇异冷僻的意象,营造出荒凉凄苦的艺术氛围,开启后世奇崛冷峭一派诗风。如《杂诗》其九采用“穷冈”、“荒庭”、“幽岫”、“凄风”等一系列荒寒意象,描绘出诗人屏居草泽的凄苦状况。“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溪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冷峭无依、萧索阴森的诗境油然而生,给人以凄寒幽冷的审美体验。《杂诗》其十所表达出审美韵味在西晋诗歌中更是少见。诗人采用“墨蜧”、“商羊”、“飞廉”、“丰隆”等相对冷僻的神话意象,为一场苦雨定下宿命的基调。“沉液漱陈根,绿叶腐秋茎。里无曲突烟,路无行轮声。环堵自颓毁,垣闾不隐形。”此段描写从色彩、声音、形状多个层面展现洪水过后残破荒芜之境,张协通过穷形写态进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美感。此种奇异精警的美学追求对鲍照有所影响。鲍照诗歌因“险俗”著称,一方面其“俗”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另一方面其“险”则与张协“諔诡”一派诗风有所关联。鲍照《苦雨》之篇,《庐山》之作,《芜城》之赋,皆求“险”、求“异”,故含逸荡之气,富有奇崛之美,与张协“諔诡”诗风一脉相承。 总之,《文选》收录了张协后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水准高超,犹如两晋之际的一颗启明星,引领着东晋南朝文学创作的新趋向。虽然历来对张协作品评价较高,但提及太康文学时,张协的文学史地位往往容易被忽略。为何后世对张协及其作品关注不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文选》中还有不少这样优秀的作家作品,有待揭开尘封的历史面纱,进一步挖掘并加以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