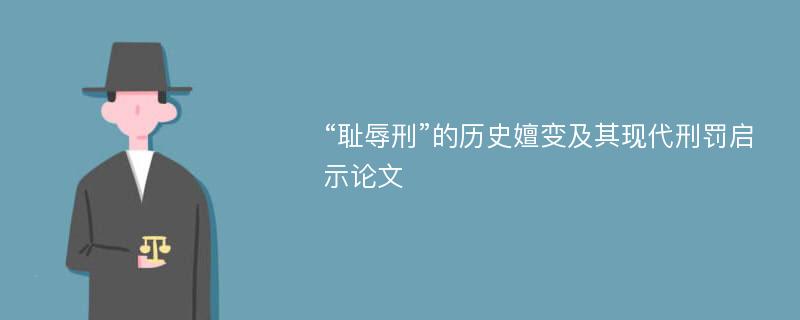
“耻辱刑”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刑罚启示
吴 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耻辱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独具特色的刑罚,由于其特有的强制性约束规范生成机理,因而能够历经千年受到统治者们追求。耻辱刑源于“象”刑,其刑罚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按照可否独立使用,可以将其分为真正耻辱刑和不真正耻辱刑。从现代刑罚理论和文明的角度看,耻辱刑是野蛮和反人类的。但是,晚近以来,随着美国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恢复性司法理论、重新整合耻辱理论,为耻辱刑注入新的内涵。改造耻辱刑落后、封建的色彩,在现代刑罚制度中彰显其现代刑罚意义,愈发显得重要、急切。
关键词: 象刑;耻辱刑;刑罚启示;重新整合型耻辱
在以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的古代社会,道德礼教被君主奉为统治民众,宣感教化的不二法宝。“礼义廉耻”被视为人之四德,是安身立命之本。同时,儒家思想重视人之“耻感”,并将其视为道德的基础。在《礼记》《尚书》《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无耻,无耻矣”“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表述表明儒家先贤们认识到“耻感”在指引和制约人们的行为和交往,引导社会风气方面的重大教育作用,将其作为管理国家的有效手段。中国古人将耻感进行发掘和深化,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1]最终,这种文化积淀内化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内生约束力,对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设置与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具有强烈耻辱色彩的古代刑罚手段,诸如象刑、墨刑、刺字、髡刑和枷号。包含着对犯罪人道德礼教的贬谪之义,以达到激活罪犯耻辱感的目的,使其感到罪恶、羞愤进而对自身行为感到懊恼、自责并寻求宽恕、原意回赎并进行补偿,[2]以期实现预防犯罪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至于明朝思想家吕坤提出“五刑不如一耻”。
总之,推崇德行、重塑世风这根红线贯穿《儒林外史》始终,为小说中一个个貌似零散独立的小故事编织了内在联系的纽带,使原本散落的珠玉连贯成耀眼的珍珠项链。
哈特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截然的社会规则,有的规则通过惩罚不服从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又有一些规则则是仰赖于社会成员对规则的尊重、信赖、悔罪或者自省来维持。毫无疑问,道德礼教的耻感教化属于第二种。但是在社会的转型发展和传统价值观的解构与重建的浪潮中,人们的耻感意识正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道德滑坡”“诚信危机”似乎预示着人们耻感意识的弱化和其内生约束力的式微。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功利主义观念的充斥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歪风逐渐有所抬头。甚至,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去实施犯罪、挑战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监狱行刑也有沦为单纯的“用刑工具”的倾向,而丧失“教育和改善”的人文化成属性。在当今整个社会重塑主流价值观念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发现和汲取古代耻辱刑的正面效应,实现“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则已实属必要。
城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主要有指路标志、预告标志、距离标志牌和视距标志牌,在特殊路段为了保证安全,需增设限速、限重和限高等禁令标志。城市道路较为平整,主要连接城市中各区域之间或各小区之间道路,交叉口较多,为了使交通参与者尽快到达目的地,每个路口均需设置相应的车道指示牌和指路牌,每隔一段距离还需设置限速标志,标志牌设置较为密集。而公路由于交叉口较少,只需在交叉口处设置指路标志和指示行车方向的警告标志就行,在靠近村庄的地方需增设村庄路名牌,标志牌相对较少。低等级公路由于线性指标较差,需增设其他一些警告和禁令标志,这是城市道路很少见到的。
一、 耻辱刑的源流与嬗变
耻辱刑上溯先秦,下至明清。不仅可以对犯罪人独立使用,还能附加于身体刑、生命刑,如弃市、凌迟等。其历经千余年而生生不息,为君主和司法官吏所青睐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耻辱刑不仅是通过司法制度维系社会规范,更像是一种政治仪式宣告着皇权的绝对与权威。福柯认为,对民众公开处刑具有独特的“司法—政治功能”,通过对罪犯的肉体施加痛苦的责罚来昭告君主权威的无所不在。通过司法适用的过程更多的是传导出重振权力的决心。[3]由此,古代耻辱刑不仅同儒家维护纲常伦理、道德礼教的内生需要暗自契合,更因其能够满足展示和树立君权的封建诉求。
(一) 耻辱刑的发轫——“象”刑
“象”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早在《尚书》中就有关于“象以刑典”的记载,《周礼》《春秋繁露》中也有类似象刑的描述。刑法史关于“象”刑的含义主要有一下几种解读:其一,象刑是一种象征性的惩戒。通过让罪犯衣着标记有特殊符号和色彩的衣物,向其他民众宣告其是受刑之人,以儆效尤。其二,有学者认为象刑,即“画象以示刑”,在器皿上刻画奴隶制五刑,使观看者受到警醒而不敢犯罪。其三,有观点认为象刑,代指“法”。即象刑是实施法律。[4]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象”刑,大抵是让犯罪人穿着特定装束,而与普通民众相区分开来。象刑的优点在于免除了犯罪人肉体上的痛苦,但同时在其精神上造成了难以修弥的损害。在以衣着显露尊卑贵贱的古代社会,犯罪人被贴上特定的标签,是对其人格和尊严的极大否认。尤其是判处象刑后,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和重视血缘宗亲的氏族家庭里,这被认为是极大的耻辱,因而犯罪人往往与原生家庭相脱节,是在社会评价体系内对于自己人格的极大蔑视。犯罪人的耻辱感将给其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内心煎熬,由此带给犯罪人的痛苦并不少于肉刑。
(二) 真正耻辱刑和不真正耻辱刑
根据古代耻辱刑是否能够独立使用,笔者认为可将耻辱刑划分为真正耻辱刑和不真正耻辱刑。
1.真正耻辱刑:奴隶制五刑。所谓真正耻辱刑,即指可以单独适用的耻辱刑。自夏禹制肉刑至汉文帝时期为修养生息废除肉刑,期间主要使用的是“五刑”。中国古代奴隶制五刑,①其中墨刑, 又称黥刑、黥面,是奴隶制五刑中最轻的刑罚。墨刑虽然在面部刺字,对受刑人的身体危害不大,但是在行为人的面部深深地烙上犯罪的标签,是对犯罪人极大的羞辱。让犯罪人赤裸裸地暴露在社会大众地目光之下,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与负担,可以说是耻辱刑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了。劓刑,是割掉受刑人鼻子的一种刑罚。其产生颇为久远,在《易经》中有,“其人天且劓。”在周朝时期,正式被确定为“五刑”之一。该刑罚在周代运用极广,以至于史记称“劓罪五百”。鼻子是人面部居中、明显的器官,割掉鼻子是对人容貌的极大毁损。受刑者往往不愿与人交往,从而消极避世。在周代受劓者往往被遣去守备边关,与世隔绝。刖刑, 又称剕刑,即断足,是指砍掉犯罪人脚部的刑罚。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刖者断绝之名,故削足曰剕。”自上周到汉唐,刖刑均是作为死刑的减等刑而存在的。被断掉一足或双足的犯罪人在外观上与正常人有明显的区别,没有脚部对受刑人的生活也极为不便,这种刑罚不仅在心理上羞辱罪犯,也是对罪犯肉体的极大折磨。宫刑,又称阴刑、蚕室、腐刑等,是仅次于大辟的一种肉刑。“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女人幽闭,次死之刑。”是阉割男性生殖器,破坏女性生殖机能的刑罚。汉代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后,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可见宫刑带给受刑人的痛苦。在奴隶制五刑中的墨、劓、宫、刖既是肉刑,又是耻辱刑, 而且是耻辱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产物。[5]
此外,弃市是一种带有耻辱刑性质的死刑。弃市是一种古老的刑罚,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在《礼记》中,“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描述的即是在公众场合对犯罪人执行死刑,弃市的执行手段多样,如斩首、腰斩、凌迟等。历朝关于弃世的刑罚选择也不尽相同。公开处刑,展现血腥的处刑画面是为了唤醒公众对罪犯的谴责,另一方面用最残忍的方式宣告皇权的绝对权威。
还有一些化学蚀刻剂在不同行业中应用,如盐酸-双氧水溶液、硫酸-过硫酸铵溶液、硫酸-铬酸溶液等,这些方法大多使用硫酸、盐酸等易挥发酸类,腐蚀过程都会产生有害气体,并不符合健康和环保的要求。
虽然目前边坡区降雨稀少,但随着雨季来临,降雨将是影响边坡稳定性主要因素,一方面降雨入渗使土体饱水,增加了滑体的重量,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降雨的入渗,使滑带土饱水软化,抗剪强度降低,力学性状聚变,从而促进了滑坡的发生。
2.不真正耻辱刑:明、髡、耐。不真正耻辱刑,即指可以作为附加刑适用的耻辱刑。明刑,始于西周时期,通说认为,让犯罪人身背一块木板,在木板之上书写其所犯恶行。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明刑是指明确法令、严明法律的意思。[6]东汉郑玄对“明刑”有注曰,“书其罪恶于大方版, 著其背”。在西周对处“明刑”的犯罪人使其背负方板在城狱中服劳役。到了秦代,耻辱刑的设置逐渐增多和完善,出现了不仅可以单独适用的耻辱刑,还能附加徒刑适用的耻辱刑,如黥、劓等。此外,秦朝律法还设置了单独适用的耻辱刑,髡、耐(或完)。髡,是指古代剃除男子头发的一种刑罚。耐(或完),则是只剃除胡须及两鬓毛发,而不剃头发的一种古代刑罚。与髡刑相比,耐刑刑罚较轻。秦代有髡为城旦、髡为城旦舂的刑罚, 就是在服城旦或城旦舂的主刑的同时, 附加剃去头发的髡刑。汉代的耐刑可以分别作为司寇、隶臣、鬼薪、城旦等徒刑的附加刑,即耐为司寇、耐为隶臣、耐为鬼薪、耐为城旦四种。[7]
(三) 中国古代耻辱刑的特点
1.用刑的符号性。耻辱刑的惩罚往往是以对犯罪人做出侮辱性的标志,例如在犯罪人的面部刺字、 穿着特定颜色、符号的衣物。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外在的符号在社会群体范围内以最直观的方式宣示着犯罪人的罪恶。如《尚书》中“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如履,下刑墨,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2.处刑的公开性。耻辱刑强制力的发生不在于对犯罪人生命、身体的高度侵害,而是在于处刑的公开性。耻辱刑往往以特定的、公开的方式对犯罪人进行处罚。无论是墨刑、象刑,还是大辟、宫刑,往往给犯罪人打上特定的烙印。这种烙印的镌刻依赖于处刑的公开性,在处刑的过程中通过刑罚的公开以达到耻辱刑强制力的警示,以期预防犯罪和教化民众。
中国古代封建刑罚大多以严厉著称,墨、劓、剕、宫、大辟等,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其所受的刑罚处罚不相适应。在以人道和刑罚轻缓化原则指导下的现代刑罚,对犯罪人科处刑罚应当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封建的自由刑、财产刑、身体刑给犯罪人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与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刑罚观相比,耻辱刑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减少受刑者身体上的痛苦,与现代刑罚轻缓化趋势相吻合。主要表现为如下:
二、“耻辱刑”传统价值的再提倡
耻辱刑是与肉刑相伴而生的,是报应刑观念下的畸形产物。报应刑理论认为,行为人不仅要受到身体的折磨,还要对其施加精神上的谴责。[9]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来,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被视为法治社会的核心,保障人权也被视为法治国家的不懈追求。在刑法领域中伴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禁止残虐的,不人道的刑罚观念逐渐形成共识。耻辱刑因其“违背人道、有损尊严”,遭到人们的唾弃和质疑。但是“某种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定是因为其暗合了社会发展的某些需求”,古代耻辱刑,或通过对犯罪者施加明显的犯罪标签,或公开犯罪者的犯罪信息,以贬损其人格使其负有精神上的负担。这种谴责和不利的负担,时刻警醒着犯罪者以及他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与他人关系的调整,告诫、规训人的自然冲动,不断赋予其社会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基层的司法政治资源需要,从而节省了社会治理成本。[10]耻辱刑以其独特的功能阻止犯罪的动机,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可以借鉴的价值。
(一) 有助于激活犯罪预防机能
国家制定刑律,设置刑罚的最终目的在于惩治和预防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态势以及修复因犯罪而破坏的社会关系。刑罚是刑法规定的必要且合理的“恶害”,是对犯罪人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剥夺,且对国家也具有诸多负面影响。刑罚的存在必须具有正当的刑罚目的,[11]唯刑罚本身并无存在之理由,其之所以成为国家制度,乃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被加以利用之故。[12]因而,刑罚的设定与配置要体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对刑罚的设置起到支配和调控的功能。质言之,具体的刑种的选择、量刑的安排要满足刑罚目的的需要。古代社会耻辱刑既可以与自由刑、财产刑和生命刑并用,也可以单独处罚。耻辱刑犯罪预防功能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澳大利亚恢复性司法学者布雷斯韦特提出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其将耻辱分为重新融合型耻辱与烙印型耻辱。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往往采用的是烙印型耻辱,通过给犯罪人施加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负担, 给行为人贴上犯罪的“标签”从而使其与社会民众相区别。烙印型耻辱追求刑罚的惩罚目的,通过降低行为人的社会评价和对其人格进行减损以使犯罪人产生耻辱感,并进而否定自身的行为以期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烙印型耻辱给犯罪人带来的持续性的人格减损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甚至再产生一条犯罪人与社会之间的鸿沟。[20]职是之故,恢复性司法学者倡导重新融合性耻辱,该理论尊重犯罪人的主体地位,而非将犯罪人作为刑罚的客体来对待。在重新整合型耻辱理论下,只要犯罪人真诚忏悔、积极改过,其就具有重返社会的可能,给犯罪人以希望。这种模式更注重犯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21]重新整合性羞辱是对犯罪人尊重性的谴责,它终结于宽恕,并将减少犯罪。[22]耻感是人类朴素而极具正义的感情,将“耻感”纳入现代刑罚体系,并作为刑罚设置与安排的重要要素,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激发犯罪人的耻感,使之成为改造犯罪人的重要方法。
2.特殊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已经犯罪的人适用刑罚进行改造,以期预防其重新犯罪。特殊预防的对象是已经犯罪的人。[14]耻辱刑激活了犯罪人的廉耻感,促使其恐惧、悔悟和羞愧,在一定程度上阻却犯罪人再犯罪,或者增加其再次犯罪的心理压力。[15]同时,笔者认为自由刑、财产刑等是“一次性刑罚”,刑期执行完毕,罚金缴纳足额,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便消灭,而无论其是否真心悔过,难以产生一种持续、长久的行为拘束力。所谓刑罚个别预防的功能也会因此丧失。但是耻辱刑却是一种“继续性的刑罚”,其所产生的刑罚效果会长时间伴随着犯罪行为人。另外,耻辱刑的特殊预防功能还体现对犯罪人打上犯罪的标签。当行为人日后在社会中实施相关社会行为时,社会民众就会仔细审视行为人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行为人也因耻辱刑增加了再次犯罪的成本,这有利于遏制犯罪,实现特殊预防的效果。
(二)有助于实现刑罚的轻缓化
3.施刑的象征性。耻辱刑是将人的肉体作为刑罚效果的载体,通过特定符号诉诸公众发生刑罚的强制效果。将人作为刑罚的对象和手段,刑罚的目的不是折磨犯罪人的肉体,而是通过刑罚所带来的羞辱,使其产生心理压力和负担。因而,古代的耻辱刑是野蛮和非人道的,不尊重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其耻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8]
1.耻辱刑作为重刑的替代。耻辱刑相较于其他刑罚而言,是一种轻刑。在威慑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下,耻辱刑的适用能给受刑者减少身体上的痛苦,体现国家的宽宥和仁慈。但是古代耻辱刑作为重刑的替代,主要是为贵族和封建统治者所享有的。如《礼记》中记载了“公族无宫刑”,即公侯士大夫犯罪当处宫刑时,代之以髡刑;再如西汉文帝时期,为了矜恤百姓,修养生息,对犯罪当处死者,允许其选择宫刑以代死刑等表明,耻辱刑的使用是其他重刑乃至生命刑的替代。
耻辱刑的使用在美国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美国最高法院也推翻了一项下级法院判处耻辱刑的判决;一些心理学家也指出,犯罪人受过耻辱刑后可能会在内心深处埋下犯罪的种子,并很有可能诱发他们再次犯罪。笔者认为,耻辱刑相较于生命刑、自由刑的最大优势在于唤醒犯罪人内心的良知与善意,以最小必要之伤害实现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的需要。耻辱刑不会伤及犯罪人的生命和身体,行使方式多样简易,在现代社会中仍有留存的余地。[25]
(三)有助于修复社会对立关系
刑罚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求,这种复仇的观念是人类当然的本能要求。而耻辱刑的适用则能快速平息民怨、修复受损的社会秩序。尤其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国家法律制度如若难以消弭受害一方对于正义的渴求,则可能引起次生犯罪。如司法审判没有权威和公信力,人民更愿意借助私力来满足其对正义的需求。古有赵氏孤儿,今有陕西“张扣扣为母复仇杀人案”等等。我们的立法者不得不有所警醒和反思: 惩罚必须具有适当的惩罚程度才具有威慑力。
如今,经过精心设计且在刑法理论上反复论证过的刑事司法制度显得精致完美,这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结晶。学者们希冀通过完善的设计安排使得刑事司法制度能够规范、统一地运行。但是,高度理想化的制度蓝图往往忽视了人们对正义的需求,即人们内心中存在的同态报复、绝对正义的渴望。当今世界各国的刑罚主要以自由刑、财产刑为主。同时还有自首、坦白、立功、减刑、假释等制度使得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变成可能。但是某些受害者看到自己的“仇人”或是提前出狱,或是缴纳罚金,亦或是被处以管制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处罚后仍能安然无恙地生活,认为不甚公平。所以说,耻辱刑的运用不仅是对犯罪人的谴责,更是对受害者精神上的最好慰藉。当受害者看到耻辱刑对犯罪人的贬损,很有可能放弃实施已计划好的“报复”行为。所以,耻辱刑的设置和运用具有良好的满足正义需求的功能。
三、将“耻感”融入现代刑罚的可能与探索
(一) 恢复性司法下重新整合“耻辱刑”
恢复性司法,也称“修复性司法”,是通过一系列修复性程序手段,达到修复性结果目的的任何方案。②美国学者希尔教授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一个过程,所有与特定罪行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如何处理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17]由此,恢复性司法包含恢复性措施与恢复性程序两个层面。传统司法模式认为犯罪是对国家规则与社会秩序的挑战,因而犯罪人被视为“敌人”位于“市民”的对立面,“被社会科处作为社会防卫手段的措施的法律地位”。[18]而恢复性司法的特征在于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并以社区等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从中协调,最终提出双方满意的方案。[19]修复性司法旨在为犯罪人提供回归社会的道路,从而对其在社会内处遇,以期其顺利融入社会。③
恢复性司法注重道德和法律的融合,但道德功能不是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充分发挥主体的道德责任感来解决刑事冲突。耻辱刑因其内在的道德评价内涵,能够为恢复性司法的提供新的理论进路。
1.一般预防。一般预防,即刑罚是维持法律规范的手段,通过刑罚的惩罚效应达到尊重规范的目的,唤醒和强化公众对法律规范的信赖与忠诚,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13]换言之,通过对犯罪者进行适当处罚,以事实证明刑法规范的妥当性,从而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实现一般预防。象刑、墨刑和枷号等耻辱刑罚,均是对犯罪人身体施加特有的印记,或是公开犯罪行为,降低其社会评价。在弃市、凌迟这类生命刑的执行中,同样包含着对受刑者人格的侮辱。残酷的刑罚和不人道的刑罚并用,彰显出君主权威的至上性和不容侵犯性,受刑者对民众还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提供商业贿赂的线索来源途径少也是“葛兰素史克事件”所暴露出的另一问题。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侦办商业贿赂案件的线索主要来源于群众举报、当事人自首以及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案件的移送。当事人之所以实施商业贿赂行为,是因为双方都从商业贿赂中获得利益,出于该考虑,往往会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盟,因此依靠当事人自首来发现商业贿赂的线索,可能会影响查处商业贿赂的效率。
显然,f=0对应于没有单向边的原始网络.如前所述,更大的测度指标G和更小的测度指标S表明网络抵制级联故障更强的鲁棒性.根据G和S两种测度,随着β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节点增加了额外容量来接收从其它节点重新分布的负载,从图2可以看出,在给定f的每种DD策略下,网络鲁棒性如所期望的一样增加.此外,图2表明,当f≠0时,带有任意DD策略的网络比没有单向边(即f=0)的原始网络(Original)具有相对较好的鲁棒性G和S, 但随着f的增加,网络鲁棒性的变化不明显.这不同于文献[16]的研究结果,即边定向方法会降低ER网络抵制级联故障的鲁棒性,这源自于所采用的不同的负载分配机制.
(二) 当代美国“耻辱刑”的再兴
耻辱刑在西方渊源甚久,最早可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寻得踪迹。近代以来,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使用耻辱刑。与中国一样,美国的耻辱刑也分为单独使用的耻辱刑和附加使用的耻辱刑,前者如强制通奸犯胸前佩带红“A”的耻辱标志,19世纪八十年代强迫华人剪掉辫子等;后者如烙刑、割耳刑、鞭刑、斩首刑等。19世纪以后,美国耻辱刑逐渐消失,监禁刑成为最常用的刑罚。但是当今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监禁刑难以满足行刑的需要。于是美国一些地方的法官开始重拾耻辱刑这一古老的刑罚。美国司法实践中首次运用耻辱刑理论做出的判决源于德克萨斯州一法官在“虐待学生案”中对老师判处其20年内不许弹奏钢琴,并且让其张贴警示未成年人不要靠近他住宅的惩罚。在该案中,法官不仅对其判处刑罚,还附加对其判处某些“自取其辱”的刑罚内容。在美国其他州的司法实践中,还做出了大量具有耻辱刑色彩的判决,如在报纸上刊登性骚扰犯的照片和信息,让小偷手持认罪书在公众场所示众,让醉酒驾驶者在自己的汽车上标志安全告知等。[23]这些判决引发了诸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判决实质上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刑法的泥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判决产生了良好的司法实践效果,耻辱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积极效应逐渐得到伸张。[24]
2.耻辱刑作为一种轻刑单独适用。将耻辱刑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犯罪人思想的刑罚,有利于从思想上控制和预防犯罪,从而减少生命刑和肉刑的使用。儒家认为刑罚违背自然规律,所以主张礼乐刑政,反对不教而诛。[16]耻辱刑作为一种轻刑主要适用于轻罪、主观恶性不大和初犯的人,体现了对犯轻罪者的宽宥。可见,耻辱刑对犯罪人有轻缓刑罚、体现宽宥之意。因而,不可否认其在刑罚宽和、刑法谦抑方面的积极意义。
我国中小学的教师每天都会给学生布置好作业,这使学生从小就产生了依赖性,离开了老师或者家长的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就没有了规划。这种灌输式、集体式的教学方式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仍沿袭着中小学的模式,以课堂为主,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大学期间学生的思想在成熟阶段,这个期间忽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发展,会阻碍学生的求知欲以及遇事时自我判断独当一面的能力。
(三) 对于耻辱刑刑罚设置的几点思考
1. 由于耻感文化容易给犯罪人贴上犯罪的标签,不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而西方推崇的修复性司法理念主张利用耻感对犯罪人进行改造的同时注重犯罪人和社会的联系,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沟通与协调,创造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可能。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等社会危害性较低的犯罪人适用刑罚的过程中要避免“烙印型耻辱”,在对其行为进行谴责的过程中应重新整合耻辱,使犯罪人重新复归社会。[26]
2.完善我国刑法中关于“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的程序与方法。法律设置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不仅在刑法理论上缺少论证,而且在实践中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应当强化书面训诫的适用、明确训诫核心内容、建构具有长效机制的训诫措施体系等优化途径。完善责令具结悔过主要是为了构建制度化的程序机制和适用形式,避免该理论成为“制度垃圾”。赔礼道歉作为一种非刑罚措施, 其适用前提在于对行为人免予刑事处罚。故而,在责令赔礼道歉时可以吸纳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注重行为人和被害人关系的调和,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介入的方式和程度。[27]将“耻感”、耻辱刑的内涵与非刑罚处罚措施相结合,不失为提升司法效力的良好办法。
本模型基于2016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汇总分析[9]以及PLATO研究[10]获得的数据进行模型假设以及模型构建,利用TreeAge Pro 2011软件,采用长期Markov模型对没有确诊或缺乏CVD症状的患者服用或不服用阿司匹林进行CVD一级预防这两种干预措施作10年期成本-效用分析。长期Markov模型气泡图见图1(图中,单向箭头表示只能从该状态转移至另一状态但无法逆向转移;双向箭头表示两个状态间可以相互转移;弧形箭头表示该状态可自身转移)。
3.应将古代耻辱刑和注入了现代文明精神的“耻辱刑”有所区别。封建社会刑罚的终极目的是要维护君主权威和君主统治,其刑罚也是残忍的、非人道的。耻辱刑也表现为对犯罪人精神的极度折磨。但是,现代社会中的耻辱刑的运用应当是罪刑法定主义下的、有限度的适用。刑事法律应当对耻辱刑的适用情形、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
注释:
①历代中国刑罚都以“五刑”为主,但是,对于“五刑”具体的刑种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认识。上古传说时期有“黄帝五刑”、“五虐之刑”;本文所讨论的五刑,盛行自周迄南北朝时期;后隋唐以迄清末,五刑分别为:答、杖、竹、流、死。参见黄源盛. 中国法史导论[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9.
②该定义源自联合国2014年《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
③社会中处遇与设施内处遇相对,社会内处遇是让犯罪人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自我行为的矫正和规范的训练,以达到改造自新并顺利返回社会的制度。具体包括:假释、社区矫正、保护观察、改造应急保护等。参见[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事政策学(新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其次,区块链强大的节点算力能够较好地弥补IoT设备的资源受限。当前区块链矿工节点具有较强的算力,以比特币系统为例,目前的总算力已经超过5 500万TH/s。区块链技术能够为IoT提供较强的算力支持,设备的资源受限不再是制约IoT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依托算力支持的安全验证等技术会进一步推动新型IoT技术朝着更加安全可信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2]尉琳.中国古代耻辱刑与传统文化[N].光明日报,2007-01-26.
[3][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12.53.
[4]吴平.我国古代的耻辱刑[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1996,(01).
[5]杨鸿雁.中国古代耻辱刑的沿革[N].人民法院报,2002-09-02.
[6]冯国泉.西周时期的德政与司法选择[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7]杨鸿雁.耻辱刑刑种试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8]李立景.诉诸舆论的司法:耻辱刑的现代流变及启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
[9]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55.
[10]苏力.法律与文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17.359-360.
[11]张明楷.责任刑和预防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12]陈子平.刑法总论(2008年增修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9.
[13]陈家林.外国刑法理论的流变与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7.674.
[14]齐文远.刑法学(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0.
[15]范依畴.羞辱性刑罚:传统价值及其现代复兴[J].政法论坛,2016,(02).
[16]李晓明,李可.耻辱刑与刑法宽和之历史进步作用[J].河北法学,2000,(06).
[17]See FRANK D. HILL. RESTORATIVE JUSTICE: SKETCHING A NEW LEGAL DISCOURSE, Legal Discourse,4 IJPS 51 2008.
[18]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63.
[19]刘东根.恢复性司法及其借鉴意义[J].环球法律评论,2006,(02).
[20]吕欣.恢复性司法的思想渊源与基础理论探究[J].理论与改革,2011,(06).
[21]于改之.多元化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22]李立景.羞辱性惩罚:当代美国刑事司法的新浪潮[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23]吴平.略论外国历史上的耻辱刑[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05).
[24]杨鸿雁.西方耻辱刑沿革与复兴[N].人民法院报,2002-09-09.
[25]尹成波.美国耻辱刑考略[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26]王平,林乐鸣.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对罪犯教育感化的影响及其现代启示[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10).
[27]石柏非.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优化路径[J].政治与法律,2010,(04).
【收稿日期】 2019-07-2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重大课题“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办案衔接问题研究”(HJ2018A03);2019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合规计划与法人刑事责任研究”(201910707 )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吴珂,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17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合规计划。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647( 2019) 05— 0099— 07
责任编辑:马先惠
标签:象刑论文; 耻辱刑论文; 刑罚启示论文; 重新整合型耻辱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