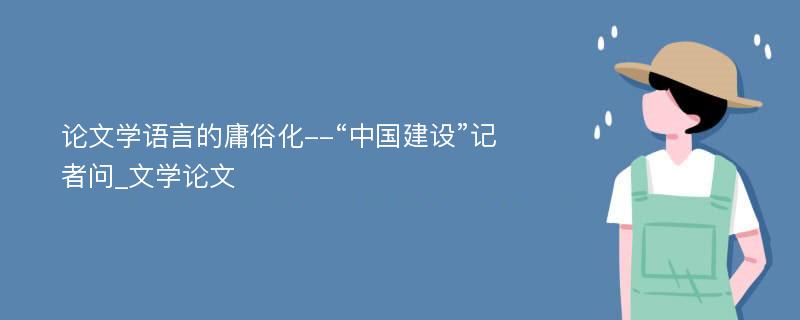
关于文学语言粗俗化问题——答《语文建设》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粗俗论文,记者问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关于文学语言粗俗化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期间收到了许多读者来稿,谨此致谢。现发表张炯先生就这一问题答本刊记者问,作为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张炯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炯先生曾参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张炯文学评论选》等,主编了《新中国文学讲稿》《新时期文学六年》等,曾任《文学评论》《作品与争鸣》主编。张炯先生的传记被收入国内外多种辞书,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成就奖”,并获得铸有他名字的银质奖章。
问:近年来我国文学作品中,粗鄙的文字包括脏词、脏话越来越多。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文学语言的演变有着复杂的原因,它反映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风尚特别是社会的审美风尚的嬗变。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传奇小说的语言是相当典雅的,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写男女的性爱相当露骨,但用语也多用审美性的比喻、象征等笔法。宋人话本和明代的“三言二拍”虽然同是小说,语言却由文言变为白话,而且变得鄙俗了。这与作者、读者成份的不同,与社会本身的变化都有关系。唐代传奇的作者多是文人,是当时社会上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乃至于达官贵人,其读者也大体属于这个范围;而宋以后的白话小说则多属民间说书艺人的话本,面对的听众与读者也多是城市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程度当然不高。当时的小说多半描写他们的生活,又是写给他们看的,这些作品要在文化市场上盈利,听众与读者的审美趣味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和小说编辑、出版商所必须考虑的。明代后期不但城市有相当发展,商业繁荣,而且贵族世家和市民阶层的社会风气都相当腐化。《金瓶梅》这样在性描写中用语鄙俗、脏字脏话比比皆是的作品出现于那个时代,正非偶然。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个性解放的主张的影响,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国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中腐败因素的繁殖,通俗文学领域也出现过许多作品语言鄙俗化,特别是黄色作品中脏字脏话充斥的现象。而严肃文学作家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主张,也使文学语言大大接近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口语。5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推进,当时的社会风气使文风也为之大变,30多年间文学的大众化取得很大成绩,但脏字脏话基本从文学新作中消失了。80年代由于社会处于新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多元化结构和城市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城市及其人口都急剧膨胀,新增的大量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却明显降低,这就形成文学读者中出现了大量的审美趣味低俗的读者,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必然要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出版商的选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传统乃至反文化的思潮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包括它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语言鄙俗化、脏字脏话连篇的现象,也给予我国作家的审美趋向相当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近年我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语言鄙俗化趋向的主要原因。
问: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上述文学语言鄙俗化的现象?
答: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语言的艺术。它的中心任务就是以语言作为表现手段,从审美的视角去描写人,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人的行为、性格、心理与情感。真、善、美三者向来是人们对文学的统一的要求。但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善的和美的,虽然美的和善的东西要以真为基础。这就要求作家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舍弃不美不善的真。这可以说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能够千古不朽而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审美欣赏的重要的规律,也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在精神上提高他们、陶冶他们,使他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俗走向崇高,从丑陋走向优美的关键之所在。列宁曾指出:“艺术并不要求承认艺术作品就是现实。”(《哲学笔记》)鲁迅也说过:“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在文学语言鄙俗化的问题上,我想道理是一样的,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任何语言都必须原封不动地搬到文学作品中去。毫无疑问,作家可以也应该从现实生活的人民大众的丰富多采的语言中吸取自己文学描写的富于表现张力的材料,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能对丰富和发展我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作出卓越的贡献,但作家对于纯洁我国的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更负有重要的责任。使文学语言无节制地鄙俗化,乃至连篇累牍地使用现实生活中的脏字脏话,不但与作家上述责任相悖,而且也与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带有基本规律性的要求不相符。
在文学语言鄙俗化的问题上目前存在两方面的误区:一是有些作家认为,为了创作真实的艺术形象,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话语就应该都搬到作品中去,写流氓就搬流氓话,写婊子就搬婊子话。这种见解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所谓“笔下人人各有其声口”,不是一向被誉为“手笔高超”吗?但这样做也不是完全可以没有节制。《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的焦大醉后骂人,《阿Q正传》写阿Q对吴妈的想入非非,也是有节制的,但两书都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声口全刻画出来了。这就是既顾及真,又顾及美与善的做法。至于像《金瓶梅》那样去描写性交,你不能说它不真,却不能说它写得美,把那些鄙俗不雅、乃至丑陋的描写删去,也无伤于作品典型人物艺术形象描写的真实。可惜现在模仿《金瓶梅》那样描写的作家还自以为得意,而实际上正走向审美创作的一个误区!二是有些作家标榜反传统,认为你不是要审美吗?我今天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就要审丑,或者说以丑为美。至于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更要写,不但写男女的交媾,还写人兽的交媾;不但写脏字脏词,还要脏话连篇。这里,我们恐怕要弄清,世上的美与丑,自然没有绝对的界线,在一定条件下,丑的东西也可能转化为美。但这并非意味着任何丑的东西都无条件可以转化为美。审丑的现象也确实存在,比如舞台上的丑角就是。舞台上的丑角是经过艺术加工而获得表现形式的美,同时又因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嘲讽和批判的态度,才使得艺术形象产生审美的效应。这就是世上的丑可以化为艺术中的美的条件。如果既没有形式上的加工和美化,对丑的东西又没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反而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来,加以百般欣赏,以臭为香,那恐怕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传统固然是反传统了,试问那又有什么普遍的意义呢?美之为美,丑之为丑,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的,并非人们可以像变魔术那样,无条件地变来变去。文学语言的过分鄙俗化,乃至把生活中有的脏词脏话都搬到作品中来,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人们不能完全无视美之为美的规律。
这里还有个正确对待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问题。
对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应有分析。人民群众当然有健康的审美追求,他们也迫切需要欣赏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但由于仍有许多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许多年轻人还处于思想成长的年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处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处于国际资本主义文化的包围中,旧社会的有害的思想残余和低俗趣味的影响继续存在,这一切,使得人们的思想存在多种取向也是事实;人民群众特别是大量市民中存在着某些庸俗、乃至低劣的审美趣味与需求,更是不奇怪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自然不应迁就他们的这种趣味需求,更不能单纯为了赚钱而去满足某些群众的“嗜痂癖”与“窥淫癖”,而应当以自己具有高尚的健康的审美品味的作品去提高和优化人民大众的审美理想。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中有些人爱说脏话,那么文学作品也必得脏话连篇,那就大错特错了。
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及其相应的思潮无疑有它们一定的合理性和创造性。借鉴它们的长处来丰富我国文学艺术的创造是完全应该的。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都是西方文化深感危机时期的产物,因而它们又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短处。不分青红皂白地反传统反文化反理性,就正是它们的短处。这方面恰恰是我们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文艺所不应该学习的。决不能因为它们的作品中充斥脏话、充斥鄙俗化的描写,我们也就照样搬取过来。那样做,在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借鉴上就是历史时空的错位。随着我国如日东升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上述错位的历史悖谬便越来越明显。
总括起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运用上,我以为顾及大众的通俗化是应该的,但刻意追求鄙俗化,乃至滥用脏词脏字,却是不可取的,是应该加以批评的一种不良的倾向。如果听任这种倾向发展和泛滥,那必将大大降低我国文学的美学水平,甚至导致文学本身的毁坏,而且还会给我国的语言带来严重污染。当然,在顾及审美创造的前提下,为了追求艺术形象特别是一定人物形象刻划的真实性和生动性,适度运用一定的粗鄙语言,乃至某些脏词脏字,又应该是被容许的。
问:该不该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来禁止文学作品的语言鄙俗化和滥用脏字呢?
答: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是否制订过这样的法律,但这方面编辑出版部门,我以为是可以有所要求的。对于过分鄙俗化乃至脏话连篇的作品就应要求作者作出必要的删改,否则就不应予以出版。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此,我们就必须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也必须不断丰富、纯洁我国的现代语言。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理应为此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语言使用的问题上要不要制订一定的法律条规,有关部门可以参照世界各国的情况加以研究。而我以为,在舆论方面通过讨论,作出必要的导引,恐怕更加重要和必要。文学评论界和语言学界在这方面无疑都负有重大的责任。所以,对于《语文建设》月刊就这一问题发起讨论,我非常支持。我想,通过广泛的讨论,这一问题一定能引起作家们的关注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