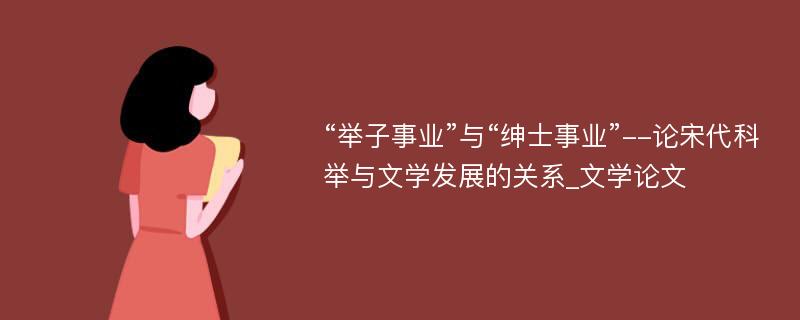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业论文,科举论文,宋代论文,君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4-0075-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论及宋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将科举及科举考试列于其中。(注: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说》,在论述“对促进文学的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因素时,第二项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且特别提到“实行了封弥制度”(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293页)。馀不烦举。)早在宋末,就有论者以为宋诗之所以不及唐,是因为宋代未能坚持以诗取士(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沧浪诗话校释》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似乎若宋代“以诗取士”不动摇的话,也会像唐代一样,成为欣欣向荣的“诗国”。那么,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详后引)。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认为唐代进士考试中,“按照对省题诗的要求,以及省题诗的具体创作实践,来比较唐代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二者正好是背道而驰的。”[1](P410)他们对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之关系的结论,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能否引申到宋代?这无疑是宋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惜乎迄无较确切而有说服力的解答。
笔者认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难以简单地描述,大体可从两个层面,即外部效应(也可称间接影响)和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主要指与文学关系相对较密切的进士科考试,下同)进行审视。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很容易产生片面性:过多地看到科举外部效应的积极面,甚至以外代内,赞美场屋时文,而忽略或掩盖了其内部运作的真实面目(当然,内、外两个层面并非截然分离,它们又相互影响,特别是社会文风,必然反映到科举考试中来)。我们认为,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也就是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考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揭示出两者的真正关系,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得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故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核心——科举考试切入,去考察宋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某些“外部”层面。
《宋史》卷155《选举志序》曰:“宋初承唐制。”具体而言,宋开国初的科举制度,乃行后周之法,而后周又承唐制。(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云云,太祖“从之”,见《宋会要辑稿·选举》14之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此后科举条制虽时有修订,但基本原则和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即在考试的同时兼采“誉望”(社会美誉度)。(注:参见《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亦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中华书局1979年版))直到真宗朝制订出《考校进士程式》、《亲试进士程式》(本文统称“景德条制”),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方始形成。景德条制的核心,是将科举考试中糊名、誊录制度化、法律化,目的是“防闲主司”。所谓“防闲”,就是严格限制考官的权力,这是宋太祖以来诸帝的一贯思想,意在杜绝以“行卷”为主要形式的请托之风,防止像中唐以后利用“门生座主”关系酿成的朋党之祸。景德科举条制在科举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对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客观上,糊名、誊录制结束了“公荐”、“行卷”等制度漏洞,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场仪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无疑是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举子也由读书作文转而专攻“举子艺业”(简称“举业”)。我们认为,欲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应当以景德条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作为研究对象。
二、有司:“文章取士,眷惟较艺”
如果说唐代“采誉望”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看平时、重素质的因素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则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这是最显著的“宋代特色”。元人盛如梓说:“前辈谓科举之法虽备于唐,然是时考真卷(按:指举子所做原卷),有才学者,士大夫犹得以姓名荐之,有司犹得以公论取之。……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进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2](注:所谓“祥符中立誊录之制”,盖就普遍实施而论,实际上早在景德二年(1005)即已在御试中采用誊录制。)这个转变实在太大,故主持科举考试的相关机构(“有司”),包括州郡、礼部及殿试三级,它们的政策也不得不同时作出重大调整。
宋代科举既以考试为中心,“有司”便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故我们欲考察宋代科举考试的特色,应当从“有司”说起,以摸清内部运作的实情。
首先是加大考题难度。为了突出考试的权威,加强淘汰,复以经义、策论可出之题有限,有司便千方百计在考题上打主意,出偏题、难题,变着法儿对付举子,于是“竞务新奥”成风。顾炎武曾说:“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3](卷16)作为国家考试,“欲其难”本无可厚非,但宋人却走上极端。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言:“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4](3之18)事实上,随着举子对付考试手段的多样化和有效性的提高,“竞务新奥”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到南宋尤为突出,所谓“关题”、“合题”就是典型。
《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21载: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二十五日诏:“自今岁试闱,六经义并不许出关题,亦不得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贯者为题。”先是,国子祭酒沈揆言:“六经自有大旨,坦明平正,不容穿凿。关题既摘经语,必须大旨相近。今秋诸郡解试,有《书》义题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据此题目,判然二事,略不附近,岂可相关?谬妄如斯,传者嗤笑,此则关题之弊。有《易》义题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止矣,而试官复摘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相连为题,据此一句,其义自连下文,若止以上四句为题,何不可?此则命题好异之弊。”宰执进呈,上曰:“出题碍理,诚不可不革。见说近日科场文格卑陋,将来省试须是精择试官,故有是命。”但此诏并没有禁绝出“关题”之风,嘉泰元年(1201)十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四事,第三事也是论“关题”:“近者经学惟务遣文,不顾经旨,此非学者过也,有司实启之。盖命题之际,或于上下磔裂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乞今后经义命题,必本经旨,如所谓断章、关题,一切禁约,庶几学者得以推原经文,不致曲说。”[4](5之24)
再看“合题”。庆元四年(1198),礼部待郎胡纮言:“欲令有司,今岁秋试所出,六经各于本经内摘出两段文意相类、不致牵强者合为一题,庶使举子有实学者得尽己见,足以收一日之长,而挟策雠伪者或可退听矣。从之。”随后臣僚言:“近者臣僚有请,自今试场出六经合题,深中场屋之弊。但本意正恐题目有限,士子得以准拟,反(原作“返”)使实学不能见一日之长。臣谓若出合题,则合题亦自有限,士子仍旧准拟。乞下礼部,令遍牒诸路,自今出题,或尽出全题,或三篇中欲合一题,听从有司,庶几不致拘泥,不为举人所测。”[4](5之20)
无论“关题”还是“合题”,目的都是与举子为“敌”。清代考八股文,有所谓缺头短尾、东拉西扯的“截搭题”,也是为了“杜绝考生抄袭的弊病”[5],“关题”、“合题”,大概是“截搭题”的老祖宗。
唐代进士考试,举子有不明题意者,可以“上请”(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中华书局1984年版)),宋初亦然,后来被禁止。洪迈《容斋随笔》卷3载:“国朝淳化三年(992),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1005),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抄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1008),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1034),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4](1之4)既出“关题”、“合题”而又不许“上请”,举子如何不“多懵所出”,如坠五里云雾?考试认题,于是形同猜谜。
其次是废除“公卷”(唐代称“省卷”)。苏颂《议贡举法》曰:“旧制,秋赋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差入贡院,先行考校,内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并行驳放。”[6]既实行糊名、誊录制,去取只看卷面成绩,则“先行考校”所纳“公卷”已完全失去意义。于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仁宗‘从之’。”[4](15之11)(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载此事,文字稍异:“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篇试,则公卷为可罢。”(中华书局1985年版))
纳公卷的目的是观“素业”,但也难免先入为主;废除公卷,意味着最后一项唐代遗制从有宋科举中消失,“考试”的中心地位,至此完全确立。
第三,考官“锁院”阅卷。每到贡举之年,朝廷要任命知举、同知举及各类考官,他们的职责就是“较艺”。(注:如《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54载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二十四日祖禹上言曰:“知贡举官止以出题较艺为职,专意抡选天下之士。”)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知举官“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4](1之4)这叫“锁院”,又称“锁宿”。锁院虽始于太宗时,但实行景德条制以后的锁院“较艺”,较之以前大不相同:考官只能批阅既经封弥、又经誊录的卷子(“草卷”)。这就切断了考官与外界所有有形、无形的联系,以真正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四,技术性问题成为去留的“关口”。虽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决定去留的往往并非诗文内容的好坏,而是程文的形式(文体程式)及人为禁忌,主要是用韵、声律(平仄)和避讳等。景德条制除“防闲主司”外,又“为《礼部韵》及庙讳之避”[7],从此确立了一整套科场技术规范和文章定格。早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日,太宗即下诏曰:“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4](3之4)盛如梓曰:“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定。”[2]自《礼部韵》出笼,就被称为“官韵”,诗赋不押官韵或落韵,便入“不考式”。(注:见《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20。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四部丛刊续编本)引《绍兴重修御试贡举式》“试卷犯不考”条,凡诗赋不压官韵、落韵、重叠用韵及赋协韵、正韵重叠,皆入不考式。所谓“不考式”,《条式》曰:“但一事不考,馀皆不考。”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某一项特定的规则,便被全部否决。)《燕翼诒谋录》卷5曰:“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准敕详定贡举条制中,“策论诗赋不考式十五条”,其中有用庙讳、御名,诗赋脱官韵,诗赋落韵(用韵处脱字亦是),诗失平仄(脱字处亦是),重叠用韵等,都在“不考式”之内。宋祁等的条制后未施行,但他们是主张放宽的,谓“旧制以词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试一字偶犯,便遭降等”,以为“拘检太甚”,主张“依仿唐人赋格”。(注:以上引宋祁等奏,见《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3。)放宽后尚如此,可推知实际施行的条制,比上述更加苛刻。孙觉《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更改》曰:“今乃拘以声势之顺逆,音韵之上下,配以缀缉,甚于俳优之辞。”[8](卷80)由此可见一斑。《四库提要·〈大全赋会〉提要》概括了宋代场屋律赋的各种禁忌,可使我们理解“拘检太甚”的含义:“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其违试不考之目,有诗赋重叠用韵,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得(疑“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又《淳熙重修文书式》,凡庙讳、御名本字外,同音之字应避者凡三百一十七,又有旧讳濮王、秀王诸讳应避者二十一。是下笔之时,先有三四百字禁不得用,则其所作,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浅庸,千手一律,固亦不足怪矣。”[9]
唐五代试进士,诗赋已讲究用韵、避讳,但远无宋代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对举子威胁如此之大,几乎成了“一票否决”的死穴,甚至连考官阅卷时如有落韵没有看出来,也要降官。(注:如《宋会要辑稿·选举》19之11载:庆历七年(1047)孙锡、李大临“坐奏名举人诗有落韵者,降诸州监当。”)嘉定七年(1214),鄂州举子宋倬赋卷中第六韵押“有”,见《礼部韵略》第四十四,上声;而赋曰“诏劝农桑,及乎令守”,“守”在第五十一“宥”韵内,去声。经湖北转运司、礼部、国子监反复讨论,最后确认落韵,由皇帝下诏“驳放”。一字失韵,不仅决定了该举子的命运,且惊动了皇帝,并煞有介事地将此事写入《宁宗实录》[4](6之20),生动地说明了所谓“较艺”的可笑。宋人别集中许多墓志文,都曾记载墓主做举子时“栽”于失韵的经历。在《宋史》中也有,如该书卷317《邵亢传》:“再试开封,当第一,以赋失韵,弗取。”(注: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论宋代律赋》(同上2003年第5期)将宋人写作四六文和律赋比为走钢丝或“戴着枷锁跳舞”,说“限制越严而又越能自由弛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他没有看到“钢丝”或“枷锁”同时有扼杀文学才华和创造性的一面,实为悖论。)
自取士变为有司“较艺”之后,选才的评价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采“誉望”,举子为获取“誉望”,就不得不努力提高写作水平并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以求得社会的承认,包括用“行卷”的手段。因此可以说,那时的评价体系是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录取与否,卷面并不太重要,社会对其作品的“美誉度”常起关键作用,所以程千帆先生说由科举考试派生的行卷对唐代文学“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见下引)。而封弥、誊录制彻底关上了社会参与的大门,使科举成为极少数人(考官)唯凭卷面的锁门“较艺”(又叫“衡文”)。考官“衡文”时注重的并非文章优劣,而在于纯形式甚至非文学因素的“技”(详下文),人为地设下许多陷阱,结果使“文章取士”徒有虚名,形形色色的限制(“不考式”)既牵着举子也牵着考官的鼻子跑。评价体系由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变为绝对封闭的、一元的,评价标准由质量转到技巧,是科举制度的重大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
三、举子:“待问条目,搜抉略尽”
如果说景德条制后,有司(考试机关)把取士变成“较艺”的话,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举子为了应对,便不得不变化策略,改变关注点:由先前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然后奔走势利之途以求“誉望”(注:宋初(太祖到真宗),科举制度处于转型期,故尽管当局禁止请托,但进士行卷之风仍然存在。参见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转移到在考题上打主意,比如“搜括题目”——现在叫“建立题库”,以便“打题”。这是科举风气的又一重大转折,对举子影响极大,据苏轼说,当时“打题”已达到“待问条目,搜抉略尽”(见下引)的程度。具体而论,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举子大量使用策括、套类。为了对付策论及经义考试,儒师、书肆相互配合,煞费苦心,从可能拟作时务策、经义题目的经、史书中进行“地毯式”搜索,然后编成策括、套类,利用“题海战术”进行“打题”。这类策括、套类又被称作“兔园册子”(《兔园策》出唐代)。上引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曰:“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10](卷25)
这不只是个人的看法,元祐八年(1093)三月二十三日中书省言,也如是说:“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4](8之36)南宋人岳珂说得更详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编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市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而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11](卷9)
上引庆元四年(1198)礼部侍郎胡纮主张出“合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打题”,他说:“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厢,无非本领(《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引作“初无本领”)。主司题目,鲜有出其揣拟之外。”[3](5之20)
看来,只要“锁院较艺”存在一日,“搜括题目”就一天不会止息:它们是科举考试制度催生的一对孪生儿。如果下看清初的情况,此弊殆无药可救。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曰:“今日科场之弊,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誉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3](卷16)
二是诗赋、策论、经义等类时文集大量刊售,以供举子揣摩。《直斋书录解题》卷15著录《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并谓“《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大抵衍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宋会要辑稿·选举》5之21载,庆元五年(1199)正月,礼部尚书黄由等言:“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从之。”[4](5之21)则《解题》所录《擢象策》,“擢”当是“拔”之误;而《擢犀策》、《拔象策》两书皆时文集,庆元前已有刊本,至是又由官府选刊(所谓“拔其尤者”)。这有如今天的考试参考书,在宋代相当流行,有的见于书目,部分还流传至今,如魏天应编、林子长注《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十卷即是。明何乔新《论学绳尺序》曰:“若此书所载,则皆南宋科举之士所作者也。”《四库提要》道:“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9]较之单纯的“打题”,这类书重在传授技法,但最多也只能培养出摹拟高手。
三是科场作弊频繁。经义考试中的传义、怀挟,各科都屡见不鲜的“代笔”(现在叫“枪手”)等等,作弊方式层出不穷。科场作弊虽不始于宋代,但由于景德条制后糊名、誊录的普遍实施,“较艺”成绩的好坏成了录取的唯一依据,于是侥幸在卷面上“取胜”,便是举子要竭力争夺的出路,以至不择手段,作弊就不可避免地普遍化和频繁化。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之[12],此不赘。唐代“采誉望”的科举模式,造成“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而为“行卷”奔忙的“风景线”(注:《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引南宋项安世语。),这固然不是科学的选举制度;但就“采誉望”这一点论,似乎多少带有重能力和素质的因素,因为“名”毕竟不可浪得,若没有一点真本事,就算得到有力者的吹拂,也未必能被社会接受。宋代自景德科举条制之后,既然“卷面”决定一切,于是“应试”遂成为举子最主要的价值取向,他们(甚至整个社会)都在为对付考题而竭思尽虑,即便有志于创作,也得待获得“名”之后。文学就这样被“挤”出了考场。
四、“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
现在可以讨论景德条制后的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了。
黄庭坚在《与周甥惟深》的书信中,把“观古人书,每以忠信孝悌作服而读之”称作“君子之事业”,而将读“一大经,二大经”、专为科举而读书作文称作“举子事业”。[13](卷1,P1924)在他看来,同是读书作文,然就“事业”论,却有高低之分。刘克庄说:“士生于叔季,有科举之累,以程文为本经,以诗、古文为外学,惟才高能兼工。”[14]他的意思是说,“本经”(程文)对士子虽是一“累”,但重要性却超过“外学”(诗文创作)。大意相同的话,宋人还说过不少。总之,在他们看来,“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本经”与“外学”,已造成价值取向的彻底裂变,而两者的轻重,则被科举完全弄颠倒了。除少数“才高”者外,一般人于二者难以兼得,士子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和放弃。
景德条制实行后,科举中那些促进文学发展的因素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举子事业”。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写道:“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15](P88)
程先生的论点是中肯的。唐代科举促进文学发展的,并非举子在考场中所作诗赋,而是在考场外的“行卷”,也就是他们为求得“誉望”而向社会“展示”的文学创作成果。“行卷”之所以能促进文学发展,是因为它不受“程试”的限制,举子可以用各种文体充分发挥自己之所长。除行卷外,还有“省卷”(公卷),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上引苏颂《议贡举法》在说了“旧制”纳公卷后,接着道:“是举人先纳公卷,所以预见其学业趋向如何,亦有助于选择也。景祐以前,学者平居必课试杂文、古律诗、赋,以备秋卷,颇有用心于著述者。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惟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诗、赋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岂所以激劝士人笃学业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举人请应依前令投纳公卷一副,……如此,庶几人知向学,不为苟且之事矣。”[6]由于实行糊名、誊录制,恢复公卷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由此可见与行卷一样,公卷也是促使举子平时努力学习写作的动因之一。如果视经义为广义的“文学”,科举也未必能起促进作用。南宋初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8中说:“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16]总之,科举“应试”严重束缚了举子的手脚,使他们无暇读书写作,如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所说:“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10](卷11)魏了翁《杜隐君希仲墓志铭》也说:“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17]
其次,上面说过,实行封弥、誊录后,取士变成了唯卷面的“较艺”,而事实上,举子科场诗赋只能算作“技”,最多也只是“工艺品”,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吕公著于熙宁二年五月上《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曰:“进士之科,始于隋而盛于唐。初犹专以策试,至唐中宗乃加以诗赋,后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8](卷78)
如前文所述,是否有技术性的“硬伤”,成为考官们的关注点,故将场屋篇什称为“尚方技巧之作”,就再恰当不过了。“采誉望”使评价体系或多或少地与社会接轨,而“唯卷面”则使两者分离,故成为“技”之后的科场诗赋策论(时文)优劣的评价标准,与社会已全然不同,俨然形成两个价值体系。欧阳修《六一诗话》曰:“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惟天圣二年省试《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采侯’。”[18](P272)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也说:“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天圣中,梓州(今四川三台)进士杨谔,始以诗著。其天圣八年(1030)省试《蒲车》诗云:‘草不惊皇辙,山能护帝舆。’是岁,以策用‘清问’字下第。景祐元年(1034),省试《宣室受厘》诗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谔是年及第,未几卒。”[8](P275)二人所举“佳作”,“佳”在声律谐和,没有掉入“不考式”的人为“陷阱”,而内容不出歌功颂德,殊无可称。如果说场屋经义策论大都为“预制板”的话,那么诗赋则多为“木乃伊”。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47写道:“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词赋取人。方其假物喻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恶之,以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故今日之经义,即昔日之赋;而今日之赋,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盖不以德而以言,无向而能获也。诸律赋皆场屋之伎,于理道材品,非有所关。”[19]
考试既将鲜活的“艺”变成了死板的“技”,则场屋时文与文学创作甚至“理道材品”失去关系,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宋代举子视场屋诗赋为“敲门砖”,得则弃之,而去追求“君子事业”。如余靖所说:“近世以诗赋取士,士亦习尚声律,以中其选。署第之后,各图进取,或以吏才成绩,或以民政疚怀,或因簿领之烦,或耽燕私之乐,回顾笔砚,如长物耳。”[20]而有志于文学者,登第(或放弃科举)后,往往要再学习,转攻原来的“外学”,如强至所说:“予之於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21]宋孝宗曾说:“科第者,假入仕耳,其高才硕学,皆及第后读书之功。”[2]这算得上是“实话实说”。戴表元曾在咸淳七年(1271)登进士第,后入元,袁桷在《戴先生墓志铭》中记其语曰:“科举取士,弊不复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异,斯可也。”[22](卷28)元人吴澄《遗安集序》则说:“欧阳文忠公、王丞相(安石)、曾舍人(巩)、苏学士(轼),皆由时文转为古文者也。……老苏(苏洵)亦于中年弃其少作而趋古。”[23]这里以欧阳修为例。他在《记旧本韩文后》写道:“是时(指其为儿童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24]
如果考察宋代进士出身的重要作家的成长历程,就会发现,他们大都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转变。否则,若得第前学习传统的古文、诗歌,必然要妨“举业”,永无仕禄之望;而得第后若不重新学习,便永远难以进入“高明之境”,有所谓“君子事业”:他们就生活在这种价值裂变后的矛盾和无奈之中。正如袁桷所说:“科举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歧孔分,厥害实深。”[22](卷43)这种状况,下延至元、明、清三代,成为年轻学者们的普遍悲哀。
但得第后想要彻底转变,又谈何容易,不少人因场屋蹭蹬,岁月蹉跎,只得拖着“举子事业”的“尾巴”,不时露出“丑”来。由南宋入元的刘塤,在所著《隐居通议》卷18中批评宋代词科,同时也抨击了“举业”时文之流弊,他写道:“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尽,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举子语在其中者,谓之金盘盛狗矢。”[25]就是不做作家,也是如此,如南宋人邵浩曾编《苏门酬唱集》,在所作《苏门酬唱引》中自述道:“绍兴戊寅(二十八年,1158),浩年未冠,乃何幸得肄业于成均,朝齑暮監,知有科举计耳,古文、诗章未暇也。隆兴癸未,始得第以归,有以诗篇来求和者,则藐不知所向。于是取两苏公之诗读之。”虽不详邵浩所举是词赋进士还是经义进士(人既“以诗篇求和”,恐是前者),但从他的窘状,可知为“科举计”之害人:他不得不从二苏诗入手,进行“再学习”。
第四,南宋后期,作为“君子事业”的传统文学(诗歌、古文)全面衰落,原因虽复杂,科举考试难辞其咎。由宋入元的作家舒岳祥在《跋王矩孙诗》中说:“噫!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26]
元初林永年在《覆瓿集引》中也说:“唐、宋以科目取士,凡习举子业者,率多留意于场屋之文,间有能兼吟事之长者,吾见亦罕矣。”元人戴表元在大德十年(1306)十月所作《陈晦父诗序》中写道:“近世汴梁(指北宋)、江浙(指南宋)诸公,既不以名取人,诗事几非。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27]
由上述可见,景德条制虽然达到了“防闲主司”、杜绝请托的目的,也保证了科举考试的相对公正,但却对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文学创作,这个被古人视为“不朽之盛事”的“君子事业”,却被宋代科举边缘化到“外学”、为人所鄙的位置。宋人并非不能辨别两种“事业”的价值,在宋代文献中,贱举业的言论比比皆是,但科举乃利禄所系,权衡缓急,人们不得不无奈地舍“熊掌”而取“鱼”。同时,对举子学业的评价又由相对开放变为绝对封闭,能否录取的决定因素并不在诗文的内在质量和艺术价值,这必然驱使“资质秀敏”的举子去“弄”时文,甚至不惜模拟、打题和剽窃,以便在科第、进而在仕途上捷足先登,而只有“窘于笔下”或不敢到场屋拼搏的才去学诗,“诗事几非”就毫不奇怪了。
如果说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是“促退”的,但“派生”出的行卷及省卷还对文学发展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景德条制则正好在这个关捩上切断了科举与文学相联系的纽带,它对文学发展“促退”的力度,必然更大于唐。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首的问题了:将唐代进士科考试对文学发展是“促退的”、两者是“背道而驰”的结论引申到宋代,不仅完全正确,而且还可加上“较唐代更甚”这类的推进语。如果要对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之关系作一简明的定性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选择“悖反”这个词。无论是黄庭竖的“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之分,刘克庄的“本经”与“外学”之别,还是袁桷所说的“二歧孔分”,也都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申本文第一节的观点,即举业对培养文学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仍然有积极作用。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曾引袁枚等数位清代学者的话,以为时文之学,虽有害于诗、古文,但若不习时文,作诗、古文虽工,但气脉不贯,理路不分明。钱先生认为所说“亦中理,一言蔽之,即:诗学(poetic)亦须取资于修辞学(rhetoric)耳。五七字工而气脉不贯者,知修辞学所谓句法(composition),而不解其所谓章法(disposition)也”。[28](P242)不过我们已将这些归入科举的“外部效应”(对文学的间接影响),不在本文所论“科举考试”的范围。
由于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是官僚而不是文学家,较之以往的选举方法,用“应试”抡才也不失为有效之举,因此从历史发展看,景德条制至少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与文学发展(当时也没有这个概念)相悖反而责难它。只是我们需记住: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收稿日期:2004-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