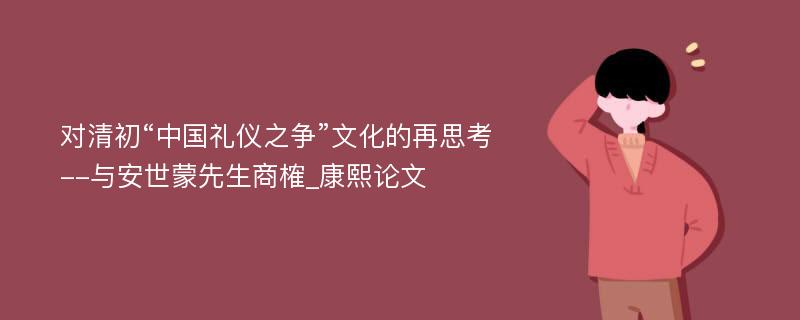
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清初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康熙年间,基督教在华传播进入史无前例的高潮期。鉴于较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取得的成功,适逢清初统治者对基督教的相对宽容政策,天主教各修会纷纷来华传教,旋即因对中国传统礼仪的理解和态度不同而发生争论,并进一步演化为康熙皇帝和罗马教廷的抗争,最终导致清廷的禁教举措,史称“中国礼仪之争”。这次争执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西方学术界对此事件的研究多从耶稣会传教士与其他系统的传教士之间神学和传教方法的争论入手,或谓耶稣会传教士过于迁就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之争”乃势所必然,或谓其他一些传教士操之过急,过早挑起争端,葬送了“中华归主”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学术界则多从耶稣会传教士与其他系统的传教士之间的争权夺利入手予以分析,虽有道理,但毕竟流于表面。至于再到它们背后的民族政治势力身上寻找原因,则因此时的中华帝国尚属强盛、西欧诸强在华利益尚无从谈起,而更显牵强。近日,安希孟先生撰文(《清初“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沟通》,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7辑,2002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更多地从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旧礼俗的冲击入手来看待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读来令人振聋发聩,确实令人有希孟先生评价先贤时所说的“痛快斯言”之感。但希孟先生的分析从总体上来说仍给人以就此事论此事的感觉,而且有一些观点也是笔者所无法苟同的。本文试图在宏观上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尤其从宗教在两个传统中分别所处的地位入手,对这一事件再进行反思,并就教于希孟先生。
一、“中国礼仪之争”的概况
关于清初的这场“礼仪之争”,历史的记载基本上是清楚的,坊间的著述对此多有论述,本已毋须再为饶舌,但作为本文的历史背景,似仍有略述之必要。
如果抛开历史上的一些传说不谈,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据现存的可靠史料记载,实起自公元635年。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教派在唐代传入的景教和元代传入的也里可温教(景教与天主教的总称),被视为基督教在华的第一、第二次传播。但这两次传播均依附于统治者的庇护,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宫廷宗教或贵族宗教,并未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上有实质性的接触。16-17世纪明清之际,基督教再次掀起对华传播高潮。耶稣会士利玛窦切实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文化差异对理解教义所造成的巨大障碍,从而开始刻苦研习中国经籍,制订了“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利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等概念来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并顺应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进行传教,取得了较大成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实质性接触由此而始,而“中国礼仪之争”的伏笔也就此而埋下。
“礼仪之争”的序幕是在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内部上演的。利玛窦逝世后,他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妥协”遭到其继任者龙华民的反对,其主要理由在于,称造物主为“天”或“上帝”以及祀孔祭祖属于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相悖。在1628年由龙华民主持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嘉定会议”上,做出了怀疑并部分否定利玛窦路线的决议。但此时,这种反对尚限于耶稣会内部,且其决议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依然为大多数耶稣会传教士所奉行。
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李安堂来华传教,对耶稣会士适应中国国情而采取的传教方针极为不满,旋即展开与耶稣会的争论,正式挑起“中国礼仪之争”。争论双方甚至各自上书自己在欧洲的总会,但也无法解决问题。此时,争论尚限于天主教各修会间的争论,对中国教会尚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无法说服耶稣会,黎玉范离开中国返回欧洲,于1643年抵达罗马,上书教皇英诺森十世,对耶稣会提出17条指控。教廷由此卷入“中国礼仪之争”。但远在欧洲的教廷苦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不免偏听偏信,在争论双方之间左右摇摆。1645年,罗马教廷根据黎玉范的指控,向中国天主教教徒下令,禁止称造物主为“上帝”和“天”,禁止参与祀孔祭祖,并谴责了在华耶稣会士的做法。1654年,卫匡国作为在华耶稣会士的代表到罗马申诉,辩称祀孔祭祖不具宗教性质。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将其报告交宗教裁判所研究后于1656年做出裁决,同意卫匡国的看法,准许中国天主教教徒在不违反天主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祀孔祭祖活动。此决定显然与1645年的禁令相互抵触。多明我会不服教皇判决,要求教皇对1645年禁令是否有效做出表态。教皇克莱门特九世于1669年答复:1645年和1656年的两项决定均有效,如何行事由传教士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就在罗马教廷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尚举棋不定的时候,1681年来华、1687年任教廷代牧主教并全面管理福建教务的阎当,于1693年断然发布牧函,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禁止信徒参与祀孔祭祖,并开除了两名违反禁令的耶稣会信徒。为了获得教廷的支持,阎当鼓动自己的母校巴黎大学神学院举行多次讨论,最终说服教皇于1704年决定禁行中国礼仪,并派使者多罗来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在争论中感到处于劣势的耶稣会士为了争取教廷的同情,精心策划了一份请愿书,于1700年由在华耶稣会士联名上疏向中国皇帝康熙请教,希望康熙出面证明中国礼仪不是宗教崇拜。康熙则明确表示,祀孔祭祖系中国传统习俗,不含宗教礼仪。康熙皇帝由此卷入“中国礼仪之争”,在华传教士的内部争论由此上升为康熙皇帝和教皇的对抗。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颇带有戏剧性了。多罗特使来到中国,康熙皇帝立即召见。但多罗本人始则吞吞吐吐,拒不吐露来华的真实目的,继而称病不见,最后又推荐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阎当与康熙讨论。阎当糟糕的中文和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激怒了康熙,被康熙斥之为“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然而,多罗一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就以公函的方式公布了教皇的禁令。而康熙则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一律驱逐出境。教廷一方面多次重申禁令,另一方面又派嘉乐为特使赴华,意图打破僵局。而康熙则在看到罗马教廷的禁令之后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此之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强硬立场,而中国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亦继续执行禁教的政策。基督教在中国虽未销声匿迹,但其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在华传播却在整体上已就此画上了句号。直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基督教(含天主教和新教)才乘坐炮舰重回中国。
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批准传信部撤销有关中国礼仪的禁令的建议。“中国礼仪之争”由此正式结束。
二、谁更有发言权
事实一旦厘清,进一步的分析就会事半功倍。
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礼仪之争”的真正起因是什么?
希孟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争夺势力范围论”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认为说“中国礼仪之争”起因于各修会之间争夺在华传教权,起因于传教士所代表的各自国家利益的冲突,或是“倒因为果”,或是“不符合事实”。希孟先生的结论是:“‘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内部传教手段与方法之争,双方均秉着满腔的宗教热忱,目的在于弘扬天主教,探索真理,并非为了国别或面子而争意气。”[1]
希孟先生未免把传教士们的“宗教热忱”理想化了。其实,就连天主教的当代大思想家汉斯·昆在谈到“中国礼仪之争”时也说:“除开教皇使节傲慢无知外,不同教派(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耶稣会)和不同国家(西班牙和法国对葡萄牙)之间的敌对感情在最后一决雌雄时往往比神学分歧起更大作用。”[2](P217)传教士固然献身于“神圣的事业”,但他们也都还是人。后来者与先到者之间、不同修会之间为“标新”而“立异”乃至哗众取宠,恐怕也不是能够完全排除的原因。但此说查无实据,说出来未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所以,我不愿犯黑格尔曾痛斥过的“仆从眼中无英雄”的错误,而宁可接受希孟先生的结论。
然而,“传教手段与方法”是服务于所传的“教”的。所谓“传教手段与方法之争”,无非是一方对中国礼仪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方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其根据是:一方认为中国礼仪能够与天主教信仰相容,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礼仪与天主教信仰不相容。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敬天祀孔祭祖等礼仪能否与天主教信仰相容?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且不说天主教信仰,单是中国礼仪,就足以让无数人提出无数种理解,否则也就不会有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了。幸好我的目的不在于回答这一问题,而在于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当时的争论各方中,谁在这件事上更有发言权?
按照希孟先生的观点,当然是罗马教廷更有发言权。理由是“罗马教廷是一个宗教中央机构,负有……定夺教义是非曲直的责任”,因此,“当耶稣会士内部出现分歧并且与其他修会发生争执时,上诉教廷乃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为了不过多地偏离本文的主题,我姑且接受希孟先生的观点。但这样一来,罗马教廷就不是争论的一方,而是争论双方的裁决者。如果争论纯粹是围绕天主教教义进行的,那么,“负有……定夺教义是非曲直的责任”的教廷按理说可以直接做出裁定。但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国礼仪与天主教的关系进行的,而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仪可以说是近乎无知。罗马教廷为此多次召开的神学会议并不仅仅像希孟先生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教廷的态度“诚恳认真”,而是同时还表现出教廷因无知而导致的举棋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负有“定夺”责任的罗马教廷本应当首先了解:在这一问题上,争论双方谁更有发言权?更进一步说,在不对争论双方在天主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做出优劣之分的情况下(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区分),问题的关键本应当在于对中国礼仪的理解,因为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是以这种理解为前提的。但这样一来,答案就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耶稣会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创者。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入华传教之时,耶稣会在华传教已逾时半个世纪之久。利玛窦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国礼仪的了解,在那个时代的在华传教士中间无人能出其右。也就是说,如果抛开其他的因素,就应当说耶稣会士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但遗憾的是,罗马教廷最终采纳了多明我会的意见,做出并坚持了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汉斯·昆对此的评价是:“总而言之,除开路德和伽利略两例,这一决定可能是教皇关于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无数错误决定中最严重的一个。”[2](P40)
这里还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事实上等于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争论、并在争论的后期成为核心人物的康熙皇帝有没有发言权?按照希孟先生的看法,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是耶稣会向皇帝“进谗言,打小报告”,而导致了皇帝以“行政手段”的“粗暴干预”。但实际上,这位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皇帝,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西方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清朝皇帝中,康熙是最开放、最有西学兴趣的。就个人而言,他真诚喜欢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学术和思想,甚至经常把天主教教理挂在嘴上,写在诗文里”[3](P74)。这说明康熙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有一定的理解。在这件事上听一听他的意见,甚至以他的意见为依据来试图说服罗马教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康熙皇帝也不是一开始就动用行政手段的。他在耶稣会士的请愿书上所做的批示只能说是一种表态,没有丝毫强加于人的意思。李天纲先生认为:“这是一份极给面子的文件,等于是屈中国皇帝之尊,请求罗马教皇允许中国天主教徒举行传统的中国礼仪。”[3](P51)多罗来华,康熙立即召见,还是准备与他讨论的。相反,真正首先采用“行政手段”、下达禁令的倒是被康熙斥之为站在门外说屋中之事的阎当主教、多罗特使和教廷。我无意于对康熙后来的反应做出对与否的评价,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教廷的“粗暴干预”,这场争论的性质陡然间发生了变化,由最初对中国礼仪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变成了政教之争。
三、冲突的症结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地谈一谈中西政教关系的差异。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种作为与国家政治分离的独立力量的宗教基本上是没有存身之地的。中国历来宗教观念薄弱,但人们却很早就认识到并认可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故很早就有“神道设教”的传统。自从周代形成“以德配天”的思想后,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在这种意义上,宗教在国家的眼中始终是推行王化的工具。宗教只有在有助于王化或者至少不损害王化的前提下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凡是有助于王化的宗教都会受到国家的欢迎。而王化的核心则是“忠”、“孝”。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几个皇帝笃信宗教,却从未有过某种宗教成为国教,甚至凌驾于政权之上的现象。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排佛乃至灭佛事件,也都是因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忠孝思想发生冲突而导致的。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基督教产生之初,也曾因与罗马帝国的政治发生冲突而受到压制。即便在后来获得国教地位的年代里,也不能摆脱依附于政权的地位。君士坦丁等皇帝对基督教内部事务的干预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罗马教会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会。作为旧世界的仅存硕果,教会借政权更迭的机会摆脱了王权的制约,甚至在中世纪发展成为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的力量。到“中国礼仪之争”发生时,虽然罗马教会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教皇要倚托各国国王才能保有自己的地位,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一大批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形成了所谓的新教,但罗马教廷对各国恪守天主教信仰的教会仍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尤其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耶稣会这些跨国修会,更是惟教皇之命是从。
中西文化传统对于宗教的不同理解,终于使“中国礼仪之争”发展成为一场政教之争。
基督教传入中国,因其信仰而免不了与中国的忠孝传统发生冲突,明末的“南京教案”可以说是这种冲突的第一次白热化。清室入关,对基督教采取了优容政策。顺治、康熙二帝都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西方传教士有良好的私人关系。除鳌拜辅政时代曾发生“历狱”大案外,清廷不仅没有干预基督教的事务,甚至还可以说有所扶持。在华传教士因对中国礼仪理解不同而发生争论初期,凭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密切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有这场争论,但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说明康熙插手其中。即便是在他被动地卷入争论之初,如上文所说,他还是想用讨论来解决问题的。然而,在阎当、多罗和教廷看来,中国基督教对中国礼仪采取什么态度,完全是基督教自己的事情,用不着考虑康熙皇帝的态度。康熙批示的耶稣会士请愿书,没有发现在教廷那里起过什么作用。多罗出使中国,带有教廷禁行中国礼仪的谕令,但多罗在京数月,与康熙相见数次,却闭口不谈禁令之事。李天纲先生认为多罗是“不敢公开来华的真实目的”[3](P61)。我倒宁可相信他认为无此必要。否则,他也不会一离开北京,就在南京公布了教廷的禁令。
多罗对中国皇帝权威的无视和挑战无疑激怒了康熙。敬天、祀孔、祭祖,事关封建中国的“国本”,康熙不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教廷的禁令虽然只是针对中国的基督徒的,但这些基督徒却也是中国皇帝治下的臣民。如果是这些臣民自觉地不行中国礼仪尚且可以容忍,阎当作为中国一个教区的主教下令禁行中国礼仪也没有引起康熙排教,但由一个国外的权力机构来对中国教会、中国教徒指手画脚,甚至事先根本不理会中国皇帝的意见,即便是特使来华公布禁令也不与皇帝打声招呼,这无疑是康熙无法接受的事情。此时的清王朝,尚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不可能允许有独立于国家、乃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宗教。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优容,本就是以其有助工化为前提的,而且这样有助王化的宗教也不仅基督教一家,基督教可说是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现在基督教不仅无助于王化,反而向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康熙的“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中,罗马教会和中国皇帝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但站在我们今人的立场上,他们又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多次的神学讨论固然证明了教皇的谨慎,但始终没有认真听取内行的意见,仍不免偏听偏信之嫌。最后在依然困惑的情况下为摆脱争论而贸然下达禁令,说他武断也不过分。事关中国皇帝的臣民却连声招呼也不打,当然是一种专行。而对于康熙来说,他所维护的是封建皇帝的权威,是封建制度的基石,是要把包括教会在内的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权力。我们不必因康熙是中国皇帝就偏袒他,但也没有必要像希孟先生那样把板子都打在康熙的屁股上。
礼仪之争、尤其是教皇的武断干预最终导致了康熙的禁教,这是不争的事实。希孟先生以中国此前此后无礼仪之争却均有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来反对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无力的,因为我们不能以昨天没下雨而是人泼水湿了地来否认今天是下雨湿了地。但我赞同希孟先生没有礼仪之争、没有教皇干预仍会发生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观点。如同前文所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是礼仪之争深层次的原因,即使没有“礼仪”之争,这种冲突仍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如果没有教皇的武断干预,这场争执也许不会以历史上的那种方式结局。不管怎么说,那样的结局毕竟是当时的争执各方、包括是今天的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四、礼仪之争的苦果
“礼仪之争对中国和西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对西方来说,礼仪之争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欧洲持续的中国热和汉学的兴起,从而使中国哲学和宗教传入西方。”[4]而在中国,它所造成的结果却基本上是负面的。
礼仪之争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对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的冷淡。康雍乾嘉四朝的禁教政策愈演愈烈自不待言,士大夫中间对基督教的反感也受到了鼓励,乃至发展到排斥整个西学的程度。清初因耶稣会士的努力而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翻译、介绍西方宗教、哲学、科技的活动基本沉寂。随禁教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它虽然并不是禁教的必然结果,但却与禁教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闭关锁国使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在强盛时期融入世界的机会。此际的西方,正处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与世界的隔绝加固了中国统治阶级夜郎自大的心态,使中国逐渐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是西方最终用炮舰敲开腐朽没落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使中国堕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礼仪之争的结果对中国基督教会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国教会的衰败。礼仪之争基本上中止了基督教在华和平传教的进程,但却没有浇灭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热情。在此之后,基督教各修会都没有停止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鉴于清王朝的禁教政策,这些传教士甚至不惜采取贿赂地方官员乃至偷渡的方式在各地建立地下教会。然而,这种备受限制、偷偷摸摸的传教方式与传教士们“中华归主”的愿望是不相称的,一些传教士开始要求用武力为基督教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始对中国的殖民化固有其政治、经济原因,却也不能排除基督教界的鼓动乃至帮助。我们固然不能否认许多传教士在传播先进文化、破除封建迷信、举办慈善事业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中国的近代史也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一些传教士鼓动本国政府侵略中国、为侵略军充当间谍和内应、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做手脚等罪恶的记录。
武力支持下的传教进一步加重了基督教在中国作为“洋教”的不光彩角色,加深了中西方的隔阂。清末频频发生的教案,甚至包括被基督徒称为最大“教难”的“义和团”运动,虽然都有其复杂的因果关系,甚至毋庸讳言包含着盲目排外的成分,但一些基督教徒仗恃“洋教”身份,在炮舰与刺刀的保护下行事肆无忌惮,甚至霸占田产、横行乡里、包揽词讼,却也是中国民众仇外、仇教心理的一个重要诱因,而这在清初和平传教的氛围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说,清初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和教廷的做法虽然有些欠妥,但毕竟主要是出自信仰的理由,甚至有“冲击”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积极作用,这至少还可以让我们有所敬重的话,那么,清末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则可以说是不仅更加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而且也更加远离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宗旨,更应当受到基督教的“绝罚”。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提出的“本色化”口号之所以在贯彻上步履艰难,在一定意义上也不能不说与这种和平传教向武力传教的转变有着某种联系。
“中国礼仪之争”的喧嚣离我们已经远去。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冲击,传统的中国礼仪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本”,罗马教廷于此时取消禁令,虽然颇有点“马后炮”之嫌,但也毕竟是一个明智之举。当然,我非常欣赏希孟先生对中国迷信回潮的担忧,而且也相信中国基督教在反迷信问题上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更多考虑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仍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如何在这种对话中保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和平的心态,仍将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老话题。
标签:康熙论文; 耶稣会论文; 基督教论文; 传教士论文; 罗马教廷论文; 天主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礼仪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西方礼仪论文; 清朝论文; 教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