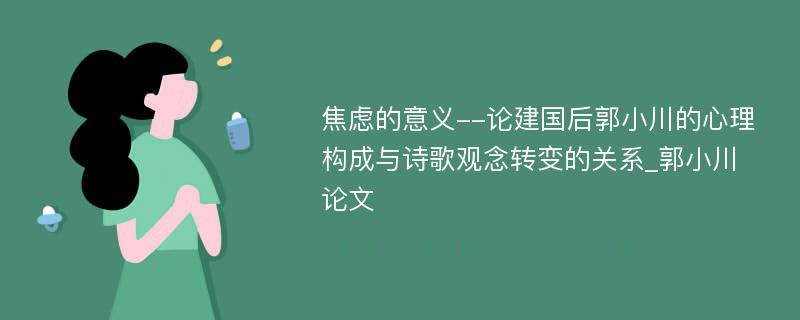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诗歌论文,心态论文,理念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9)02-0106-06
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诗歌演变历程中,无论是诗人精神世界,还是诗歌文本创作都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的现象,透过这些已然历史化的“现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曲折与艰难,还能更加深入了解当代诗歌的问题与症结。在这些“现象”中,“郭小川现象”吸引了不少当代研究者的目光。综观郭小川的研究,人们主要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问题的探究,这样也就无法从研究对象中提取重要的命题,深入而有效地揭示“现象”的复杂性。在郭小川的生命世界里,“焦虑”是他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心态要素,同时也是建国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症候。那么,究竟是何种“语境”催生了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有哪些维度?不同维度的焦虑与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变迁及思想转换之间有何内在关联?简言之,郭小川建国后焦虑心态的意义何在?我们试图以“焦虑”为核心命题,探察1950-1970年代诗人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其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身份焦虑
郭小川曾在《小传》中说:“我的写作差不多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稿费成为必须的收入的一部分。”[1]3,25这表明为谋生而写作是他最初的创作动因。在1935-1950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工作”中,由于政治仕途上的腾达,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热望和以“诗”安身立命的期盼,此时“写作”逐渐变成了自身施展才华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在进入“作协”之前,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行政官员,其“作家”或“诗人”身份始终是模糊的。
郭小川的“诗人身份”问题直至他调入“作协”之后才凸显出来。杨匡满回忆说:“郭小川是属于那种在群众中人缘极好却有部分老干部说他是‘天真’、‘不安分’的人。”[2]的确,他同意调入作协是有自身的“想法”的,除了服从组织的决定,想“跟党组和白羽同志把作协整顿一下”,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借助“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创作恢复起来”[3]25。尤其是进入作协不久以后,他就“在作家面前有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因为他曾听到“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之类的非议。[3]25。无疑这些“非议”,一方面让他受到一种精神刺激,觉得非作家在“作协”很难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作协这样的文学团体中,郭小川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作家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作协秘书长”,他处理的大多是日常繁杂的事务,如果想要让他人信服,获得更多的尊重,就必须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在这方面,郭小川是相当自信的:他坚信“只要有机会写作,我的才能也不见得比你差”[3]26。“我相信,我的才能是很高的,只要我去钻,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在创作上干出一番事业来,成为大作家。”[4]166显然,郭小川不仅有明确的目标和饱满的激情,还有坚定执着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在“诗人”身份确立过程中,他陷入了一种持续的情绪焦虑的漩涡之中。那么,郭小川的“焦虑”来自哪些方面呢?
他的“焦虑”主要源于作协繁杂的“事务性”的工作。郭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必须处理日常工作中相当多的“杂”事:“这个秘书长工作,头绪纷繁,党内党外,会内会外,国内国外,又是组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又是编辑工作。”[3]26在单位上班时是如此,有时在家里也“不断有人来”找他,谈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这使他非常苦恼,因为工作挤兑了他创作的时间,为此,他只好充分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拼命写作。写诗没有时间的保证,加上又患有“精神衰弱症”,有时为此诗写不成,心情也变得异常郁闷。在此期间“时间”焦虑感爬满了他的心头。不仅如此,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不得不应对许多相当棘手的事情,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心境。比如1957年为了写丁玲和陈企霞的结论,他的精神紧张到崩溃的边缘,心情坏到了极点:“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了我,情绪有时就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压人。”[5]9“心中郁郁……工作又压得很多……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5]85在这样的压力和心境中,他说:“如果能够摆脱这个工作,我也许会完全沉浸在写作中的。现在却不行,有时心中非常之不安。”[5]43可是,他所期盼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创作空间最终还是被这些“棘手”之事无情摧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给他带来的是难以摆脱的“空间”焦虑。郭小川在确立诗人身份过程中的“时空焦虑”,常使他卷入悲观绝望的情绪流中,有时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把这种情绪移到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如《深深的山谷》一诗所书写的男主人公对革命工作逃避,某种程度上就是郭小川借“男主人公”之口,浇胸中“块垒”——对“作协”工作的厌烦与恐惧。
有趣的是,持续的精神焦虑非但没有使郭小川创作出现滑坡,反而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刺激,使他养成了诗歌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的“自觉”意识。在创作方面,他收获颇丰,诸如《投入火热的斗争》(1955);《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致大海》(1956);《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1957)等诗歌的发表,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让他牢固地确立了诗人身份。显然,“焦虑”之于郭小川是有意义的。虽然紧张、压抑、惊恐等会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场”,并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焦虑”的作用并非都是负面和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作为主体实现能动转变的动力源。心理实验表明,在正面处理焦虑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让心智得到锻炼,实现精神自觉,而且还能提高生命存在所必需的张力。郭小川把“身份焦虑”的压力转化为诗歌探索的动力,从而引发了“诗歌”探索的自觉,即对诗歌“写什么”、“怎么写”进行紧张的思考与求索。比如,在许多诗集“后记”中,他经常谈到自身的某些困惑和“焦虑”:“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情感表现出来;我在探索着和它相应的形式,我在寻找着合适的语言。”[6]259诗歌“所谓‘楼梯式’的排列方法”,“我常常想,反正是一种摸索,还是摸索摸索看吧。等摸索出一点头绪再说吧。”[7]384“几年来,在业余时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自己称意的诗作,至今还一篇也没有”[7]393。“这期间,我写的诗大部分实在不成样子”,“想到这里,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够总是让这淡而无味的东西去败坏读者的胃口吗?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不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荣誉呢?”[7]394正是在自身的诗歌创作困境与出路的探求中,郭小川提出了关于当代新诗“独特”的见解:“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诗歌必须有“思想”才能“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长久的深思”,“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是作者自己的,是新颖而独特的,是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加工的,是通过一种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7]394-395简言之,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和个体的生存语境中,确立“诗人身份”(或“成名”)的焦虑不仅激活了郭小川对当代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索潜能,还点燃其“绝不认输”生命激情,同时也促进了他探究诗歌本体的自觉。
如果说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使郭小川实现了精神自觉,那么双重身份(诗人和文化官员)的矛盾冲突产生的焦虑,却造成了他的精神危机。在这里,“身份”冲突主要体现为“角色”冲突。作家角色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角色期待”,即“社会他人对身份的期望和要求”;二是“角色认知”,即“自己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符合自己的身份的理解”;三是“角色行为”,即“个人按照角色期待的要求和期望,按照自己对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去实现角色的行为方式”[8]82。可以说,郭小川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认知之间出现“错位”。周扬、刘白羽把郭小川调到作协当秘书长,一则希望他“担负起斗争的任务”[9]31;二则希望他能安心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鼓足干劲去做,决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做一点违反团结的事”[9]45-46。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文坛领导对“作协秘书长”的角色期待。就前者而言,郭小川确实表现出很强的“斗争”勇气,比如对丁、陈的斗争,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当党内发生分歧之后就变得犹豫起来,对丁、陈的结论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求组织上向他们道歉”[3]23。同时,他在反右斗争时,政治上表现“软弱”,“有不敢得罪人”的倾向,甚至有传闻说,“文艺界党员中只有四个人跟党外没有墙,其中一个就是郭小川”。这些表现与周扬、刘白羽对他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不但使周、刘大感失望,而且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就后者而言,郭小川是相当“不安分”的,他觉得作协不仅“事情繁杂”、难以应付,同时还“容易犯错误”,“常常想做个比较单纯的工作,能够腾出手来,研究一些问题”[3]26。更严重的是,他在情绪激动中写信给刘白羽,表示自己在作协“身心都快要崩溃”了,甚至提出要离开“作协”,并且还和王任重联系调动的事宜,后因陆定一和周扬不同意才作罢。郭小川向刘抱怨“作协”工作,提出离开作协的要求,被认为不做“党的驯服工具”遭到批判。由于郭小川身上依然保留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率真、反抗奴役压迫等性情,因此当他以诗人(或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眼光”而不是以文化官员应有的“政治眼光”处理复杂的人和事时,必然会产生时代所不容许的“角色行为”。他为此进退维谷,内心始终处一种紧张、忧虑和恐惧的情绪状态之中。
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出现了不见容于时代的“角色错位”。如《一个和八个》主要以“肃反”和“审干”时,出现一些“冤枉好同志”和“斗错人”的现象为故事原型,试图展现八路军指导员王金的“人格魅力”。郭小川从“诗人”而不是“政治家”的角度来选择这一敏感且歧义丛生的题材,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必须有新颖独特的东西,才能“引起人长久的深思”。虽然他对“这样的题材也没有把握”[3]30,但是他还是被王金的形象深深吸引,于是在反右斗争结束后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在作品正式面世之前曾送给臧克家、徐迟、巴人、陈白尘、靳以和周扬等人“审阅”。藏、徐、巴“赞口不绝”,陈白尘则“犹豫不决”,靳以则“尖锐批评”,周扬则“没有看”——不同反应成为郭小川诗歌探索陷入焦虑的重要诱因。这首诗歌虽未发表,但该诗却在1959年11月被当作了“内部批判”的材料印了出来,作协党组内部开始无休无止的开谈心会、批判会。这一“事件”的发生,与郭小川的“角色认知”和“角色期待”之间出现的“错位”有关:一是郭小川认为自己从“诗美”角度选择题材并无大错,而当时文坛权威者则认为他的诗歌缺少“政治”眼光,问题很大;二是在郭小川心目中“诗人”身份高于“文化官员”身份,而在周扬们眼中他的“文化官员”身份比“诗人”身份更重要。郭小川这些“错位”已显露了他的“不安分”:不安心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作协秘书长”,不安心做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诗人”。这样一来,《一个和八个》遭到批判成为时代必然。当党组谈心会上,有人提起这首诗时,他说:“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想到这首诗问题会这么严重,更重要的是,他没想到诗歌没有发表居然也能可以成别人批判的把柄!?这一批判成为郭小川身份归位和诗歌理念转变的重要“事件”。在1959年反右斗争中,他不得不对自我的“角色行为”进行反复的思想检查。(如《在作协总支党员大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检查》、《再检查》和《第二次补充检查》等等)。三番五次的检查使郭小川在艺术创作上越来越不自信,他对自我原有的诗歌理念也渐渐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了精神危机。他不断地责备和贬低自己,认为自己作风“散漫”,思想动机“险恶”,“自我扩张”严重,丧失革命“立场”,“向党伸手”,斗争“态度妥协”,“理论水平低,逻辑能力差”,内心空虚,情绪低落等等。同时,他也为自己定了具体的奋斗目标:一、“努力学习、辨别风向”;二、“好好安排工作和创作”,创作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四、“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五、“安心,不管做什么,要安心”[3]32-33。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诗歌理念上还是在个体思想精神方面,郭小川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说:“我两个月来的检查即使还不能说深刻地认识错误,也已经至少发觉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心中充满了向党赎罪的愿望,无论叫我做什么工作,都将积极以赴,这是不成问题的。”[10]206
郭小川身份冲突引发的精神危机,使他离开作协的愿望变得相当迫切。在他看来,辞去作协的职务也许是消除内心焦虑的出路之一。1961年6月,他接连两次致信党组,强烈要求调离作协,向刘白羽、邵荃麟表示他“梦想着离开作协到下面工作”,“合法地(而不是提心吊胆地)写点东西”[10]200-201。经过多次努力,他终于有机会到上海、福州、厦门、广州等地了解作家创作和生活情况。1961年9月19日,他在致杜惠的信中说:“下午,与周扬同志谈了话,谈得相当愉快。他最后同意我下去一年——这也是一件好事。但为了这事,我几乎一夜没睡觉。”[10]231从中可以看到当他获准创作假一年时内心是何等地激动与兴奋。这次“诗人”身份的外出考察,让他感到一种身心的解放。这期间除了接客访友之外,他常常陶醉于当地的名胜古迹、民俗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之中,心情“兴奋得很,愉快得很”。1962年他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曾决心不搞文艺创作,不进作协的门,不与周扬、刘白羽、张光年等发生任何往来,甚至决心不写文艺作品”,只写“通讯,把写通讯当成终生的事业”[11]259。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在努力实践着。这里,郭小川想放弃“诗人”身份,只当一个通讯报道员,足可以看出他对那段精神“焦虑史”的恐惧与逃避。他希望尽快消除内心的紧张、焦虑和惶恐,回归愉悦与平静。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独特的现象:在“身份确立”和“身份矛盾”的焦虑中,郭小川把这种“焦虑”的情思投射到诗歌所营构故事或意境中(如《深深的山谷》、《一个与八个》、《白雪的赞歌》、《望星空》等),使生命个体存在意义与历史现实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并且让诗歌在多重声音的交织中充满诗意的张力;而当他的内心远离焦虑,走向愉悦时,他的诗歌则变得单纯且明朗,激情有余而回味不足。比如诗集《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诗歌,开始主要以“颂歌”形式歌颂创业时代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表现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此时的郭小川已逐渐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歌者”和“鼓手”。
二、道德焦虑
郭小川度拥有的精神愉悦时光是相当短暂的。1966年12月,他开始在人民日报社受到群众的批争。1967年“被作协群众组织揪回作协批斗”,并写检查材料。1968年被隔离审查三个月之后又不断写思想检查材料。1969年几乎整年在写检查、思想汇报和接受批斗。在此期间,郭小川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焦虑——道德焦虑之中。在“十七年”和“文革”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呈现泛政治化倾向,也就是政治权力毫无限制地全面入侵并控制文学的各个领域,使文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释义的政治符码。有趣的是,对创作主体的“政治化”规训常常通过政治的道德化来实现,即主流意识形态将政治立场和理念的正确与错误指认为道德行为的高尚与低下,从而使创作主体产生一种道德焦虑,进而检视自我既往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实践,从道德层面进行深刻忏悔。
这里不妨以郭小川1969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为例给予说明。在这篇检查中,他把自己过去的思想行为置于革命者“道德”的显微镜下,加以对照并放大,于是出现了种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是“不忠诚”。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伦理中,对“革命忠诚”是一种极为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文革”期间,“革命”的忠诚已演化为对“领袖”及其思想的忠诚或崇拜。郭小川说:“我自己有千条罪行、百条错误,最根本的是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怀疑甚至抗拒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的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大节中的大节、要害中的要害”[4]162;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从来也没有达到‘三忠于’、‘四无限’的地步”;“人民群众从心里唱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声音,而我却想不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想到写到:‘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这不是态度问题吗?”[4]180。他试图通过话语修辞把“问题”放大藉此进行道德自责。二是“私欲膨胀”。就现代的革命伦理而言,集体和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个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至于个人欲望那更为革命者所不齿。郭小川认为“私欲”的根源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只好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爬”,同时在学校培养了“姿势特殊”、“出人头地”的思想。他甚至夸张地说:“我到旧作协,是怀着强烈的个人目的,甚至是个人野心的”。从事创作,是想“当大作家,名利双收”,不愿当作协秘书长,是认为“要当秘书长,还不如到省委去当个秘书长呢!”[4]166这种力求通过夸大乃至歪曲自我欲望的动机,目的以准自虐的方式给道德焦虑减负,获得精神解脱。三是“动机险恶”。理想革命者应当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在这一理想的道德比照下,他感到自己思想阴暗、动机险恶。此类“罪行”包括“围攻鲁迅”,试图创办“同仁刊物”,写了一个特大的毒草作品——《一个与八个》。四是“趣味低级”。毛泽东曾号召人们做一个“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低级趣味”无疑是革命者身上的道德污点。郭小川居然在自己的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污点”。他认为《白雪的赞歌》中,表现出“浓厚的对战争的感伤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一部反战作品,美化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谈情说爱,低级趣味”[4]173。为了解决灵魂深处的“道德问题”从而“第二次获得政治生命”[4]161,1968年起,他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并因不能完整背诵而焦虑不安。知识分子在“检查”和“背诵”双重夹击中“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有效地实现了新旧思想的“置换”与“植入”过程。
很显然,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倾向,使与文学相互关涉的各个方面都染上道德的色彩,由此培养了一批自觉产生道德焦虑、学会自我监督和自我反省的主体,使他们不断追求崇高革命道德情操,同时也自觉自愿俯仰于意识形态之召唤。可以说,在1969-1971年间,郭小川几乎都在这种自虐式的道德焦虑中度过的。在这种情势下,他也只能通过书写歌颂领袖和解放军的诗歌及歌词,来缓释心中的“罪恶感”和焦虑感,并藉此表明自我对领袖和新政权的无限认同及其自我转变的彻底性。诗歌不再是诗人主体精神、复杂内心的感性显现,而是展示自己革命的忠诚与纯粹的另一种深情表白。
三、存在焦虑
人的存在的焦虑,不仅表现为人在物质世界中求生存的困境与挣扎,还体现为人在精神世界里追问生存意义的紧张与恐慌。前者关乎“如何生存”的问题,后者则关系到“为何生存”的问题。对于一个处在动荡、残酷和异化的生存语境中的生命个体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也相当棘手。为了探索和解决这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人们常常陷入一种焦虑的情绪场中,轻则苦不堪言,重则悲观绝望。当然,对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焦虑也强化了他们摆脱外在环境与精神桎梏的渴念,以及以艺术为“武器”找回自我、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望。
1970年,郭小川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可是,在这里“气候条件之差,劳动强度之大,军宣队管教之严,思想整肃之深,都使干校的人们不堪精神重负”[4]173,郭小川概莫能外。他必须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生活条件。这里“地势卑湿,沼泽密布,水恶山穷,气候恶劣”[4]161,住的是“简易的土房”,吃的是“发霉的粗米”,虽然郭小川“能吃苦”,以自己的体力挑战生存的艰辛,但是他还抱怨说:“这里的气候,对我实在是极不适应的”;而且一个月内犯病八次,“一犯病,就喘息不止,其势凶猛”。他感慨道:“我已五十五岁,再有三年五载,我这个人就报废了”[12],这种慨叹既有身体之“痛”,更有时间之“伤”,个中滋味难以言尽。这样的生存条件,加上干校高强度的劳动,使他觉得这里的生活“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为此,他“曾上书干校领导”,认为“生产任务太重”,干校应“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结果“干校的L政委一见到郭小川就要批评,把他当成典型”。然而,有些事实却是不能不正视的:1971年,侯金镜在“‘双抢’时累死,相当多的同志得了肝病、肺病、胃病、肾病”[13]66-68。这些都让他深切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与抗争的无力。1974年12月,当他转移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时,“身体虚弱,走一段路就得在路边歇一会儿”[14]。而此时他又成为“中央专案组”“专案审查”的对象,在那里他的行为受到极大的约束,甚至他提出回京治牙的要求都遭到拒绝。面对审查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他身上有“异常的压力和无奈的感叹”,并且情绪极度低落,精神“焦灼、烦躁”。在压力面前,他一面喊出:“我要革命,革命!”[15]一面却常常靠抽烟喝酒、吃安眠药来刺激和麻醉自己。而在团泊洼干校的晚期,面对着逐渐离去的人群,郭小川在遥遥无期的等待“结论”中,心里笼罩着一团不安的迷雾。
实际上,郭小川更为关切的是“为何生存”的问题。在干校,军宣队“非人性化”管教和“专案组”非人道的审查,使得人处在一种“异化”环境中如履薄冰,甚至尊严也时常被践踏。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为了守护生命的尊严,他常常在政治与现实的缝隙之间进行艰难言说,并试图通过诗歌重建生存意义。
无疑,在言论管制极为森严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另类”言说带有极大的风险,有时他们在“说”与“不说”问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比如,当时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过程中,“专案组”经常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进行审讯,当这一局面愈演愈烈时,郭小川“决定向干校最高一级的军宣队写信,对军宣队的工作提出全面的批评和建议”[16]。但是,他的这番举动非但没有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使“自己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挨训、写检讨似乎是唯一的“收获”!他曾抱怨:“我在家养病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场”,并且“尽量做到‘祸’不从口出”,但他在致王榕树的信中又说:“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也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的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都是‘发言集’。”[16]这里的“革命”既可看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可看成是内心的革命。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一诗正是他向“非人现实”的“发言集”。他把个体的生存境遇置于“团泊洼”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这里,蝉、麻雀、蛙的嘈杂声音都消失了,也就意味着时代“多重声音”已消退,“野性的河流”不再“喧哗”,意在表明知识分子身上的“野性”已被驯服,这无疑是单调死寂的“团泊洼”。“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这又是充满斗争、攻击和暴力的“团泊洼”。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空间萎缩了,个性变得模糊不清,而暴力的声音却如利剑直指心胸,他们的生存意义遭到严肃的拷问。虽然“沉默”成为时代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但他预感到了“沉默”力量:“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为挣脱精神桎梏和重塑自我发出的呼喊,也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泣血叩问!他深信“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这不仅是他历经精神磨难后“重振士气”的宣言,更是对诗歌“介入”现实和重建生存意义的精神期待。
[收稿日期]2008-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