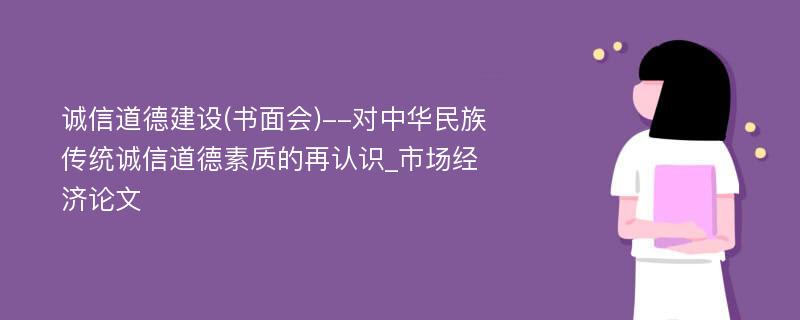
诚信与道德建设(笔谈)——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素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诚信论文,笔谈论文,中华论文,道德建设论文,道德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享誉于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诚信为本、一诺千金的美德修养。近些年国外有一些对中国持非善意的人,在妄言中国“崩溃论”,指责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虚假化”的同时,甚至责难中国人的诚信美德,竟然诬称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这样的大谬之言,确实是对一个有着极高道德水准的古老民族的严重污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样的诬蔑不实之词,应引起国人的高度警觉,并给予迎头痛斥。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至迟自孔子始,中国古人就已经将诚信道德规范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上了。《论语·颜渊》中记载的子贡与孔子关于政事的对话,确实可以视做儒家对诚信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实。’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成为后来执政者的警世之言。后来,孟子讲“五伦”,其中一伦便是“朋友有信”。西汉之后逐渐成为官方伦理纲常的“三纲五常”,其中在“五常”中也包含着“信”这一规范。宋代时朱熹讲“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继承的仍然是孔子以降的“道统”。清朝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格外重视“诚”和“敬”这两个规范,承接的也是从孔子到朱熹的一贯思想。
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在作“三民主义”的演讲时,还专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的“旧道德”的问题。孙中山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P243)孙中山提出的这著名的“八德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信”包含在这“八德目”之中,可见革命者孙中山并没有“革”“诚信”的命。
孙中山不但未革“诚信”的命,而且还对中国人的“信”的道德水准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1](P245)。有意思的是,孙中山所列举的,恰恰是商业交易的例子。孙中山说,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相互订货,中国人不要求立合同,只要记入账簿即可,外国人则一定要立合同。中国人虽然不立合同,但在交货时哪怕货物价格很低,要赔很多钱,也一定会守信用,不情愿退货。所以外国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还要守信得多。孙中山还批评日本人,说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纵然与日本人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因此,外国人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孙中山所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真实故事,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美德。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人诚实守信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只要不是无知,不是心存偏见和敌意,就根本得不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的荒唐结论。在回击国外不友好人士的敌意诋毁时,我们需要大力颂扬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不容动摇。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环境和新挑战时,又需要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如何将古老的诚信美德与时代的信用体制、诚信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诚信道德规范体系。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诚信美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一美德是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基础的产物。第二,这一美德在主要调节对象上,属于“公共信用”的范围,而不是经济领域所独有的,至少不是以调节经济交易关系为主要使命的。第三,这一美德在自己的调节领域内,约束力量是直接的和极其强大的。
中国古代诚信美德的第一个特征,决定了其在原有的内涵上,适合调节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经济关系,而在调节复杂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时,就会显现出它的无能为力的一面,诚信道德的失范效应也很容易产生出来。孙中山在20世纪初谈到的中国人在做生意时不订契约、不立合同而同样守信的现象,一方面固然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固有的诚信美德品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诚信道德仍然处在当时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现实境况。简单的商品交换还能够允许口头承诺的交易形式,而在复杂的商品交换中,在市场经济中,对交易的口头承诺,则显得非常不够了。契约、合同,作为基本的交易约定方式,不仅是交易的正规化,而且是现代商品信用制度的必然要求。只有依靠现代的社会商业信用体制,才能够有效和可靠地进行大宗量、长距离和长时间跨度的商业交易,这些交易靠小商小贩式的口头承诺是很难兑现的。
中国古代诚信美德的第二个特征,决定了它的主要调节使命,一是调节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就是“取信于民”,即孔子所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二是调节朋友之间的关系,即孔子所说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即孟子“五伦”说中的“朋友有信”。中国古代大量的诚信典故中,如商鞅“悬金移术”,曾参杀猪慰子,季札心诺挂剑,季布“一诺千金”等,主要记录的正是取信于民和朋友有信方面的内容。而像明山宾卖牛这样的史实,被记录和传诵的则相对少了许多。
中国古代诚信美德的第三个特征,决定了它确实能够使人做到一诺千金,不食其言。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了许许多多将信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故事。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曾记载了田光因见疑而“自刎而死”的故事。燕太子丹因忌恨秦国对他的摧残,为了报仇雪恨,燕太子丹请求“智深而勇沈”的谋士田光帮他出谋划策。田光向太子丹举荐智勇双全的荆柯,并商讨刺杀秦王之计。在送田光出门时,太子丹告诫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见过荆柯并向荆柯交待完任务后,感慨地对荆柯说:太子丹所告诫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因遂自刎而死”。田光的故事,很能代表古人特别是“士君子”对于“信”的一种罕见的“执著”遵奉的精神。在中国古代,一个“士君子”如果“信而见疑,忠而受谤”,将被视为人生际遇中的大不幸。正是由于古代的诚信美德有如此大的约束力,因此,儒家在强调“信”时,也同时强调“信”的“权变”,即“信”并非机械死板地“说到做到”,“信”要以“义”为基础,在遵行“信”的道德规范时,要区分是非曲直,如果“信”与“义”不符,那么“士君子”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否则,要是机械地遵守“育必行,行必果”,在孔子眼里,这样的人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21(P185),也就是“不问是非曲直而只管贯彻言行一致的小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非常有限的环境中,古代道德包括诚信道德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对人们言行的约束力是相当大的。也正因为这样,“一诺千金”才不是社会的道德理想而是社会的道德现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尤其是经济交易的范围急剧扩大之后,仅靠口头承诺的古代诚信道德,其对人们言行的约束力,将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思考诚信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所必须认识到的新变化。
正如孙中山先生当年所批评的那样,日本人上世纪上半叶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糟糕的诚信素质是被世人讥讽的。日本人不仅在履行契约方面不守信用,而且在商品的质量上也是不守信用的。当年的“东洋货”,便是“劣质货”的别名。日本商品在质量上的洗心革面,是在二战之后的生存抉择中发生的。二战之后,一个战败的民族,已决无可能再用劣质商品到世界市场上去强买强卖。恩格斯当年在谈到德国商品的质量改进时,也是说德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在美国费城的工业上的“耶拿战役”之后才醒悟过来的。1876年5月10日,为了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在美国费城举办了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为了与英国和法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争夺份额,德国也参加了这次博览会。然而德国人因其产品的质量远不如英国和法国而惨遭失败,就像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的耶拿战役中惨败于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一样。德国人自己不得不承认本国工业遵循的是“价廉质劣”的原则。
日本和德国的例子都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严格的社会信用制度,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上的诚信道德规范,任何国家都会在商品竞争的战场上败下阵来。中国固然有优秀的古代诚信道德的传统,我们应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资源,以作为今天建立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借鉴。但我们却不能躺在传统的宝库上面不思进取,不能将传统的诚信美德简单挪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来,以为这就是现代的社会信用制度和诚信道德规范的惟一内涵。即使是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因而“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这样一些话,也应结合复杂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盲目认为中国有深厚的诚信道德的历史积淀,从而不需要去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制度相适应的现代诚信道德规范体系。为着正确处理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们需要将传统的诚信美德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不可取的。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道德素质论文; 诚信论文; 道德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人论文; 国学论文; 田光论文; 一诺千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