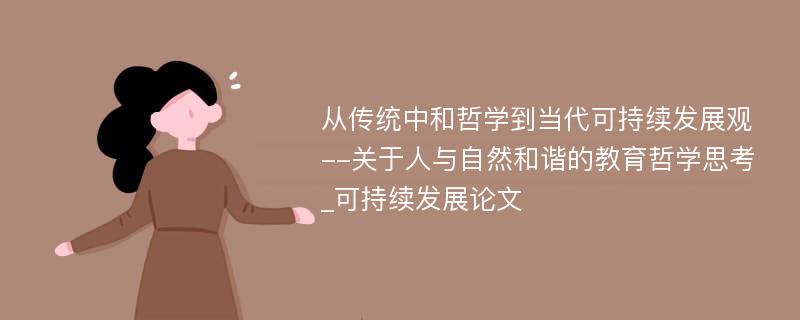
从传统中和哲学到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的教育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人与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自然和谐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认识和把握中和哲学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蕴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系,以此审视当代乃至未来的教育,进而确立与现代化及未来相适应的人与自然和谐观,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一、传统中和哲学的文化意蕴
“尚中”、“贵和”是中华文明的古老精神。华夏先民早已探知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准确性之存在,这就是“中”,并由此引申为准则。孔子首倡“中庸”学说,视“中庸”为“至德”(注:《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并将其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和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贵和”的观念也由来已久。在远古农耕文化的土壤中,就已滋生了“和”的朴素观念。先民们早已认识到,只有天地有序,并顺物之性,才能获得自然的恩泽,并成就事功;反之,若天地之气失和,逆物之性,则会带来自然灾难,并危及生存。先民们还意识到人人相和的重要性,为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聚族而居,亲睦协力,和谐相处。古人以“和为贵”,常把天地阴阳、宇宙万物最高层次的和谐称为“太和”。
在传统文化中,“尚中”与“贵和”历来紧密相关。“和”并非构成事物各种因素的任意掺和。事物要达到和谐,其构成因素必须保持某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规定了各不同因素所应具有的“度”。即是说,“中”就是“和”的要求。事物的各要素只有适度协调,处于适中状态,事物总体上才能和谐。“中”的要求,也只有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从整体和谐的要求出发,才能作出适度的把握。因此,“中”与“和”常常被合称为“中和”。先哲们不仅就“中”与,“和”做出界定,视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首次提出“致中和”的命题(注:《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天人、主客、物我三重意义上建构中和学说。
先哲们普遍认为: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是由该事物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若要达到该事物理想的存在状态即整体和谐,就要使各种因素的作用适宜地发挥,而每一因素又都有其自身的限度,若达不到或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造成事物理想状态即整体和谐的破坏。所谓“中和”,即是将不同因素或对立的两端适当配合,使事物合乎法度准则,达到最佳状态与和谐境界。
中和意味着调适与生机,是一切事物生成、转化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礼记》提出:“和,故百物皆化”;《荀子·天论》也有“万物得和以生”之说。颇具代表性的是《国语·郑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如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事物的和合才能导致事物的产生。和的根本功能是“生物”,即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事物的成长发展。“和”是动态的,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形式,唯有如此,才能生成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但若“以同裨同”,将相同的东西简单地加到一起,虽然在量上会有所增加,但难以产生新的事物,甚至会使事物无继而弃。《礼记·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说,若能推及中和于天下,则天地万物各正其位,一切生灵因此而孕育繁衍。
传统中和学说的实质是确认并追求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人及群体社会的和谐。老子看到,“天之道”的本性是和,“人之道”应“法自然”、法天道,对万物“利而不害”,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先哲们确认,天不是与人相争相敌的,而是与人相辅相成的,事与物都有其自然和谐性,人们理应追求天人合德、万物一体的理想,以其中和之德而化育天下。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由个人的和谐推及家族、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和谐。受其影响,和谐一直成为中国人生活目标的价值追求。
中和哲学有其不可多得的积极而合理的因素。由于尚中贵和传统,使中国文化对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个体身心关系的阐释颇具特色,而且富有价值。不仅如此,通过长期渗透于文化教育,对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国民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整体中辩证思维的生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中和学说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传统中和哲学,关注人与自然、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怀国家、人类的命运,强调适度、协调与秩序,追求安宁与普遍和谐,这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致的。
可持续发展曾成为世界各国迈向21世纪的行动纲领,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史、文明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若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变成现实,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今世与后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并使之和谐化。“和谐”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追求。
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持续性发展,要求当代的发展应着眼于未来,需兼顾未来的发展,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发展的基本前提,并使二者相统一,从而确保人类社会自身具有永久不断发展的能力。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致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既要功在当代,又要造福后人,泽及千秋。这就要求人类必需从过去那种视“征服自然”为成功与荣耀,以“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为天经地义,转变为爱护人类仅有的唯一地球,珍惜各种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人类赖以生息的生态环境。这实际上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界价值的统一,人类生存发展权利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权利的统一,生态的延续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的统一。
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平等性发展,要求除了当代与后代的代际平等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本民族与他民族、农村与城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都应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如果一部分国家、地区、民族、阶层与个人的发展和富裕,是以对相应的另一部分的剥夺并造成其贫困、停滞、倒退为前提条件,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和谐安定。
可持续性发展还需要整体性发展,要求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将地球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整体,蕴含其中、环绕其周围的资源、人口、生态及环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基于此,必须用整体发展战略将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与利益加以整合,致力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谋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
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协调性发展,无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只有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才会带来可持续发展社会。若只顾其一面,不及其余,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即使有所发展,那也只是片面或畸形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持续性发展、平等性发展、整体性发展与协调性发展,都致力于对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构成发展的各种要素“各当其可”,以最大可能地实现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并不是传统中和哲学在当代的简单的回归,而是时代变迁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恰恰是传统中和哲学观在当代的体现,其本质都是对和谐的理性追求,力图以适度的原则、“时中”的精神,消除人与自然的对峙,化解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协调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代人与未来人和谐的稳妥之路。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的世纪。在一百年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几乎可与以往数千年中所创造的一切财富相比。然而不可否认,人类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曾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资源的滥用、能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危机、疾病的肆虐、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道德的沦丧、人情的冷漠、人权、贸易之争、核弹威胁、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这既不合乎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如何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与即将面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重大难题,如何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以弥合、超越而找出一条走向未来的稳妥之路,引起了人们的苦苦思索与探求。有识之士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发现富于“天人合一”精神的中和哲学的价值。英国学者汤恩比一再指出:“和”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它有助于使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营垒所形成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注:参见汤恩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59、286-308页。)这一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充分肯定了“中和”之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与导向作用,也可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的思想基石。中和哲学所涉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身心等谐和关系问题,正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关注的。这一理念无疑会为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思维视角与价值取向。近年来,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论”的悄然兴起,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与初步实施,无不因应时代之需。当今时代所最需要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睦的人际关系,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正确的人与自然观,以求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教育哲学思考
传统中和哲学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都是对和谐的理性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适度处理多种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素养的富有主体意识的全民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而人的素养的提高,恰恰有赖于教育。中和哲学所涉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身心等谐和关系问题,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关注的,而且是现代教育哲学所迫切需要回答的。
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系统的持续性发展,其核心内容是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保证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就为当代教育哲学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报告中,曾以“人类与地球相和谐——走向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表达了人类“保护和改善自身环境”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提出了“实现与环境相和谐的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并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和形成普遍的环境道德等主张。(注:参见赵中建选编:《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第12-20页。)在此,基于中和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着重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作教育哲学思考。
首先,要教育现代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观。
传统中和教育观,注重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适度的协调关系。孔子要求作为理想人格的智者、仁者应对山水之类的自然之物采取悦纳的中和态度,看到“四时行而百物兴”,强调人的活动应“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要求“使民以时”,尊重自然生物季节演替的规律,并以此作为治国的自然法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注:《论语·述而》。)的提出,更能体现其反对无节制地猎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自然保护意识。
万事万物均有其不可违背的内在规律性。古人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注:《管子·形势》。)在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能力十分有限的先秦时代,先哲们注重教人崇信自然法则,“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注:《论语·宪问》。),既要求对自然给予能动性地适应,又看到了人在维持和协调自然生态平衡中的能动作用,这是极其可贵的。近人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一面应该顺应他,一面应该驾驭他。非顺应不能自存,非驾驭不能创造。”(注:《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10页。)诚然,古人注重教人顺应自然,不甚教人驾驭自然,改造自然,这有其时代的局限,但看到顺应自然的必要而又能自强不息,故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儒家和道家无不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不在于对抗、征服,而是顺应、适应、效法和利用。但由于过于重视“天行”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创造力的衰弱,驾驭自然的能力之不足。尽管如此,传统天人观仍给人以启迪:人类所需,固然必须取自自然万物,但这种索取无疑应是理性的、有节制的,应“善假于物”,而切不可“暴殄天物”。
自然是人与万物之源。人本身是由自然界分化出来的,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或如马克思所言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这正确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互动辩证观。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无疑应建立起某种和谐关系。若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危害,另一方生命则难免受到威胁。优胜劣败,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不宜将其泛化或绝对化,否则难免带来祸患。“人定胜天”的命题,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其重大意义。然而,“胜”的方式、程度也必须适度把握。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和未来社会,人类如果总想显示其无所不“胜”的力量,总以对立面的消灭或消亡作为自身力量的实现,那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的扭曲,而且必然自食苦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人类由于对自然的无限制的摄取和占有,由于毁灭性地开发自然,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枯竭,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多种灾难。一切由人类自身所已酿成与即将酿成的苦酒,都只能由人类自己来饮尽。所幸的是,世人已对此有所反省和明察。新加坡学者钟志邦尖锐地指出:“回顾西方先起步的现代化以及东方跟着来的现代化,全人类可说都犯了滥用、剥削以及污化自然的罪,结果导致今日全球性的生态与环境的危机。”(注:《儒学与廿一世纪》(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936页。)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含99位健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向人类的警告》开篇就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该声明最后警告:“在我们能够避开现在所面对的威胁及人类前景不可估量地消失的机会之前,我们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年或几十年。”这当不是危言耸听。时至致力于现代化的今天,若仍把发展经济视为一种向大自然无限制地单向索取的活动,将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仅仅看成是任意对待的生产对象,那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失调,进而影响现代化的顺利展开,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诚然,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关系的原始和谐,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对峙。合理的思路应该是,在打破旧的和谐的同时,又在总体上建构新的和谐。人既是自然的光环与荣耀,却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尚能持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宽容,当今人类更不应“竭泽而渔”或“杀鸡取卵”。“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对“自然”这一惠泽人类的家园,理当怀有感恩之情,爱护之意。
现代教育观念的变化,理应包含人与自然观的变化。必须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所致力于培养的现代人,应对自然持有某种新的态度,其基础则是与自然的协调而不是相互抵触或一味征服。这也意味着,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教育价值目标。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观,要求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而现代教育哲学,必须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新型关系,树立适应现代与未来社会发展的新型的人与自然观。
其次,重视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关系。人是认识的主体,人通过自身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机制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然而,由于过于强调人是自然界中的主宰,背离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任意掠夺与破坏,致使人与生态环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与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对立与冲突,必须着眼于文化教育,转变陈旧的思维方式,重视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在儒家看来,整个宇宙天地的生命系统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而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由于“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注:《荀子·王制》。),能“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传统中和哲学依循天地“生生”这一最高的自然和伦理法则,高扬人类的仁爱之心,兼爱自然万物,尊重和爱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无论是《易传》的“好生之德”、“厚德载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还是张载的“爱必兼爱”、“民胞物与”,或是程颢的“以生为道”、“物我兼照”、“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朱熹的“以生物为心”、“爱人利物”,都以保护天地万物为己任,履行维护生态的义务,体现敬畏生命的伦理。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施韦兹对中国“强调人通过简单的思想建立与世界的精神关系,并在生活中证实它合一的存在”表示由衷的赞许与敬佩,称这种思想“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他将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他因此而主张,人类应具备“敬畏生命的伦理,促进任何人关心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注:参见施韦兹:《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26-27页。)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界共生、共存、共荣。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但其承载力和蕴藏的资源是有限度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库;对人类废弃物的可容量和自我净化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也并非可以任意肆虐的垃圾箱。若超出其限度,必然带来生态的失衡和环境的污染。人虽为万物之灵,有能力驾驭自然,但人并非天然地具有剥夺其他生命的权利,只能认识自然规律,而不能粗暴地改变自然界运行法则,只能利用自然而不宜无限度地损害自然。因此,必须确立教育生态伦理观,即教人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确立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利,其基本原则是:教人懂得善就是尊重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妨碍生命和毁灭生命。这种教育生态伦理观,应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大到自然界和所有生命,把人类道德规范扩展到生态环境中去。其基本要求是:关心所有生命和自然界,重视自然界中的生命共同体,确认所有生命都有在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人类不应是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还应当用环境道德来善待一切形式的生命与环境资源,而不可只限于自身的利益来对待其他事物。必须用环境道德来约束和规范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行为。是否讲求生态伦理,有无环境道德,应成为当代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缺乏环境意识与环境道德的“环盲”,与文盲、科盲一样,都应成为教化的对象。经常性的有力度的生态环境教育工程,应成为落实全民教育的新的“希望工程”,成为现代教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应成为教育的系统工程,使所培养的新人在未来社会中,能理智而友善地对待生态环境。如今,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远未尽如人意;生态环境意识,显得极其薄弱。基于“中和”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观,教育现代新人自觉增强生态文明意识、环境忧患保护意识和总体协调的发展意识,乃当务之急。
再次,教育现代人在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以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为基础的新的科技观。
科学文化教育在维系人与自然系统的持续性发展方面,起关键作用。通过教育而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依托。科学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重要媒介,无疑有助于增强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人类与自然的许多矛盾冲突的化解往往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每当科学技术有所进步,都使人类作用于自然的能力有所加强。人类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从完全依附于自然恩赐,到初步顺应并局部干预自然,进而发展到对自然的全方位多纬度的影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没有任何过错。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人类不可束手无策,任其摆布。
然而,人类不应该由于掌握了科学技术而忘乎所以,对大自然随心所欲,索取无度。由于受到以“人统自然”为价值目标的唯科学论的影响,人类在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却又接连不断地以其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而且毁坏的程度日益严重,即人类在进行过多的榨取的同时,破坏了当代人未来生活以及未来人生活的自然基础。尽管因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初步满足了当代人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但伴随而来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人口、疾病、道德、战争等全球性问题,已引起人类的普遍关注和忧虑。海德格尔预言:“科学的进步将使对地球的剥夺和利用……达到今天还无法想象的状况。”(注:引自宋祖良著:《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8页。)可见,科学技术的应用本身,有其局限性,极容易因盲目利用而造成始料不及的恶果。历史和现实表明:学习和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若滥用其支配权,必然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将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显然,仅靠科学本身难以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误区,难以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危机,也不会必然给人类带来福祉;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真正实现人类的幸福,还必须学习和运用哲学包括科学哲学,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念,以把握自然与人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把握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所引起的变化与利弊得失,把人对自然的作用限制在适宜的范围内。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的掌握与利用,都必须借助于教育。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说到底是教育的危机。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简单地归因于科学技术,那是不公道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负效应,并非单纯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纯追求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所致,涉及复杂的社会因素。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基础工程是教育,其基本依托是发展融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应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必须建立在科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人,才能自觉遵循自然规律,以其智慧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才能真正看到人类存在发展的利益和崇高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进步对人类发展的强大驱动功能。
四、未来的启迪
人类已永远告别战争与和平交替、灾难与发展并存的二十世纪。回顾扑朔迷离的人类历史,人类不再像从前那样为盲目地以自身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自鸣得意,而是在为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苦苦求索,寻觅人类自救的良方。面对现实,放眼未来,不能不令人深感中和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价值。
中和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都是与对立、冲突相联系的;无冲突就无所谓中和,也无所谓“可”与“不可”。二十一世纪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都关系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发展利益。为了求索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冲突的化解之道,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反映中和哲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尽管不可能含有解决现代与未来所有问题的现成方案,但无疑可为解决上述冲突提供新的视角和足以影响人类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
基于“中和”学说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化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冲突,未来社会的文化教育应从宏观上把握某些基本准则,即“和利而和爱”、“和生而和处”、“和立而和达”,以利于化解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并为未来文化教育带来积极因素,同时也为未来文化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世纪,需要培养具有“和利而和爱”、“和生而和处”、“和立而和达”意识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应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身心的多种关系。而这首先应从懂得爱、学会关心开始,以增强智慧为基础,以谋求人类的幸福与长远利益为宗旨。
二十一世纪仍将是多元文化的世纪。基于中和精神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人类多元文化必将随着经济、交通、信息尤其是科技的高度发达而带来各种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道德观念的日益沟通与涵容。未来的岁月,尽管仍将是人类不尽协调、不尽和谐的时代,而又必将是致力于有序、协调、稳定而持续和谐发展的时代。中和这一突出体现中国智慧的文化哲学,一旦与可持续发展观相融合,就会远远超出古代的文化范畴,而且将具有更为深远、更为广泛的文化意蕴。运用中和哲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富于智慧的人类,必将不断化解各种矛盾冲突,不断追求新的协调,不断实现新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