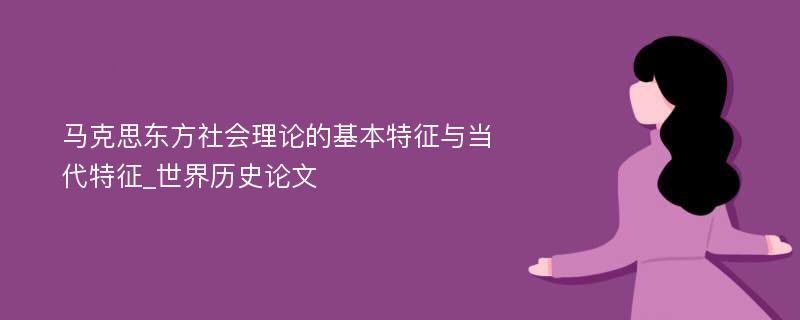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基本特征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3-0028-06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其最初的理论关注点是西方社会。19世纪50年代, 当马克思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后,便把研究视野转向东方社会,直至其晚 年的《民族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对东方史前社会的考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 究持续了30多年,在此过程中,他剖析了东方社会的“三位一体”结构,阐释了东方社 会的“停滞性”和“东方特有的形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揭露了西方殖民者对 东方社会实施的暴行,探讨了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道路,在改造资产阶级东 方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本文试图较详尽地梳理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性,以深化对马克思东方社 会理论的研究。
一、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这一思想。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背景下,马克思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历 史命运。他认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差距日益地扩大了 ,那些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利用先进于其他落后民族的强有力的工业体系实 施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掠夺和统治,东方社会也未能逃脱这一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 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比如,印度成为西方征服者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 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而中国则在西方资本 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稳定性”和“顽固性”,并没有成为西方的 完全的殖民地。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着重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背景下预测 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的话,那么,马克思晚年更加侧重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探索东方社 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设想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 展道路。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他发现俄国的农村公社 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在这一时代,俄国农 村公社如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经济成就,那么公 社就注定要灭亡。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充分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等 种种文明成果,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P438)直接作 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马克思还提出俄国革命反转影响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相互补充的思想。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P326)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东方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中来考 虑,以东方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作为 东方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条件,说明了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过程中的相互依存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马克思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坚决反对世界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看到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受 其侵蚀和影响的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方社会,都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经济 危机形势,这种形势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马克思并 没有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之外来理解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他批判了俄 国“民粹派”把俄国落后的村社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论,认为跨越资本主义本身恰恰 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东方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跨越落后停滞的状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二、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 线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原来在一个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运行的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跃出了民族的疆界,具有了世界性。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正是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来探讨东方 社会的历史命运以及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 民族或国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 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的狭隘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的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2]人类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 就越突出。在古代乃至近代早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般都是在单个民族的地域 内运动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世界历史形成 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对于某一国 家来说,“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 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 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P115-116)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产 力的发展,不仅受到本国生产关系的影响,还受世界上的其他落后或先进的生产关系的 制约。同样,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不仅受到本国现有生产力的作用,还受世界上先进生 产力的冲击。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整合出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此系统 中,既有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国家之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既有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落后的生产力与落 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既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有先进 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系统中,某些较落后国家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往往会加速走向激化状态,从而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他在 分析“印度公社”灭亡的原因时指出,“印度公社”灭亡与其说是不列颠的收税官兵和 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自由贸易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历史向世界 历史的转变”才产生了一种先进的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通过殖民侵略引入了东 方社会,使这种“外来”的新的生产力与东方社会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决定 了东方原有社会基础的崩溃。马克思从俄国与“现在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这个现实出 发,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及西欧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进而提出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同样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 一主线。在马克思看来,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在世界性的历史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西 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与本身“保存下来”的公有制成分(生产关系)相 结合也可以产生那种“类似的矛盾”,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落后的俄国农村 公社也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尽管马克思 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他无疑为我们正确理解历史上的某些落后国家“跨越” 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走向更高级的发展程度,为我们探索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 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事实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立足于“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历史环境观。所谓“历史环境”是指在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各种社会矛盾所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的总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历史环境既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又可以分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 内部环境和外在环境(国际环境)。我们通常笼统地把某个国家或民族特定的自然地理条 件、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该国家或民 族所处的国际关系等具体的历史条件作为构成历史环境的诸因素。
立足于一定的“历史环境”来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 论的一大特色。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关注历史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 样性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着 亚细亚的、古代的、斯拉夫人的、日耳曼的等多种形式。至于不同的社会选择什么形式 ,这“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 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 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 等等的变动”。[4](P484)这些不同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后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发展中发展成为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而使人类社会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
以“历史环境”为基点来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的一贯作法。19 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批判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无视“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持 守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普适性的僵化观念。到了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 社未来命运和前途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进一步领悟到这一分析方法的魅力。在马克思看 来,如果没有有利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就不可能转变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 支点”。换言之,撇开一定的“历史环境”,侈谈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能成为“俄国社会 复兴的因素”,那只能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指出:“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 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450-451)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俄国农村公 社所处的“历史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其中,国内环境又具体指 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条件和俄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凑合”,国际环境具体指俄 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以及与俄国革命相互补充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马 克思依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国内历史环境和国际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试 图探索俄国农村公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四、立足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东方社会
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要用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来评价东方社会以 及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社会的入侵。这两个观点亦即“从历史观点来看”和“从人的感情 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马克思始终是运用历史尺度和价值 尺度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东方社会的。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关注东方社会尤其是沦为西方殖民者的“猎获物”的印度的 历史命运时看到,西方殖民者破坏了印度古老的村社制度,印度国家宗法制的祥和无害 的社会组织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 传的谋生手段。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是会感到难过的”。他怀着极 大的义愤,痛斥殖民者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 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他认为殖民者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更为可怕 的“欧洲式的专制”,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 ,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
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纯粹的“道德义愤”和价值尺度来评价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社 会的侵略,他在提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这一价值尺度之后紧接着强调,“但是我们 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 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 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3](P765)在马克思看来, 虽然西方殖民者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 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在殖民化的过程中,殖民者又在东方 社会建立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这样就在客观上造就了有 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马克思着眼于历史尺度,对西方资产阶 级在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认为殖民者承担着 “双重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历史尺度意义上,马克思慨然而语:“无论一个古老世界 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 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3](P766)
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及其实现。马克思与抽象 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价值尺度看作是空洞的超越现实的抽象原则,前者则把 价值尺度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联系在一起,并以历史尺度为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价 值尺度与历史尺度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在其晚年继续立足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 证统一来探索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当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 峡谷”设想时,他的出发点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波折”、“痛苦”和“ 灾难”,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所遭到的致命危机”,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牺牲和代价。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既不是人道主义情怀支配下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 物,也不是把设想的深刻基础仅仅限定在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单纯关心上,而是建立在 对俄国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国内外条件的充分分析之上的,这一分析显然是基于历史尺 度的分析。
五、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回应
后殖民主义是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在西方乃至全球都较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 殖民主义站在东西方文化的“裂缝”处,采用文化分析范式解读殖民,旨在考察昔日帝 国殖民地文化与原宗主国文化间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探讨西方帝国与东方殖民地在 文化方面的“建构”与“解构”,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无论是赛 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西方传统东方学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 还是斯皮瓦克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解构,以及巴巴对“模拟”策略的强调,都旨在揭示现 存的东西方关系的不平等性、不合理性,关注东方社会的未来命运,展望东西方文化之 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是当代的东方社会理论 。
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之间无疑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尽管马克思的 东方社会理论与后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但马克思研究视野的东方 转移、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考察、对西方政治、经济殖民主义的批判以 及分析东方社会的某些方法或多或少地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主题的 确立以及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展开,深深影响了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关系中存在的西方对 东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揭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不讳言这一点。赛义德在其后殖民 主义的开山之作《东方学》中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78页,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东方学》一书的中文翻译者王宇根先生根据《东方学》的英译本将马克思的这句话译 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并把这句话置于该书的卷首扉页, 作为全书的主导思路。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地研究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 ,批判了西方对受殖民主义控制的那些地区和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意识形态迷雾的 制造。他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东方化东方”的产物,是西方对东方的“建构” 和“表述”,(注:英文“represent”既有“代表”、“代理”之意,也有“表现”、 “描述”、“表述”之意。赛义德在这里把马克思的“represent”(代表)换成了自己 的“represent”(表述)。)其目的是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服务。东方之所以“无法 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 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归根结底是“表述”和“权力”以 及两者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对文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了缜密的探讨。斯皮瓦克曾 公开宣称她“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她说自己是进入“马克思理论深处”的人。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不仅征引了被赛义德置于《东方学》卷首扉页的 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话,而且还通过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观点专门分析了马 克思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消解的和错置的阶级主体的结构原则”。不仅如此,斯皮瓦克 还从马克思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时代所起的作用那里受到启发,她在肯定帝 国主义殖民本性的同时,也承认帝国主义的积极作用,以至于在她的著作中多次将其以 典型的悖论方式称为“有益的暴力”(enabling violence)或“有益的侵犯”(enabling
violation),在对现代社会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合理秩序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斯皮瓦克 认为在当代不能否认“社会化资本”的开化作用。就连一向对马克思持敌视态度的巴巴 在近几年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2002年6月,巴巴在北京清华大学与中国学者生安锋 交谈时强调指出,“在20世纪或21世纪,一个人如果不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不能成为 一个思想家,这一点非常清楚”。[5]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进一步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疯狂的瓜分世界和掠 夺殖民地、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实施对东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时代。在这 样的时代,西方对东方的政治殖民和经济殖民显然是它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从政治经济 角度解读殖民、关注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运也就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后殖民主义所 处的时代是文化作用日益彰显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获 得独立,摆脱了以前的政治“依附”状态,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虽然经济上的“ 依附”状态依然存在,但传统的那种赤裸裸的靠枪炮利剑敲开国门进行抢劫和掠夺的政 治经济殖民主义行径的“合法性”已受到挑战。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加剧,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原来一直“默默无闻” 的文化因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政治家、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在国际关系、国际 交往、制度变迁、人类进步等领域所起的重要作用。身处文化作用日益彰显时代的后殖 民主义理论家关注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注重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是理论逻辑 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殖民主义把马克思从政治经济角度对东方社会的分析、对东 方历史命运的考察以及对“政治经济霸权”的揭示深入到从文化角度关注东方社会的历 史命运、建构新型的东西方关系,并结合当代的社会现状和主题精神,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文化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犀利分析和无情抨击,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霸 权”思想的范围和视域扩大了。虽然后殖民主义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毕竟把马克思 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关于“霸权”的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个层级,从而使马克思的 理论更“丰满”、更有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是马克思东方 社会理论当代性的重要表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霸权”思想的当代回应。
收稿日期:2004-02-08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