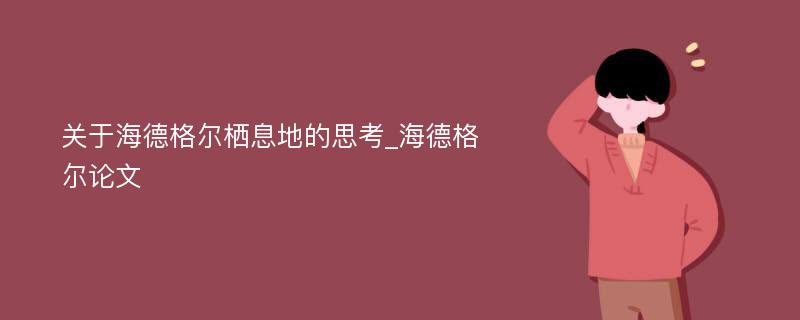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4-0038-07
至少从1946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开始,“人之栖居”便成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天空中颤抖不已的主旋律(注:其实,这个主旋律在《艺术作品的本源》、《荷尔德林 和诗的本质》、《当如节日的时候……》等30年代的文章中就已经不可遏止地袭向我们 ,只不过似乎尚在“专题”的起伏和跳跃中时隐时现。)。这个在“前期”尚含而不吐 的主旋律,穿透“诗人何为”、“从思的经验而来”、“技术的追问”、“语言”、“ 物”、“筑—居—思”、“……人诗意地栖居”、“什么召唤思”、“泰然任之”等等 “后期”专题论域的界限,直截了当地宣泄而出,持久地触动着我们,并在存在的深度 上开显着一个人之栖居的自由境域。
一、栖居的困境与栖居的本质
尽人皆知,这是一个技术四面环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已按技术的方式被对象性地分 割为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工业领域、农业领域、军事领域、教育领域、新 闻领域、娱乐领域等等,而每一领域又有更进一步的切割。于是,人之栖居便顺理成章 地被划归于某一个具体领域,比如消费领域或者娱乐领域。由于现代技术的日益推进, 人的活动范围从“宏观”伸张到“微观”乃至“宇观”和“渺观”,生存样态似乎愈来 愈丰富多彩,生存空间也似乎愈来愈广阔。技术主宰着一切:普天之下,莫非技术之疆 域,率土之滨,莫非技术之臣民。然而,与现代技术的这种摧枯拉朽般的扩张态势相呼 应的是,作为能在之人的生存在质的深度上急剧而又全面地萎缩。专业化、资本化、规 范化、功利化和一体化使人之生存益发为技术世界所占用,益发归属于技术世界格局中 的一个有机部分。技术性的“摆置”充斥着世界:“耕作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 空气为着氮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 目的而被释放出来。”[1](933页)到处都是海德格尔称之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座架” 的索逼着的订造(注:关于“座架”以及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需另文思之。),自 然界被挟持着拖入开发、改变、储藏、分配、再开发、再分配的仿佛永不回头无限发展 的订造过程。完全可以说,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已从广度和深度上被现代技术一网打尽 。
与此同时,作为索逼着之订造的座架绝不会止步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事实上, 它已经向“主体”世界全面渗透。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以降的时代通常被看成是一个 高扬主体的时代,而且正是这种高扬才使得主体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现代技术世界。 可是,“高扬主体”的辩证法就在于:在主体不断创造、发明、运用、改造和完善技术 世界从而俨然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之前,主体之为主体的“主体性”就已经拂袖 而去了,而被剥去了主体性的主体实际上已然沦为技术世界维系自身以及再生产自身的 “螺丝钉”或“润滑剂”。海德格尔极深刻地指出:“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 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人根本上并不能事后才接受一种与座架的关系。”[1](942 页)在技术座架的先行控制下,作为主体的人是作为“人才”被摆置、被订造的:人被 摆置为“人力资源”,被订造为“人才库”或有灵魂的“生产力”,并以“就业”和“ 失业”的方式在“人才交流市场”的吞吐中内在地归属于技术世界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人一生的基本生活方式均是按各技术领域的发展态势和需求而被规定、筹划、调整和 算计的;即使像诞生和死亡这样的“自然事件”,也以诸如“出生率”和“死亡率”之 类的方式而被吸收于技术世界深不可测的自我再生的黑洞中去。
技术座架在提尽了客体的“自在性”和绞干了主体的“主体性”之后,人之栖居的沉 沦状态或者说技术性栖居的本质便裸呈出来了。栖居是什么?按技术性栖居的算计本质 ,栖居不外乎就是对一个空间位置的占用问题,是一套可诉诸“人均占有面积”来精确 衡量的住房问题,最多是一个诸如“住房的周边软硬环境”之类的问题。
的确,居住面积的窘迫和居住环境的恶化,一直是一个让现代社会深感棘手的难题。 但是就人之栖居来说,即令解决了居住面积和居住环境这样的专题性难题,也远不等于 便消除了栖居的困境,甚至根本上就还未触及到人之栖居的真正困境。海德格尔写道: “不管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栖居的真正困境都并不在于住房匮乏。 真正的栖居困境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工人状况更古 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 习栖居。”[1](1204页)对深陷于技术性栖居方式之中的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 判决。在这个判决中,至少有两点引人沉思。
第一,何以栖居的困境比世界战争、毁灭事件、人口快速增长、现实工人状况等等更 古老?按照海德格尔这话的逻辑,“更古老”意味着,即使居住的面积和环境已完全不 成其为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彻底摆脱了“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人口压力”、“教育普及”这些问题的困扰,不再面对战争、毁灭、贫富悬殊、宗教冲 突这类问题的威逼,一言以蔽之,即使我们已然可以“随心所欲”或“各取所需”了, 我们,作为曾在、现在和将在着的必死者的人类,仍然深深地置身于栖居的困境之中。
在此困境的烛照下,近现代以及“后现代”技术性栖居的本质便一览无遗:它使人之 栖居在本质上沦落为一个像居住的面积或环境这样的专题性问题,即沦落为从某种现成 的生存状态跳向另一种“理想的”但同样是现成的生存状态的问题,从而使栖居困境的 “古老性”转化为一个似乎只是“临时性”的问题,就是说,它遮蔽了人之栖居困境的 古老性或源发性。因此,当代技术性栖居的真正困境,与其说是诸如环境的恶化,生态 的危机,核战争的悬临,文明的冲突等等这样的问题,不如说在于它始终只“表现”为 这样的专题性问题,即始终以派生的、不真正切己的专题性困境顽固而又至深地荫蔽着 人之栖居的那种古老的、源始的、真正切己的困境。
第二,何以“重新寻求栖居的本质”、“学会栖居”乃人之栖居的“真正困境”?这里 显得异乎寻常的是:栖居之本质尚需要去“重新寻求”吗?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栖 居”这个词的本源意义是“持留、逗留”[1](1190页),“栖居始终已经是一种在物那 里的逗留”[1](1194页)。但如此一来就更奇怪了: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逗留”着,又 何须乎去“学会”呢?难道“栖居的本质”不是早已明摆在那里,又何须乎去“重新寻 求”呢?更重要的是,所谓栖居的“困境”从何而来?而且还是“真正的”?
不言而喻,栖居作为一个日常的“概念”,刻画着一种“普遍的”逗留现象,就是说 ,栖居作为无论怎样都已经逗留着的“逗留”,的确是不用去“学会”的,不用去“重 新寻求”其本质的。但是对人的栖居之本质的遮蔽恰恰就发生在这里。栖居作为逗留, 说的根本就不是一种“普遍的”逗留现象,而毋宁说是人作为人的“存在”本身。海德 格尔将逗留经验为“置身在平静中,被带入平静中,持守在平静中。平静(Friede)一词 意为自由,即Frye,而fry一词又意味着:不受伤害和防止危险,防止……也就是保护 ;使……自由实质上就是使……受保护。保护本身不仅在于,我们不伤害所保护的东西 ,真正的保护是某种积极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事先任某物存在于其本质的时候,发生 在我们特别地让某物返归其本质存在的时候,就‘自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发生 在我们让某物自由地进入一种平静的持存中的时候。”[2](149页)海德格尔将逗留思为 “平静”,说的显然不是与“张皇”或“不安”等相对称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说 的人之为人源始的开放状态,人作为人切己的“自由”生存状态。作为人之生存状态的 自由,既不是那种派生的“主观的”“随心所欲”,因为不仅这时的“心”是现成的主 体之心,而且此心指向的对象即“所欲”直接构成了此心的内在界限,因而从根本上堵 死了“随心”的自由的通道;也不是那种同样是派生的“客观的”“掌握客体”,因为 当我们将诸如本质、规律、实体等等玩弄于鼓掌间,以为由此便主宰、征服和支配了物 之际,物之为物即物之“存在”已因被刚性化而弃我们而去了。
所以,真正的自由乃是积极的保护,即让……自由:让物自由,从而也让栖居者或逗 留者自由。栖居者只有让出物之自由的空间,才能为栖居者自己也让出栖居之自由的空 间。但是,犹如“存在”总是呈现为“存在者”一样,自由总是展显为主体的“随心所 欲”的自由或者“掌握客体”的自由,因而栖居作为逗留也总是沉沦为某种专题化、现 成化的在主体或客体那里的日常逗留。这意味着,人之栖居始终置身于从其本己的自由 逗留不断跌落成现成的日常逗留之中。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真正的栖居困境”。事 实上,只要人作为始终非现成的人而生存,人就陷身在栖居的这种困境之中;历史的人 在构建起某种栖居方式之际(如技术性栖居的方式),这种“构建”也同时就冷却、填满 了栖居之本质,从而遮蔽了栖居之本质,即从人之栖居的那种不断涌出的自由境域跌落 了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困境,因为此困境乃存在本身的困境,乃作为存在的栖居本身 的困境。
海德格尔写道:“栖居,即置身在平静中,意味着在自由和保护中持守在平静里,这 种自由让一切守身在其本性之中。栖居的根本特征就是这种让……自由和保护……。它 贯透整个栖居领域。一旦我们考虑到,人存在于栖居中,确切点说,人是作为终有一死 者逗留在大地上,那么整个栖居领域便向我们开显出来。”[2](149页)若要按海德格尔 这段话给人之栖居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栖居,真正的栖居,乃置身于平静中、持守在 保护中的终有一死者在这个大地上自由的逗留。这绝非通常所谓的“诗意”描述,毋宁 说,这是由存在本身而来的对人之栖居的切己“经验”,由将人之栖居“思为人之存在 的基本特征”[2](148页),并力图让这种栖居之思真正成为存在本身自由境域的质朴应 答和源始归属。
但是,由存在本身而开显栖居,入思栖居,这意味着终有一死者始终不得不去“重新 寻求栖居的本质”,不得不永远去“学会栖居”。为什么呢?栖居作为存在在放出自身 时已经撤回了自身,在敞显自身时已经荫蔽了自身。这种放出同时又收回、敞开同时又 遮蔽实际上就是栖居的“栖居—存在”的源始“现象”,栖居真正切己的“本质”,亦 即栖居—存在本身的“自由”。人之栖居就奠基在此源始的放出又收回、敞开又遮蔽的 自由存在之中。这意味着,栖居之为栖居始终只能兑现在栖居者对栖居之自由的重新找 回、重新学习和重新见证的道上,而始终不会穷尽、硬化在任何一种历史的栖居方式上 。所以,栖居的本质就是栖居本身的“真正困境”,而此困境作为存在本身的困境,用 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那种深度切己的“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日常被掩蔽着”[3](318页)。“一旦人思到了他的无家可归,它就不再是 一种痛苦了。只要正确思之并且牢牢持守之,这种无家可归便是那把终有一死者唤入其 栖居之中唯一的召唤。”[2](161页)作为自由的存在,人之栖居注定是无家可归的,这 并非什么“悲观主义”。倘若人之栖居塌缩为某种仿佛提尽了生存之可能性的固定质态 ,那才真正是“可悲的”,因为无论有多大发展张力的生存质态都已经遮蔽了栖居本身 的困境,褫夺了栖居本身的存在性自由,从而把人之栖居推入了真正的危险之中。
如果说,栖居的本质就是栖居的困境,就是说,栖居之为栖居始终发生为、绽出为“ 重新寻求栖居的本质”或“重新学会栖居”这种由存在本身而来的困境的话,那么对栖 居着的人来说,真正的事情就不是如何去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困境,而是如何本然 地去进入这个困境,也就是纯然地去倾听那把自己唤入栖居的“唯一的”呼唤,并进而 平静地将自己遣送入那无家可归深不可测的自由生存境域。
无家可归……,这声音飘忽却又顽强地应和着中国两千多年前那个伟大的声音:道, 可道矣,非恒道矣;名,可名矣,非恒名矣。人之为人就始终兑现在“道”与“可道” 、“名”与“可名”之间,栖居在“家”与“无家”之间;或者干脆说,人之生存就是 这个“之间”,就是对这个作为人之天命的“之间”的应答和归属。“终有一死者除了 努力尽自身力量由自己把栖居带入其本质的丰富性之中,此外又能如何响应这种呼唤呢 ?”[1](1204页)无家可归……此乃栖居之为栖居的真正本质,因为说到底,这就是那沉 默而又永无止息的深沉呼唤,即人作为人而生存的自由本身的呼唤。
二、筑造与人之栖居
栖居乃人的存在本身。但人究竟是怎样栖居的呢?筑造,人筑造着栖居在这个大地上。
筑造与栖居。一眼看去就能直感到这两个词之间的某种内在勾连。筑造指涉着人类活 动的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各式各样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私人居所和公共建筑,四通 八达的公路、铁道和桥梁,星罗棋布的工厂、学校和商场,还有那雄伟的电站、庄严的 庙堂以及那数不清的汽车、飞机、卫星、坚船利炮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筑造 的产物,从而都是为人之栖居服务的。筑造是手段,栖居是目的,两者间的这种关系完 全是不证自明的。
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只要我们仅仅持这种看法,我们就把栖居和筑造看作两种分离 的活动,从中表象出某种正确的东西。但同时,我们通过目的—手段的模式把本质性的 关联伪装起来了。”[1](1189页)手段—目的的认识论图式虽然正确,但却既以“手段 ”的概念放逐了筑造之本质,又以“目的”的概念软禁了栖居之本质,因而也就阻塞了 我们通往并且归属于本真的筑造和栖居的“思路”。他认为,“筑造不只是为了栖居的 手段和途径,筑造本身就已经是栖居”[2](146页)。
通常所说的“筑造”,按海德格尔的分类,可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关照、守 护”意义上的筑造,如农夫耕种土地,看护农作物之类的筑造。“这样的筑造仅仅是关 照,它守护着那种源于自身的成熟结果的成长”[2](147页)。另一种基本方式是“建造 或制造”意义上的筑造,如上文提到的建造公路、桥梁,制造飞机、汽车等等。这样的 筑造不同于看护和照料,“这样的筑造乃是一种建构”[2](147页)。在海德格尔看来, 这两种类型的筑造都不是源始的筑造。“筑造的这两种方式,即作为守护的筑造(拉丁 字是colere,cultura)和作为建构起建筑物的筑造(拉丁字是aedificare),均被包含在 真正的筑造亦即栖居之中”[2](147页)。根据海德格尔的考证,动词“筑造”最源始的 意义本来就是“栖居”。“buan这个古词不仅告诉我们筑造说到底就是栖居,而且同时 也暗示我们必须如何来思考由此词所指示的栖居……筑造源始地意味着栖居”[1](1190 页)。但是,由于筑造的源始意义即栖居总是显现为我们日常的栖居经验,故而这种作 为栖居的筑造便退隐到栖居的多种形式的背后,隐身到“关照、守护”和“建造、制造 ”等筑造形式的背后去了。“这些活动随后取得了筑造这个名称,并借此独占了筑造的 事情。筑造的真正意义,即栖居,陷于被遗忘状态中了”[1](1191页)。
不管海德格尔的考证在学术上是否无懈可击,将筑造思为栖居本身确实开显了筑造和 栖居的源始意义域。筑造与栖居的专题化,使得筑造冷却为纯粹的“手段”,栖居冷却 为抽象的“目的”。实际上,作为手段的筑造和作为目的的栖居,不过是人的源始筑造 或栖居的蜕变形式,是从真正的筑造即人之自由的栖居中跌落出来的沉沦样态。所谓蜕 变、沉沦,说的并不是筑造—栖居的手段—目的图式“错了”,或属于某种“低级”的 形式,而是说这种图式不是真正源发的,因为它从“筑造即是栖居”这个“事情本身” 中脱落了出去,沉沦或消散到手段—目的的现成“世界”中去了,从而既遮蔽了筑造之 本质,也遗忘了栖居之本质,并且始终为此种遮蔽和遗忘所攫获。
海德格尔说道:“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筑造,我们才栖居,而是因为我们栖居,就是 说,因为我们是栖居者,我们才筑造并且已经筑造。”[2](148页)要切己地通达筑造— 栖居的现象本身,就必须突破手段—目的图式的压制。海德格尔这段充满学究气的话就 是要力图解除这种图式的遮蔽,从而将筑造着的栖居或栖居着的筑造突显出来。海德格 尔这段话无非是想道出“事情本身”:筑造就是栖居,筑造本身“直接就是”、“已经 就是”栖居,而且是真正源始切己的栖居。若用海德格尔的更准确也更切己的说法,作 为栖居的筑造,“乃是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的生存方式”[2](148页)。
“在大地上生存”,这话向我们非专题性地道说,朝我们充满“思意”宁静地吐露自 身:“但‘在大地上’已经意味着‘在天空下’。这两者也意味着‘在诸神面前的逗留 ’,而且含蓄着‘归属于人之相互共在’。渊于一种源始的同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 凡人这四相共属一体”[2](149页)。天、地、人、神四相的聚集,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思 途中,被海德格尔来回吟咏,沿途弹唱,当真是“舒之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 淮南子·原道训》)。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天、地、人、神的聚集到底是一种“文学性 ”的抒情呢,抑或是一种势域沛然的“存在”或“思”本身的强烈召唤呢?毫无疑问是 后者,尽管我们完全可以只滞留在前一个浅表的层面上。
“在大地上”就意味着“在天空下”。海德格尔思及的“大地”与“天空”显然与我 们日常关于大地和天空的表象以及科学上有关的概念无关。“大地是说:由此涌现也由 此收回,并隐匿自行涌现的一切。在此自行涌现中,大地作为隐蔽之道而到场”[2](42 页)。这就是说,大地不是通过我们感性和理性的“经验”过滤后成形出来的那个焦点 式或对象性的“存在者”,大地是活生生涌出着又缩回着的大地—现象本身;这种现象 不是被“反映”或“规定”定格出来的,而是不断聚集着“存在”出来的,不断境域弥 漫地“发生”出来的。因此,大地作为命名,绝非一个关于某个对应的刚性对象域或“ 所指”的“能指”,命名着的“大地”始终是柔性的,召唤性的。不断绽出着又幽闭着 的大地召唤着“思”。思大地不是去凝视一个冷却了的现成对象,而是去倾听从而跟随 大地本身的不断放出着又收回着在—此的召唤。在这样的倾听和跟随中,思通达着大地 本身筑造着的承纳和庇护:大地承纳着万物的绽放和归隐,滋养着那些开花结果者,庇 护着水流、岩石、动物和植物等等。
然而,无论是开花结果者,还是水流、岩石、动植物者,在大地上万事万物的升起和 降落中,已经栖居着天空,已经是天空的创生化育:开花结果者、动植物者,沐浴着天 空的阳光雨露,分享着四季的轮回和昼夜的光明和黑暗;水流、岩石者、宏观微观者, 领受着天空太阳的运行,月亮的途程和群星的闪烁。“大地之为大地,仅仅是作为天空 的大地,而天空之为天空,只是由于天空高屋建瓴地对大地产生作用”[4](197页)。所 以,“在大地上”这话总是已经道出了“在天空之下”,尽管我们习惯的表象或概念方 式通常总是听不见这一宁静的言说。
在大地与天空之间。谁存在在此“之间”?当然是人,更准确点说,是终有一死者的人 。“人被称为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他们能去死。去死意味着能够作为死而死”[2](150 页)。在《物》一文中,海德格尔说得更透彻:“只有人去死。动物只是消亡。动物的 前面和后面都没有死。……我们现在将终有一死者称为终有一死者,并不是他们尘世的 生命会有一个终点,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作为死而死。”[2](179页)如果说,“在大地 之上”已经道出了“在天空之下”,那么,在“天地之间”便已然让人作为终有一死者 到达。人生存于天地之间,这种生存乃“终有一死”的生存,而此终有一死之生存实质 上就是这个“之间”。所谓“去死”,所谓“能作为死而死”说的就是这个“之间”。 人不是一个与现成的天空和大地并排而立的第三个存在者,人是此—在;此在不是任何 现成的“什么”,而是始终以已经去死、能死、终有一死的方式生存着。以有死的方式 生存,就是以有限的方式响应存在本身的召唤,以有限的方式让存在现身到场;而当存 在以这种方式开启之际,大地与天空于是便入住于终有一死者的近旁。这意味着,不仅 那开花结果者,那岩石、水流、动植物者,而且那运行的日月,闪烁的群星,飘忽的云 彩和深邃的天穹等等,都聚集着现身到场,拉出终有一死者栖居的“天地之间”,即显 现为围浸和撑托着有死者之栖居的“天空和大地之间”。
正如“在大地上”已经道出了“在天空下”一样,“终有一死者生存于天地之间”这 话也已经意味着“在诸神面前的逗留”。人非但脚踏着大地,并且也仰望着天空。这种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生存方式,实乃人作为会死者最源始的生存方式。大地 和天空或故乡和明月,这就是终有一死者的“生存世界”。此世界不是现成的万物之总 和,而是在世之界限,即终有一死者有死、有限的生存现象本身。但是,当人被作为人 而命名,即人被命名为生存于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终有一死者”之际,实际上就已经命 名了“诸神”,已经意味着人之生存乃是“在诸神面前的逗留”。不言而喻,海德格尔 所思及的“诸神”,绝非那种作为表象和概念之对象或某种宗教信仰之对象的存在者。 “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在此栖居中他们期待着作为诸神的诸神……他们并不为自己制造 神祗,并不崇拜偶像。在不幸的深渊中,他们还期待着那已被收走了的福运”[2](150 页)。在海德格尔看来,诸神只是“神性之召唤的使者”[2](150页),在对诸神隐而不 显的支配中,神性遣出诸神而显现到场,而此遣出—显现同时也自行收回—隐入。因此 ,所谓“在诸神面前的逗留”,说的绝非在自造的神祗或偶像面前的逗留。“诸神”闪 现出人的信仰之维,这种信仰之维尚不是任何专题性的宗教对象,而是人作为终有一死 者的“终有一死”的源始生存现象本身。作为源始的生存现象,“诸神”一方面命名着 人的向死而在的栖居,一方面作为神性隐而不显的使者,守护着包括终有一死者在内的 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隐秘。
这就是在海德格尔后期思途中被一路吟咏的天、地、人、神的“四相聚集”,或者叫 “四相一体”。假如“天”、“地”、“人”、“神”是四个音阶,那么当由它们构成 的“乐音”或“旋律”在艺术之思的“农鞋”中,栖居之思的“桥”中,物之思的“壶 ”中,语言之思的“排钟”之中不断弹唱、反复响起的时候,听起来难免让人生出“老 调重弹”的印象。再“普遍”的概念,也经不起“重复”的敲打:一旦它们作为框架性 的“基调”被反复回溯,四处套用,就势必丧失其普遍之为普遍而蜕化成某种机械演历 的僵死套路。作为概念,天、地、人、神也不可能例外。可问题在于,海德格尔思路中 的天、地、人、神压根儿便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概念”。它们是“命名”,仅此而已。 作为命名,它们只是力图不作切割地、不打折扣地响应、发送和归属于“事情本身”, 亦即存在本身。因此,海德格尔的四相一体绝不是指四个现成的在者或方面的“对立统 一体”,不是先有四个现成的东西,继而将它们硬拉到一起,让它们外在地聚为一体; 毋宁说,在四相一体中,根本就没有概念性意义上的“指”与“被指”,四相中任何一 相的“存在”,均已经就“是”其他三相的聚集到场;也就是说,只有在四相一体的“ 一体”中才有“四相”,一体使四相成其为四相,而不是相反。这个作为聚集本身即存 在本身的“一体”,“它既不是大地,也不是天空,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大 地和天空、神和人的更为柔和的关系”[4](200页)。并非“四相”(概念性切割)然后“ 一体”(概念性推导),而是首先已经源始地给予着的、柔和涌现着的“一体”,然后才 流溢为切割或区分性的“四相”。质而言之,四相一体之为四相一体,并不是一个用来 反复套用的公式,作为命名着的命名,“四相一体”不过是一质朴的邀请和守护:它邀 请那不断绽出着又归隐着自身的“存在本身”质朴地到来,并在质朴的呼应、发送和归 属中守护之。
海德格尔说:“终有一死者通过栖居而在此四相一体中‘存在’。但栖居的基本特征 是让……自由,是保护……。终有一死者栖居在这种方式中:他们将四相一体保护在其 本质之存在中,保护在其在场之中。所以,作为栖居的保护也是四相一体的。”[2](15 0页)栖居之为栖居发生在四相一体中,故而真正的栖居就是让四相守身在其“自在”之 中,即保护在其自由的存在之中。海德格尔将这种保护四相一体的自由栖居具体地思为 “拯救大地”、“接纳天空”、“期待诸神”和“发送终有一死者”。需要指出的是, 海德格尔这里说的不是诸如增加植被、降低污染、爱护动物、减少贫穷这类策略性的“ 环境保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栖居的真正困境向来就不是发生在“策略”的层面 上。那种主宰大地,征服天空,利用诸神和控制终有一死者的技术性栖居方式,只不过 是人之栖居困境的极端方式而已。将栖居的困境降格为总是可以“应付”的策略性困境 ,这才真正使人之栖居坠入了“困境”,因为这种方式不但从根本上使物不自由,使栖 居者不自由,更为重要的是遗忘了栖居的真正困境,而且连这种遗忘本身也遗忘了,从 而彻底地从栖居的“存在”中跌落了出来。“在拯救大地、接纳天空、期待诸神和发送 终有一死者之中,栖居发生为四相一体的四相保护。让……自由和保护……意味着:照 料和看护在场着的四相一体”[2](151页)。这就是说,所谓拯救大地和接纳天空,所谓 期待诸神和发送必死者,就是让天、地、人、神自由地进出自身,亦即始终照料和看护 着四相一体的“存在”;而守护四相一体的在场或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拯救和接纳栖 居的本质,以及期待和发送栖居之自由或自由之栖居。
倘若栖居之为栖居就是守护四相一体的存在,那么,终有一死者是如何在栖居中实现 这种守护的呢?如果四相一体是在恍兮惚兮的“存在”中才成其为四相一体的,那么必 死者又是怎样去守护这种存在的“深渊”的呢?依照海德格尔,对四相一体之自由的守 护,实现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即“物”中,而且“在物那里的逗留是在四相一体 中的四相逗留一向一体地实现自身的唯一方式。栖居通过将四相一体的在场带入物之中 而保藏着四相一体”[2](151页)。人之栖居不单单是在天、地、人、神处的逗留,栖居 作为逗留,始终已经逗留在物那里。然而在物那里的逗留不是在四相逗留之外的第五种 逗留。在人之栖居中来照面的首先且始终是“物”,即使这种照面之物仅仅以“客体” 、“对象”、“本质”、“规律”等等的形式来现身。这意味着,四相一体“存在”于 物中,或者说在物之“物化”中,四相一体才聚集为四相一体,而作为看护的人之栖居 ,也只是因为向来已经逗留在物那里才实现着对四相一体的守护。所以,在物那里的逗 留乃是守护四相一体之存在的“唯一方式”。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当物作为物本身被允许在自身的在场中存在,物本 身才庇护四相一体”[2](151页)。那么,究竟怎样通过物本身而守护四相一体呢?筑造 ,作为栖居的筑造,正是在筑造中(包括作为关照、守护和作为制造、建造这两者派生 的筑造方式),人逗留在物那里,栖居在物那里,从而将四相一体保藏在物之中。“就 其将四相一体保留或保护在物之中而言,栖居就是作为这种看护的筑造”[2](151页)。 所谓保藏四相一体,说穿了就是海德格尔终生殚精竭虑的“守护存在本身”。守护存在 本身,说的不是守护一种叫“存在本身”的东西,对后期海德格尔来说,“存在本身” 实质上被命名为边缘的、境域弥漫的天、地、神、人的四相聚集,而这种匿名的、非专 题的四相之柔和聚集就是“物”,即那种不断自行涌现又自行收回着的柔性之物。因此 ,如果筑造意味着在物本身那里的逗留,而这又意味着在天、地、神、人的四相聚集中 逗留的话;如果栖居也意味着逗留在物本身那里,从而也意味着保藏着四相一体的话; 那么,筑造作为在四相聚集的物中的逗留,就是栖居;栖居作为在物中对四相一体的保 藏,就是筑造。在栖居着的筑造中,让物自身自由地涌出和收回;在筑造着的栖居中, 让四相一体安居在物中,这便是海德格尔栖居之思在存在的深度上向我们发出的质朴劝 告。
收稿日期:2004-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