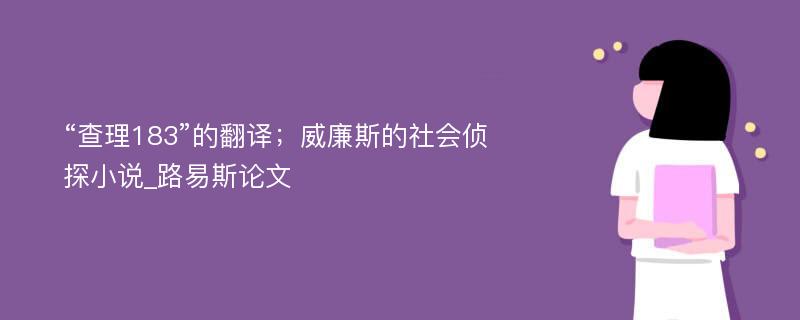
译查理#183;威廉斯的社会侦探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侦探小说论文,查理论文,威廉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求主宰世界和征服死神的超人王,双手托起非洲大陆,向旧殖民政权宣战,来惩儆在拉姆寺宫自由教堂中施用魔法驱走非洲国王的坎特布里大主教(《迷乱的幽灵》);帕维劳热姆副主教发现了出版社办公桌下面的被害者尸体,脑袋因此遭了闷棍,继之,耶稣最后用过的圣杯失盗(《天主堂大战》);一施展妖术者,企图盗取所罗门王冠上的一颗奇宝石,而被司法大帝所阻止,司法大帝的属下慧眼识破阴谋,原来,俏丽非凡的美女乃为妖女所扮(《天地万象》);两位青年人在去往哈德福夏的路途上遇到一只硕大的母狮子,他们惊奇地发现这原来是柏拉图的一种原型;一位书写恶意中伤匿名信的作者竟然变成了一条蛇(《狮子的圣地》);有人用新式的坦罗特算命牌搅起一场雪暴企图藉此杀死他未来的岳父,当暴雪骤起,肆虐失控之际,是无私的爱显示了神力,拯救了此般险境(《牌胜一筹》)。
将查理·威廉斯的小说进行分类实属不易。上述所引,基本上公正地反映其色彩绚丽的小说世界,当然,挂一漏万,偏失难免。我们不能仅凭最初印象简单地将其归为极端通俗闹剧。一旦展卷细读,就会发现,作品中表现的诗一般的描绘和内涵使得尽管离奇的情节变得十分富有感染力,令人不忍释卷,难以忘境。威廉斯的作品明显不同于现代的幻想小说。基本认可的观点是,威廉斯的作品重要性在于表现了文学的某一种真谛。
对部分读者来说,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作品情节离奇,悬念迭起,耸人耳目;另一方面,又重在表现耶酥精神、基督价值和世界观,典型的表现为固守传统教条。作者笔墨酣畅,神秘莫测,但是,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其作品并没有突破传统宗教信仰的氛围。不过,话说回来,果真是如此吗?即使考虑到“超自然惊险(恐怖)小说”──费伯尔这般习称──的特点,难道威廉斯在作品中没有过分潜心拘泥于神秘性吗?这与其明显的宗教信仰又当如何和谐一致呢?
上述问题的答案与下面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如果当初不是与西·斯·路易斯结下一段金兰之好,从而带来一份好运的话,威廉斯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不被历史湮没和遗忘呢?”当初,正值其文风过于陈腐并拘泥于宗教信条且又怪诞不经而失去读者市场、濒临歇笔之际,也因传统精神和宗教色彩过于浓厚而无法吻合时代观念之际,时年四十九岁的威廉斯结识了路易斯,二人缘份不浅,志趣相投,成了忘年之交,威廉斯的文学生涯从此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费伯尔曾一度评赏和推荐道,威廉斯的小说“具有一个稳定的小范围的但非常狂热的读者群,崇拜者们总是希望能多得到几部威廉斯的作品以馈赠亲朋好友”。
事实上,西·斯·路易斯所经历的情形正好如此。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册威廉斯的小说《狮子的圣地》后,在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刚刚读完一部很棒的著作,我认为它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好书”。“基于柏拉图理论,在另一种境界中,作品显示了地球体系的万物原型。尽管布局有点儿欠妥,但这无关紧要。浩浩一派景象,大有吞纳整个世界使其返祖归宗之势……。它不仅仅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幻想小说,作品具有深邃的宗教意境和博大的知识面……。去买一本吧,如果看第一遍时理解不透也不打紧,它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如今要想得到一部如此幻想作品真是太不容易了。”
无巧不成书,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供职的威廉斯此刻正在校对路易斯的大部头处女作《爱情寓言》。他们之间本不相识。路易斯向威廉斯写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威廉斯答复:“您如果推迟二十四小时给我写信,我俩写的信肯定会在路上撞到一起,在我崇拜一位作家的同时,他也在崇拜我,这样的事以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下来自然是两位作家的会面、往来和建立友情,后来,威廉斯和牛津大学出版社驻伦敦人员一并撤退到了牛津。在这里,威廉斯成了一个称之为“墨友”文学团体的成员,他们每周三以酒会友,每周四晚聚到路易斯的家中朗读和讨论他的新作。并非大家都像路易斯那般崇敬威廉斯,但是,威廉斯在这种环境中其创造生涯一下子变得活跃旺盛和辉煌了。尽管威廉斯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获得大学文凭,但路易斯以师资匮乏为由,借机将威廉斯纳入牛津大学讲师之列。一九四五年曾有消息说,如果威廉斯愿意离开出版社,牛津大学就聘他做大学研究员。
但是,好事难能善终。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五十八岁的威廉斯因消化系统疾病需要手术治疗而住院,据称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五月十五日十二时五十分,西·斯·路易斯的哥哥瓦利·路易斯从电话里得到消息:“查理·威廉斯先生于今日上午逝世了”。瓦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经常有人描述,噩耗如雷轰顶,慑人心魄,愦人耳目。事实上,今天的情形何止如此,我感觉到自己好像一步登空脑袋朝下倒栽在马路沿子上……。与威廉斯融融相乐、举盏咏诵的光景一去不复返,大幕落下了,灯光熄灭了,‘墨友’不再是从前的‘墨友’了”。
显然,不论其作品功绩何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与路易斯及“墨友”的关系,威廉斯才取得了如此这般的殊荣。任何喜欢路易斯作品的读者,自然会对给路易斯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感兴趣,这样,在威廉斯周围亦形成了一个稳定、热心、殷切的读者群,这般好事在以前可是未曾有过。不过,对威廉斯帮助最大的恐怕还要数下面讲的这种情形。
在和路易斯结识之前,威廉斯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事实上,他的经历也正说明了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英格兰,一个缺少金钱、没有靠山、书生气十足而又腼腼腆腆的年轻人要想在社会上闯荡出一番业绩是多么地艰难!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环境里,如此这般命运的人物,很容易遁入忙乱于常规杂务的芸芸众生圈子之中去。一旦混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有那些出类拔萃者或莽撞勇敢者才会不甘寂寞、不甘落魄、揭竿奋争。请看一下,《哈瓦德的结局》(福尔斯特著)中的赖纳德·巴斯特,像威廉斯一样身处上流社会的边缘,可没有威廉斯那样的好运气,他只因为出身贫贱而一生无成。
尽管威廉斯文才不浅并得到双份的奖学金,但他在不满十八岁就辍学了。纵观上述社会现实,对这种选择是不难理解的。父母亲对他的文学志向并不反对,但是,家里经营的店子赚不了多少钱,威廉斯自然不能上学堂了。他酷爱阅读,并经常写诗。不善于干力气活的他有一天惊喜地发现姨母登广告招收书店助理员,他便兴冲冲地去了那里。威廉斯家族属于英国圣公会教派,当发现对方是卫理公会新派教徒时,曾一度感到不安,但后来一直相安无事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威廉斯在那里呆了四年,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谋得了一个职位,第一份工作是帮助校对英国小说家萨克莱的十七卷作品集。他默默地咬文嚼字,勤奋地埋头于书案工作。
威廉斯对这份工作似乎很喜欢。生活在伦敦大都市,跻身于堂堂出版社,熏陶在上乘文学气氛之中,这一切对他形成了相当大的吸引和安慰。上述三种因素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和小说诗歌的早期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威廉斯在出版社表现良好,出落不凡,聪颖博学,颇受称慕,尽管这样,无论在业务上还是在政绩上他都算不上是大腕人物。
牛津大学出版社环境宜人,在这里威廉斯的创作冲动一再受到鼓舞和得到升华,加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他的部分作品被载入该出版社发行的世界名著系列之中。然而,威廉斯拥有的读者量还是十分有限,他的作品仅在出版社的部分同事和听课学生中间流传。在和路易斯相识之前,他的诗作没有能够得到大众的赏识,最明显的莫过于他的五部小说的遭遇了,由于没有什么销路,出版商十分沮丧,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亦到了尽头。在威廉斯的最后九年生命历程中,情形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期间的作品,包括两部诗集、一部但丁考、神学文丛及另外两部小说等,都赢得了特·斯·埃力奥特和道若赛·萨耶斯的赏识,前者帮助威廉斯出版小说,后者热情提供赞助,以支持但丁考一书的出版发行和古朴新颖的神学研究。
在传记文学《墨友》一书中,哈姆詹瑞·卡派特引用了威廉斯曾在牛津写给妻子的信中的话:“《墨友》乃我良师益友”。《墨友》对威廉斯产生的具体影响尚有争议。卡派特认为,在诗歌创作和基础思想方面这种影响并不重要,而关键之处在于给威廉斯的构思及创作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刺激或挑战。这对威廉斯显然非常重要,首先,面对热心的读者们,他不能不扪心自省,从而消除自满情绪,提高创作质量;第二,有点儿奇怪的是,威廉斯在这种环境中能挥洒自如,摆脱陈习,从他前期作品表现出的神秘氛围的困扰之中解脱出来。
倘若认为上述说法言过其实的话,我们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威廉斯年青时全力着手整理《牛津版神秘体诗韵集》,并与出版社的两名编纂人员结成好友,他们是堤·尼柯森和列维·李,后者为英国国教牧师。该诗集“专门收集体现纵深意识流的诗和诗摘”,有人曾为此指责威廉斯,“从文学角度讲,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杂烩玩艺儿”。为成此书,尼柯森和列维·李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工作,其中包括了一大批不同类型作家的神秘派诗作,他们是叶芝①、埃维林·恩格海尔、埃·依·魏蒂和阿莱斯特·柯让莱等。
威廉斯对柯让莱及其作品的过分表现并不感兴趣,柯让莱的一首诗竟有八处之多的脚注以诠释其隐意。威廉斯与魏蒂则交往从密,他研读过魏蒂的部分作品,并接受魏蒂之邀而加盟“金晨社”。魏蒂其人,作为一个学者,很难说他在宗教和学术两方面十分出色。在新近一部分介绍魏蒂学术风格的书中描述他“古怪、迷信、偏执”。他的作品包括有《炼丹术的秘密传说》、《魔鬼志》、《密藏圣杯的教堂》、《坦罗特算命牌图解》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热切但阅历不深的威廉斯就此涉入了一种十分局限的创作意境。
威廉斯做为“金晨社”的成员大约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他在这期间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作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岁刚出头的威廉斯其时不嫌麻烦用心学起了魔典语言,离开“金晨社”后他还将社徽精心保存了下来,并曾一度召唤诗歌创作的灵感而给同事们以极深的印象。后来,威廉斯不断地在小说和诗文中引用神秘素材,并且还写过一部专著。虽然如此,威廉斯的确切的信仰问题仍然是个谜。
威廉斯的女友安妮·瑞得勒在给威廉斯的文集《城市肖像》作序中指出,教堂是威廉斯成长的土壤,“金晨社”则是一种“临时追肥”。埃维林·恩德海尔也曾这般讲过,但她后来专辟“神秘教主义”篇章以阐述自己的新观点。相形之下,威廉斯于一九四三年编辑和介绍恩德海尔的书信集时,毫无掩饰地引用了史实,指出恩德海尔曾加入“一个称之为‘金晨社’的神秘团体”,并对这一重要史料未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威廉斯对神秘论的兴趣和介入比之他自己所表白的要浓厚明显得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他还一再建议女友安妮·瑞得勒拿一本魏蒂的著作去读一读。一九九○年盖瑞思·钧特著文《墨友与魔界》,其中剖析道,神秘之趣味熏陶污染了《墨友》,他清楚地记述了威廉斯与欧文·巴费尔德(路易斯的朋友,一职业人类学神秘诡辩家)之间的关系,但涉及路易斯与托尔金的关系时,证据则难以取信。托尔金想入非非的世界,乃源自劳西和古英国的神话传说。路易斯尽管在其科学幻想小说三部曲构思中毫无疑问地借鉴了威廉斯的部分思想风范,但在其自传中却断然否认与神秘主义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路易斯和托尔金只是写一写幻想作品而已,并不涉及到他们是否信仰神秘论问题的话,威廉斯大不相同。集目光短促、阅历不深、喜欢循规蹈矩及恪守家庭生活于一身的威廉斯对大自然缺乏兴趣,一生只出境旅游过一次,那是他短途去巴黎,在后来的回忆中他称巴黎为查理曼大都市②。做为一个诗人,他对生活的感受十分强烈,但是,他基本上是闭门觅句,生活在想象之中。结果,迷恋于神秘主义不仅使他神往不已,同时也给自己以后的道路上设下了陷阱。
毫无疑问,对神秘论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当归之于宗教仪式。英国教会注重宗教仪式,高教会派教徒更是如此。约翰·卡雷在《知识分子与群众》一书中则提出了更为本质性的见地。他指出,叶芝曾是“金晨社”的成员,这表明了“神秘主义的广泛复兴……,解释了为什么知识分子渴求荣誉与力量的源泉,而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理这个茬”。一方面,卡雷的论点并不完全符合威廉斯的情形,因为,威廉斯是彻头彻尾的自学出身的郊区平民,根据卡雷的观点,文学知识界最不愿意让这种人领享风骚而使自己掉价难堪;不过,另一方面,威廉斯又是体现卡雷论点的典型代表。不难看出,常人难以理喻的超越人类常识的思想体系对威廉斯具有非同小可的感染力,这种思想体系至少能给他循规蹈距的生活润色添彩。当然,如果信仰神秘论的话,还能藉此去理解宇宙奥秘。
选择奇特的主题做为幻想和惊险作品的素材,同时,以此来弥补自身有限的阅历,这对威廉斯来说恐怕是难能避免的。威廉斯既没有毕得斯利的冷酷无情,又缺少叶芝的浪漫的想象力,做为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神秘学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但他仍然觉得神秘学是颇具诱惑力的一门学科,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恰是宗教社会提供给他作素材的重要源泉。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威廉斯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数没有一个确定的职业。在其早期作品中,出版社便是小说主人公们活动的主要场所,除此而外,书中人物似乎都在云游度假。虽然《牌胜一筹》讲的是发生在圣诞节前后的事情而无此嫌疑,但是,早期作品中有名的人物如坎特布里大主教、首相、司法大臣以及境遇可怜兮兮却又聪明机敏的男男女女们好像都拥有没完没了的消闲假日。
所有这些都表明,威廉斯确实是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对别人的生活,他并不了解。假若果真是这样的话,迷恋于神秘论则只会使情况更糟糕。神秘论者本质上注重的是一些潜在的理性及其中蓄积的力量,而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有人曾就威廉斯的小说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故事八面威风地开了头,自由和平博爱地收了尾”。
《天堂大战》于一九七六年再版时,封面上简介该故事轮廓为两个肆无忌惮的恶魔“为占有圣杯以借助其神秘威力而达到各自罪恶目的所进行的搏斗”。事实上,威廉斯的五部早期作品中全部都贯串有这种冲突,都是相似的主题,为寻求神秘威力的自私动机导致了一场又一场酣战,结果是善者充分领悟了神圣的真理,而恶者愈加可恶,自作自受,终被超自然的神力所钳灭。尽管有一些描写是十分成功和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但是,普遍来说,威廉斯的人物塑造颇欠精致,他的得意的女主人公中,有那么几个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简直让人受不了。塑造最为成功的角色要数吉力斯·杜马提,他是出现在《天堂大战》和《天地万象》两部作品中的一个幻想形象,十分逼真,活灵活现,威廉斯的意图可能要通过小说再现阿莱斯特·柯让莱的形象,确实,威廉斯在描绘柯让莱之精力充沛、蔑视他人方面(见《柯让莱自传》)十分地道,画龙点睛,维妙维肖。
《遁入地狱》和《圣诞节前夕》是威廉斯的两部后期作品,其表现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但“更加幽暗更加复杂”,而且越来越注重作品中人物个性的不断演变。虽然大部分主题仍源自神秘论素材,但是,从整体上看,此时的作品其背景益发严肃,人物个性逐渐鲜明,情节发展相对更加合理了。威廉斯心有向往,言之有意,终归是恶善自有定数,各得其报。在威廉斯的影响下,路易斯亦采用了相同的表现手法,写就了精彩幽默的天堂地狱的《大决裂》寓言。
对人物个性越来越深刻的刻画似乎源自他对生活越来越多的关切和认识,并反映了威廉斯神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假若不相互矛盾的话)。由于身体不适而躲过了战乱的威廉斯,因为没能与朋友们患难与共和作出牺牲而异常痛楚不安。于是,他萌发了“共同禀承”这样一个新概念,并先后贯穿进了他的诗文创作之中。早期作品中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概念,而在最后两部小说中,意境环绕,着墨不少,并做为《遁入地狱》的主题思想而一再发挥渲染,其中将“共同禀承”称之为“爱的迭替”。威廉斯用心良苦,想通过冥冥之中神力让真诚永恒的爱去剥掉虚伪的爱的伪装。
威廉斯的后期小说的确表明直到晚年他依旧信奉神秘主义。另有人则认为,作品的真正含义并非如此,威廉斯精通神秘学,善于写作惊险神秘题材的作品,小说中时常表现一些奇景怪遇,但总不能说一个人的作品内容就一定是他的信仰之所在了。
威廉斯的崇拜者总是不愿意承认威廉斯信仰神教。毕竟,基督教训一贯地反对魔法。基督教中有关“上帝的魔法”的概念,应该说无论如何去定义和解释它,在逻辑上它起初就是一种错误。凡事总不能一概而论,譬如,苏联作家米哈依·布尔加柯夫滥仿的故事中,魔鬼在莫斯科显出了人形,而以此来中伤诋毁斯大林的“恐怖”政权(《主人和人造奶油》),没有人会认为这位作家是信必言,言必信,真当有那一档事了。但是,当有人声称自己洞悉了“天堂之苍穹、地狱的深渊”(埃力奥特评威廉斯)时,这就完全应该另当别论了。
好在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尤其与路易斯结识后,威廉斯逐渐失去了对神秘主义的依赖性。当初,神秘论对威廉斯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那些东西能给本来就十分平淡的生活增添许多色彩。及至后来,在缺乏充分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他便将刺激想象力和产生小说及诗歌创作欲望的源泉归之于神教的力量。到了最后十年,在路易斯和“墨友”们的伟大友谊的感染下,通过开始注重关心他人生活这样一个简单过程的转变,威廉斯真正开始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迈出知识沼泽地,从而步入了有益的、成功的和丰富的一段创作生涯。
舟挥帆译
注释:
①威廉·巴特勒·叶芝──爱尔兰著名诗人、作家,曾获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
②查理曼大帝──世称查理王或查理一世,为西罗帝国之前的法兰克王,故称巴黎为查理曼大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