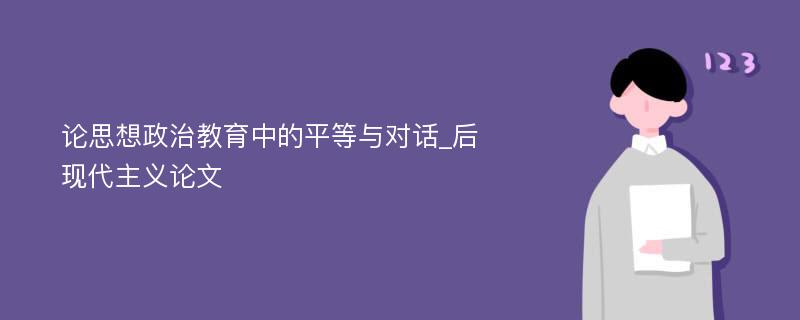
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平等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1-0053-04
从哲学层面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相对于教育对象这一客体是居于逻辑先在地位的,但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先在性,决不意味着教育者可以把自己的政治愿望生搬硬套在教育对象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建立在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客体二分基础之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处于不平等地位,缺乏必要的对话与沟通,不能相互理解从而使师生相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受教育者对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厌倦。
一、传统哲学认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对教育文本的灌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低效
从知识本体论看,“灌输”的教育观是视知识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它假设教育者是社会理性的化身,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相信学生只要获得了这些外在的知识,就是达到了教育目的;对于外在于人的知识,受教育者是没有任何选择权和建构权的。这种在“有限知识”时代占绝对优势的灌输理念,教育者认为找到了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想方设法把材料上的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受教育者,用文本上所要求的思想观念规约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仅仅扮演一个被驯服的接受者角色。在此,教师是他自己所传授的一切知识的主宰者,教师对文本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学生只能听从教育者对文本的最高权威性解释,而且必须当作真理不得怀疑。总之,“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1](P294) 而我们知道,文本的存在意义在于阅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主动把文本的意义变成阅读者自身的。如果阅读者只能阅读文本而不能转变为自身的,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拼贴并无意义的生成。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低下,原因就出在这里:一方面,它把以课程形式确定下来的文本看成一成不变而非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它还低估了受教育者对文本与生活的理解与建构能力,俨然以教化者的身份对他们予以矫正。所以,在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似乎都在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很多思政教育的场面看似在对话实质在独白。更糟糕的是,教育者成了教育的控制者,无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他异性,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受教育者,使他们成了思想政治知识的无心无情的容器,甚至成了教学的旁观者。
(二)受主体性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单主体论
在哲学发展史中,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古代哲学单纯就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转变为近代哲学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带来了近代哲学物质与精神、事实与价值、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并预设主体的优先地位,把主体放在绝对权威的位置,从而造成主体和客体地位的不平等。此哲学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影响是:只界定了主客体之间单向式的一面,而且往往把主体放在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表现为或“教师主体”或“学生主体”的单主体教育模式。
“教师主体”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主体”模式即赫尔巴特的传统教师中心论;它强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和课堂中心,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被教育的客体,教师处于积极主动地位,学生处于消极被动地位。该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居高临下强迫式地灌输,往往忽视了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和主观能动性,这造成了权威的教师和服从性的学生,使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异化为“工具”和“手段”的关系。
“学生主体”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主体”模式强调学生中心、经验中心和活动中心,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而教师是客体。该观点来自于杜威所强调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生在“做中学”。总之是要求教师不要站在学生前面的讲台上,而是站到学生背后去,把教师降到一种辅助性的地位。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在反对给学生背上沉重的“美德袋”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造成“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德”。
总之,传统主体性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处在二元对立状态,要么强调教师的权威,要么强调学生的绝对中心,这与迅速发展的时代、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相悖的。
二、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以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了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在价值取向上立足于对传统思想的超越和决裂。用后现代主义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关照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消解和颠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二元对立、主体至上与话语权威,以建立一个平等与对话、理解与沟通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一)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不是既成的,而是不断生成和建构的,“意义不是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从我们与文本的对话中创造出来的”[2](P193)。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如何去认识文本、解读文本是教育的核心,因为正是在受教育者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实现其思想转化。
后现代主义主张多元论,反对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认为统一代表统治,即以同一性的名义取消差异。后现代主义学者纷纷批判理性主义的一元论,尼采认为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对错及善恶的标准,费耶阿本德主张“怎么都行”,利奥塔则奉劝世人“拯救差异”。后现代主义还反对以寻找知识和行动的可靠准则为核心的基础主义,倡导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侧重于清晰的起点和明确的终点——将让位于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或网络。这一复杂的网络,像生活本身一样,永远处于转化和过程之中”[3](P5)。持该观点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中,罗蒂就认为任何一种基础的东西都是历史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哈桑也主张“不确定性原则”,德里达认为在语言系统中容忍差异,就是避免垄断真理。所以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是随机的、混沌的、非对称的、复杂的而不是决定论的、有序的、对称的、简单的。
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当今中国,正处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图景中:知识更新速度极快、信息爆炸、知识随机、混沌而复杂,这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是要求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以应对信息的爆炸和思想变化的日益复杂;二是要求教育的高效性,以应对人们对应用性知识的高度关注而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短平快;三是要求学习的自主选择性,以满足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人们高涨的自我教育热情和受教育过程中人的尊严的满足;四是要求教育过程的开放性,以应对人们日益开阔的视野和对新信息的高度敏感。
(二)后现代主义诠释学要求尊重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权
后现代主义学者主张作者一旦创作完文本后,文本就成了独立的存在,作者就不再能控制文本的意义,取而代之对文本具有权威地位的是读者,于是“人死了”,“作者死了”。在对文本的解释过程中,首先,海德格尔认为:人们不可能精确重建文本过去的意义,因为解释者作为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人,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性:人所拥有的前有、前见、前识是他能作出解释的基础和前提,人在解释文本时无法排除其影响。其次,加达默尔指出:解释中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存在的,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没有一种固定的本体论的客观意义,它会随着解释者的改变而生成不同的意义。再次,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释者的对话中形成的,即文本因为有解释者的参与才成为文本。既然文本无所谓原意问题,也就无所谓对文本惟一正确的真理性解释,文本的意义因解释者对文本的创造性解释而产生,所以文本不能离开解释者而存在,解释者的参与使文本最终得以完成。
基于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还提出:解释者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哪个解释者比他者更具有权威性。他们的解释是平等的,无优劣、高下与正误之分。以此观点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对文本就应当有自己的解释权,教育者不应该也无权剥夺。教育者不应该追求受教育者对文本的整齐划一的理解,而应该鼓励受教育者对文本解释的多元性、差异性。教育者所需扮演的仅仅是一个中介人和精神助产师的角色,以帮助受教育者阅读文本、生成意义,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复制和强迫灌输。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解释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也不是强制灌输,而是使用受教育者所能接受的语言,而非用师者的思维、语言来进行教育,从而有助于受教育者理解文本。
(三)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平等的交互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着力颠覆传统的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和他人、和自然相比并没有更为特殊的地方,人没有理由获得对他人、对自然的统治权和占有权,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有机联系的形式而存在,人只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和构成性的存在。所以后现代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倡导主体间性——即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均是主体,这就消解了人我之间的对立。这种主体间性的理论对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建构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中相互影响。”[3](P6) 此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处于同一个平面中的两个平等主体,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同样是受教育主体,他们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使基于理解之上的交谈和对话成为可能,而不只是作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孤独者而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贯彻主体间性,教育者就应当是好的倾听者和交往者,而不仅仅是好的讲解人。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声明的:“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4](P108)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互主体性”就是要使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存在,充分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并为师生间创造文本理解的对话平台,以实现哈贝马斯所讲的“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一致”,从而创建一个意义的世界。
三、心理咨询在“平等与对话”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一门“人学”,遵从人性就能事半功倍,心理咨询是很人性化的一门学科。根据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所强调的平等、对话、理解与沟通,在方法论意义上把心理咨询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可行的。在理念和技术的应用中,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平等、对话以及受教育者对文本的主动解读等方面做一些初浅探讨。
(一)贯彻“无条件尊重原则”,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平等
平等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过是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者,不再是教育过程的主宰者,不再是受教育者的对立面,教育者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心理咨询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尊重”来访者,强调咨访双方的地位平等,咨询师绝不是高高在上于来访者,咨询师不是来访者未来发展的设计师,咨询师只是导引和陪伴来访者走过他心灵的痛苦期,来访者之所以愿意接受咨询师的帮助,只因为咨询师能给来访者创造平等的心灵空间;无条件尊重使咨询师能进入来访者的内心深处,帮助其自我探索,剖析自己缺失什么、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跟随自己的心灵找寻发展的方向。这与前面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胡塞尔的“交互主体论”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均是主体,而且是作为平等的主体存在,消解了二元论的人我对立。而心理咨询中无条件尊重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对促进思政教育中授受双方的地位平等,展开受教育者思想深处的自我探索,追寻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发展平台。
(二)使用“专注与聆听”的晤谈技巧,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话与沟通成为可能
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只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单向制约关系,而应是双向交流关系。那种教育者居高临下、不关注受教育者的信息反馈、单向灌输的强制性教育格局,必然以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而告终。而双向交流型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前述的信息授受双方地位是平等的,教育者相对受教育者,由高高在上转为平等相处,由教导者转为“对话者”;他们的信息流动也是双向的,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与尊严在其中受到尊重。
心理咨询特别强调利用“专注与聆听”实现晤谈中的双向交互性,表现为:其一,晤谈主要以对话形式出现。咨询师不仅要同理、专注与聆听,要听得到来访者所传达的有声与无声的信息,更要聆听到来访者心灵深处。同时,在对话中,说者和听者还在不断转换,对话不依赖任何一方,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对话存在于咨访之间。咨询师不仅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致被卷入来访者的情感旋涡,又要能有效控制交流的节奏与深度,能听到来访者的真实内心,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技术,也是一种极强的交流能力。其二,交互性体现在交往的内容上。咨询中全面而深刻的对话使得交往双方在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的关系中不断重构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情感、认识。其三,交互性还体现在咨询师关注来访者的整个“生活世界”及其成长。这就是师生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式和策略,而且是教育本身。教育就是对话,是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对话,是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是人类的历史经验与学生个体的对话”[5](P134)。它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具有完整人格的“我”与“你”相遇,它只可能发生在“我—你”世界之间,心理咨询的晤谈过程中,每一方都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交流的“你”,双方都真诚地投入到“我”与“你”的对话中,双方都在理解中获得沟通与共享。心理咨询“专注与聆听”技巧的应用,使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双方面对面地平等对话得以可能。
(三)借鉴“自我探索与挑战”技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对文本的主动解读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解释理论,受教育者对文本意义的主动的、创造性的解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接受”意味着理解和内化,“接受”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实现。在此接受过程中,受教育者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按照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习惯所产生的“期待视野”而自主思考、自主选择,通过自己的理解而生成意义。前文已论述过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从我们与文本的对话中创造出来的,受教育者对文本有自己的解释权,教育者不应该也无权剥夺。
心理咨询旨在“助人自助”,通过咨询师的引导,促动来访者的内心记忆与情感体验,引发来访者对心灵成长轨迹的自我探索,发现问题,找到成长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障碍,找寻到曾被遗忘的心理资源,并在咨询师精心设计的挑战之下,激发其自助、成长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总之,来访者的成长与发展主动权必须交还给来访者自己,让其通过自我探索、自我理解、自我发现、自主成长,把成长的责任交还给来访者。借鉴“自我探索与挑战”技术的理念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将认识到,教育者只是参与解读文本的一个主体而已,并不象传统所认为的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知识复制;而且教育者要从有助于受教育者理解文本的角度来解释文本,包括使用受教育者所能接受的语言,而不是用教师的思维、语言来进行教育。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借鉴心理咨询中“自我探索与挑战”技术,引发受教育者对文本的主动而深刻的思考,尤其是有“心”的思考,并把思考所得纳入自己的生活和成长意义中,才可能带来受教育者的思想转化,而使狄尔泰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顽症——“知识和生命的脱节”不再重演。
收稿日期:2006-10-2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为06A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