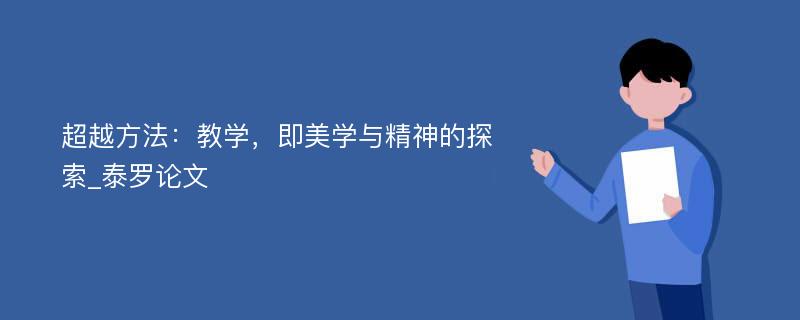
超越方法:教学即审美与精神的探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用方法代替审议的念头……恰恰是一种妄想。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82)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34-10
方法是教学的核心,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对于这种观点,无论是根据教学和方法的本质还是根据教育和教学的本质,我们都会提出质疑——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77/1945)的话来说,它构成了“思想的虔信”。当前,方法占据着教育事业的核心:它规定了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课程计划、我们的教学方式以及我们培训教师如何教学的方式。没有关于“方法”课程的教师教育方案不能称其为教师教育方案;正如没有讲授“方法’,的教科书不能称其为教科书一样;也正如不具备方法论的课时计划不能称其为课时计划一样。简言之,方法已经成为一切教学的意义载体——这是不言而喻的,它得到了彼得·拉莫斯(Peter Ramus,1515-1572)的点头赞同与微笑认可。他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通过“方法化”(methodizing)来解释“如何教一门课程”这一当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拉莫斯是第一位方法论者,毫无疑问也是至今最伟大的方法论者。但是,在阐述拉莫斯的方法论思想及以其作为基础的一些假设之前,尤其是在阐述涉及到方法是如何既塑造了我们的教学概念又塑造了教学本身的思想与假设之前,我乐意首先审视一下这一方法化运动给予20世纪的一些馈赠——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馈赠。有时,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对它如此谙熟,以至于必须回过头来才能重新理解它——也许我们还是第一次体察到它。方法的概念不仅框定了我们的教育思想,而且也框定了我们的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事实上,正如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86)所声称的那样,方法作为一种思维的有序化的手段——科学的、理性的、有效的手段——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一种范式。杰克布·布鲁诺斯基(Jaeob Bronowski,1978)指出,这种方法具有“原因——结果”的程序性的“本质”,以及由此导致的简化论和可预测性,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我们不能开辟思维的另一条途径——它已经成为我们看待所有问题的一种自然的方式。
美国人很自然地就会把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的工作之上。泰罗本人曾于189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斯里恒(Bethlehem)钢铁厂进行“时间——动作”(time-and-motion)的研究工作。但当我们反观杜威采纳并发展这种方法以适合其实用主义的时候,很明显上述的视角是很狭隘的。我希望开展我自己对方法的探索,其根源可上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至少可回到拉莫斯(Ramus)和拉莫斯主义。于是,不需要多少绘画艺术的才能,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划出一条从拉莫斯到泰罗的直线,如果这条线不是笔直的、线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话。在这一幅画中,泰罗就算不是先驱,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他的工作仍然是基础的,尤其是对于热衷弗雷德理克·泰罗—拉尔夫·泰勒原理的教育者和课程专家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在泰罗意义上的方法和泰勒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提出的四步课程设计程序之间是很容易让人作出直接联系的,而正是这条泰罗-泰勒轴心线仍然继续决定着我们今天教育规划的方向。这条主线的存在价值已经贯穿于整个现代主义时代。我相信,在我们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则需要取而代之。
对弗雷德理克·泰罗的批判
早在1890年代末,泰罗(1856-1915)就犹如彗星般在美国灿烂一时,在进步主义时代辉煌燃烧了短暂的时间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归于沉寂。然而,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仍然被视为对美国工业景观的影响超过“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阿尔弗雷德·斯隆、汤姆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而且泰罗主义和泰罗体制已经成为“我们道德的内在组成部分”。法国的百科全书主义者把他们的研究组织工作划分为两个宽泛的阶段——前泰罗主义阶段和泰罗主义阶段,这是很正常的。正如卡尼格尔(Kanigel)在泰罗的传记《一条佳径》(The One Best Way,1997)一书中所说的,事实上在泰罗所能触及到的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智力、心理(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上教育)领域,“泰罗是一个最佳的标准,其它的都要与之对比。”他是“科学管理之父”——这一短语已经刻在他的墓碑上——是泰罗体制或泰罗主义的缔造者。
1898年夏天,泰罗在伯斯里恒钢铁厂2号机械车间所做的事情,就是改变工人的工作方法,把按日计酬改为按件计酬;工人从作为一个群体一起工作而获得固定薪水(那时每天把92磅生铁锭搬运到火车上获得1.15美元),变为基于所搬运的生铁锭数量而按件发放薪水。泰罗所完成的事业使美国的工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转变了工人的操作方式,这正是因为其“方法”——泰罗方法—利用了“时间—动作”研究去规划、控制每一步骤的详细细节和工人做出的每一个动作的缘故。正如他对亨利·诺尔(Henry Noll)——在他的文章中作为施密特(Schmidt)提到过的劳工所说的,“如此愚蠢……他几乎像一头公牛”——“一个价值高的人就要从早到晚恰当地完成要求他做的事情……正好一直干满一天。而且,不要回嘴,毫无怨言”。这样,泰罗体制的核心便是:把人安置在工作上——施密特是最理想的——然后把他(或者材料,如果要为他设计用来工作的工具的话)推向可利用的极限。找到这种精确的极限或精确的最佳状态是泰罗所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工作的“科学性”。他往往把工具和工人一起推向可利用的极限。事实上,施密特被奉为理想的、“价值高的人”,他每天能赚1.71美元而不是1.15美元(因为他的生产率提高了400%)。他也是唯一的理想人物:他是泰罗及其计时小组最初选择的工作人员中的唯一能够以精确的方式,连续进行1100次举起——上台阶——装载的工人,他每天搬运92磅生铁锭。在计时研究中选出的30个人中,有10个是精挑细选的,有5个人是在最后阶段加入进来,只有施密特能坚持下来第一个星期,只有他继续以每天超过45磅的速度装载火车——生产率提高了大约400%。以这一数据为依据,泰罗于是(科学地?)把每人每天搬运45磅作为“标准”,每天薪水1.70美元。尽管对于大多数劳工来说很难达到这一“标准”,但数量众多的按件计酬的工人能够以每吨5美分的薪水装载火车,低于以前每吨10美分的按日计酬。随着利润的增长,管理者喜上眉梢,泰罗及其计时小组(“分析专家”)被拥戴为美国工业的大救星。
这种个人声誉是短命的。在两年内,伯斯里恒钢铁厂的不熟练工人从600人下降到140人。幸存下来的140人构成了作者(泰罗)所能看到的“挑选出来的最好的劳工群体”。然而,是“另一些”不再继续在伯斯里恒工厂工作的460人引起了国会议员威廉姆·威尔逊(William Wilson)的注意。威尔逊是宾州中部煤矿的前矿主,当时担任“泰罗及其它商业管理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们感到迷惑了。泰罗雄辩地描绘了他为所有的美国人、工人和管理者所提供的繁荣。威尔逊想知道这一“制度”对于那些不属于“一流工人”的人起什么作用。双方不能展开对话。在委员会听证会的第三天,经过8个小时的煎熬,泰罗的感情终于爆发了,并开始叫喊,谴责那些不能或不愿领会他的观点的人——他坚信,只要提供适当的管理和动机,所有人都能做到施密行所做的事情。“其他人”是,用他的话说,“能够歌唱但不愿歌唱的鸟儿”;他们不值得去注意。1912年1月30日午夜,威尔逊结束了他的听证会。带着心碎般的伤痛,泰罗在地中海休假了一段时间,几年后便与世长辞,享年不足60。
今天,泰罗已经被视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部分,那是一个令人着迷又充满矛盾的时代。对威尔逊和其他人来说,泰罗是一个灵魂的破坏者;对于他自己和很多人来说,他是劳动者的最亲爱的朋友、最伟大的协调者。一位欧洲人是这样评价泰罗的逝世的:“泰罗体制对欧洲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的教训’,也是整个美国的教训”。泰罗看到了这一教训。个体必然被这一体制所约束,根据这种认识,他也看到了这一教训的道德意蕴。他在《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中写到:“在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在未来,本体制必然是第一位的”。
我乐意从我们所关心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一体制的三个方面:它的“方法”、它的“标准”的概念以及它的“科学性”。它的方法是对17世纪瑞恩·笛卡尔(Rene Descartes)追求“恰当地操纵理性并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继承,并兆示着20世纪拉尔夫·泰勒将列举课程开发的四项标准。泰罗方法的细节——管理应注意的原则——我早已列举过,下面再列举一下。正如笛卡尔和泰勒方法的四步一样,它们是:
第一,必须为人们工作的每一因素开发一种科学,以取代旧的经验主义的方法。
第二,必须科学地筛选和培训工人,不允许让其以自己的方法工作。
第三,保证所有的工作是根据所开发的原则完成的,这一点必须注意。
第四,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工作与责任必须进行平等分工。(Doll,1993,第41页,from Taylor,1947/1911,第36-39页)
仔细审视这一方法的概念,一些问题就会凸现出来。一个是,这种方法要求计划,甚至可以说是进行计划前的准备;就是说,在动作开始之前就必须倾注大量的注意力、寻求精确性并搜集细节。当然,这既可以在笛卡尔的方法中看到,也可以在泰勒的方法中看到。活动和经验——搬运生铁锭、或从课程中学习,或思考理性问题——并没有构成计划的基础,而是由计划所形成。计划先于行动;行动受计划制约。计划者实施控制,在整个经验中这一点还是没有消解。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一(预先)计划方法的概念感到如此舒适,以至于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自然的。然而,杜威指出(1922),所有的计划和结果实际上都是“视野之内的结果”(ends-in-view),它们来自活动,并非先于活动。我认为这一点很明智。想与做直接对应着计划与行动。他说:
强加的目的在每一点上都是与真实的目的相背离的……强加的目的是固定的、僵硬的。在教育上,致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变得机械性和奴性的责任,应该由强加的目的来负担。
当然,强加的目的或目标集中体现在控制上——一切控制都由计划者操纵。对于泰罗来说,这种“控制集合”(concentration of contro1)是很自然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它是“现代科学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因素”。泰罗将容忍“不要回嘴”,工人和管理者按照类别进行分离,工人们(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学生)要“毫厘不爽”地既要接受他们被告知要做的事情,又要在确定的时间内按照所要求的工作方式完成任务。尽管把这种方法论直接引入今天的学校教育将是一种讽刺,但它仍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份遗产,而且在过去并不久远的几十年里它的确是一个现实(Doll,1993,第2章)。今天,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严重分离以及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分离仍然保留着,其中前者又服从于后者。如果说课程中有一个幽灵在游荡,那么它就是控制以及由其带来的恐慌。
在今天的学校中,很多改革都是围绕着“控制应当表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展开的——管理者/官僚进行(预先)计划,工人/学生进行体检,或教师/家长在决策者和决策针对者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在公理教会唯心主义的标牌下,杜威相信,控制存在于情境自身之中——它无需外求,它内在于人们一起做事、交流和反思的活动之中。他说:
一般经验能从自身的方法之中发展而来,而方法保证经验发展的方向并创造内在的判断标准和价值标准。(1958/1929,第38页)
杜威相信,这种激进的、事实上是异端的声明也会变成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获得生命、精神和活力——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发展一种哲学或“经验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论,且它不是强加的,而是体验到的。
在随后的引证中,杜威使用的“内在标准”(inherent standards)这一术语是很有趣的。因为他假定,能够接受的标准可以在经验自身的情境中得以生成。生活在同一时间阶段的泰罗——他们都出生在1850年代——把标准看成是一个仅仅是外部的、强加的东西。泰罗的观点绝对占优势,在今天的“标准运动”中这一点很明显;人们往往认为,标准的概念来自于活动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标准是由那些有知识、有权力的人来施加的或制订的。但在关注自组织(Capra,1996;Kauffman,1993,1995)的后现代框架里,被强加的标准的概念是无意义的。连同目标和目的,标准是(在情境中)显现出来的;他们不是由外部强加的。当前教育思潮中的标准运动牢固地根植于19世纪的现代性思维中。
作为泰罗使用的一个概念,标准这个词值得仔细剖析。这一词来自罗马语esten-ere或拉丁语extend-ere,意思是“伸出或延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第504页)。它最早作为“旗帜或准则”来使用,指集合地点和在战斗中突出于人群的启迪人们的向导。后来,3个世纪之后,在1400年代,其用法要么作为“测量或称量的一个权威的模范单元,要么作为被认可的完美的和正确的典范”。这一扩展了的标准之含义是泰罗曾在提到诺尔(施密特)的著作中用过的——挑选了30人,只有诺尔能够坚持下来那令人精疲力尽的节奏,每天装载100磅生铁锭,日复一日。一旦泰罗发现了能够以这种节奏工作的人,那么,他就把这一“绝对的优秀水平”描述为一种尺度。在这一定义下,我们发现它分裂了最初的涵义,几个世纪以来弄乱了标准的概念。它被认为是“正确性和完美的典范”。诺尔每天搬运45.75磅生铁锭,于是泰罗制订的“标准”就是45磅(卡尼格尔指出,这是武断的)。然而,所有的人都要满足这一示范性的“标准”,于是这一单词也就意味着“一个标准的单元或数量;一个规定的最小量”。于是,诺尔独自一个人能做的45磅既是典范又是标准:一种典范和最低限量。显然,在泰罗到来后,该工厂超过75%的搬运生铁锭的工人离开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其他类型的人”、非“一流工人”人是威尔逊想要了解的。对标准的这种界定在今天仍使我们深受其影响。它们是优秀的榜样,所有的人都要达到。它们描述了最低限量,也剔除虚弱者。在现代性的框架中,我们把标准作为集合点,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它聚集起来——只有那些不能唱歌的鸟儿不能来,因为这里没有那种在适当刺激下不能唱歌的鸟儿。泰罗不需要科学地(仿生学地?)利用这些鸟儿,即“那些另一类型的人”。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中,这种要么/要么、渴望/都达到的概念既不正确也不错误,它仅仅是无意义——因为判断和价值的创造内在于过程和经验活动本身。我们已经超越了现代主义及其方法,泰罗是不会理解的。
南北战争后进入鼓吹时代的美国接受了英国人赫尔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暗示——斯宾塞相信,“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而且只有科学,因为它真正“为一切活动秩序作最好的准备”——钟情于科学,实际上是对那些所谓科学的东西的盲目崇拜。科学及其使行为(最高)秩序化的方法把时间和动机置于控制之下。两者不再放荡不羁,它们被用于工作,为“人”谋福利。《科学管理》这个书名成了进步主义的一个咒符——即使杜威也经不住诱惑而屈服。有两个人用该书名写过专著:一个是泰罗(1911),一个是杰瑟芬·梅耶·赖斯(Joseph Mayer Rice,1914),后者从一个药剂师转变为一个教育改革者。时髦的杂志把科学管理的特征撒播到家庭、教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看待如何有效率时往往精确到千分之一。这种“效率狂热”的表现之一,就是成立了“家政实验站”。在这里,人们劝告妇女停止“家务服役”而投入到工作中来,鼓励其成为“生产公民的伟大工人的一部分”。告诉妇女去发现“家务工程的原则”(Haber,1964)。
作为众所公认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出生于南北战争时代的费城,当时正是美国工业主义心潮澎湃、悸动不已的年代。美国建立了鲍德温机车厂并在全球扩展,制造了重达30吨的庞大的蒸汽发动机,这是工业美国的象征。泰罗出生在费城的一个有影响的显富之家,他十几岁就在欧洲广泛游历,进入菲力普埃克赛特学园,在那里,他在当时要求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方面连续获得年级最高分,但没有毕业。在哈佛入学考试中获得奖学金,但选择了作图案设计师菲拉尔和约翰(Ferrell & Jones)的学徒——他跟那些“正规雇员”一起努力工作,忠实诚恳,躬行于实践。
年轻时,泰罗协助建立了哲蒙顿科学社区,实际上是由他的一群年轻同伴组成。作为图案设计师的学徒直至后来成为机械师,泰罗对于机械并不真正感兴趣,但作为年轻的“科学家”,他无穷地迷恋数学和精确性。当他十几岁在欧洲旅游时,他广泛阅读数学方面的书籍并对于金钱、时间、距离作了详细的记录,还对奥地利如何开采盐矿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种对精确性的兴趣让人厌烦。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回忆到:
在我们少年时代的一伙中,泰罗的观点是很怪异的。我们有时真想对那些严格的规则和精确的公式群起而攻之,但他坚持所有的游戏必须遵从它们。
泰罗的“科学主义”是一个综合体,是把精确性、努力工作、服从于体制以及致力于把人和材料推向可利用的极限的狂热揉合在一起的产物。他使这点在诺尔身上体现出来,还表现在制造了一种能以四倍于先前的速度切割金属的高速钢钻头。泰罗觉得,他们发现的这些极限就是科学的规律,都是“在数学的旗帜下得以包容的”。一旦发现这些规律,泰罗就感到,把它们作为标准而强加到跟他发生联系的每一个人身上是他道义上的责任和虔诚的使命。
上面对泰罗的科学主义——他对于程式的形而上学的专注——作了大体的介绍。我并不是说,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中没有别人可称为科学的东西,如果这样,那是不切合实际的。泰罗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而且他确实开发出有用的工具——钢钻头、铁锹等。然而,在关于科学方法由什么构成的观点中,他的武断和私人激情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知道,泰罗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比他年轻三岁的杜威被称为“科学方法之父”。在1910年的著作中(1933年修订),杜威提出了著名的方法的五步:(1)觉察到问题情境;(2)界定这一问题;(3)提出假设;(4)形成推理;(5)通过行动检验这一假设。这一方法对于孤寂失落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的影响,不能过分强调。它构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程式,我们用它来告诉学生怎样思维,用它教导自己如何根据这一嘱托做事情。这一方法无所不在,从幼儿园到博士学位课程,它统治了我们整个的学校程式。
但是,杜威是一个严父。他不想让其关于“方法”的思想过于张扬。他说:
假定学生……在学习和思考一门学科时能够为其提供可模仿的方法模型,这种假定陷入一种自欺,会导致可悲的后果。
还有:
把一种既定的统一方法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会带来普遍的平庸,极少有例外。(1996/1916)
但是,杜威并不反对方法——方法构成了他的逻辑、经验、反思的核心。他所反对的——而且是极力反对的——是方法教条化的概念和实践。这方面有一条主线,从拉莫斯到泰勒。对于杜威,方法并不能被直接呈现,要从对当前具体情境的观察中推导出来,并直接应用于该情境(回到自己的终点)。当方法与主体分离、方法与产生方法的经验分离时,它们便具备了“机械性统一”的特征从而失去了其在扩展经验中的作用。那么,“方法”:
必须很权威地推荐给教师,而不是教师们自己天才的观察的表达。
这种把方法与人分离的做法仅仅在伯斯里恒钢铁厂里才能有意识地发生。泰罗不想让工人去思考。事实上,“一流”的人并不思考,而是去做那些被告知需要做的事情。在这种态度下,就可以控制他们及其经验了。幽灵不仅游荡在课程之中,而且蛰伏于科学管理的神秘的内心深处。
美国进入工业时代后,杜威和泰罗都是这个充满躁动的同一时代的人,他们认识到,方法是生长和发展的关键。泰罗的理想是通过物质生产发展一种更好的社会;杜威的理想则是通过丰富、加深人们的经验、审美和精神而发展一种更好的社会。这两种目的很不相同,用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本身也是不同的。显然,在教育中这些差别会贯穿于教育(及与之相伴随的学习的概念)之中,相互之间又彼此包容。
我首先将从拉莫斯时代开始,探索我们所了解的学校教育,然后阐述一种取代它的教育,即杜威等人倡导的审美与精神的教育。为理解拉莫及其馈赠,首先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与该时代的关系也是重要的。
拉莫斯及其馈赠
拉莫斯绝对是16世纪的人(1515-1572)。由于卷入了骚乱,他在巴黎的宗教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1990)把1550到1650年的一个世纪作为西欧社会躁动不安和智力变革时代——德国、法国、英国发生了政府的革命变革,人口随之变动;联邦体制、罗马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科学和形而上学趋于崩溃。与此同时,教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百年期间,现代性和方法化接踵而来。对于现代性,我已经在其它地方阐述过了,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教学和方法化运动:拉莫斯及其之后的拉莫斯主义。
中世纪的西班牙人彼得(Peter)——药剂师、逻辑学家——在其《逻辑学》(Dialectic,1543)中提出了逻辑(实际上是修辞)的概念。在拉莫斯重新提出这一令人迷惑的逻辑(logic)之前,教学是通过对话进行的。有时这种对话是一种交谈,有时是一种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正式的讨论。阿尔伯塔(Abelard)在12世纪出版的《是与否》(yes and no)一书是这种教学的很好的例子:对照讨论,要求学生指出自身存在的矛盾。拉莫斯时代的这种对话/论争被神圣为一种方法。让他的同事惊慌的是,拉莫斯改变了所有的方式。他提出一种新的途径来表征这种“方法”。他的新方法论假定,当时年轻的青少年渴望轻易地获得一种产品,而无需经受无休止的过程。这样,沃尔特·奥格(WalterOng)把他的其中的一本书命名为《拉莫斯、方法和对话的衰退》(Ramus,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1983/1985)。在当时广泛流行、颇有争议的拉莫斯的“方法”,征服了忠诚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尤其影响到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的著作,并飘洋过海来到清教发源地新英格兰,在这里,“肤浅的简单”最具吸引力。
在16世纪,年轻的拉莫斯担任普瑞斯莱斯学校的校长,从事教学工作。他被迫记忆无穷无尽的、毫不相干的拉丁语法的细枝末节(人们需要掌握语法来阅读当时存在的文本)。“逻辑”是需要进行修辞学上的争论的,少年和儿童记忆象征性的“卡片”——很像今天仍然使用的塔罗特卡片(Tarot cards),当小鸟(没有提供一般的术语)在头顶上飞过时,一个人会拿着三捆树叶,分别代表着“什么、什么种类和多少”。奥格说,“在头脑中有了这幅图画,男孩子——不管他的拉丁语是如何地糟糕——就能够记住西班牙人彼得及其‘逻辑就是一切’了”。这里凸现出很多社会的和教育学的观点:(1)拉丁语是学术书籍出版所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语言;19世纪末期拉丁语能“锻炼心智”的神话是对非常具体的和颇具实践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抽象;(2)年轻的拉莫斯所教导的是在8岁到16岁之间的孩子,其思想还没有成熟;(3)他们所对待的拉丁语和逻辑是极其简单的,几乎构成了记忆规则和记忆种类的全部。简言之,当方法被用来教导一个人“思考”时,这种思考需要具备的是记忆和规则的跳跃性。事实上,我们从中世纪所继承下来的学校思维的概念,仍然与记忆和规则有很大关系。为了思维而发展教育或开发课程包括了个人审议、反思、行动和选择——这正是杜威所极为强调的——也是今天的课程专家和教育者所努力争取的。
拉莫斯是一位校长,不是一位学者——虽然他似乎自命为学者,也是一位皇家教授。作为校长和教科书的编写者,他致力于简化(但并不是无条件地改变)记忆和规则的学习程序,这些记忆和规则是需要他的学生在学习“逻辑”时去完成的,而“逻辑”实际上是以虚饰的方式条理化了修辞学讨论。拉莫斯通过利用可移动类型的巫术进行他的简化(它被称为终南捷径),这种巫术使他能够生产“视觉抽象”。在这种可视的框架中——有点像今天在网球和篮球等体育项目比赛中使用的图表支架——拉莫斯感到人们(他自己更优越)能够处理所有的知识。这一图表可以把很多学科分为下级分支部分并再分为更小的分支学科。我们的体育图表从很多变为一个(最终的胜利者),而拉莫斯的知识图表从一般的唯一到具体的多个。拉莫斯图表延续了下来,它是第一次(1576年)在使教育秩序方法化或顺序化的意义上使用“课程”这一词语的。
通过这种方式对知识进行图表化处理,拉莫斯——出于对教学便利的兴趣——“把知识从对话中剥离”(Ong,1983/1958,前言)。现在,教学从“在对话中提出问题”转变为“为了让学生吸收而散播知识”。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是“教学方法”,它通过“从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到基础的单元部分安排各种事情”而“把在知识的绝对顺序中处于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其次的放在第二位,依次类推下去。(Ramus,1569,edition of the Dialectic,in Ong,第245、248页)。在“方法作为效果的程序”这一概念上,他与跟随于其后的泰罗和泰勒一样,似乎从未认识到,他所崇敬的知识的绝对顺序其实是他的知识的顺序——正如泰罗的“标准”或泰勒的“哲学的筛子”一样都是私人化的概念。
在他的学位论文“重新思考课程”的第二章中,斯蒂分·特瑞克(Stephen Triche)追踪了学校中的方法化运动,从拉莫斯的“视觉抽象”经由弗朗克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素养经验”和夸美纽斯(J.A.Comenius)的“教养”,到笛卡尔的“正确推行理性的方法”,再到英国和美国清教徒关于“简单秩序”的概念,他考察了方法化运动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一运动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在该过程中,教学逐渐具有了从未有过的教养色彩,并失去了探险、刺激、对话性或实验性。其造成的冲击是教科书式的学校材料大量出现,它用于以有效的方式提供给8到16岁的儿童并让其掌握。这就是我们从先辈们那里所继承的传统的教学。
杜威的回答
传统的教学独白多于互动,说教多于对话,这极大地困扰着杜威。但菲力普·杰克逊(PhilipJackson,1998,第4章)指出,杜威本人在教学中实践着对话(除了在演讲中带有修辞色彩以外),这一点是与实际不相符的。杜威的烦恼是教育学上的,但不是厌烦实践教育学,他所厌烦的更多的是一种植根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教育学:它以条理化的方法去教学,剥夺了学习者的经验,使学习者远离学习过程。对杜威来说,这种把教学与学习二元分离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在杜威看来,没有一方屈从于另一方,只有双方进行彼此的互动。有关这种隔离,杜威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儿童和课程(学习者和教学)不是以绝对的分离状态存在的,而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每一个因素在与另一个因素的联系中获得意义。众所周知,对于杜威,知识并非独立于人类的经验而存在,而是人类在反思其经验、努力解决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遇到的问题时的副产品。他认为科学并非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般的程式,而是活生生的实验。杜威相信,认知从积极的反思中来,他把公开的、能够观察到的内在于科学的行动看作是方法。他感觉到这种方法把我们的认识论、我们认知的方式从中世纪的程式中挽救出来。他说:
科学的(新)方法就是实验,就是(需要在)审议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由此,经验告别了经验主义,变成了实验……通过它,行为(人类活动)得以拥有丰富的内涵。
奥根在《拉莫斯、方法和对话的衰退》的最后一章中认为,当中世纪和后中世纪时代的认知途径从听觉和口头转变为文献——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发明——真理也从个人化转向文本化。真理的特征变成了去个人化、抽象化和符号化。形式主义的逻辑取代了修辞及其一切激情。文字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理性成为公式。与这种趋势相对照,杜威希望他的哲学(其实是他的整个世界观)不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他的“逻辑”是一种有正当理由的主张——而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之上的。正如我早就引证的,也相信这种普遍经验在其自身内部能够产生出方法,这种方法将为自身确定方向并将创造内在的判断标准和价值标准。
杜威相信,经验——其实是经验情境——能够通过把行为与反思整合起来而发展自身。杜威把行为的经验称为基础形式,把反思的经验称为第二种形式。正是情绪性的行为和反思的智慧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使杜威振奋不已。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很多篇幅(尤其在第11章,第150页和第12章,第163页)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当然,在《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中提出了他著名经验操作理论(1963/1938,第2章)。然而,詹姆斯·加里森(Jams,Garrison,1997)和菲力普·杰克逊(1998)——他们领导着“新杜威学派”的复兴主义者——指出,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Arts as Experience,1934)中对“经验”的概念进行了最好的阐发。在本书中有一章内容阐述经验的转变,或把我们每天的活动——被反思、引导和发展的活动变成一种经验。
这一章一开始就声称,在普通的意义上,经验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活动、事件、发生的事情和“痛楚”(sufferings)。用“痛楚”这一个词是很有趣的;当他想超越一种未成型的、无意识的、具有审美质量的经验时,杜威会回到这一点上来。这就是他所定义的经验。经验的精神意义——充满着生活的动力学的活力——即审美,它“包含了痛楚,它是与所获得的整个感知相一致的、实际上也是该感知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审美的质量把经验还给了生活,它“使经验变得彻底和统一而丰满起来”。几页后,杜威继续发展了审美经验的主题,认为“进行阶段的经验”不仅包括痛楚,而且还包括放弃——权利的放弃和经验驱使的无奈:
要使我们沉浸于某一学科,我们首先要投入其中。(我们需要让它)震撼我们……把我们击倒(因为我们已经很激情地沉醉于其中)。(但是就在这一时刻, 当我们就要被震撼时)我们必须聚集力量,把它作为回应我们的关键从而获得(经验)。
拉莫斯和杜威两个人的血脉中流淌的血液是如何地不同,头脑中内在的精神又是何等地相异!对于拉莫斯,知识在学生接触到之前可以普遍地(由他来)进行编撰,学习是与如何“清晰地”呈现已编撰的知识相联系的。对于杜威,知识是一种结果,实际上是一种副产品,是个体的行为及对个人经验的反思的副产品。学习发生于反思性互动:通过反思,人们(学生和教师)进行学习,并学会如何去学习。拉莫斯留给我们的馈赠是需要克服的,而杜威留给我们的馈赠则是一种挑战:我们如何去实现它。
一种方法?
方法的概念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的方法(拉丁语为methodus)。在教育上,这种方法与有序的学习相联系——通过那些外部的无中介的学习程序——以一种连续的、单一的方式进行联系。这一传统从今天流行的行为取向的加工程序中全方位地铺展开来,可追溯到加琳(Calen)的对心理学家的训练。在这种框架下,教学基本上是把一种既定的秩序强加到学习者的身上。最著名的老师、最应该为这种框架和散布这种概念负责的是拉莫斯,他不仅规定秩序、绘制图表并使青少年需要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序列化,而且还详细规定了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时间与方式。(他吹嘘到,十五岁的青少年在离开他的学校之前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训练)。在很多方面拉莫斯似乎是泰罗的先辈:都强烈惩罚那些没有精确地根据他们所预先描述的方式去做的人,都是熟练的修辞家,用泰罗的话来说,都是“人的操纵者”。在那些批判它的人看来,这一方法化概念可以看作是操纵的、强迫的、封闭的、破坏想象力的、非人道主义的、简单的,还有,用杜威的话来说,是“令人悲伤的秩序”。在那些支持它的人看来,这一方法化概念被看作是科学的、有效率的、具有社会生产力的——暗示着可以用“理性”这个词来表达其意义,如果不是直接声明的话。
对于方法是什么,杜威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同样对于科学、教学、学习、知识、效率、道德社会等的概念他的观点也相去甚远;但这里我仅仅针对方法进行阐述。对于杜威,方法是一种程序;但这一程序并不同于拉莫斯到泰罗所认为的程序,杜威把方法看作是转变(transformation)而不是传递(transmission)。因此,他认为学习者的经验并非从建立在强迫/教学基础之上的“逻辑”知识开始。对杜威来说,教学并非强迫性的说教,而是集体性[他经常用“共有(conjoint)”这个词]的发展。未成年人的经验通过与同伴和成年人的互动而发展、生长和转变。
经验的发展并不是一个不容分辨的过程;其方法(反省思维的方法)既是开放的又是直接的。它是开放的,因为没有呈现结局,唯一的结局就是生长,一种没有结局的结局。它是直接的,因为情境朝向自身的丰富性方向发展。[复杂理论已经出现(Kauffman,1993,1995),杜威第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而这不是初次声明。]对于一个指导性的情境,在或然性上需丰富些(但不要太丰富),并充满可能性(但不要过满)。在情境中我们作为相互作用者,需要“投入”其中——审美地、精神饱满地接近它——积极寻找存在于情境中的可能性。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A.N.Whitehead)“把思想抛入每一种可能性的集合”的警告在这里是很合适的。现在,教学越来越不是一个高效传递的过程,更是一个与其他人一起在学习之路上旅行的过程和个人转变的过程。
一个教学信条
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反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并没有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而是,教师要求学生把对权威的怀疑悬置起来,要求学生跟教师一起加入到他们所经验的事情中去。教师答应帮助学生去理解所给予的建议的意义,对学生的对抗作出准备,与学生一起反思,达到心照不宣的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