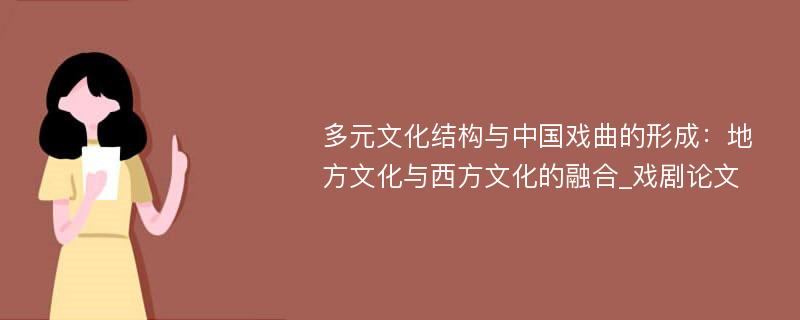
多重文化结构与中国戏曲的形成:本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文化论文,文化与论文,本土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夏大地,以千姿百态的山水、风土人情,孕育了古老的中国戏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戏。从艺术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史进行一番扫描,也许会给我们一点新的启示。
戏剧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既有时间上的承接性和延续性,又有空间上的连绵性与伸展性。每一种戏剧文化,都占据着特定的空间,各种戏剧文化之间,都有着迥然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地域差异。细加推究,便可以看到各个特定地域戏剧的形成,都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独特关系的综合结果。这一客观规律,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戏曲形成的问题时,不能不关注不同的特定环境对戏曲的形成之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人的活动形态,即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国的辽阔广大决定了中国各个地域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和联系,因此,中国戏曲的形成远非一时一地文化积淀的结果,它是在广袤土地的不同地域彼此呼应,先后出生的。具体的说,中国戏曲的形成,是华夏本土文化(包括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与西域文化(包括古代西域本地各族文化与外来的印度文化等)多重融合的结果。
中国本土文化大体以长江为界,区分出北方与南方的不同地域特征。在不同地域中产生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戏剧的形成自然产生不同的影响。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夏、商、周、秦、汉、唐等朝代均崛起于这个摇篮之中。这些朝代屡次建都,迁都,人们都是围绕着黄河和它的最大的支流渭河在移动。以这两条母亲的水系为轴心线组成了一个宽阔的文化带。这是由古老的都城长安、洛阳、开封等为中心组成的文化带,是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核心。包括齐、鲁、秦、晋文化在内的这一文化带由于经济、政治的原因,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等原因,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史书记叙这一地域的文学艺术时,就将它与南方作过一些对比,认为“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定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32)这里指出的河朔之文深于理,当与春秋以降北方推崇儒学的史官文化和人文风习有关。这种推崇的结果,造成北方人生活的“泛戏剧化”现象,反而推迟了戏剧在北方的形成。不过,在北方民间,前戏剧因素的幼小生命并未被完全窒息,它们在一些农村迎神赛社的活动中被保存了下来。而这幼小的生命,也许正是后来长成的参天大树——元代的杂剧的胚芽。质朴,沉稳,凝重,井然有序,这种北方气质浸入民间迎神赛社的社火活动之中。及至唐代和宋金,这种洋溢着浓郁的北方民间人文气息的活动发展到了巅峰状态。据宋人记载,所谓赛神活动仍然依循先秦北地的习惯:“今人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因相与饮乐。”(33)金代“每当季春中休前二日张乐祀神,远近之人不期而会。居街坊者倾市而来,处田里者舍农而至,肩摩踵接,赛于庙下。”(34)1985年秋在山西潞城县崇道乡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是世代相传的关于晋地迎神赛社这古老的祭祀仪式的程序规定。这本抄写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的有关赛社仪式的程序规定,实际上承袭的采金遗制。中心部分内容是按二十八宿顺序,分排出迎神赛社值日的次序。其中,有关值日的装扮、食性、分野、进行时所奏宫调曲牌详细规定,还有关于祭祀仪式、供馔次序以及献演内容(包括音乐、舞蹈、队戏、院本和杂剧等等)的规定。所列剧目繁多,要求具体而严格。从这本《礼节传簿》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自自成体系的北方民间祭祀仪式模式,笼罩在这个仪式模之上的,是北方地域特定的人文地理氛围。这种氛围,孕育了北方民间祭祀仪式,也孕育了植根于这仪式之中的北杂剧。北杂剧表现出来的从文学语言到整体风格的质朴,结构布局的严格整齐划一模式及其凝重感等等,均可以在以山西、河北等地农村社火仪式中的赛戏为代表的民间戏剧中,找到最好的印记。
从漫天雪花的北方,来到遍野桃花的南方,其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是那样的明显。尽管在上古时期,荆楚乃蛮荒之地,但就狭义的长江以南,即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吴、越来说,其自然条件对于农业发展的优长之处,远非朔风怒号的北方可比。自魏晋到隋唐宋金,天暖雨润的南方(包括荆楚、吴越、巴蜀以及福建广东沿海),孕育了清绮、芊秾、瑰丽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鲜明区别于北方的人文地理环境。特异的南方文化氛围使得这个地域的民俗与北方地域民俗在细密的相互联系中又显出各自不同的特性。唐代开始,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财政几乎全靠江南,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气侯温和宜人,山水秀色可餐,物产繁盛富庶,难怪唐代诗人一唱三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韦庄)到了宋代,经济愈益繁荣,文见日趋鼎盛。当时,“七闽二渐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盖饶之为洲,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者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者为辱。”(35)如此人文风气,自然为人才的脱颖与戏曲的抽芽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若细加考察,同为南方,荆楚、吴越、滇黔、巴蜀以及闽渐沿海在自然地理和人文理环境方面多少有些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南方(尤其是荆楚滇黔巴蜀)因山陵起伏,雨水偏多,植物繁茂,致使山水蒙上了一层既带几分娇艳绚丽又带几分幽冥诡奇的色彩。这种自然环境极易使古代南方人的心萌生神秘的鬼神观念。不仅荆楚之人信鬼及巫,巴蜀吴越及福建广东沿海亦如此,而滇黔尤甚,与北方民间傩仪的质朴、严整、沉稳风格相比,南方民间傩仪似更弥漫着一种热烈、浪漫、奇诡的气氛。这种傩仪的风格,以《九歌》和滇黔少数民族傩文化最为典型。至唐代以后,以娱人为目的民间傩歌傩舞傩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傩仪中独立出来,这一点,从明人的《唐人勾栏图》一诗中可以寻到某些迹象:“朱衣粉裤纷相剧,文身倛面森前傩”(36)。傩仪虽依然还是人们驱除疫鬼的祭祀仪式,傩仪中的傩歌舞和傩戏却同时又进入了唐人的“勾栏”,成为了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专供人们娱乐观赏。傩仪和傩戏在宋代的南方,似乎较北方更为兴盛,尤其是在富庶的杭州、温州、漳州等地。仅以福建漳州为例,就可以想见当时闽浙一带民间以祭祀活动驱灾逐鬼,娱神娱人的热烈景象:“有城邑至村墟,淫鬼之各有迎神之礼,随月选为迎神之会。”“一庙之迎,动以数十象,群舆于街中。且黄且伞,龙其辇,(原字不清)其座。又装御。直班以导于前,僭拟逾越,恬不为怪,四境闻风鼓动。复为优戏队相胜以应之,人各全身新制度帛金翠,务以悦神。或阴策其马而纵之,谓之神走马;或阴驱(原字不清)而奔之,谓之神走(原字不清)。”(37)这两段资料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关于“复为优戏队相胜……务以悦神”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傩戏已相当独立且具相当规模。总之,在北方,在南方,中国戏曲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已分别孕育成熟,它在焦渴地待待着破土而出的机缘。这个机缘终于在宋代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到来了。它的到来的总体背景,是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这次南移给中国南、北方文化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强烈也最广泛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前戏剧便在这碰撞和融合中跃上了中国戏曲的台阶。北方文化的优越的区位条件,大约保持到隋代之前便开始丧失。“安史之乱”的动地鼙鼓,则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推进惨痛的浩动之中。政局混乱,外族入侵,战事频仍,加之黄河改道,水旱连年,居民流陡,田园荒芜。至唐末五代时期,虽然金国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整个北方文化环境已日趋恶劣。“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这仓皇辞庙之日,便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伊始之时。随着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南方的浙江、福建、江苏、湖北、四川,包括北宋杂剧在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也从北方来到了风光明媚的江南。于是,以杭州、苏州、扬州、温州、泉州等和以成都为中心的文化带,取代了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中心的文化带而成为南方以至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在这种艺人集中、百艺荟萃、齐聚江南的情况下,中国戏剧的成熟形式之一——南戏呱呱坠地了。(38)先是在温州、在泉州,接着在杭州、在苏州,一种比较成熟的戏曲形式,逐渐在由傩祭仪式发展而来的民间社会活动中热烈地凝聚。这是南方民间傩戏与北方民间傩戏的凝聚,是南方与北方民间说唱的凝聚,是南北两方歌舞和“百戏”的凝聚。这是凝聚,同时也是诞生——中国戏曲的一个精彩的、响亮的诞生。
从历史背景的深处传来的阵阵悠远、清脆的驼铃,伴和着充满异域情调的音乐,把我们的目光牵向辽阔国土的茫茫西陲——那里还有一片与中国戏曲形成的历史密切相关的神秘的土地。那片土地在历史的大波中与当时(秦汉至隋唐宋)的中国本土发生文化的冲荡,使它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西域一词,有两种含义。广而言之,古代西域泛指中亚、西亚和西南亚等地域,即我国新疆、中亚细亚、印度半岛以至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亚洲腹地的葱岭以东到我国敦煌地区的玉门关、阳关一带。无论在中国、亚洲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西域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两千多年之前,汉武帝的使臣张骞率队凿通由中国本土连接西域多国的道路。从此,一条横贯东半球,飘荡在中国、印度以至希腊、埃及之间的五彩的“丝绸之路”,便将亚洲、非洲、欧洲人民之间对于友谊和未来的憧憬联结了起来。成百上千峰的沙漠之舟——骆驼,将古老的罗马、印度文化驮着,由这条路走向古老的中国;又将古老的中国文化驮着,由这条路走向古老的罗马、印度。正是这种巨大的交流,使得西域文化,尤其是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狭义的西域的文化,具备了由多种文化交融的而形成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特征。
岁月的流转,将佛教文化冲积成为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的主要色调。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创立于古印度的佛教,从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经过公元二世纪贵霜王迦腻色迦王时期,陆续向国外传播。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随着丝绸之路上征旅往还的日趋频繁,印度佛教和古代印度佛教艺术开始向沿途各地渗透。史书记载,公元一世纪,当大月氏人建立贵霜王朝时,佛教便开始传进新疆地区。到公元二世纪迦腻色迦王时,在该地区各国中广泛流传开来。这样,经过西域地区,以古代印度佛教文化艺术为主,古代的阿旃陁、犍陀罗、萨珊王朝,以至古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便从容流进当时的中国本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艺术逐渐实现不同程度的融汇。这种气势磅礴的大融汇,构成了隋唐五代以至宋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戏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说到以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为主的西域文化对中国戏曲的形成的影响,最明显者,恐怕要推佛教的讲经。为了使僧众和老百姓了解和掌握佛教经典的要义,从而在宗教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思想阵地并聚敛钱财,佛教要进行讲经的活动。六朝以后,中国佛教就有斋讲,即通过转读(咏经)、梵呗(歌赞)、唱导(说唱教导)等方式来讲演佛经。据日本僧人圆珍记述,“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之,僧被官责)……”(39)。可见,唐代讲经分为僧讲(以讲解经文为主,讲给出家人听)俗讲(以讲佛经和市俗故事为主,讲给市俗男女听)。当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俗讲日,湖上少鱼船”。(40)这种往往是韵文与散文相结合的形式的俗讲,和变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变文,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易主体,即将佛经的故事和文字改变成通俗的口语化的故事。这里,所谓“变”,还含有与佛教之变相通的奇异之变、魔变的意思。因此,变文,又可以理解为讲唱奇异的故事的文体。向上连接着俗讲的变文,又向下连接着诸宫调以至戏曲。这是可以从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变文写本中得到证实的。敦煌变文与戏曲的联系,首先表现在途述方式和文体上。变文都是围绕一个完整的故事(宗教的咸世俗的)而写成的半白话的叙事文。在形式上,多半是散文体或散文与七言为主的句式的韵文相同,与后来出现的诸宫调以及戏曲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妨看作是变文的边说边唱的讲唱方式对诸宫调和戏曲的影响。或者说中国戏曲文体的叙述性特征的形成是受到变文影响(当然不是唯一的影响)的结果。向达先生在四十年代曾经指出:“至于由诸宫调演为剧本杂剧,自应溯源于唐代大曲,顾与俗讲亦不无些许瓜葛。……而与讲史书说经说参请以及杂剧有若干关系之俗讲,其中如变文之属,虽似因袭清商旧乐,不能必其出自西域,而乃大盛于唐代寺院,受象教之孕育,用有后来之盛。此为中国俗文学史上一有趣之现象,其故可深长思之也。”(41)他已经看到了变文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可惜当年这些话并未引起戏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敦煌变文与戏曲的联系,更表现在题材内容方面。从目前一般确认的十多篇敦煌写本变文中(42),我们可以找到其故事内容与后来的戏曲的情节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其中最明显的,是《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和《王昭君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的故事源于佛教经典,多种经典都涉及目连故事。其中,在中国流传较早的是由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唐五代时期,根据《佛说盂兰盆经》、《佛说目连所问佛》等经文敷衍的讲唱变文便出现了好多种,故事情节也渐趋完整。北宋崇宁至靖康(1102-1127年)间,在都城汴京,每年自农历七月八日至十五日这八天里,便连演目连救母的杂剧(43)。因此,有人认为,目连救母杂剧比南戏出现得更早。目连救母变文对戏曲的影响极大。自北宋以降八百余年中,关于目连救母题材的剧作常演不衰。元代有《目连入冥杂剧》、《行孝道目连救母杂剧》,明代有《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代有《劝善金科》,规模从四折发展到三本一百零二出和十本二百四十出之大。在民间,更形成一种目连戏。目连救母题材的戏曲广泛生存于安徽、湖南、浙江、江西、福建、四川等省的地方戏曲中,成为许多地方戏的戏母、戏娘、戏祖(44)。《王昭君变文》在唐代俗讲中相当盛行,“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45)。可见,当时连地处偏远的四川也有讲唱。戏曲中,最早搬上舞台的王昭君故事,是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汉元帝哭昭君》(已佚),接着又有马致远的《汉宫秋》。明清两代,昭君戏更为流行,出现了无名氏的《和戎记》、周文泉的《琵琶语》、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尤侗的《吊琵琶》、薛旦的《昭君梦》以及仅存残本的《宁胡记》,《青冢记》、《昭君》等。从上述情况看来,变文对中国戏曲的形成产生过很大影响。变文的出现,给中国前戏剧带来了情节完整的故事、散韵相间的文体和散文体叙事说白,使它获得了中国戏曲的某些基本特征。美国学者维克多·H·麦尔将变文视作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转折点(46),他的这一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也许,舞蹈和音乐,更是一把能够打开中国戏曲的形成历史的神秘之门的钥匙。而历史上的西域各国,正是热情奔放的歌舞之乡。自汉代以降,印度佛教音乐、印度歌舞以至罗马的某些歌舞经过中国新疆地区这个中继站,辗转传入中国北方和南方,与中国的乐舞融合,对综合音乐、舞蹈、表演、杂技等于一体的中国戏曲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舞蹈而言,在胸襟开阔的唐人那里,对于外来舞蹈,更是如此。隋唐的中国本土歌舞,可谓盛极一时,举凡雅乐、俗乐、散乐中,一部分系中国本土的宫廷舞和民间乐舞,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是从西域各国各地流传而来。而在西域地区,受印度、中亚细亚各国以及中国本土的音乐舞蹈影响而形成的西域音乐舞蹈,则空前繁盛。与后来的诸宫调和杂剧有着血缘关系的唐代大曲,便是一种胡乐与唐乐的组合。如隋唐之初的九部侍乐大曲,其中两部为江南旧乐,而另外七部均系胡乐,即西域各国流入的音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天竺乐。在音乐方面对戏曲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的,恐怕首先要数古龟兹(今新疆库车)乐人苏祈婆。他与郑泽等人反复研究,用西域琵琶七调校订汉乐七音,最后演变成隋唐燕乐二十八调。从此,宫调音乐便成为诸宫调音乐始祖,并成为戏曲唱腔中的宫调的源头。在唐代教坊乐舞中,也有一些来自西域各国。如自今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和今中亚细亚的塔什干分别传入中国本土的《胡旋》舞和《胡腾》舞,自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细亚传入中国本土《浑脱》(即《苏幕遮》),以及《凉州》、《兰陵王》、《柘枝》、《阿连》、《剑器》、《苏合香》、《甘州》、《达摩支》等等,原来都是异域他乡的劲歌健舞或轻歌曼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歌舞中某些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这些歌舞表演给尚躁动于民族文化母腹之中的中国戏曲输入了相当丰富的营养,使即将问世的中国戏曲在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和高度技巧化方面独具特色。由歌舞《胡腾》发展而来的《西凉使》,表演的是狮子随二位西域胡人迁居中国本土,胡人思念故乡,但由于凉州失陷,归路阻绝,胡人十分忧伤,不禁对狮啼泣。这时,狮子也通人情,向人发出同感,西望而哀,伤心而吼。整个歌舞表演中由二人扮演狮子,二人扮胡儿,表情丰富真挚,舞蹈动作感人,在唐代颇为观众喜爱。“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47)白居易的诗句,生动地记录了演出效果。这段精彩的歌舞表演,不仅在唐代的西域和中国本土广为演出,而且一直传演至十七世纪的明代。在明代湖北圻州民间的傩仪中,有人还见到过《西凉使》的演出(48)。当西域文化踏着奔放的舞步飘然移向中国本土时,中国本土文化也同时向西域文化投去初恋的目光——中国戏曲正是这种交流的产物,这种融合的结晶。
我们不能不以无法抑制的兴奋,轻轻揭开罩在西域古剧那俏丽脸庞上的面纱。于是,我们看到了被沉沉黄沙和漫漫岁月掩藏了多少年的古老的戏剧的雏型:《舍利弗传》(残卷)、吐火罗文A(古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等。(49)
当梵剧在印度渐渐走向衰落而中国戏曲尚未呱呱坠地的时候,在古代的西域却生气勃勃地存活着一种象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这样的戏剧的雏型,确实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戏剧文化现象。大约写于公元八至十世纪的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所讲述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孤绝山说法,要召见跋多利婆罗门,但跋多利婆罗门年迈多病,便委托聪明的弟子弥勒代替他去见佛。弥勒与十六位男子一起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赶到王舍城鹫头山见到了佛,并被收纳为佛弟子。然而,正准备继承佛位的弥勒却因触犯天条,被降生到翅头末城,后来在龙华菩提树下得以正觉,然后广施佛法,带着该国国王和自己的父母出家成道。从写本本身看,似乎是一种能讲唱也能扮演的带有文学色彩的古剧的雏型。据德国学者葛玛丽研究,唐宋时代在西域地区高昌,确有过原始戏剧的演唱活动:“在民间节日,如正月十五日(回鹘),善男信女云集寺院,他们进行忏悔、布施,为死去的亲人举行超渡,晚上听劝喻性的故事,或者欣赏演唱挂有连环画的有声有色的故事。讲唱人(可能由不同的人扮演不同角色)向人们演唱诸如《弥勒会见记》之类的原始剧本。”(50)原始佛教戏剧或西域古剧雏形的出现,生动地说明了奇谲、深妙、靡丽的印度佛教文化对西域文化和对中国戏曲的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就是这样在市俗文化与宫廷文化的交汇、本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其中包含着娱乐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渗透)的过程中,跳着,唱着,谈着,笑着来到了当时还相当无奈的世界上。它的问世,是那样的热闹而精彩,以至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听到从历史大峡谷中隐隐传来的回声。
(续本刊1994年第5期《多重文化结构与中国戏曲的形成:市俗文化与宫廷文化的交汇》一文)
责任编辑注:续前文请见本专题1994年第12期复印资料
注释:
(32)《北史》八十三《文苑传》序。
(33)高承:《事物纪元》卷八。
(34)《耀州三原县荆山神泉谷后土庙记》,载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五八。
(35)洪迈:《容斋四笔》。
(36)张宁:《方洲文集》卷六。
(37)陈淳:《上赵寺丞论淫视》,见《遗山集》。
(38)祝允明《猥谈》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刘念兹进一步提出:“南戏产生的地区,不仅在浙江一带,而且还有福建的一些地方。”参见《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29页。
(39)《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大正藏》卷五六。
(40)姚合:《赠常州院僧》,《全唐诗》卷四九七。
(41)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4页。
(42)敦煌写本中究竟有多少篇变文?学术界看法尚不一致。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有十四篇,国外学者则认为大约有十八到二十一篇,其中,标准的变文则只有七篇。
(43)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
(44)目连戏的形成和流传,实际上是宗教文化与娱乐文化的渗透过程。中国最早的剧场出现于寺庙,寺庙中的演出既为酬神,亦为娱人,这些现象,均与目连戏的历史有关。而剧本内容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戏曲音乐受到宗教音乐的濡染,在目连戏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部目连戏的历史,似可看作中国戏曲形成过程中宗教文化与娱乐文化的渗透过程的缩影。
(45)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全唐诗》卷七七四。
(46)参见《变文和戏剧及其他——敦煌通俗叙事文学》,《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6期。
(47)白居易:《新乐府·西凉传》。
(48)据明人顾景星《圻州志》所载,参见任半塘著《唐戏弄》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49页。
(49)对于各种写本的《弥勒会见记》,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专家认为它是代言体戏剧文学,一些专家则认为不是剧本,而只是叙事体说唱文学,另一些专家认为它是戏剧的雏型,一种过渡的形态。
(50)葛玛丽:《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1250)》,《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