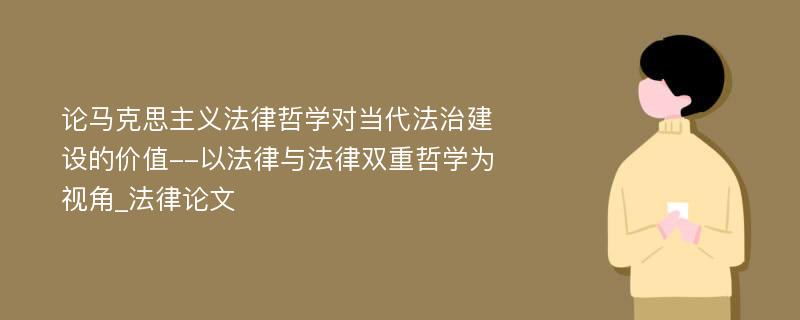
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当代法治建设的价值——以法与法律的二元哲学观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法治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12)05-0006-04
法哲学是人类社会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哲学指导和作用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理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通过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建构,不仅能实现“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的固有价值,而且为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深邃的法律思维。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经历了从早期的自由法律观到成熟时期的利益法律观的演变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法与法律相互区别的二元哲学观的基本线索。把人类社会应然的法与国家政权制定的法律进行理智的区别,并从理论上探索消除其二元对立的条件与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区别于剥削阶级法哲学的重要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不仅要运用马克思法哲学的人权自由观、公平正义观、劳动异化观、有限政府观等思想来推行宪政法治,还要破除迷信法律文本的固有思维,切实树立清醒、理智、客观的法律二元哲学观,并将其作为判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自由观对当代立法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坚持通过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权得到尊重、自由得到保障。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宣示的那样,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强调人权自由对国家立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提出了“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光辉论断。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自由观,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在这些论断和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当代立法必须坚持法律与人权自由观的高度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法与法律二元哲学观的警示下,理性审视中央立法、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的水准与趋势,实现社会需要的应然法与国家法的基本结合和高度统一,以充分发挥国家立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保证人民自由等方面的固有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二元哲学观是在对康德法律二元哲学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德法哲学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其原因不仅在于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三位人物都是康德法哲学的忠实信徒,即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老师腾巴赫、马克思未来的岳父维斯特华伦男爵,而且在于康德法哲学通过诉诸先验的逻辑解决了法的形而上学模式,使法在人的理念中完成了最完美的人性复归,康德法哲学所主张的在应然世界中进行发现的研究思路,为马克思法哲学世界观中法权对抗问题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渊源。但是,当认识到康德以先验为原则的法律二元观哲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在遭到现实的权威时却显得束手无策时,马克思即开始了在现实社会中研究法与法律二元对抗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历程。
在马克思二元法律观的指引下,要实现立法保障人权自由的价值,当代立法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对特定时期的国家立法的成败乃至国家的兴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是人民代表权的体现,国家应当而且必须克服私人利益而维护普遍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考察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法权对抗问题时,总结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位思想,即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对抗。国家本位强调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应当首先考虑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强调国家至上原则。而个人本位强调立法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没有边界,追求自由的最大化,利己主义、绝对自由自己、无政府主义,都是个人本位的典型代表[2]。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富强、繁荣,而且已经带领历史辉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依然形势严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国际竞争的实质与主体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每个国家的国民除了跟随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外,别无选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当今世界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两者关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下,当代中国的立法在处理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时,应当坚持国家意志优先的原则,即国家的整体性与权威性在立法过程中不容挑战。
中国今天已经实现了人民的当家做主,中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已经成为了确保人民自由的坚强后盾,坚持在立法中采取的国家意志优先原则,其本质也是坚持了人民整体自由的依法保障原则。当然,在保障立法过程中体现国家意志优先是有前提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法律二元观点,认真区别究竟哪些是真正的国家意志,哪些是特殊的利益群体以国家利益为名号,拉大旗做虎皮,滥用国家立法权,发生立法权的异化,从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当代立法中,如何正确地处理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关系,是社会实现真正和谐的重要命题,也是国家内部得以稳定的重要前提。依照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所主张的那样,社会应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当代立法的落脚点转回国内后,在处理公共权力的执行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方面,需要坚持两个原则,即在公民权利领域,坚持“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在公共权力方面,则坚持“法不授权皆禁止”的原则[3]。只有在立法中,牢牢坚持这两个原则,才能在一国之内的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定一个相对客观的分界线,使应然法与国家法的固有差距得以缩小。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观对通过法律手段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价值
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创立了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至上的异化理论,他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及其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是指在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主体自身产生而又反过来敌视和支配主体的异常现象,如工人同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贫困和毁灭是其劳动成果和生产财富的产物。认真解读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相应的各种异化社会现象,而且有助于我们通过法律手段公正解决诸多社会矛盾,进而实现社会的高效、廉洁、平等等正常秩序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观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权力异化的根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加上我们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社会权力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即权力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原本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的宗旨,反而成为了少数利益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即国家和社会权力异化为群体特权,权力的代表性和服务性异化为扩张性和掠夺性。在国家和社会权力异化的进程中,贪污、受贿、腐化也成为官员人性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实际上,在中国今天的腐败案件中,社会权力的异化、利益群体的权力寻租、官员人性的异化,构成了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其本质内容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观。
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观为我们采用法律手段反腐倡廉、从严治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观出发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我们的分配形式还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按需分配形式,按劳分配依然是我们今天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主要分配方式,即劳动依然是作为社会成员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谋生手段。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提倡人民群众自食其力、努力工作,通过劳动来赢得社会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社会报酬。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触目惊心,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逐缺乏成熟法制的公正监督。在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一些掌握社会权力的公务人员,在巨大社会财富的诱惑下,在一夜暴富观念的主导下,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顾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大搞权钱交易,成为了当今社会劳动异化的具体形式——权力异化与人性异化合二为一的始作俑者。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社会权力异化、人性异化的泛滥,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无情打击,否则,社会的公正、人民的权利,将无从谈起。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统治方式,应当在打击社会异化现象,反腐倡廉、严格治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基于中国今天的法律体系实际状况,我们所谈的法,是应当从广义上理解的,它既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以“行政法规”形式表现的法律,同时还包括地方人大、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通过法律手段来反腐倡廉、严格治官,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观的必然要求,同时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法律二元哲学的观点,坚持在通过法律手段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过程中,既要明确法律的打击对象,防止在对象上出现偏颇,又要明确“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构建以法律打击为主导,兼采道德引导、教化辅导、人性熏陶等多种方式,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模式。
法律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法律打击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法律二元哲学观告诉我们,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于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法律打击的对象是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是人在违法犯罪过程中的社会工具或者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对于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损害公民人身权利或者财产利益时,不能夸大《国家赔偿法》的作用和价值,应当实行严格责任、责任自负的原则,在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后,重视对因违法犯罪而引起国家赔偿的公务人员的追偿(追赔)力度,而不能使国家成为“冤大头”。此类司法实践中,公务人员因获罪而豁免其对国家的赔偿义务的情况应当逐渐消灭。另一方面,法律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过程中,必须反对株连原则,如检察机关在进行职务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应当切实保证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止“贾府抄家”、“浑水摸鱼”等法治进程中丑恶现象的出现。
法律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过程中,要遵循“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法治规律,力求建立全方位、体系化的廉政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二元法哲学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即是主张对法律的价值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过分迷信法律的思想,如《共产党宣言》即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二元法律观,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法与法律才能合二为一,对法与法律的错误观念才能消失。在中国当代社会,不仅因为广泛存在的法与法律依然二元对立的法律现象,而且还因为我国的法治进程充满许多不确定因素、是一种渐进式的法治发展之路,因此,在采用法律手段反腐倡廉、从严治官的过程中,还要构建以法律为核心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如廉政警示教育方法是一种极大震慑内心、效果很好的法制教育模式,应当常抓不懈;如从学生时代在广大中小学生普及反对官本位思想、反对特权主义、反对不劳而获、反对一夜暴富的教育,这是构建一个公正、廉洁、自律社会的必经程序和先决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对公民社会习惯权利保护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大特征,即是将利益哲学观与法律二元哲学观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从而鲜明地展示了法律的利益色彩。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利益具有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特点,它只考虑自己[4]。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即“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利益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种,私人利益是指体现单个社会成员或者极少数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公共利益才是代表社会整体意志和关系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利益。法律代表利益,法律体现利益,这是法律与生俱来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法律的这个特征,相反,马克思对法律的这个特征十分重视,并肯定了其在社会秩序维护、社会争端解决方面的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仅仅体现和代表个人和社会少数群体的法律,即代表私人利益的法律。马克思对假借法律名义、体现少数利益的法律行为极为愤怒,并在其诸多著作中进行了坚决的抨击。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认为,私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难道无视法律(本能)的东西能够立法吗?在这些论述中,实际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法思想的尊重,坚持了“恶法非法”的朴素观点,坚持了法与法律不可混淆的法律二元哲学观。在谈到私人利益立法的前景时,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这种“法律”是没有前途的,是会被历史所抛弃的,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所断言的那样:“私人利益并不会因为人们把它抬上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
马克思主义要求立法者应当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也使法律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法律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法律必须重视对社会习惯权利的保护。实际上,重视对社会习惯权利,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习惯权利的保护,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资产阶级法哲学的重要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并应当成为解决社会诸多矛盾的指导性意见。社会习惯利益,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如拾荒者对其捡拾所得物品的所有权,不动产使用者对该不动产的占有权,房屋的承租人享有的租住房屋“买卖不破租赁”习惯保护,商事交易中基于对方缔约过失而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相邻人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而享有的正常同行、获得光照、引水通电的习惯权利,公民对不属于国家专有的自然资源(能源)的长期使用权。
社会习惯权利之所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其原因不仅在于上文所叙述的那样,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更重要在于,社会习惯权利和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息息相关的联系,而不会因为该社会成员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大的区别,就好像我们买卖物品一样,今天我们享受了买方市场的好处,说不定明天我们就会处在卖方的尴尬地位上。也许有人可以说,他(她)一辈子不会与刑法打交道,因为他既不会成为犯罪嫌疑人,也基本上不会成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她)不会与社会习惯权利打交道,因为拒绝与社会习惯权利打交道,就意味着个人的吃、穿、住、行、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难以正常进行。一句话,社会习惯权利的社会成员绝对参与性决定了其公共利益范畴的绝对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观点,要实现法与法律的融合,达到法治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就应当尊重社会习惯的公共利益特性,在推行当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上,注重对社会习惯权利的保护。笔者之所以颇费笔墨地论述社会习惯权利的表现形式多样性与公共利益属性,还因为在社会实际中,往往社会习惯权利并没有获得国家法律体系的明确保护,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社会习惯权利成为了国家法律体系的打击范畴。2012年2月,发生在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的“乌木案”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习惯权利保护的艰难性与紧迫性。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闲逛时发现了埋在地下的楠木乌木,而市场上该种品相的乌木价值不菲,每立方的价格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正当吴高亮以准百万富翁的身份兴奋地开始挖掘乌木时,彭州市通济镇政府责令其停工,随后该镇政府耗资百万组织挖掘力量、修建专用道路,将市值数百万的七根乌木挖出后全部运回了镇政府[5]。
通济镇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强烈质疑,而且该镇政府也自嘲为“吃了回夹生饭”。实际上,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习惯权利被侵犯的案件。首先,乌木并不是矿藏,即不能像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等物品那样,属于国家矿藏资源的保护范畴;其次,乌木并非人为的埋藏、隐藏之物,即不属于《民法通则》第79条所规定的那样:是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既然国家无法从法律层面证明其对乌木的所有权,就应当还原其社会习惯权利属性,像拾荒者对其拾荒所得的财产一样,由发现人取得其所有权。国家通过法治,对社会习惯权利进行充分的保护,是最能增强国家权威、赢得人民尊重的方式。实际上,在社会习惯权利属性上,价值百万的乌木和价值微薄的垃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国家如果弃垃圾于不顾而热衷于将乌木宣示为国家所有,所得到的,是与民争利的不尽人言,所丧失的,必将是最为宝贵的国家公信力。
在此文即将修改完成的时候,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关地方立法的新闻。2012年6月14日,某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个人或者企业今后在该省境内探测获得的风能和太阳能由该省享有所有权。该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引起社会民众与业内专家的众说纷纭。但依笔者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法规属于越权立法行为的产物。因为根据《立法法》,涉及国家自然资源、能源的所有权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在于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会到社会法治进程中,对社会习惯利益保护的紧迫性,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指导法治进程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