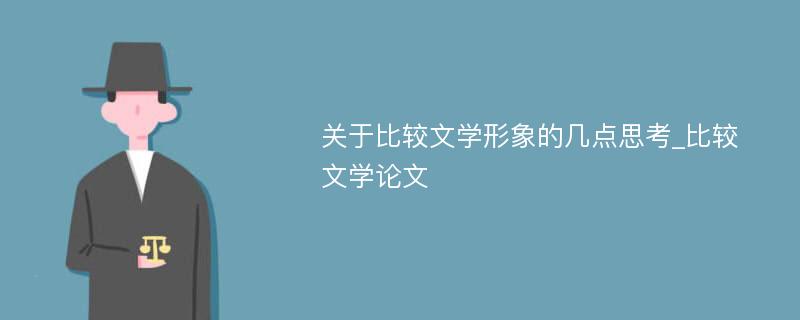
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1999)03—0069—05
一
形象学(imagologie)从比较文学领域中萌芽、壮大,现在的影响遍及整个文学和文化研究,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对人文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1929年,我国著名作家、学者郑振铎写过一篇叫《西方人所见的东方》的文章,提到英国的一份杂志议论中国的事情说,慈禧的墓在上海附近。杂志还刊登了一幅中国军阀的照片,相貌凶恶,下面却注明,此乃中国总统孙中山。郑振铎批评西方人对东方形象的歪曲和夸饰,他感慨:“东方,实在离开他们(西方人——引者注)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郑振铎写这篇文章的理论背景,仅从题目看,是典型的形象学题目。但总体而言,现代学界对形象学是隔膜的。近几年不同了,经过孟华等学者的介绍,形象学逐渐为中国所了解,它对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形象学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但它并不要求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求证这些形象像还是不像;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作者对他者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形象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异国异族神话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形象学脱胎于影响研究。传统的影响研究已经包含了一些形象学的因子,如在证明B国文学受A国文学影响时,会引述B国作家对A国文学、文化的看法和议论。但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影响和接受的“事实”存在,以考据为中心,目的是挖掘文学继承和创新的资源及其关系。形象学基本摆脱了文化、文学交往中“事实”的羁绊[2], 从而把“影响”和“接受”引申、落实到文学文本中不同文化面对面的冲突和对话上来。
法国是形象学的诞生地。早期有巴尔登斯伯格、让—玛丽·卡雷、基亚等,为形象学大声呼吁并有出色的实践,近晚又有莫哈和巴柔等在形象学学科史及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早期美国学派以主张平行研究著称,他们对法国学派重视的影响研究颇有微辞,这也连带造成他们不能正视形象学的创新意义。韦勒克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比较文学的危机》中说:“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作法也很难使人信服。”[3]他认为形象学道路与过去的影响研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充其量只是在狭窄的意义上增加一些特别的内容。但形象学没有在批评面前止步,反而获得了长足进展,包括在美国。
形象学的当代发展能够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美国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解剖了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和形象学在精神上都是相通的。受福柯的影响,萨义德把东方主义看成一种话语方式,指出欧洲在生产东方主义知识的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地位。同时,东方作为欧洲的近邻,最大、最富饶、最古老的殖民地,广泛、频繁出现的关于他者的想象,也帮助欧洲(或者说西方)确立了与其形成对照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意象、观念的基本成分[4]。
形象学同样能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把重视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文化的日记、书信、故事的研究看成“比较文学最近一些年最重要的变化”,而且认为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富成果的领域”[5]。支持她的论断的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她在《比较文学》一书中,研究了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和想象,以及这种隐喻和想象背后潜藏的种族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例如欧洲文化史上从来就有南方与北方的二元对立,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对立。北方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南方(如土耳其)是美艳的、肉感的。这种对异文化的成见、误解在一代代欧洲人的记忆中保存着,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她的论述对萨义德的理论提出挑战:欧洲从来不是单一文化统一体,也就不是东方主义的必然承载者,至少女性游记作家的著作“完全不能纳入东方主义的框架”[5]。
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异国异族现象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形象学的专利了。“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我觉得这是好事,也就像没有人能给比较文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来不会怀疑比较文学的价值一样,对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不管它属于什么,它正在改变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面貌。
二
文学理论把形象定义为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作家根据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集中、概括、创造出来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具体可感的人生图画。而形象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形象的学问,它所指的形象与文学理论所言的形象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以下作几点说明。
形象学面对的形象首先是异国异族形象,其覆盖范围自然要比文艺理论所讨论的形象小得多;再就是创造者自我民族的形象,它隐藏在异国异族形象背后,但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起决定作用;一般文艺理论把形象看成是作家个人艺术独创性的结晶,它的研究重点也在这里,而形象学研究中,作家充其量只被看成媒介,研究的重点是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只把形象学的对象局限在人物形象上,显然是不够的。
异国异族形象,虽经作家之手创造,但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只充当一个媒介。法国学者把这种在“他者”形象创造中起支配作用的,来自其所属社会的影响源称为“社会整体想象物”,认为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都受制于各自的“社会整体想象物”。比如研究吉卜林笔下的印度,康拉德笔下的刚果,罗伯·格里耶和加缪笔下的非洲等,都不能忽略当时的殖民主义侵略、发现新大陆、探险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作家对异域的想象,也与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观念息息相关。
法国学者认为,社会整体想象物并不是统一的,它有认同作用和颠覆作用这两种力,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我们说某一作家笔下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意识形态化的,意思是指作家在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国,对异国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国,向意识形态所竭力支持的本国社会秩序质疑并将其颠覆时,这样的异国形象叫乌托邦。其实对大多数作家,认同和颠覆都是相对的,很难截然分开。
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关系也一直受到形象学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因为作家在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导致对自我民族的对照和透视。正如胡戈·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6]他者形象生成时,一定会伴生出一个自我形象,二者是孪生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者形象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别人,也照见了自己。文本中的自我形象,并不仅限于自我民族的人物,还来自小说的隐含叙述人,由他的语气、角度、态度、评价等主观因素聚合而成的本民族意识。它更常见,但较隐蔽。
本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移民潮大规模频繁涌动,作家的族属和国籍已很难单一划定,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给创作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进入西方文化圈或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在多数民族的文化语境中写作,这两种情况,给形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前者如美国的侨民作家,海外华人作家等,在他们的作品中,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之间面对面的对话和冲突,叙述人在对母体文化和客体文化进行选择时,表现出来的左右摇摆和深刻矛盾,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
我们已经知道,他者形象是作家在社会整体想象物支配下创造出来的幻象。从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保罗·瓦莱里这样解释“东方”:“为了要使‘东方’这个名词在头脑中产生充分作用,首先必需不曾到过它所指的那个朦胧的地区。”[7] 他直率地说出了所谓“东方”的秘密。法国学者乔治·居斯多夫在评论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时说:“欧洲的学者们自开始世界探险以来,就发明了东方学和人种志,作为适于了解劣等并通常不发达的兄弟的认识方式。稍加思考便会知道,不存在什么东方,东方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其根本理由就是在于东方人从来都是某个人的东方人。”[8] 他认为经由社会整体想象物参与创造出来的“东方”完全是靠不住的。
“东方主义”这个术语,经过萨义德的使用,已经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东方主义者描述的东方的虚构性,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异国异族形象的普遍特性。但尽管如此,异国异族形象对于本民族来说,它又永远是可信的、切题的、合乎逻辑的。作家们赋予他者形象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总是有意无意在维护、扩张或颠覆自我文化。因此,他者形象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自己,对自我民族意识发生巨大影响。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狄泽林克呼吁“急需对形象以及形象结构的能量和威力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探索各种形象所带来的那种特定的、难以驾驭的、似乎无法控制的影响和作用。”[6]
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同样深刻地论证了异族想象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纳粹德国时期的游记作者关于冰岛的描述,强调那里的洪荒、孤傲、克制、自律、庄严、成熟、强大以及尚武的传统,在严峻的气候条件下生存的人类勇敢的美德。这种体认与德国人对自己种族优越性的神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冰天雪地的北方虚构成德国的过去,德国文化的摇篮和精神的家园,雅利安民族的理想范本及纯洁性的象征[5]。
另一个例子,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美国建国过程中,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对美洲大陆的想象和预见所唤起的激情和巨大推动力。美洲这块古老的土地世世代代居住着印第安人,所谓“美洲的发现”,主要是欧洲人世俗性质的冒险活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势力向海外扩张的结果;欧洲人在那里通过土地掠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灭绝等野蛮手段进行控制。但清教徒们在各种各样的宗教小册子、布道文、清教哀诉故事中把这一切合法化、神圣化。他们发明了一整套宗教语汇,把美洲看成是上帝赐予的土地,是“伊甸园”,是“新迦南”,是新天新地;把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视为《圣经》中的大迁徙和类似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动;把早期以囚犯、冒险家、受宗教迫害者为主的移民描绘成上帝的选民;视领袖人物为摩西、亚伯拉罕、约书亚等《圣经》中的先知和圣徒;把对印第安土著的掠夺美化为“上帝的战争”。这些语言的隐喻赋予清教徒崇高的使命感,并最终积淀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埃略奥特主持编纂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就认为:“从大觉醒到美国革命,从向西扩展到南北战争,从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到冷战和今日的星球大战,在贯穿美国文化的每一个主要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上述精神遗产的痕迹。”[9]
塑造他者形象,是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也是数千年中外文学表现的一个常数。过去,人们认为有一个绝对、永恒的真理,后来,人们发现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看法,都受认识主体主观的制约,形象学正是在这种认识论发生转变的基础上出现的。于是,原本不是问题的地方出现了问题,奇迹也发生了。这一领域极其广阔,也深具研究潜力,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