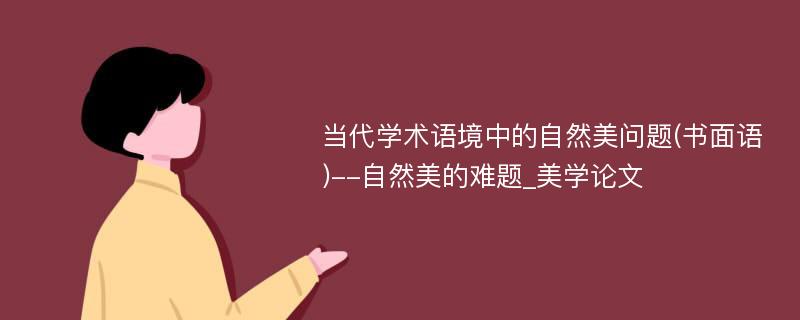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自然美问题(笔谈)——自然美的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美论文,笔谈论文,语境论文,难题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4)04-0106-09
在美学研究中,艺术所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自然美,以致自然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于是美学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艺术哲学。而试图讨论自然美的人又会发现自然美的问题似乎非常复杂。
在中国美学中,没有任何前提地使用“自然美”这一概念使得自然美的研究很难进行。这一概念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中国当代美学背景之下对它的使用往往会使人停留在把美学等同于美的科学或美的理论这种思维模式上,因此美学的中心问题又被归结到美的本质或“什么是美”的问题上了。李泽厚提出的:“就美的本质说,自然美是美的难题。”这一说法几乎成了国内美学界关于自然美的共识。一说到自然美,人们首先肯定就要问什么是自然美,最后不可避免的要回到什么是美的问题上来。可以说,自然美的难题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它容易让人陷入传统美学的思维模式中。但这尚不是自然美问题的全部。
如果仔细考察理论中对自然美的讨论,我们发现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讨论的实际上是艺术中的自然美,而很少是现实中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经验。这样就会产生类似于黑格尔和朱光潜所提出的问题:艺术美是美的更高级的形态,自然美包含在艺术之中,因此就没有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必要。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当代的美学论争中,自然美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就有些奇怪了。我们发现,实际上,当时之所以对于自然美的问题如此关注,并不在于对自然的特殊的审美经验的考察,而是把“美是什么”的问题转嫁到了自然美之上。也就是说,出于讨论的方便,以“什么是自然美”代替了“什么是美”这一问题。毕竟讨论具体的自然对象如何是美的更容易说明问题。今天我们重新讨论自然美的问题,更多的是从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点已经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出现得比较早,在中国对此产生普遍的意识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学界对于自然美问题的提出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注,想从美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甚至解决的方案,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学界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倾向。和学界其他领域相似,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思想,认为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可以为今天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帮助。特别是当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的理论出现以后,中国美学似乎觉得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与艺术哲学并立的自然美学。这种想法有没有根据呢?让我们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美学是怎么一回事。
最近几年来,英美最具影响力的两家美学刊物《英国美学杂志》与《美学与艺术批评》发表了许多讨论自然美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环保的角度出发,反对人类把自然论为满足自己目的的工具,强调对于自然的审美鉴赏要把“自然作为自然”来欣赏,甚至提出要建立一种自律的“自然美学”。
怎样才能“把自然作为自然”来对待呢?Stan Godlovitch提出,仅仅指出对于自然和艺术作品价值评价方式的不同并不能把自然真正作为自然来看待,除非超越价值的评价,以“自然之所以为自然”来对待自然。因为在他看来,按照价值对于自然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就如对于自然的经济化、科学化的解释一样,都是对于自然的“人化”的解释,要想完全摆脱把自然同艺术相类比的解释,只有采取一种“非人化”解释。他说“自然之所以为自然并不会因为没有价值而缺少价值,就像颜色不会因为没有香味而缺少香味一样。自然之所以为自然——自然美学最合适的对象——就是不能被评价之物”,”用尼采的话说,是超越于美丑之外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自然美学的自律。这里对于自然自身特性的强调,无非是要人类改变把自己作为中心的态度,试图培养一种对自然的尊重。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与根据当然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无法相比。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对自然的人化还是非人化都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本质上都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看做自然”是由人所作出的,这里所说的自然实际上就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不管对自然进行不进行评价,人都是自然价值的赋予者,这样,自然不可能被尊重。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然具有一种超越性,这种价值不可能由人赋予,甚至人的价值也源于这同一种超越性,因此人就不是主体,自然也不是对象,人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看到,对于自然的不同态度是由对于自然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不同的自然观念所决定的。我们现在有必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具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观念,它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可能以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来代替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自然观念?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对自然观念的考察上,就会发现自然美的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
不同时代由于特定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状况决定着人们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自然观念,对自然的审美往往是处在不同的自然观念的支配之下,或者说不同的自然观念决定着自然美的命运。我们依据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人类自然观念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神化的自然观念、人化的自然观念和物化的自然观念,或者也可称为宗教的自然观念、科学的自然观念与经济的自然观念。
神化的自然观念或宗教的自然观念是指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人对于自己的有限性有着强烈的意识,尚未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中心,认为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人以外的万物与人具有同等的地位,万物同人一样具有神性或者某种超越性,人对于万物持一种尊崇的态度。在多神论的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人们所具有的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观念。在佛儒道三家思想支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也是类似的自然观念。不过前者把万物价值的来源归因于神,而后者则归因于天、道或佛。在这种神化的自然观念支配之下,人们不会把万物当成纯粹利用的对象,但也不会形成真正的审美鉴赏。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自然的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爱好正是在这种宗教或准宗教的自然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但对于自然的尊崇绝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在西方工业化已经比较发达时期所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表现出对于自然的同样浓厚的兴趣,以致于白壁德把它与中国的道家相比。不过这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时易世移,自然观念相应的也发生变化。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方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提高,越来越推崇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相对万物具有绝对优越性的主体地位得以建立。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自然越来越被当做纯粹的物质世界,当做可以通过分析彻底认识的对象。自然失去了令人尊崇的神圣性,成为野蛮、无理性的对象,是要通过人的理性和力量来驯服和改造的,成为可以任意研究和利用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中,形成了人化的自然观念。所谓人化的自然观念就是说自然被理解为价值完全由人来赋予,来决定,因而成为等待着由人改造的纯粹的物(康德的作为知性规律总和的自然概念是在哲学上相应的表达)。在另外一方面,对于自然的真正的(脱离了宗教意识的)审美意识恰由于自然的超越性的丧失从以前对自然的尊崇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自然美是在人化的自然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是一种与科学或工具理性的相对立的审美的或价值理性对自然的改造,前者是从实用的目的,后者是从审美的目的,也就是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的。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与科学相对立的审美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为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化的自然原来所包含的实用的和审美的两个方面最终被整合,自然对象的价值最终被统一在所提供的经济利益之中。自然完全论为经济活动的对象,自然的审美完全为旅游商业所代替。在经济主义或者商业主义支配之下所形成的对自然的理解,我们称为物化的自然观念或经济的自然观念。因为这时候,自然对象和商品没有了任何的差别,人们会像崇拜商品一样崇拜提供经济利益的自然对象。如果说人化的自然观念还表明了人对于自身所具有能力和心灵情感的尊崇,那么物化的自然观念则表明这种尊崇从人转移到了物的身上。
当然,我们对于自然观念的演变所描述的只是一种倾向: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越来越世俗化。但自然观念的演变并非是交替出现,一种自然观念一旦出现,就会一直存在并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只是其主导地位会为下一种自然观念所代替。那么到今天,神化的、人化的以及物化的自然观念应该是同时并存,而以物化的自然观念为主。从神圣到世俗其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倾向,在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神圣性不会完全消失得不再发生影响,它会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或者在世俗化发展到极端时重新获得统治的地位。无论如何,神圣性不会再以过去的形式发生作用,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像卢梭一样,看到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于是就想保持原初的状态,这最多只是发一发思古之幽情。无论是希腊的、基督教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化的自然观念那不可能直接地拿到今天的社会中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自然美的讨论只有在特定的自然观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今天,也只有在物化的自然观念的前提下讨论自然美的问题才有意义。
在当代西方美学中,除了环境美学外,还有两种讨论自然美的方式。法国的杜夫海纳从现象学的角度提出审美经验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方式,它可以按照对象自身的特性来感受对象,因此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并且“当它与艺术结成联盟时,它保持着自己的自然特征,并把这一特征传给艺术。这种特征就是自然向人类挑战并显出深不可测的相异性的面貌”。这一解释虽然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避免了环境美学没有克服的“人化自然”的倾向,但由于缺少历史的观念,仍然难以为人所接受。由于自然观念的变化,自然美的意义绝不可能按照在近代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被理解。在当代社会的状况下,对于自然美的解释如果不突破理性主义的模式,不赋予新的含义,这个概念就会成为理性化进程中的一个牺牲品。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针对这种现状,提出一种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的否定的辩证法。按照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在对事物的理解中,特殊性和多样性不是被扬弃、被整合成概念,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概念成为众多的特殊性聚合而形成的星座。按照这一解释,自然美不是被艺术扬弃,完全消失在精神里,而是成为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契机。阿多诺所讨论的核心并非自然美的问题,他更在于考察现代文明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但自然美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现代文明中的消失也在揭示这种文明的危机。理性化的进程是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结果却造成了人的物化,成为物的奴隶,成为发展的奴隶。所以环境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自然美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们都是现代文明危机的表现。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能放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来考察,不能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指向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这些研究自身的意义和结果都是令人怀疑的。在我看来,如果自然美的研究还要继续下去的话,阿多诺所提供的是惟一的方向。但即便如此,我也心存疑问:这仅仅是理性主义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问题,还是人的有限性的问题呢?人自身的问题不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怎么可能解决呢?
收稿日期:2004-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