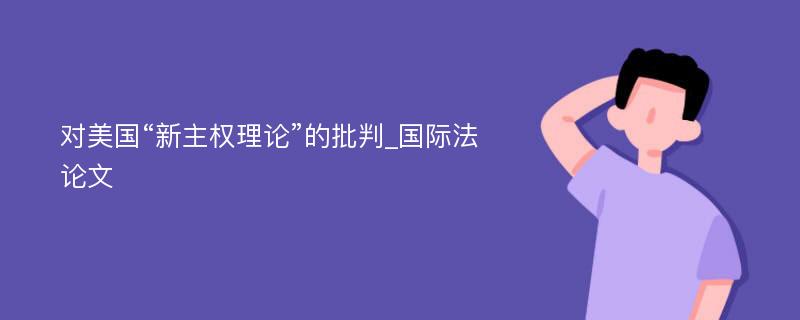
美国“新主权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春秋,华盛顿与西雅图的大街一度控制于反全球化的新进步主义者之手,不过在美国的决策者中,反国际主义的旧保守分子仍属主流。美国虽然接受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却对其他重要的多边体制不屑一顾,这些体制涉及武器控制、环境保护、战争罪行、人权维护以及其他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
任何一位历史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反国际主义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其顽固性与经久性显而易见。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个运动正在赢得学术圈和政策分析人士的推崇。在冷战时期,反国际主义与赤裸裸的霸权论和凡尔塞条约留下的孤立主义遗产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得到了政治精英们的通力支持。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倒是在知识界,反国际主义运动越来越有了市场。学术圈里的这批人已经绘制了一张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蓝图,保护美国的国家制度不受国际体制的蚕食。其实,这批人并不反对美国卷入国际事务,因而不能简单归入孤立主义者之流。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可以对国际公约“择其善者而从之”,有利于己者奉之,不利于己者弃之。
在上述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国家主权。按照这一思路,正是国家主权要求美国来抵制国际体制,并为美国拒绝国际准则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宪法外衣。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杰里米·拉布金(Jeremy Rabkin)说道:“就因为美国享有完全的国家主权,它才可以自己来判断其宪法有何要求。而宪法必然要求主权不受侵犯,因为只有这样,宪法才不会受到侵犯。”新主权论解释了美国何以一再拒绝参与许多国际体制的原因。正是这种观点导致了参院拒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导致了克林顿政府拒不在地雷公约和罗马条约上签字;导致了关乎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备忘录未能提交参院批准。惟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受到了新主权论者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该协定仅限于贸易,而不涉及环境、劳工或人权等问题,这对美国显然是有利的。
新主权论者完全从自己的政策取向来考虑具体问题。他们只是一味地为不参与国际体制作辩护,结果限制了美国今后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也令国家和世界为此付出代价。由于国际关系越来越与这些国际体制及体现它们的公共机构不可分割,新主权论者的做法只会危害美国的国际领袖地位。
照我的方式做
新主权论对当今国际体制有三项指责,每一项都漏洞百出。第一,它指责形成中的国际法律秩序混沌不清,对国际事务构成了非法侵犯;第二,指责国际性的立法程序莫名其妙,也没有强制力;第三,认为美国凭借其国力、法定权利以及对本国宪法所负的责任,可以独立于国际体制外自行其是。
新主权论者不客气地称:国际法的大多数标准混沌不清,要美国认同这些标准毫无道理。其中,倍受新主权论者鞑伐的是人权公约的宽泛条款(broader provisions)。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质问道:“国际人权公约反对任何理由的歧视,包括基于‘身份’因素的那种歧视,那么这个条款的应用是否可以扩大到对同性恋、年龄、体重、容貌和才智的歧视呢?”实质上,这种推理是在提醒人们注意某些国际条约可能存在“调包计”,即有些条款在今天看是无害的一般性原则,而明天却会变成对美国有害的具体条款,华盛顿不能在这种国际条约上签字。
他们又进一步指出,某些国际制度,特别是那些与人权有关的国际制度,与历史上国际法的实践有天壤之别。他们认为,“新的”国际法侵犯了作为民族国家内核的内政权,甚至还侵犯了在美国一向由州政府保留的那些权力。他们悲叹当今的国际法将使政府与其公民的关系受到制约。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约翰·波尔顿(John Bolton)嚷道:“公共政策的每个领域都会碰到全球主义的建议,其始终指向一个总目标,即削弱单个民族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权力。”
其实,这两点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如果按新主权论者的思路,我们在建国之日就该拒绝我国的宪法,因为它对“正当程序”和“提供同等保护”这两条承诺缺乏详尽阐述。要知道,在最高法院后来使这两条承诺精确化之前,它们一直是“混沌不清”的。可见,“混沌不清”并未使当时的各州拒绝批准联邦宪法,因此,“混沌不清”也同样构不成阻碍美国遵守国际人权制度的理由。再者,虽然国际公约里有些条款确实不着边际,但许多条款还是十分明确的。并且,宽泛的承诺也在国际组织日积月累起来的决定和报告中得到了限定。
再说“侵犯论”。不错,传统的国际法的确旨在干预国家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但这种所谓的“侵犯”往往只局限于涉外领域。人权原则进一步将国际法的干涉扩大到了国内公民,但并未给内政或地方性权力的行使带来质的变化。
说到国际立法程序,新主权论者又断言:由于国际官僚阶层得到了壮大,又因为他们不对美国宪法负责,国际立法只会漏洞百出。他们指责国际层面缺乏直接选举,还继承了冷战时代批评国际法的传统观点,对国际法的生命力和可行性表示怀疑。这些论点无非都是新瓶装旧酒,是历史上反对美国参加国际体制的观点在今天的回声:当我们信守诺言而人家却并非如此时,承担国际义务不是作茧自缚吗?实际上,新主权论者是在置疑这样一个问题:国际法除了是个国力较量的问题外,还有什么深文大意?
在这些问题上,新主权论同时还是片面的理论。诚然,力量日益增强的国际体制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但国际组织却不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实体,握有不受限制的大权。实际上,它们总是受到民族国家的牢固控制。但是,新主权论者却否认国际体制有可能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体制。借助对新保守主义取向的曲折表露,他们竟将非政府组织通过国际体制施加影响的行为看作是个“责任问题”,而不是解决“责任问题”的良方,这真叫人匪夷所思。
关于国际法的可实施性问题,应当看到,近一个世纪来,大多数国家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认真地遵守国际法。这一点不容置疑。可以说,国际法正处于伟大的复兴时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必不可少的力量,控制和掌握着法律所涉及的每一领域内的跨国因素,家庭、刑事犯罪、经商、破产等内政问题无一例外地被囊括其中。20世纪最后20年,对人权的尊重有了巨大进步。当然,总是有害群之马践踏法律,任何制度都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但只要法律总体来说受到尊重,我们就不会在无赖面前丢弃法律。与冷战时代相比,多数国家实际上都遵守了它们所承诺的国际责任,虽有行为不轨者,但是这构不成拒绝国际制度的借口。
不要来冒犯我
新主权论的关键问题是,它认为美国有力量不受国际准则的制约而自行其是,谁也对它无可奈何。拉布金就说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完全可以捍卫自己的主权。一个独立于形形色色国际承诺之外的美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了世界的大门外,恰恰相反,我们有绝对充足的理由期待别国不断调整自己来适应美国的口味,他们不是急巴巴想进入美国市场、盼望在其他方面与美国合作吗?”
同时,新主权论者认为,在美国的内政框架内,联邦政府缺乏宪法赋予的权力来参加某些国际组织。例如,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柯蒂斯·布拉德利(Curtis Bradley)就认为无条件接受国际人权公约会违反联邦主义的限定条件。说到底,美国不仅有能力拒绝国际体制,而且许多事例都证明了联邦政府负有拒绝它们的宪法责任。
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形式主义地理解宪法,有选择地解释历史。新主权论者忘记了一件事,即宪法虽重视国家利益,但也时常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国际体系的剧烈变化。联邦主义、分权原则、个人权利等价值还不至脆弱到如此地步,一与全球化交汇就要土崩瓦解。
事实上,宪法迟早都要使自己适应全球化的要求。20世纪,美国所以能藐视国际准则,仅因为别的国家不愿意承受为限制美国作恶而要付出的代价。然而,经济全球化则必将迫使美国入轨。
同时,国际社会还可通过对付美国社会的主要成员(如大公司和各个州)来推动国际法的实施,绕过联邦政府直接来约束这些实体,从而在程序上挫败联邦一级的反国际主义的决策者们。以禁止核试验为例,法国1995年进行核试验时,非政府组织就对法国的酒类发起抵制运动,迫使希拉克总统让步,表示将来不再搞核试验。美国也一样,只要美国胆敢宣布核试验,抵制运动将使美国重要的产业受到打击(如快餐业),这又反过来会使联邦政府不得不尊重禁止核试验条约。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人权领域。美国一直不取消死刑,是仍对少年犯和精神障碍者实施死刑的极少数国家之一,这一点使其至少在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孤立。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绕过华盛顿,直接对实施死刑或有争议地使用死刑的州进行抗议。虽然经济战和羞辱战并不针对美国政府,但却能在州一级得手。包括公司在内的外国活动家在决定是否在此地投资或采购时,总会把人权因素考虑进去。1998年,欧洲议会驻美国代表团主席曾警告乔治·W·布什,在德克萨斯州拥有380亿投资额的欧洲公司受到了股东和舆论的压力,考虑从实施死刑的美国州抽走资金。对州一级的政客来说,将要失掉的汽车厂、商务合同及旅游美元是如此之多,以至死刑大大丧失了它的价值。中期内,各州无疑将停止执行会激怒国际社会的死刑判决,长期看,它们会完全废除死刑。国会又将以遵守这一国际准则而收场,尽管并不是以正式步骤来接受它。因此,可以这么说,新主权论者或许会在国会赢得灿烂夺目的胜利,但却将在更为重要的战场上输得一败涂地。
标签:国际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