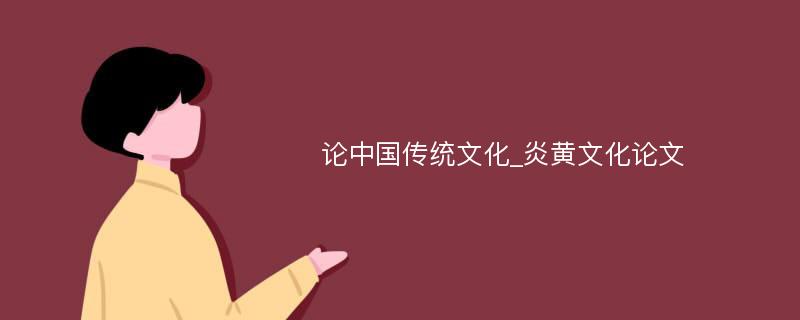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哺育、积淀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其主体部分经过时代的洗礼,生生不息地延续传递至今,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
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近年学术界认为有一万年)的中华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璀璨耀眼的丰富传统文化。从世界文明史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与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并列的、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世界四大文化系统。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
在学术界,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有二:第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同义。第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当代文化相衔接又相区别的以往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源与流的结合上进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而且,这些主体形式的文化都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性格,深深融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意识等各个领域,积淀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并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传统文化是新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石
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新文化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延伸。
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继承性,尤其是文化中的那些观念意识形态部分,更是无法将之一刀两断。与传统文化全盘的、盲目的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合理地选择、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成分,抛弃其中落后、消极的因素,使传统文化积极因素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所以,新文化诞生的重要前提是认识传统文化,依据传统文化,继承扬弃传统文化,而决非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为目标,去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应该说,传统文化必然是新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石。
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光照中华,泽被东亚,历久弥新。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它包含着诸多的积极因素,例如:自强不息、刚毅奋进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注:《礼记·礼运》。)的理想精神;以德治国、修身为乐的重德精神;重人轻神、人贵物贱的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献身国家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协和万邦”(注:《尚书·尧典》。)、各族一家的共处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人和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注:《孟子·滕文公上》。)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广博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济困救苦、舍已为人精神;“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先义后利的高尚价值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礼记·礼运》。)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
可以说,这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因子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持中国近代之文明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像《礼记·大学》所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现有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因为华裔遍全球,当然也在西方有影响了。”(注:《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它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了人际关系,推动了历史发展。尽管孔孟儒学从其创立之时就不断受到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责难或批判,然而它不仅没有退出中国文化舞台,而且由于它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是调整和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非常重要和有效的伦理道德学说,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文化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巨大的生命力,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成为东亚国家(如日、韩、越、新)文化的内核,形成中华文化圈。
在20世纪下半叶,儒家文化更是成为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繁荣的重要精神力量因素。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亚洲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尽管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从最近数十年东亚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来看,这一地区整个的经济状况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成功使关于亚洲文化在经济成功与政治确认上发挥作用的新理论产生了……这一成功的取得部分地、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应归功于亚洲文化的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这样,人们的注意力自然就转向了儒家学说的特定价值观,换言之,就是中国、日本以及大多数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着的这一文化联系。”阿马蒂亚·森还特别指出:“在反面模式方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大概应该记取:欧洲文化并不是实现成功的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注:原载1998年10月27日法国《世界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0月29日第1版。)可见,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已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即能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加剧、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灾害频繁、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等等;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精神危机,如:集体意识淡薄、价值观混乱、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等等。人的心性和物欲的恶性膨胀,不仅用科学克服不了,而且相反——有许多犯罪就是现代高科技的畸形产品,例如使用计算机技术的犯罪等。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忧心忡忡的西方有识之士们所普遍关注的。
人们惊喜地发现,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艰苦创业、安贫乐道等人文精神,对于克服西方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极端自私等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衰落现象,具有特殊的“疗效”。因此,当代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关注着中华传统文化,关注着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希望从中汲取到能够疗救西方工业文明病的良药和营养。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序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汤因比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90、425~42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西方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包括76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于1989年的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认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
1989年的《温哥华宣言》指出:为了改善21世纪科学、文化和人类的生存发展,要更新思想,更新观念,要展示一个不受机械规律硬性制约的、具有持续创造力的宇宙形象。如何展示这种形象呢?人们仍然求助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求助于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一宇宙生命观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标榜和追求的是人自身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这种从微观的个体自身到宏观的宇宙环境和谐统一的人生哲学观、世界观,对于新世纪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为,净化心灵境界和社会环境,对于物质文明进程中构建精神与物质、局部与整体、客体与主体、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相沟通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以实现物质文明在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列宁曾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许多趋向变革、有利进取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有不少落后、消极、负面的惰性因素。例如,阻碍人们民主意识、民主风气形成的等级观念、家长制,阻碍经济规模化、市场化和管理科学化形成的小农经济思想,阻碍竞争观念、探索进取精神形成的保守思想,阻碍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形成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心理,阻碍开放思想、兼容并蓄精神形成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心理,等等。这些落后、消极的思想观念及社会心理,许多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它们根源于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方式。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糅合并存的复杂体。
当然,当人们审视具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时,对精华与糟粕的鉴别和把握并非易事。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并非相互格格不入、泾渭分明的,相反却常常是精华与糟粕相互掺杂糅合在一起。同一种传统文化往往同时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素,或者从一个角度看是积极因素,从另一角度看又是消极因素;或者在一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看是积极因素,而在另一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看又是消极因素。
例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既有“民贵君轻”(注:《孟子·尽心下》。)、“民为邦本”等精华,也有“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注:《论语·雍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论语·泰伯》。)、“民斯为下”(注:《论语·季氏》。)等愚民和奴役、卑视民众的糟粕。又如,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从其认识问题的立足点看,都是存有偏颇的,但从性善论和性恶论,又可引申出人才培养成长的不同侧重面及不同的教育培养原则和途径:性善论重个人内在修养,重内省,重自律;性恶论重环境因素影响,重外育,重他律。这对教育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这种良莠杂陈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这里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我国古代的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中所包含的两种因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注:《论语·子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注:《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所一直奉行的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教育和学习的动机与目标是入仕为官治人,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一切条件。传为宋真宗所作的《劝学诗》表白得更为形象直率,对芸芸众生更具吸引力:“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这是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教育学习观。在“左”的年代特别是在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10年动乱期间,这些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受到“体无完肤”的批判是不足为奇的。然而,恐怕由于批得太狠太久,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条件反射——只要看到“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字眼,便不加思索地与“封建、腐朽、反动”的性质挂上号。
其实,中国传统的教育、学习、读书观中,也有许许多多并非功利主义的,这类名言不胜枚举:“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汉·刘向)(注:本文所引名人之言,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转引自《中外名言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北朝·颜之推)“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唐·皮日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唐·韩愈)“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唐·翁承赞)“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宋·欧阳修)“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宋·程颐)“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并明月霜天高。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宋·朱熹)“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清·袁枚)“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清·张维屏)
在当代,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总结了世界发展史后科学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其基础在于教育,在于已有的书本知识,而产生的新的科学技术又将成为教育和书籍的新内容。
欧洲的教育、学习、读书观中,既有追求精神的充实和人格的完美,也有很多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条件的功利主义的成分。在精神和人格追求方面,许多哲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座右铭:“没有书籍的屋子,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罗马·西塞罗)“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英·莎士比亚)“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英·培根)“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法·孟德斯鸠)“你一翻开珍贵的羊皮纸古籍,整个天国就会降到你身边。”(德·歌德)“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美·富兰克林)“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苏·高尔基)
立足于精神和物质(即功利主义的)两方面来看待知识的一些名言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学问是庄严、神圣的女神;对其他人来说,学问是一条能供给奶油的能干母牛。”(德·席勒)“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源泉,既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法·左拉)“知识哟……有了你,人就有了一切。”(法·爱尔维修)
“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在当时是着重于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王佐术治之才,是为了教化民心、开启民智,使处于愚昧状态的百姓能知“道”,了解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及其社会秩序,并予以遵守,最终达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这种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将读书、学习置于最高地位,毫不掩饰地轻视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行为。应该说,这有其片面偏颇的一面,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透过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又可看到存在于其中的另一种积极的价值因素。
先看“学而优则仕”。春秋末期,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不学而仕、仕而无学的现象颇为普遍,而私学的发展和士阶层的兴起,又产生了学而不能仕的情况,两者遂形成尖锐矛盾。面对现实矛盾,孔子一方面大力提倡礼贤下士、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陈腐血统观念和风气,主张延揽任用天下既有贤才;一方面他极力依靠教育——兴办私学来培养新的君子贤才。我们的先哲在几千年前就充分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掌握知识,而且只有很好地学习,成为优秀人才,才能统御治理好国家。应该说,这种观点是颇有见地的。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优”字作“有余”解,“学而优则仕”是指学有余力则去做官,但实际上后人无论是颂扬、遵从还是批判,都一直将之理解为“学习优秀者则可以为官”,这是不争的事实。宋代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此语至今仍有参考借鉴价值。
再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的先哲早就认识到,知识是人间最可宝贵的财富,读书、学习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崇高行为,是一种最可贵的社会活动。汉代的王充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注:王充《论衡》。)这比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要早了一千年!而“知学”则主要来自“读书”。如果一位外国名人说:天地间一切活动都没有读书可贵,读书是万事万物中最高尚的活动,我们难道会去批判它而不会将之作为现代学习的座右铭吗?卢梭说:“在所有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之似乎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最后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提出的这句话,不同样也是说,掌握了文化知识的、能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方可以从事国家的治理统御;没有文化知识、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不能从事国家的统御治理工作的。换言之,国家的统御治理工作必须由掌握文化知识、能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去担任;而不能让没有文化知识、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去担任。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知识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由粗放型和劳动(劳力)密集型向集约型和知识(劳心)密集型转变,也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推行,知识型、技术型的“白领”队伍将不断扩大,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更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政府的领导管理者还是经济企业的领导管理者都更加必须是拥有知识、头脑睿智的劳心者。从当今世界范围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仍是劳动(劳力)密集型的,其治理国家和企业的领导管理者缺乏科学文化知识,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贫穷落后,在国际上将受制(治)于他人,甚至挨打!
总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当今时代,在反复强调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的跨世纪的新时期,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中,我们恐怕不能再以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我国传统的含有积极因素的教育价值观和学习价值观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要看到这样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的先哲们所反复标举、一再推崇的那些优秀的价值观念、高尚人格、民族精神,常常正是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所最匮缺的。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例如:推崇先哲们尊师重教,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地存在忽视教育、轻慢知识的愚昧现象;标举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正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帮派门阀的流弊。所以,任何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非理性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那么,究竟应怎样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呢?
1.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科学、严谨、审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然存在着正负、优劣两方面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封闭的社会环境等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如果没有积极向上的因素,没有一种向前的推动力,它不可能在历经无数次内忧外患后仍然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地延续至今,广播东亚;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消极落后的因素,没有一种停滞的或向后的拖拽力,近代的中国便不可能在科技、文化、经济迅速崛起的西方世界之后踽踽而行。因此,数典忘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是危险的;全盘肯定、盲目自大、敝帚自珍的国粹主义同样是有害的。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去审视、剖析、鉴别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优秀的成分,拒绝和抛弃其落后的成分,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并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2.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提高洞察能力
第一,要坚持历史观点,站在历史的时间点上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评价历史人物。因为一切传统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纵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着历史的烙印及其局限。鉴于此,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不颂古非今,也不以今非古;只有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才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而不会以主观片面的标准去评判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看成是一堆陈旧过时、不合时宜的历史包袱。
第二,要站在现代的时间点上,用现代的科学观来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和现代的两种视角贯通、结合起来。只有很好地做到这种贯通、结合,才能对传统文化作出客观科学的评判与选择。如果脱离了历史的视角,就难以给历史遗产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如果抛弃了今天的科学思想,又无法做到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遗产和古为今用。正如高尔基所指出:“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峰看遥远的过去。”(注:转引自《光明日报》1995年4月24日第5版。)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机械的复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并非盲目地照搬,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需求,进行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和发展。例如,孙中山针对古人的“忠孝节义”,根据民国初期的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并两相对应地作了具体分析:“忠君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注:转引自黄济《关于传统教育现代化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论断, 就点石成金地使传统的对君王的愚忠,一变为充满新思想、具有时代活力的积极向上的忠国忠民之德。孙中山先生认为孔子标榜的“仁”和墨子推崇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意义相同,而中山先生则进一步提出“公爱”与“私爱”的分别,认为只有“公爱”才是真正的“仁”。这就创造性地发展了“仁”的思想。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泥古唯古、食古不化,而必须站立在现代的时间点上审视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
第三,要切实地把握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而不是只在其外部特征上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兜圈子。
3.面向世界,博采众善,广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用以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欠缺
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主要是指包含着西方传统文化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是西方社会在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凝聚的历史文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世界全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西方文化为人类文化作出了的巨大贡献,可为其他文化提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段,由于开始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体系、性质很不相同的两种文化。粗略而言,西方文化是一种注重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智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强调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中庸和谐关系的“道德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应该说,这两种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并且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性正是西方世界开始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创新精神也正是中国由落后的农业经济迈向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即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极为需要的。实际上,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性本应是完美文化中的紧密融合的两个方面。因此,在21世纪,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和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走到一起,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时候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应“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7 卷第60页。)。对此,我们应抛弃疑虑和偏见,加大吸取西方文化积极因素的力度,而不要扭扭捏捏、患得患失——从这一意义上讲,完全不必去担心所谓的“全盘西化”。这是因为:
第一,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它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多次经受到外来文化(包括来自印度的佛教)的强大“入侵”,但最终并非中华文化被“外化”,而是外来文化被“华化”、“汉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有人企图推行“全盘西化”,以根深蒂固、底蕴深厚的稳固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被“全盘西化”的。这种情况已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明确证实。
第二,进入后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尚在为西方文化的负面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发愁担忧,进而希望从以2500年前的孔子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疗救的针石药剂。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全盘西化”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和无需担忧的。
这里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文化是中华(东亚)文化圈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方面要快于、优于中国,比中国更能调适、消化西方文化呢?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日两国虽同处于中华(东亚)文化圈,但两国在该文化圈内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并不一样。中国系中华(东亚)文化圈的发源地、核心区,是“源文化”;日本只是处于中华(东亚)文化圈的被辐射、被影响区,是“流文化”,其主体文化并非其本土固有。中国的中华文化中消极、保守并与西方文化优秀因素相抵触的部分比日本的中华文化中的这些部分更为突出、更为根深蒂固。同时,日本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原就是外来文化,日本原始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传统态度便是亲和、吸纳而非排拒。这一基本态度决定了它既能很好地吸收中华文化,也同样能较好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华(东亚)文化圈内处于被辐射、被影响区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泰国等都是如此。由此也可见,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传统文化架构在保守性、稳固性、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性方面较之中华文化辐射区的文化架构更为突出。
也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传统文化具有超常稳固性,其负面、消极、落后的因素也必然同样具有超常稳固性、保守性和顽强生命力,因而必须加大引进西方文化积极因素的力度,以便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给予重力的冲击。蔡元培曾说:“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创造文化,而创造文化,往往发端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这多种文化交汇、碰撞、激活、融合的时代,这使中华文化有了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机会。而中国21世纪的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也正需要在这多元文化的激烈交汇、撞碰、融合中进行。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也在变,不断吸收,不断变化更新,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创造。”“你们青年人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学到手,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化,再熔为一炉,创造出有你们特色的新文化来!”(注:《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国学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读书论文; 兼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