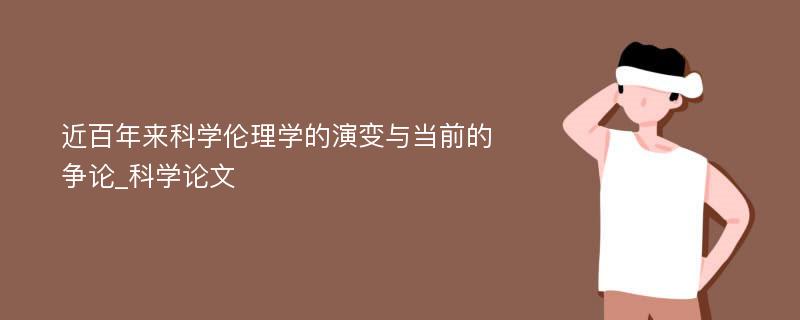
百年科学伦理的演进与当前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前,科学家仿佛生活在象牙塔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于兴趣或好奇而从事科学研究,并不考虑其工作的结果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建立时,科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科学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自此,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成为科学家普遍具有的精神品质。
20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科学成果被滥用,给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科学家们为此而忧虑和困惑,但探索大自然、宇宙及生命秘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仍驱使他们不停地追求新的发现,从而又可能带来新的负面效应。因此,重视科学活动的伦理规范,注意科学成果应用的负面影响,加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全民关心的一个紧迫问题。
百年科学伦理演进的五个阶段
面对科学成果被滥用并可能对人类造成灾难,科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道义责任,越来越意识到科学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和科学伦理的意义。百年来,科学家为反对科学技术成果被滥用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战、反生化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特别是化学研究的成果被用于战争,被制成毒气弹等化学生物武器屠杀无辜的人民。科学家与人民一道反对战争,反对科学成果被用于杀人。法国科学家郎之万起草的反战宣言有多位科学家签名,登载在《化学战》小册子上。他们强烈谴责科学研究的成果被应用于战争,对人类、对文明构成威胁,竭力阻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倡导“科学要为人道作贡献”,主张拓展和推进国际主义思想,寻求世界和平。在20世纪20-30年代,科学家们继续为反对战争与保卫和平而大声疾呼。
第二阶段:反对原子武器的和平运动。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了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伤亡,激起了科学家强烈的反战声浪。爱因斯坦于1945年12月10日发表题为《赢得战争不等于赢得和平》的演讲,表达了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1946年7月,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成立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提出“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的宗旨。
1948年制定了《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个人和集团应担负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1949年9月,通过新的《科学家宪章》,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家的权利和责任。
1954年12月23日,哲学家罗素发表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严重危险的声明。1955年7月15日,康普顿声明“科学是使人类生活趋于完善的一条途径”,要避免使其“为人们提供自我毁灭的工具”。
第三阶段:直面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冷战结束后,科学家们意识到,尽管核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但人类又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新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这一阶段争论的重点是针对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面临生存环境的威胁而出现的科学伦理问题以及科学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呼吁人们从“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宣战”的隆隆炮声中惊醒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1972年6月5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只有一个地球”。宣言强调,人类如不重视环境问题,必将对地球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必须担负起明智地管理好地球的责任。
1983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出版,“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问世。
1987年2月27日,《东京宣言》发表。
1989年9月10-15日,科学家发表《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宣言提出:要把“更新思想”、“改变世界观”、“建立星球意识”作为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该宣言意味着,当人类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危机和新的转折时,科学家要向人类揭示出旧世界观的危险性和进行革命性转变的重要性。这是以往科学家从未意识到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
第四阶段: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的伦理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高新技术大量崛起,起先是信息技术,其后是生物技术迅猛发展,这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繁荣,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
如果说,大杀伤性武器和生态问题只是涉及人与人或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与道德责任的某一方面,那么新科技革命实践所涉及的价值伦理层面就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已经从科技共同体的内外分野,拓展到社会、文化、人与自然之间等各个新的领域。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有许多道德抉择亟待人们作出。科学界日渐意识到,在运用科技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必须放弃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主动担当起日益增长的科技力量所带来的相应道德责任。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脱氧核糖核酸)研究,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恢复,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伦理挑战的经典之举。
从本质上看,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核心依然是人的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例如,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取别人的有关信息,其中有些是允许的,有些属于个人隐私,这就使保护隐私权这一现代社会一直面对的人际问题又有新发展。又如,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医生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与设备就可以做出判断,常常忽视与病人交谈,甚至不听或少听病人陈述病情而开出药方,漠视了病人的知情权。由此,“知情同意权”这一传统的医学伦理问题又遇到新情势。不论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所遇到的平等参与、信息共享、信息审查、信息权、信息接入权、数据作伪问题等,还是与生命科技相关的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堕胎、艾滋病、安乐死等等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都需要科技共同体乃至全社会主动反思新的科技进展对人的深远影响,努力揭示与廓清其中的价值负载、伦理意蕴和道德义务。
第五阶段:围绕以克隆人为主题的伦理争论。
1997年2月,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了多莉羊。从此,人们就开始进行克隆人问题的讨论,因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克隆人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允许克隆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如何看待克隆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大致可分成三种立场:一种是,无论是从科学或技术的角度都反对克隆人;一种是,无论从科学或技术的角度都可以克隆人;还有一种立场是,作为科学研究应允许研究克隆人,但用技术手段克隆人应慎重。
在上述百年进行的五个阶段的科学伦理争论中,科学家和全体公民一道,为合理公正地解决有关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每个重大问题都未能完善彻底地解决,但毕竟成绩斐然。如在生态问题上,人们的环境意识大为增强,全球环境正在改善,新的措施不断出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正在研究解决中,人类的道德境界正在提升。
新的伦理争论
百年科学伦理问题的演进从外显的、直观的逐渐变成隐含的、内在的,科学伦理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和专门化,但又变得日益重要和意义深远。
当前的科学伦理争论除了前述的信息网络伦理和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以外,重点是围绕克隆人相关的伦理问题进行的。
以往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大都是人以外的东西,即使把人作为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研究其构成,而现在已经研究到其生成问题上来了。而对人生成的研究,原先也只是抽象的宏观的探索,如生命起源、智能生成,而今天的克隆技术不但可以揭示其机理,而且可以按此机理制造出新的生命。人们对此缺乏思想上充分的准备,因此产生了各种疑虑和恐惧。对此赞成的或反对的均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本人对此争论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关于混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而造成的危害,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过了。我主要强调,不要笼统地提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主张,科学无禁区,技术应慎重。不可把技术造成的后果加在科学探索的头上。科学只有认知价值,而技术则是负荷功利价值的。所以,决不可把科学与技术混淆了。有人认为,“20世纪的科学研究活动正在经历着由个人的事业向社会的事业转变过程,科学的体制化和科学家角色的职业化是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特征。这种性质的变化,使人们不得不把科学事业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也即“大科学”。但“大科学”并没有改变科学的本质,基础研究不但不能削弱,还必须加强。我们已经深深感到了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创性能力的重要性,认识到厘清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的重要性。
基础研究不应该设立禁区,因为一旦设立了禁区,研究就要停止,认识就此止步。事实上,一项研究的成果对人类生存发展到底是否有害,害处有多大,如何兴其利而避其害等等,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被认识,先验判断总是靠不住的,是要犯错误的。这不言自明。
第二,区分宗教信仰与科学自由的界限:敬畏生命的自然性。
克隆技术直接对生命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提出了挑战。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理智的分析。
敬畏生命是人的情感、信仰。如有些宗教敬畏生命,反对杀生;素食主义者敬畏动物生命但可以饮食植物生命,然而植物毕竟也是一种生命。生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不是上帝或无上的神灵创造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性。
对生命作科学研究是从生命的自然性出发的,是科学理性。而对生命的敬畏是人的情感。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是理性对情感的克服,从而推动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当然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理性概念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的。
生命的形态是发展的,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科学研究是获得认识深化的最基本的手段。它不应有终止的时候,除非最终生命形态泯灭了,但至今我们还看不出有任何迹象。然而,按我国某些生态主义者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意见,任何克隆生命的行为,包括克隆动物或植物,都是不道德的,都是对生命的亵渎。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情感上的顾虑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对生命作理性探索和科学研究的理由。
第三,伦理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又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的。
过去挖人的祖坟被视为大逆不道,现在许多有识之士连骨灰都不留了。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尸体解剖是被禁止的,这也许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但没有尸体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就很难取得进展。曾几何时,这种伦理观念被破除了,伦理规范随之改变。现在我们甚至鼓励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并视之为一种高尚的境界。当然,伦理规范标准的制定,不能只考虑伦理概念,还要考虑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从生命涵义的进化演变与伦理规范的历史沿革来看,克隆人的科学研究不应被禁止,正如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不能等同于反对对原子作科学研究一样。任何变革都将面临风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当理性的选择消除大量随机性时,有害结局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绝难完全避免或绝对消除。据报载,美国科学家已成功地克隆出人类胚胎,但这胚胎将暂时被冷冻保存。在胚胎的遗传稳定性以及是否具有发育成健康婴儿的能力等问题尚未搞清前,他们不会将胚胎植入人体。我认为这是科学的态度,因为这是作科学研究,而不是技术应用,更不是成批地生产孩子!当然,对此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四,正确处理开拓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关系。
对科学讲伦理(这里不是指科学家的社会伦理责任)就是给科学设禁区。给科学设禁区就意味着为科学中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原创性)设置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过去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做过许多蠢事,将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当作资产阶级、当作唯心主义加以批判。我们对控制论、相对论、共振论、量子力学的批判所导致的危害,令人至今记忆犹新。希望在新时期、在新情况下力戒简单从事,以免重蹈覆辙。一门新科学常常会与旧传统相抵触,甚至会受到强烈的反抗。所以,当一种新科学可能的成果尚未为公众正确理解时,我们需要帮助人们逐渐清除传统文化心理背景的障碍,为其正常发展开辟道路。我们要支持创新,中华民族在科学的原创性上对世界的贡献太少了。毫无疑问,创新就会有风险,我们应尽可能地降低风险,但不应让许多清规戒律限制创新。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的智慧,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