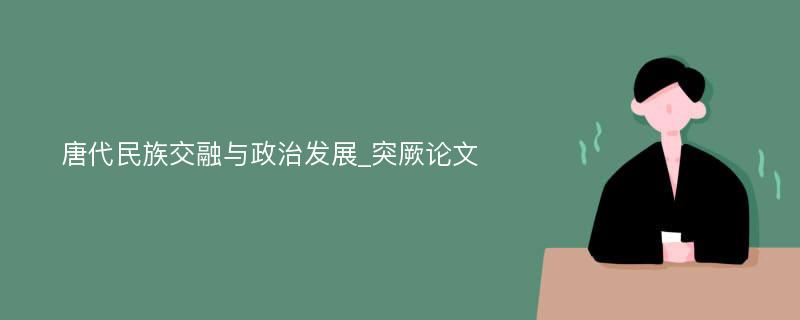
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民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4-0008-07
有关唐朝的民族融合、文化交往课题,近年来似乎成为学术研讨的热门话题。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他撰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认识中古社会有两把钥匙,一是文化,二是种族。他说: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陈先生将种族与文化视做理解中古社会的关键因素,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时隔60年以后,他的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引起人们的再次关注,这说明上述问题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时至今日,人们愈来愈重视种族、民族和异质文化对中国民族整体发展产生的影响。韩国学者朴汉济提出了五胡、北朝、隋唐史“胡汉体制论”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民族移动构成当时社会的主流趋势,它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还包含胡汉两个民族在同一地区、同一统治体制内并存经过冲突、反目、融合而形成的文化体制。[2]唐长孺先生在他晚年撰写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虽然没有大篇幅阐述民族问题,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北朝以后中原走的路线掺杂了胡系内容,使得传统遭受某种程度的破坏。唐朝建立后面临的变化,即如何摆脱特殊的道路而重新转向汉魏传统。这实际上涉及了文化、民族的问题,只不过他认为唐朝的路径是从特殊的道路走向传统的普通的道路。[3]本文即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唐朝胡汉民族的融合与中央王朝政治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作一研讨,旨在揭示政治一体性对民族互动的一统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
朴汉济在他的论文里指出隋唐帝国形成最大的因素“可在其前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寻到。也就是隋唐世界帝国的成立也有南朝及北朝的功劳”。[2]实际上,当时社会发展的过程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联系。魏晋南北朝民族互动导致的民族融合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唐朝建立的基础。陈寅恪在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时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4]这三源既包括了中原汉魏的传统制度,也采纳了北方胡系民族的文化因子。而就唐朝统治集团来源讲,他们主要来自于所谓的关陇集团。此集团由西魏宇文泰创立,他为与东魏北齐抗衡,依靠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制定以该地区为旨归、结合胡汉双重体制的政策,即“关中本位政策”。[1]唐朝统治阶层既源于此地区集团,又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他又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等阐述”。[1]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5]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李唐王朝,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在兼并其他势力,特别是各地区胡系势力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比如与唐朝对抗的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等,他们均依靠突厥与唐对峙。唐高祖李渊起兵之际,也曾向突厥求助,获得突厥兵马的支持。但是,随着唐朝实力的加强,特别是唐欲取代隋朝而立,与突厥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后者不希望中原王朝重新强大,他们力图割裂中原,从中控制,如同当初北周和北齐那样。于是,突厥由支持唐朝变为直接与唐朝对抗。自唐朝立国后,东突厥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唐朝边地,甚至进兵长安。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唐太宗通过玄武门政变夺得权力,七月,东突厥可汗颉利自率十万大军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东南),长安戒严。唐太宗急中生智,以香火之盟退兵,暂时减缓了突厥的威胁。贞观四年(630年),唐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属部纷纷脱离自立、天灾人祸之际,派大军将其征服,东突厥政权灭亡。
唐朝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经过反复的讨论,太宗最后接受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即将他们安置在西起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的沿长城地段。之所以选择该地区,整体的思路是既可保持突厥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又可消除他们返回旧有地区重新崛兴的企图。具体的方式是所谓的羁縻府州。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指外族附唐部落受到朝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府州体制,以原来的部族酋长和首领充任府州的都督、刺史,他们有觐见皇帝、贡赋版籍的义务,但实际事务仍旧归自己掌握。(注:王小甫先生将羁縻府州概括为:第一,羁縻府是为保证唐朝的安全和边疆的稳定而设置的,必须执行唐朝法令;第二,各府州设都督、刺史等官职,由本部首领担任;第三,羁縻府州按规定属边州都督或都护管领;第四,各府州有无版籍不定;第五,其名称往往采用当地或附近城镇、部落的名称。见《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8页。)它们与内地的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四夷边疆的基本行政格式。
上述羁縻府州是在太宗征服东突厥和漠北铁勒诸部归降的形势下设置的,太宗因此被胡人称为“天可汗”。羁縻府州体现出唐廷对诸族的安抚与控制,表现为唐廷的抚慰政策。但是它是以唐朝整体实力强盛为基础的。唐廷之所以如此,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既它要在西域地区对抗西突厥和其他势力,北部形势一旦稳定,唐朝就要重新调动军队西进。唐廷不希望北部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因此善待降部是诸策之中的最佳选择。这是唐太宗政府设立羁縻府州的现实背景。
但是,羁縻府州的作用却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正是源于自身。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控制了部族首领就等于控制了全部族,但是如果某些首领背叛或与唐廷发生矛盾,也就变成所属州府的整体行为。东突厥灭后,漠北崛兴了薛延陀势力,它试图取突厥而自立,并欲趁太宗东封之际向南用兵,这引起唐朝的警觉,于是唐将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府体制转用到北部,设置燕然、瀚海二都护府。都护府的职能是“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除了安抚的功能外,它主要是征讨叛唐的部族,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羁縻府州的缺陷。然而,都护府尽管有征讨、镇压的功能,但是它自身实力的有限,使它应付、处理较小规模的叛离活动尚显有余,但遭遇大规模的反叛,就束手无策了。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北部的突厥降户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先是由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及单于都护府属下的二十四州叛乱,继有阿史那伏念、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率领的叛乱,参与者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阿史德温傅和奉职二部原隶属单于府,他们叛乱时,单于府长史萧嗣业率军镇压,但是萧军难以抗衡叛乱的几十万人,唐廷随后遣派裴行俭出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领三十万大军镇压。由此可见,都护府对待大规模的叛乱显然是没有办法的。
突厥降户叛乱之出现,与这个时期形势有关。吐蕃崛起之后,随其自身实力的加强,它迅速走上了扩张道路。它对唐朝展开了频繁的攻击,先是吞并了夹处在唐、蕃之间的吐谷浑,随后在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唐、蕃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唐军十八万惨败于吐蕃,而突厥降户叛乱的发生,就是在这第二年。显然,他们的行动是受吐蕃进军的影响的。唐长孺先生指出,仪凤以前,唐朝国力强盛,而周边诸族势力相对衰弱,唐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对外采取的是攻势战略;在这之后,吐蕃打破了唐朝的优势,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唐朝的攻势战略受到挑战,逐渐转为守势。伴随着这一形势的转变,周边的其他民族势力也在逐步地崛兴,北部的突厥不断地南进,并带动东北的契丹和奚人骚扰唐朝东北边地;吐蕃在西北和西域又与唐朝展开拉锯战,西域地区的西突厥余部、突骑施和其他势力亦参与其中。唐朝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加上朝廷内部武则天上台引发的朝政之争和危机,使得唐朝受到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唐朝被迫将攻势战略转为守势战略。到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周边相继设立了十个节度使、防御使体制。《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条记云:“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略),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仿制突骑施、坚昆(略),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吐蕃、突厥(略),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略),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略),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略),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略),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略),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略),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略),兵万五千四百人。(略)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
可以看出,十节度使的设置,完全是为了防御边地各个民族势力而采取的防御措施,旨在保卫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本部地区。这与唐朝建立初年太宗向周边开拓扩展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节度使本身是军事制度,反映了唐朝军事格局的变化。但是从实质上讲,它则是唐朝与周边民族势力关系的产物。因为正是周边民族势力的崛升,特别是像吐蕃、突厥的频繁进攻,才迫使唐廷加强防御。
二
安史之乱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这已为人所熟知。就安史之乱本身而论,它正是前期唐廷与周边民族势力关系转变的结果。叛乱的首领安禄山是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他和史思明的任务是防御东北的契丹、奚和突厥的南进,然而安禄山却暗中积蓄力量,招收大量的胡族作为自己依靠的武装力量。安、史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证。安、史本身是防御周边民族势力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却利用了这个条件向唐廷发动进攻,几乎倾覆中央王朝。叛乱在时人和后人看来,属于军事背离的性质。但是其后隐藏的分明是当时的社会和民族矛盾。节度使体制所防御的对象首先是周边诸族,周边形势的变化导致唐朝军事格局的变迁,而这个变迁又被胡系将领安禄山所利用,从而引发了以地方军镇为基础的军事叛乱。安禄山之有力量率领众多的属下对抗朝廷,显然是有社会基础的。他所在的地区,特别是营州,当地胡族成分占据着相当的比例。
这里所涉及的胡族是指中亚的羯胡,今日一般称为昭武九姓。当初突厥败亡之后,随其降服的势力甚多,其中大部分被安置在灵州至幽州一线。突厥势力中掺杂着昭武九姓人,这早已为人所熟知。突厥兴起后,在南下进攻中原的同时,也向西域腹地进军,并征服了河中,其地的昭武九姓人自此之后受突厥的影响而逐渐突厥化了。他们与突厥保持着密切关系。这在汉文史籍和出土文物里有不等的反映。1981年在河南洛阳出土的安菩墓志铭,内容有这样的记载:“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6]安菩是昭武九姓之中安国的首领,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归属唐朝,据研究,他归唐的时间正是东突厥败亡之际。联系上文的讨论,安菩的归国,与铁勒系属诸族的归附是同样情况的。这合墓志记载的昭武九姓人归唐具有典型意义,而他们随突厥的南下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突厥复兴之后,骨笃禄、默啜的势力迅速扩展到东北地区,降制了契丹、奚人等势力。芮传明研究突厥碑铭总结说:“阙碑、毗碑、暾碑所言‘东征’一事,发生在默啜可汗在位期间;突厥于696、697年对契丹的奔袭和征服,乃是‘东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突厥人在‘东征’中接近或抵达的‘大洋’系指今辽东湾,‘绿河’则是指今西拉木伦河”。[7]他在《古突厥碑铭研究》一书中对突厥复兴后向东、西部扩张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看出突厥涉入东北的情形。这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相互印证,说明安禄山所在的地区居住着相当数量的胡系民族。他之所以能崛起,正是有这些势力(包括胡化汉人)的支持和帮助。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力量并没有因为安史的失败而消失。事实上,安史叛乱的结束不是叛军军事上的被消灭,而是朝廷无力将叛军剪除。持续八年的叛乱,使得唐朝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唐朝所可依靠的较为完整的节度使军队只剩下朔方军,又借助回纥军队使尽全身解数终于将叛军击败,但却不能将他们消除。代宗下令收降安抚,方才收拾了残局。这样,叛军的力量就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叛军的根据地河朔则由此走上了割据自立的道路。
关于这些,学术界的讨论相当热烈,论述的根据也十分充足。陈寅恪先生将他们割据的主要原因总结为该地区整体社会的认同与长安朝廷之间出现了差异。他说:“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中略)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1]时至今日,陈先生对长安与河朔两个地区所代表不同文化类型的论述,仍有极强的说服力。正如上文谈到的那样,陈先生将种族与文化视为社会的关键而刻意地强调,从流传至今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等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对河北社会出现的文化变形(即与长安出现了差异),的确有证据可查。例如《通鉴》卷二四一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六月条记载穆宗当政时,卢龙节度使刘总因杀自己的父兄而内心自疑,向朝廷奏乞弃官为僧,唐廷调派张弘靖出任,云:“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娇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弘靖庄献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也。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字丁!’由是军中人人怨怒。”这段文字的背景是,宪宗在位期间,先后镇服剑南西川、夏绥、魏博、淮西、淄青等藩镇,河朔地区的节度使亦对朝廷表示归顺,“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这个形势是自安史之乱以后所没有的。宪宗朝廷取得了镇服藩镇的空前胜利。
但是,穆宗即位之后,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根据我们的研究,穆宗决策集团本意是想延续宪宗的政策,保持对全国(特别是河朔地区)的控制权,甚至在宪宗的基础上还有所作为。为此,他先稳定了西部与吐蕃的关系,然后转而处理东部的藩镇问题。穆宗的决策集团是想借宪宗之余辉,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力量,宰相萧俛、段文昌以自然减员为准,提出了消兵百分之八的减员计划,这引起了河朔地区藩镇的强烈怨愤。因为9世纪初期的藩镇军士,他们早已脱离土地,以征战戍守为职业,与节镇大小将帅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割断这种联系,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业。这些人与前期府兵时代的军士完全不同,府兵以土地为生存条件,而他们一旦离开军队,就失去依托,既不务农,也不另谋生业,“皆聚山泽为盗”,对新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加上像张弘靖这样对河朔习俗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官员前去处置边务,双方思想观念中出现的裂沟很快就转化为冲突。河朔再一次地背离朝廷,成为独立的力量。
可见,河北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与长安朝廷本部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的地区了。河北的风俗受到胡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胡化是当地的主导风气。活跃在该地区众多胡人是构成这种文化的主导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河北胡人并不是唐后期才有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却发展成不同于长安的文化呢?该地的胡系民族早在唐前期就已陆续迁移于此,但在当时这个胡化问题似乎并不明显。我们认为,就胡化本身而言,前期的河北同样地存在着,但是没能成为气候。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央王权的强大,使得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样处在中央王朝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前期以太宗当政最具典型,唐朝不仅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有效的统治权,而且将周边民族地区纳入到它的体系之内,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太宗征服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并被周边势力冠以“天可汗”的名号,就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开始覆盖了中原以外的广远区域。这些区域随着外族的进入,其文化和习俗作为大一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纳入到中央王权的控制之下,其间出现的差异被掩盖在强权之内,对王朝构成的威胁尚未显露出来。但是随着中央王权的削弱,民族地区势力所受的羁控逐渐减弱,这给了分离势力以更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以往不存在问题的地方很容易被他们所利用,转为分离或叛乱行动,上文东突厥的复叛即是明证。
由于周边力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亚洲力量格局的变迁,唐朝维护局势的努力面临着新的挑战,这迫使王朝本身也必须进行调整。唐朝军事格局由前期的攻势战略转向守势战略正是这种形势发生变化所出现的转化。尽管这并不符合王朝决策集团的愿望,但唐朝不得不做如是的安排。比如节度使之代替原来的都护府军力、行军体制,就是因为周边势力(如吐蕃的崛兴、东突厥的复国)向王朝州县发动的攻势打破了唐朝的战略、使唐朝逐渐地陷于防御的结果。节度使就是满足这种防御政策的。节度使设置的目的原本是防御周边民族势力,但是节度使军队自身征用的就有许多民族力量。安禄山正是利用了这里的民族问题挑起战争,破坏了王朝的战略体制。那么,是不是民族问题导致唐朝整体实力的耗损呢?先看一段引文。《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国家自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蒿、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源。’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安)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这段引文经常被用来证明李林甫重用胡人将领而导致安禄山叛乱的理由,现在看来是忽视了当时的现实情况。李林甫个人有野心,这个问题无须赘论。但是他之提出任用胡系将领的问题,一直是唐朝惯行的用人方略。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太宗既任部落之酋长为将帅,则此部落之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效力。功业成后,则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如唐代中世以后藩镇之比。至若东突厥败亡后而又复兴,至默啜遂吞并东西两突厥之领土,而建立一大帝国,为中国大患。历数十年,至玄宗初期,以失政内乱,遂自崩溃。此贞观以来任用胡族部落酋长为将领之覆辙,宜玄宗以之为殷鉴者也。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哥舒翰则其先世虽为突厥部落酋长,然至翰之身,已不统领部落,失其酋长之资格,不异于寒族之蕃人。是以玄宗亦视之与安禄山等,而不虑其乱叛,如前此复兴东突厥诸酋长之所为也。由是言之,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5]唐朝任用蕃将不始于李林甫,在唐朝的建立和立国之后,蕃将一直成为王朝统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即唐朝的立国基础是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这个问题在太宗时期处在隐藏和平缓阶段,以后则随着唐朝与吐蕃、突厥等势力关系的变化,唐朝维持自身力量所花费的代价越来越大,终于引发了防御战线军队的叛乱。这是朝廷未曾预料到的。安禄山叛乱反映了唐朝处理民族问题在政策上出现了某种变化。只要有胡系势力的存在,问题迟早会出现。但遗憾的是,唐朝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现叛乱以后几乎束手无策。
三
安史之乱是以地方节度使的叛乱为表现形式的,但它反映了唐朝胡汉民族势力的协调、融合、分解的关系。太宗开启唐朝的盛世,容纳了周边众多的外族势力,并曾被外族供奉为“天可汗”而景仰。太宗的后代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保持这种大一统的盛世。但是,唐朝自身政治力量发生的变化使得王朝陷入内争而耗损了王朝的精力,特别是周边和亚洲力量格局的变迁,使得唐朝的实力受到了挑战,吐蕃的崛起和进攻打破了唐朝的攻势,王朝转为防守。其防守的局势又被安禄山所利用,引起叛乱。安史之乱与胡人之受重用有密切关系,但不能归结为胡人叛乱。这是因为胡汉问题自唐朝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安、史的图谋有某种偶然性,并不在唐廷的预料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倒是,安、史的叛乱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王权,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受到挑战,地方节度使的力量迅速上升。到了晚唐,朝廷又遭到农民起义的打击,王朝维护正常的运转机制失灵,地方节度使与民族势力迅速地结合,向中央施加压力,唐王朝调节功能丧失,在朱温后梁政权的取代下,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不受任何阻力限制,终于产生了五代十国众多权力的对峙局面。究其原因,分立局面的出现,与民族势力有关系,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这个时期局势的变化,本质上表现为中央王朝对全国,特别是对周边地区控制力的减弱。中央大一统的控制能力,是中国多民族一统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央王朝势力如果强大,国家就处在强盛的阶段,反之就会削弱,对周边控制的能力就相应地减弱。唐朝前后期出现的不同情况,就是这种控制力的表现。
〔收稿日期〕2000-07-02
标签:突厥论文; 唐突厥战争论文; 唐朝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安禄山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安史之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