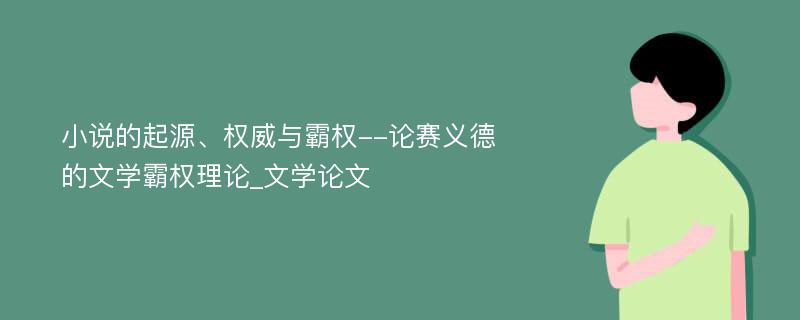
小说的“始源”、权威与霸权——萨伊德“文学霸权理论”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萨伊论文,理论论文,权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Said,1935—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教授,著名批评家。他的批评理论强调政治、社会意识与文学的关系,富有创建性地将文学与霸权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也从萨伊德接连推出的几部理论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源泉。本文试对萨伊德“文学霸权理论”的发端、发展与成熟作一溯源性的评述。
“始源”与“意图”
“始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肇始于萨伊德的《始源: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Method)一书。 所谓“始源”系英文beginning的汉泽,之所以将它译为“始源”, 完全是为了区别于origin(我们一般已经习惯将origin 译作“起源”); 而“始源”(beginning)不同于“起源”(origin)则正是萨伊德在创立“始源”这一概念时的主要批评观点之一。
在《始源:意图与方法》一书的前言中,萨伊德就明确指出:“始源”有别于“起源”,“起源”具有天赐、神话以及特权的性质,而“始源”则是一个由凡人创造的世俗概念,它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在《始源:意图与方法》中, 萨伊德还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叙事(narrative)与文本之间的联系。他通过研究文本是什么以及叙事小说的形式与表征手段是如何在“小说意识”(novelistic consciousness)的左右下去摹拟生命的形成、繁衍和死亡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了一种权威理论,将作者、遗传品质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对于后工业(即后现代)社会中的霸权具有了初步而具体的理解。
在萨伊德看来,“始源”对于作家们来说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理论问题。任何一个作家都知道,为将要创作的作品选择一个“始源”(即下笔处)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因为“始源”将确定嗣后的内容,而且还因为一部作品的“始源”实际上是作家进入“始源”所诱发的内容的入口处。这就使得萨氏的“始源”具有了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萨伊德将“始源”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是为了澄清“始源”(beinning)与“起源”(origin)的异同从而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一部作品的肇始是它的真正始源吗?或者是其它什么神秘之处真正地诱发了该部作品?欲澄清“始源”与“起源”的异同,尚要从弄清“始源”的表层意义着手。这里的所谓表层意义实际上就是人们一般对于“始源”的常识性理解。萨伊德列举了一组句子:
Pride and Prejudice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sentence.
Befor he began to write Hemingway would sharpen a dozenpencil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1〕
在以上这组句子中,虽然“begins;began;beginning”等词所侧重的意义层次不同,但是作为“始源”这一概念的变异形式都指涉的是时间、地点、宗旨或者是行为的某个瞬间,都带有“先”或“前”的含义。换言之,以上所列举的每个“始源”都旨在标明、解释或者界定嗣后的某一时间、地点或行为,都昭示着嗣后的某种意图。这种意图虽然有时未被言明,但是所谓始源就是指在完成某一具有意义的、持续性的成就过程中,其时间、空间或行为上的第一起点。用萨伊德的话说,“始源即有意图的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第一步骤”。〔2〕这实际上是“始源”的深层意义,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及物”的意义;“始源”另有一种表层意义是“静态”的、“非及物”的,它除了“先”和“前”的意义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意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萨伊德的“始源”包容了“起源”(origin)的意义,只是他更侧重“始源”的动态意义,而“起源”则正是他的“始源”所涵盖的静态意义。如果从是否具有意图的角度来划分,则可以将“动态”的始源称作是“有意图始源”,而将“静态”的始源称作是“无意图始源”。
萨伊德至少赋予了“意图”如下两层意义:“意图”首先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包括了由“意图”所肇始的一切新的发展与结果,而不论其发展或结果是多么地离谱和无逻辑性;“意图”还是一种欲以某种独特方式行事的原始智能渴望,这种渴望或为有意识、或为无意识,却每每以某种表述始源意图的话语形式得以体现,并且总是有目的地致力于意义的生产。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始源意图无外是一种容作品的情节发展于其中的“洋洋大观”。〔3〕
萨伊德将“始源”和“意图”的概念引入了对于作家创作态度、创作状态以及文本的世事性的研究之中,他在《始源:意图与方法》中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写道:
若干年前,当我最初对于始源产生兴趣时,就发现始源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文学批评”感兴趣的作家的职业性困惑:他应该如何开始自己的写作?继而我又发现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至少另外四个问题:一,作家在接受了何种训练以后才开始写作?二,作家头脑中带有何种主题开始写作?三,写作的起点是什么,是探寻新的途径还是重蹈故辙?四,文学研究是否具有一种特有的始源?也就是说是否有一种重要的、特别适合于文学研究而又完全不同于历史性的、心理性的或者文化性的始源?所有这些问题都强烈地冲击着当今的作家,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了,它们所代表的绝不是一个专有的“职业性”问题。正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仅涉及到许多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在同样程度上涉及到许多实际性的问题。〔4〕
“始源”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活动。这种内在活动同所有其它的活动一样,都与活动范畴、思维习惯以及亟待完备的条件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联系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也就是说被放置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它们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被重新确定的状态之中。对于“始源”的研究实质上主要是对于某个肇始者所使用的语言的研究,所以我们所能理解的始源的本质状况实质上也是局限于词句性的。虽然始源的本质状况与社会、历史性的时空不可割离,但是它仍旧是具有自己特有的连贯性和延续性的。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始源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就是写成的书面语言——即完整的文本。始源的这种状态性质与社会现实的延续性和连贯性不同,使得它更为内在化。因此,作家的思想、情感和洞察力实际上是创作的始源行为的功能。
“权威”与“骚扰”
萨伊德在始源的概念下考察西方小说时,将小说的创作过程视作是“创始”与对于“创始”的“遏制”之间的矛盾运动。他认为,所有的小说不仅是某种形式上的发现或发明,同时也是将这种发现或发明适应于某种特定的“小说性”阅读过程的方法。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是将小说这种文学类型既看作是自己创作的可行条件,又看作是对于自己创作能力的遏制。萨伊德将这种创始能力称作“权威”(authority),将对于创始能力的遏制称作“骚扰”(molestation)。
“权威”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按照萨伊德的解释,除了具有“控制、指挥、影响等方面的能力和权力”的一般字面意义以外,它与作者,即肇始者、生产者、父亲或祖先等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归纳起来讲,权威的概念建立在以下四层含义之上:
一、任何个体都具有发起、创立的能力,即始源能力;
二、这种能力及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在既有基础上的增强;
三、行使该能力的个体操纵着能力所衍生的结局;
四、权威保持自身的连续性。权威的以上四种特性较好地表达了小说是如何通过作者的写作技巧从心理和美学角度来申明自身的权力的。因此,在书面陈述中,始源、增强、占有和持续就是“权威”的全部内涵。〔5〕
“骚扰”,顾名思义就是权威在被行使时所受到的烦扰,它伴随着权威实施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小说家的权威,无论它如何的完善,都绝对不是至高无上的。所谓“骚扰”,就是个体(无论他是作家还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对于虚构的文本的制约性和对于自己的两重性的意识。用萨伊德的话说:“骚扰对于一部小说中某个人物的醒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论及叙事体小说中的权威,就不可能不论及与权威同生存的对于权威的骚扰。”〔6〕
萨伊德之所以在他的小说始源体系中引入“权威”和“骚扰”的概念,是因为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抗体系最终维系了小说的生命,小说家们不是将它们视作毫无限度地扩展小说创作的条件,而是将它们视作是小说的始源条件。
所谓小说的始源条件即是指小说生成的条件。我们往往将小说的生成和存在看成是想当然的事情,而萨伊德则认为,小说所具有的生殖性的始源能力依赖于三种特定条件的同时存在。第一种特定条件是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认可这样一条原则:任何一种观点或者一些观点的权威都不是完备的和至高无上的。萨伊德指出:
在读者、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三者形成的团体中,任何一者都希冀着另外一种观点的陪伴。任何一者都从另外一者那里听到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新生命始源的声音,即不同于自己的观点;然而,任何一者(尤以小说中的人物为甚)都在这种伙伴关系中渐渐意识到一种对于自身真实性的系统化的背叛。〔7〕
萨伊德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制度解体的前提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劳动者若要成为直接生产者,只有在他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不再隶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实现:
他要成为劳动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制度,摆脱行会关于师傅身分、行会理事会的规定以及行会学徒法等等……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8〕
萨伊德认为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匹普是这一法则的极好的体现。匹普自封为绅士,刻意地追求绅士的生活方式,但是实际上却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弃儿——流放犯人麦格韦奇。由于麦格韦奇的策划,匹普才得以过上绅士般的生活。匹普的“远大前程”是依赖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支持的,小说既给予了匹普拥有远大前程的可能性,同时又限制了匹普的远大前程,因为匹普所拥有的所谓远大前程其自身是有局限性的。具体地讲,如果没有恩主的赐予,匹普既不可能拥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前程,匹普的自由是依附于一个匿名的恩主的。
小说生成所需要的第二种特定条件是一种貌似自相矛盾的观念——真理只有通过间接的方法才能得到,即谬误使得真理更为正确。换言之,更为正确的真理是通过淘汰的方法将近似于真理的成分筛选掉后而得到的。在萨伊德看来,处于小说中心的人物与经典戏剧中的人物不同,并不是在创作之初就是家喻户晓。所有小说中的人物如汤姆·琼斯、鲁宾逊·克鲁索等,无论他们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物,都是作者刻意塑造的原始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会与某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相仿,但是这种亲缘关系是间接性的;因为无论我们从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发现了什么样的品质,我们都可以从该人物的个人权威那里找到根据。
萨伊德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得益于维柯(Vico)的权威理论。维柯认为“权威”起源于“财产”,所以权威的原始意义就是财产,而财产的所有权取决于人的意志和选择。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的财产,其意义取决于人类的最初意志和选择,真理的意识便由此而来。〔9〕所以说, 作为作家的财产的文学作品则必须遵循作者的意志和选择的权威。
萨伊德认为,在个人权威产生之前有一种空虚感,对于这种空虚感的恐惧就是小说生成所需要的第三种特定条件。这是自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以来就有的主题:虽然海船失事将鲁宾逊置于荒岛险滩的困境,但是正是在这种境地中鲁宾逊“诞生”了。死亡的威胁促成了鲁宾逊的诞生,小说也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说,鲁宾逊在落魄无援的状态下所感受到的死亡的威胁以及他随即获得、并且日渐成熟的对于荒岛这片领地的权威(以对于“星期五”的驯化、征服为标志),为鲁宾逊这个人物形象的维系提供了保障。其他一些属于被打乱了正常生活秩序类型的小说人物如孤儿、社会弃儿、流浪汉、暴发者等等也都是在这种前提下诞生的,他们不是被社会排斥就是身份背景不明。例如,在《远大前程》中,若不是由于一种莫名的空虚感的排斥,匹普这个人物便不可能存在。
小说的生殖能力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在逃避死亡的欲望中获得虚构的权威,因此小说的叙事由于这种生殖能力的存在而得以持续下去。不难发现,许多英国经典小说如《鲁宾逊飘流记》、《远大前程》等都是建构在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之上的:由致力于开创对生活的再现开始,而最终揭示出小说中的权威原来只不过是一种“借来的权力”。〔10〕“在小说中,权威的最高目标就是提供一种意向,这种意向总是试图避开旨在限制、挫伤甚至是彻底摧毁权威的障碍。”〔11〕亦即“权威”与“骚扰”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小说的始源与存在的前提。
霸权与小说
霸权,在传统意义上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本义是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和垄断关系。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其著作中给霸权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霸权作为一个文化理论术语已经渐渐淡化了其暴力和强制的含义,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霸权系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优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推行为其他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准则。
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对霸权的定义是:霸权是关于生活全部的一整套规范与期待,它是我们的意识与能量的配置以及我们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感知;它是一套既寓意义与价值于其中又形成意义与价值的经验化的系统。 〔12〕
而萨伊德的“霸权”最初则是通过“东方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述的,他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中给予“东方主义”这个并不算全新的术语两层全新的“霸权”含义:东方主义还是一种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之上的思维方式;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自有殖民活动以来对待东方世界的共同规范,或者说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宰割、重建和话语权力压迫。
显然,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支配关系与霸权关系,它包容了涉及到美学、经济、社会、历史以及哲学等领域的不平等的话语交流。就文学而言,“东方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历史、文本相互关系的极好的范例,而且也表明了东方在西方世界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是如何将东方主义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逻辑关系等与文学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13〕。
虽然《东方主义》并不是以文学批评著作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的,但是它无疑令当今一些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家们找到了理论源泉。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积极鼓吹者斯皮瓦克(Spivak)曾这样评价该书:
萨伊德的这部书不是关于边缘性的研究,甚至也不是关于边缘化的研究。它旨在研究如何建构一个用于研究和控制的客体。然而,由萨伊德的著作所直接引发的关于殖民话语的研究已经花开满园;在这个花园里边缘人得到了评说和被评说的权力,甚至得到了声援。现在它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并且是不可分割的)的组成部分了。〔14〕
如果说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通过将东方主义当做是“西方的话语”来研究,对于霸权的概念进行了独特的观照的话,那么他15年后(1993 年)出版的另一部理论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 (Culture andImperialism)则标志着他文学霸权理论建构的完竣。
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分析了霸权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权关系”之间的亲和性。他认为帝国主义系指宗主国家对于远方领地进行统治的行为、理论以及态度;而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向远方领地进一步扩张的必然产物。宗主国与远方领地之间的控制或统治关系就形成了所谓帝权关系。这种帝权关系,无论其形式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可以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政治合作或者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依附关系来实现。在当今的世界语境之下,以武力征服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的领土殖民活动已经结束,然而帝国主义霸权依然在广义上的文化领域内存在。〔15〕
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试图探索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帝权扩张与其整体民族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着意研究了19世纪英国的小说,因为小说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美学形式,在帝国主义霸权态度、霸权参照系以及霸权经验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英国小说中,对于帝权关系的隐喻俯拾皆是,萨伊德认为所有这些隐喻就构成了他所谓“态度与参照系结构”(a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reference)。〔16〕因此, 萨伊德在该书中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些作品是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如他自己所说:
我在整个这本书中试图说明一个问题:文学总是在表明自己是如何从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的;因此文学便构成了威廉姆斯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支持、参与并且巩固着帝权的实施……〔17〕
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是萨伊德在《始源:意图与方法》、《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三部著作中频繁提及的实例。《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匹普早年曾经帮助过罪犯麦格韦奇,麦格韦奇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发了财,便暗中施舍给匹普一大笔钱使他过上了向往已久的绅士生活。但是麦格韦奇非法潜回伦敦以后,匹普对他十分厌恶,因为他是从澳大利亚跑回来的人。澳大利亚作为18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放逐罪犯的殖民地,时至狄更斯的年代虽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领地,但是在狄更斯笔下,麦格韦奇只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决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重返家园。在萨伊德看来,狄更斯对于麦格韦奇重返祖国的限制不仅仅是惩罚性的,而且是带有极强的帝国主义霸权性的。
《黑暗之心》历来被评论界认为是康拉德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彻底的揭露和谴责。小说所描写的叙事人马罗的刚果之行,不仅是进入黑非洲中心的航程,同时也是一个探索自我、发现人的内心黑暗世界的历程。主人公科兹是个英、法混血儿,在小说中显然是欧洲帝国主义霸权的象征。他贪婪、暴虐,恣意愚弄、奴役和杀戮非洲土著居民。
萨伊德认为,帝国主义的霸权态度被非常巧妙地编织进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形式。康拉德试图向读者展现一个事实:科兹的抢掠行径、马罗的非洲之旅和小说的叙事自身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行使对非洲(或关于非洲)的霸权统治和意志。康拉德的这种叙事形式衍生出关于后殖民语境的两种观念:
一种观念给予传统的帝国主义霸权以广阔的扩张范围,即以正统的欧洲或西方帝国主义的观点来描述世界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后殖民语境中巩固自身。换言之,西方殖民者虽然已经离开了他们过去的殖民地,但是他们不仅将它们作为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将它们视作是“意识形态地图上的地点”,继续从道德与思想方面实施统治。
第二种观念则不像第一种观念那样显出强烈的霸权色彩,如同康拉德看待自己的叙事一样,这种观念仅适应某一时刻或某一地点,而不是绝对化的观念。萨伊德进一步解释道:
尽管康拉德笔下的叙事人都拥有欧洲人的名字和作派,但他们并不是通常那种不善反思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见证人。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帝国霸权观念:他们思索、他们担忧,他们为自己是否能够使它成为规范化的东西而担忧。然而它从来就不是规范化的东西。康拉德为了说明常规的观念与自己对于帝权的见解之间的差异,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断提醒读者注意各种观点与价值是如何通过叙事人语言的错乱而被建构(和被解构)的。〔18〕
说到这种语言的错乱,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萨伊德所提出的“权威”和“骚扰”这一对概念。叙事人语言的错乱实际上就是由“骚扰”所致,因为任何一个叙事人或者作家的思想观念(即权威的体现)都不是至高无上、一成不变的,它必将受到文本结构和个人双重性的制约(即骚扰)。这在《黑暗之心》中的叙事人马罗和主人公科兹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马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同时在他身上也有着科兹的影子,有评论家认为科兹代表了马罗精神上受到抑制的邪恶部分,马罗对科兹的探测因而也是对自我心理中黑暗部分的发现。〔19〕而科兹本人则既是帝国主义霸权的作恶者,又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受害者。
萨伊德认为康拉德的作品包容了帝国主义不相同但又紧密相联的两个方面:建立在对领土强行掠夺能力之上的一种强权观念和对于强权观念的伪装、欺骗行为。这种伪装是通过在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作恶者之间建立一套关于权威扩张的辩解体系来实现的。
霸权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是萨伊德文学霸权理论的核心问题。他的“态度与参照系结构”是维系两者间关系的纽带,因为它从被认为与霸权无甚大关系的早期小说和关于霸权的后期小说中间找到了连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帝国霸权也就没有今日之欧洲小说。在仔细考察了欧洲小说的始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内部的叙事权威模式与隐含着霸权趋向的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趋同性。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与霸权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关系。
通过对于萨伊德的文学霸权理论的发展脉络的追溯,可见无论是小说的始源、权威,或者是霸权都突出强调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将文学创作视作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活动。萨伊德在美国是较早接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原则的批评家之一。近十几年来他的批评理论越来越显露出其受到以雷蒙·威廉姆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创作状态以及文本的世事性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他认为以往的文学批评或过多地夸大了读者对于文本阐释的无限制性,或把文本与作者和实证割裂开来。他的“态度与参照系结构”旨在考察文本与作家的态度和文本的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作家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念是如何通过文本形式得以申明的。也就是说作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倾向必将通过文学作品的霸权倾向表现出来。
从理论谱系上来看,萨伊德的文学霸权理论可以追溯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尼采认为,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事物之上;因此,一切知识与意识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世界上并没有绝对至高无上的真理和客观知识。某些哲学观点或科学理论被看作“真知”,是因为它们恰好迎合了现行的知识体系、政治权威或统治精英所认可的规范。在话语与权威的关系问题上,萨伊德与福科的理论也完全一致:话语总是与拥有权威的社会机构相关,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艺术领域,权威是通过话语获得的,或者反过来说,话语是人类对于一切事物的“篡改”。
萨伊德的文学霸权理论是一套实践性很强的体系,它特别适用于分析、阐释19世纪欧洲的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因此在理论性和适应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似乎很难将他的文学霸权概念简单地归属于某一个学派或某一种主义,它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到今日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西方文论已经不再是孤立地考察实证、文本和读者,而是转向在伦理、道德的语境下研究实证、文本和作家三者之间的关系。
注释:
〔1〕〔2〕〔3〕〔4〕〔5〕〔6〕〔7〕〔10〕〔11〕Edward W.Said,Beginnings:Intention & Methdd,Columbia Univ.Press,p.4,5,12,6,83,84,88,94,95.
〔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第769页。
〔9〕参见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73页。
〔12〕Raymond Wi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Press,1977,p.110.
〔13〕Edward W.Said,Orientalism,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24.
〔14〕G.C.Spivak,Post—structuralism,Marginality,Postcoloniality and Value,in Literary Theory Today,ed.by Peter Collier et al.p.221.
〔15〕〔16〕〔17〕〔18〕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Alfred A.Knopf,1993,p.9,62,14,29.
〔19〕参见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年,第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