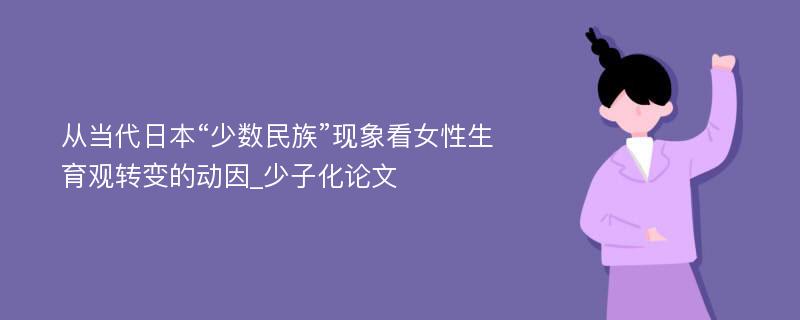
从当代日本“少子化”现象析女性生育观变化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子论文,动因论文,日本论文,当代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人口现状
最近,惯以极端言行惹是生非的东京市市长石原慎太郎,又因诬说女性不生孩子就是“老巫婆”等等,而被119名日本女性向法院提起诉讼。石原此次生事也是事出有因,其背景即来自本国形势严峻的“少子化”现象。
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女权运动而发生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子化”不同,日本的“少子化”问题由来已久。从上一世纪初开始,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就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最近50年中,除战败后的1947年到1949年因老兵复员返乡而出现人口出生高峰及由此带动的20年后的1970年代初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外,人口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一般来说,人口生育率保持在2.1‰左右的话,社会人口规模可以维持良性置换。但是,1989年,这一标志妇女一生平均生育数的记录,下降到日本有人口统计记录以来的最低点——1.57‰。因其带给日朝野上下的震惊,丝毫不亚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而被称之为“1.57危机”。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以《少子化社会的到来及其影响与对策》为题,发表了平成4年《国民生活白书》,以警示国民。但是影响甚微,丝毫没有阻挡住“少子化”匆匆的脚步。适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数由1989后的1.57‰又下降到1991年的1.53‰后,仍一路下降,1995年降至1.42‰,1998年1.38‰,1999年更降至1.34‰。2000年虽有上升,但仍滞留在1.36‰上(日本劳动省,2000)。
上述的日本“少子化”现象所引起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日本总体人口基数的减少。据日本厚生省预测,日本人口总数将由2000年的12689万人,在2007年达到12778万人的最高值后,转呈下降趋势。50年后(2055年前后)将降至一亿以内(推算为9600万人)。100年后,全部人口总数将只有现在总数的一半(推算为6700万人)。
由于人口基数的减少,若干年后日本社会将面临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的问题,据1997年日本劳动省所进行的未来劳动力人口推算,日本社会劳动力人口将由1997年前后6700万人下降为2005年的6300万人(山本肇,1998:30)。
更令石原慎太郎在内的日本决策者头疼的,不单单是“少子化”问题,而是与少子化“齐头并进”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1997年,日本全社会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年轻人的总数。根据日本厚生省的推计,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1990年为12.1%,但是这之后速度加快,预计2010年为21.3%,2020年将达到25.5%。
同时,65岁以上的高龄者人口与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在职劳动力年龄人口相比,1990年为1∶5.8,而2010年为1∶2.9,2020年将达到1∶2.3。换句话说,一位6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社会保障费用,在1990年的时点上,还由将近6人的在职劳动力承担的话,2020年时的日本则仅有2.3人的在职劳动力来承担(日本经济企划厅,1992)。由于后续劳动力人口不足,劳动力的年龄构成也将主要由中高年龄层劳动力构成。
人口基数缩小、劳动力人口不足、税收负担与社会负担过重,势必导致国力衰弱,有关人士还指出了“少子化”将会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其他种种后果,如全日本社会独生子女的增多,也将难以避免类似于中国的独子女的“社会性欠缺”等社会病理的发生,等等。
日本女性生育观变化的动因
1989年的人口出生危机后,日本朝野上下各方人士就其产生的原因与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自然,矛头大多指向女性。他们认为出生率的降低,“罪魁祸首”毫无疑问地在于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独具生育能力的女性。笔者认为,引起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决不会只在女性一个方面,而是社会因素多个方面的综合反映,即“综合症”。人口生产毕竟不是一件仅靠女性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人口生产的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同近期日本“少子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女性的高学历、就业率,一直被认为是引起日女性包括生育观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战败不久,日本便迎来了近代第一个经济高速成长期。急需劳动力的缺口为女性所填充,因而实现了女性就业率的迅速提高。同时,素有重视教育传统的日本,女性素质的提高被看作是“优生优育”的前提,在战后的民主政治气氛中,女子教育更受重视,义务教育已做到全民普及。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即,女性一结婚,最迟至怀孕就得辞掉工作,回归家庭,而且,这一做法也受到政府的间接鼓励。但是,女性的高学历、高就业率的实现,使这一做法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的职业女性,即使结婚也不想放弃现有的工作,或不想长期放弃工作,放弃自我追求。因此,尚未结婚的她们尽量推迟婚期;已经结婚的她们尽可能地推迟生育,或尽可能地减少生育数,缩短育儿期,以争取尽快回归职场、回归社会。
其次,家庭、工作负担过重,也是导致女性生育观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定程度的教育过程完成后直接回归家庭或在短期工作后回归家庭的女性,在日本被称之为“专业主妇”。女性回归家庭,使得家务、育儿等家务劳动由其全部承担也成为理所当然。但既使是“专业”的,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买、汰、烧,也委实不是一个小负担。据NHK与日本总务厅每五年一次的“生活时间调查”,“专业主妇”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6小时23分,比欧美家庭主妇5小时29分长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同时进行比较的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丹麦、荷兰、芬兰等七个国家中,日本人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36分,是最短的。最长的是英国,8小时30分。日本女性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7小时20分,远远低于其他六国女性的8小时18分。其中,日本职业男性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21分,职业女性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零5分,“专业主妇”是7小时零8分。
也许与上述“结婚后回家去”、“生孩子回家去”的不成文的约定俗成有关。由于女性的家庭回归,使家务、育儿等主要家务劳动在每个家庭内部自行消化,因而相应的社会公共设施,如育儿设施与制度极不完善。托儿所、幼稚园少,子女入托难的问题,困扰着不少家庭和职业女性。而迟至1992年,日本政府才颁布、实施了一部《育儿休假法》。而实施近十年来的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不少职业女性反映,迫于职场的环境气氛与因经济不景气而日益恶化的就业形势,使她们要么象以前一样辞职回家,要么有假也不敢休。
由于日本职业社会的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习惯,加上“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日本男性的家务劳动的参与度始终很低。据资料显示,日本30岁左右的男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1986年前后仅为6分钟,10年后的1996年是8分钟。1998年日本厚生省的家庭调查表明,仍有80%的男性几乎一点家务都不做,即使是在双职工的家庭中,也有50%的丈夫表示今后没有参加家务劳动的打算。
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女性的肩上,除了“家务”、“育儿”和“工作”这三副担子外,还将增添“护理”的重任。在一份有关“谁是老年与病弱者护理与照顾的主要承担者”的问卷调查中,被护理者为男性的情况下,护理的主要承担者依次为:配偶(即妻子)72.6%,儿媳12.4%,女儿9.0%;而被护理者为女性的情况下,护理的主要承担者依次为:儿媳40.7%,女儿31.1%。可见,不管被护理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护理的承担者主要是女性。
压力大、负担重的现实,迫使不少女性在事业与生儿育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进而影响到年轻一代女性的婚姻观与生育观。不少年轻女性干脆拒绝结婚,甘心做轻松快乐的“单身贵族”。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正是“单身贵族”的出现和流行,才是近期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最大原因。
还有年轻女性虽然有结婚的打算,但又不想过早地陷入繁杂的家务中去,于是尽量将结婚推迟,而形成“晚婚族”。据2001年《国民生活白书》统计,日本男女平均初婚年龄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平均初婚年龄,1947年男性为26.1岁,女性为22.9,而2000年则分别为28.8岁和27.0岁。初婚年龄的提高,必然导致头胎生育年龄的提高,因为考虑到“大龄危产”及因年龄大而产生的育儿过程中的体力、精力透支等因素,不少人修正和减少了她们原先所预想的生育数。调查也显示,超过35岁而做流产或妊娠中止的人数陡然增高许多。
有女性运动者提出,女性的“少生”与“不生”的行动,正是对社会长期以来加于她们的“不公、不平”以及对她们的呼声“不理、不睬”所能作出的“无言的呐喊与反抗”。
再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导致“养儿防老”的功能趋于弱化。另外,育儿经济负担重与青少年问题频发、教育难而导致的精神压力等,也影响到女性生育观的变化。
从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在《国民生活质量调查》中,就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所做的调查来看,认为“养育孩子的费用负担太大”的,占54.6%,“育儿设施与制度不完善”的,占51.2%。另外,有24.7%的人认为“不结婚的人增加了”,19.9%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变糟糕了”,19.3%的人认为是“晚婚的原因”,还有17.7%的人认为是“居住条件太小”的原因。
在日本,抚养子女的费用对于一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的教育费和生活费,全部加起来大约需要2000万日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则需要近200万日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负担是相当重的。因为不少日本家庭都还同时负担有住房按揭贷款。而实际上,为人父母的责任和负担也不是只到子女大学毕业为止。子女的结婚费用,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根据日本1992年的《国民生活白书》的统计,1991年的平均结婚费用为768.5万日元。其中,父母的援助份额占40.3%。因经济不景气,1998年平均结婚费用虽下降至550万日元左右,但父母的援助份额所占的比例,却并无太大变化。
由于在日本为数不少的女性因为结婚或生子而不得不辞掉工作回到家庭,这样一来,在以工作年限为基准确定日后年金(养老金)额度的社会保障体制下,辞掉工作就意味着年金的减额。虽然日本也有家庭主妇年金制度,以保障家庭主妇老有所养,但其所得额与正常年满退休的所得额之间是有差距的。如果把这一部分的损失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育儿的经济成本将会更高。
除上述抚养子女承受的精神、经济方面的压力以外,在咨讯泛滥、信息爆炸的今天,青少年的教育难也让不少人望“生子、育子”三思而却步。
近几年来,少年犯罪率上升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低龄化、凶恶化也成为少年犯罪的新特点。1999年日本文部省的学校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除去因病或因经济原因等不能到校的情况外,拒绝上学的中小学生人数已达到13万人。其中,小学生约2.6万人,中学生约10.4万人,平均每41个中学生中就有一名拒绝到校上课的学生。另外有近三成的小学校,有课堂秩序混乱,无法上课的情况发生(西日本新闻,2001,10.3)2001年日本总务厅的调查资料显示,有70%的家有未成年孩子的母亲表示对育儿没有信心。
在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养儿防老”的功能性渐趋弱化的今天,女性自主性地减少育儿数,从而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是否可理解为女性在“育儿成本”与“自活成本”之间权衡之下所作的选择呢?
以上是对影响当今日本女性生育观的因素所作的分析。包括东京市市长石慎太郎在内的不少人认为,“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主要是因为女性的社会责任感淡漠,竟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甚至有人说“不生孩子的女人应该逮捕”。相比之下,石原的“巫婆论”还算是客气的了。但是,这是一个强调“个性”与“自我”的时代。“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涉及女性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问题,而且,从上述分析来看,影响女性生育这“水银柱”升降的,不仅仅是因为“水银”具有“活泼”的属性,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即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