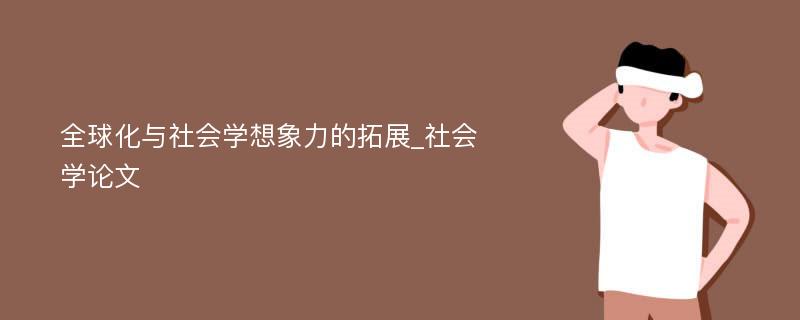
全球化与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想象力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全球着眼,从地方着手”(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行动口号了。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一种意识形态,从学术探索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一种分析框架,一种想象空间的拓展。
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中曾有这样的论断:“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那么,在社会学中,这种“范式转换”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当然,全球化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现象,一个正在热烈讨论的话题,现在就要全面评估这种范式转换,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再说,社会学本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元范式”的并存。如果要说社会学中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范式转移,那就必须是对所有现存范式中的“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的突破。
不过,尽管全球化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但就其对于“社会学传统”的挑战而言,确已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来。在此,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即对社会学得以安身立命的所谓“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应当如何看待?事实上,我们将看到,全球化对于社会学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将想象的空间扩展到民族国家之外,而且也涉及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民族国家框架的局限
最宽泛地看,社会学被视为“有关社会的研究”。但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Touraine)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社会学还是有关社会的研究吗”?这种质问方式,或许会让许多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感到诧异:社会学不是有关社会的研究,那还能是什么?图雷纳自有说法,“在早期阶段,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研究;但是现在,应当将之界定为有关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研究”(注:Touraine,Alain,"Is Sociology Still the Study of Society?",in Beilharz,P.,and et al.(eds.),Between Totalitarianism and Postmodernity:A Thesis Eleven Reader,the MIT Press,1992,p.178.)。因为以往所谓社会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秩序的意象,同民族国家的成功确立密不可分。“如果社会学将现代性界定为理性化、世俗化和祛魅化,也就消除了社会生活所有的内在统一原则,那么社会系统的统一性就不能不是外在的;它必定是国家。惟有国家才能整合社会行动者,因为市场将他们分离开来,阶级关系让他们相互对立,理性个体主义把他们化为原子”(注:Touraine,Alain,"The Waning Sociological Image of Social Lif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xxv,1-2,1984,p.36,p.)。以国家为社会的界限,并不纯粹是理论上的建构,也有其现实基础,边境海关办事处就是标志。当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这种将社会与民族国家相混同的做法,变得极为不合时宜。所以,图雷纳多年来都希望“以一种有关行动者的,甚或是有关主体、行动系统、阶级关系和冲突,简言之是有关社会运动的社会学,来取代有关社会的社会学”(注:Touraine,Alain,Return of the Actor: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158.)。
如果说图雷纳是从社会学关注的实质内容上,意识到社会学必须突破原有的潜在假设,那么沃勒斯坦等人则从反思学科发展及其基本范式的角度,更为彻底地揭示了束缚社会科学想象力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现代社会结构不言而喻地处在现代国家之内”(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但是,也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拒绝承认国家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再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关键性的建制,一项对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有着深刻影响的建制”(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页。)。我们所不需要的是下述假设,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我们不仅不应在社会分析中抛弃国家——即便是在超越民族国家或者后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仍然是全球舞台上最重要的行动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恢复“国家学”。因为,在原有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国家尽管是不证自明的界限,但恰恰对于这个包含一切的容器的行为缺乏足够的研究。
根据沃勒斯坦等人的观点,“国家学”主要是19世纪在日耳曼地区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学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地强调个别性,而是探寻制约着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页。)。但是,这个韦伯也曾充当了领军人物的领域,最终却由于“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怯懦而败下阵来”,被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取而代之。
不过,我们觉得沃勒斯坦等人关于这个学科的败落的解释,仅从是否关注普遍规律的角度着眼,是不够全面的。所谓“外部的进攻”,主要是指英国和法国看待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学术传统。我们知道,在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在法国,则主要由于政治革命而打乱了既定的社会秩序。所以,两国的学者都对社会中所蕴涵的巨大的自主力量,怀有独特的兴趣。相对来说,德国则是一个较晚完成统一的国家,而且是通过王朝战争立国。所以,当“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分析范式在英、法大行其道的时候,德国人坚持的是“有机国家论”。公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的框架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即弱小的国家政权面对强大的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被看作是一种零和关系。而在所谓的有机国家论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有机身体的大脑、心脏和四肢的关系一样,是无法分割的。故尔,在德国人的学术思想中,一个民族内的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同生同灭的有机整体(注:参见丁学良:“社会转型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载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22页。)。这种取向上的分歧,加上德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失利,“国家学”终于陷入沉寂。而在整个社会学传统中,“社会”突显了出来,国家则沦为一种背景。国家的问题,尽管在所谓“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对于国家本身的探究,似乎从学科分工的隙缝中漏掉了。
但事实上,无论是为理解社会内部的问题,还是分析国际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国家都应视为一个至关紧要的行动者。而在如今居于主导地位的二分视野中,国家与社会一方面是截然分开的,另一方面又将社会隐含在国家之中,于是,许多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比如在民主问题上,当今所谓民主的国家,仅将平等适用于内部,而把各种“他者”置于平等之下。由此不难理解,遵循公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模式的美国,何以经常奉行“双重标准”,即对外采取一种霸权态势。这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这种二分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值得反思的。
将社会从国家的框架中释放出来,并不单纯是学术反思的结果,其实也是对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倾向。我们知道,“领土原则”不仅与“主权原则”和“合法性原则”,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不过,应当注意到,领土原则的全球化恰恰是这一原则生效的前提),而且“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注:[德]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在社会科学中,这种领土倾向体现为:只有在将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组织与国家所控制的领土等同看待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和组织“社会”、“文化”、“民主”、“经济”这些在一个整体中相互联系又具有不同功能的领域。民族国家就是领土国家,是“不在场者的共存”,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通过民族的集体同一性为不在场者的社会共存划定了界限。
在摆脱了虚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规定和限定之后,则就可以看到“全球行动者”了。其实,对不少人来说,已经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人生层面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全球时代,“个人生活意味着一种无定居的生活,即在汽车、飞机和火车上,或靠电话和因特网生活……人们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没有回答却又自动回答,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送并接收人们用技术手段在世界其他地方发送和储存的信息。人生的多地域性、个人生活的跨国特征是民族国家主权遭到侵蚀的另一原因。……迄今为止,人们总是把社区、家庭、朋友或其他各种能够感受到的共同体与地域联系起来,而现在我们却日益生活在这样一种状况中,即不再能说我们所经历的共同体存在于某个地方。相反,我们所处的地方未必与共同体有关。我们可以完全游离式地共存,但同时又是不受地域局限的网络的成员”(注:[德]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当然,对于引文中的“我们”,我们可不能想象为所有的人类。这种意在将“我们”等同于全体人类的叙述策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过,从这一部分“我们”来看,“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验,归根结底是“不在场者的共同体”或“不在场者的在场”。
活跃在全球舞台背景上的行动者,是多层面的,从个体、社团、国家、跨国公司到国际组织,乃至恐怖组织,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行动,如今都或多或少需要以全球作为行动和思考的参照框架。那么,这个所谓的全球舞台是怎样的呢?到底具有哪些特征?我们又该如何去勾画?下面我们所探讨的,仅是社会学如何建构全球舞台的系统特征?即,当社会学的最终参照单位不再局限于以往所谓的社会,而将目光投放到全球体系时,这个全球体系对于行动者到底呈现出哪些“结构性制约”(structural constraints)?这种结构性特征也应该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维度。
全球体系的结构想象
常见的社会学理论谱系,几乎都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开创了把世界作为单个体系来分析的先河。其实,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世界主义视角,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再明显不过了。无疑,坚持“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的沃勒斯坦,本身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学统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使他获得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称号。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视角,在学院化的社会学中,特别是曾经主导着对社会系统的理解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被淡忘了,社会秩序被等于民族国家治理下的制度体系。当然帕森斯的一个学生,维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全球社会学”,主张跨越国家边界,将世界视为一个“单一的系统”(注:Moor,Wilbert.E,"Global Sociology:the World as a Singular Syste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6,Vol.LXXI,No.5,pp.475-490.)。但由于摩尔基本上是从结构与文化趋同来立论的,所以,这种主张没有特别的冲击力。
虽然沃勒斯坦不是将世界视为单一体系这种观念的发明人,但在使这种视角成为一种影响甚大的观察方式上,确乎无人能出其右。他认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即“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在世界帝国中,“存在着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但“在现代以前,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了”(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而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存在了500年,仍然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就是沃勒斯坦主要考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资本主义能够一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而作为一种分析上的乌托邦设想,沃勒斯坦认为这世界体系最终可能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
不过,沃勒斯坦主要还是关注现存的世界体系的形式。作为“广泛劳动分工的实体”,世界经济体具有自身的结构,即可以分为“核心国家”、“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沃勒斯坦认为,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据优势的地区,是所谓的“核心国家”:“在这类国家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创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现象被称为一体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与此对应的则是边缘地区,而之所以被称为是“地区”而不是“国家”,就因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特征就是本土国家很虚弱。介于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则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看来,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起到转移政治压力的作用,否则“处于边缘地区的集团有可能直接反对中心国家和那些利用中心国家机器在国内操纵的集团”(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所以,世界经济体的分工实际上也就是各种职能性任务的层级体系,其中凡是需要较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由较高层次的地区来承担。不仅如此,“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注重国家之间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贸易关系所整合起来的体系,并没有使沃勒斯坦忽视国家内部的结构。“如果世界体系是仅有的真实的社会体系,那么,就必须把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巩固和政治上所起作用必然被看作是世界体系的要素。由此可见,在分析一个阶级或者一种身份集团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是它们的自我意识的状态,而且是它们自我限定的地理范围”(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尽管沃勒斯坦主要是分析世界体系形成的里程,所谈论的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些结论,却不乏启发。沃勒斯坦认为,“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从社会各个阶层接纳其成员的过程……中产阶级声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他们所采用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发展民族感情,这为他们的主张披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龙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谈论全球化肯定避免不了要讨论世界体系理论,而沃勒斯坦本人却认为所谓“全球化的话语”,比如国家主权已然衰落、任何人都无力抵抗市场规则、文化自主的可能荡然无存、我们所有的认同的稳定性都成为问题等等,“是对当今现实的一个巨大的误读”(注:Wallerstien,I.,"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0,Vol.15(2),p.250.)。他宁可称现在是“转型的时代”,不是落后国家需要赶上全球化精神的转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要转化为另外一种样子。不过,这种“系统性的分叉”(systemic bifurcation)将导致怎样一种新的结构,沃勒斯坦认为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或许能够容许人类更多的介入和创造。
其实,全球化是否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现象,主要还是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但是,将全球作为一个体系来分析,于今不仅更加适当,也更加迫切。我们不能因为从长时段来审视世界体系的轨迹,就忽视当今全球体系的独特性。我们固然不能斩断历史——其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中,“其他”(the rest)都已成为“没有历史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延续性恰是西方之外的“我们”所不应忘怀的——但也没有必要因此而忽视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体系的突生性。
如果说沃勒斯坦从纵向来叙述全球体系的历史形态,那么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的分析框架虽然简单了一点,但也可以看做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横向解剖。斯克莱尔拒绝以“弹子球模型”来分析全球体系,这种模型只看到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实还是一种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ist)。在他看来,“国家的地理意象”,必须让位于“系统的行为意象”,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全球体系中所发生的一切。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无疑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却是跨国力量的结果,不能单从一个国家来理解。斯克莱尔分析全球体系所使用的模式的基础,是跨国实践,即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所从事的并跨越国家疆界的实践。模式其实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在经济上,跨国实践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担纲;在政治上,存在一个“跨国资本主义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则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挂帅。
这个模式除了将全球作为一个体系来加以考察外,还提出了“跨国资本主义阶级”的概念。在斯克莱尔看来,跨国资本主义阶级之特征,在于他们视自身的利益和/或他们祖国的利益,在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最好地实现。从构成上看,他们主要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地方成员、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官员、拥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和专业人士、消费主义精英。斯克莱尔还指出,这个阶级将越来越把自身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的利益等同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反对自身社会的利益。斯克莱尔还认为,支配全球体系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注:Sklair,Leslie,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Prentice Hall,1995.)。应该说,斯克莱尔的观点还是颇具见地的。消费主义虽然具有西方的源起,但是借助于“美好生活”的诱惑以及其它扩散机制,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旋转轴心,消费主义在向其他地方传播的时候,逐步淡化了“西方的”色彩,尽管西方在许多方面是消费时尚的极具优势的引导者。忘记西方起源,可以克服民族主义的障碍,使消费主义畅行无阴地在全球蔓延。更主要的是,以消费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变成了一套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意识形态实践。而组织并促进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的,是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主义阶级。过去曾被认为是纯粹文化的东西,现今愈来愈多地由商人兴办。
当然,斯克莱尔对于文化的这种狭义的理解和处理,在同样以全球体系为分析焦点的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看来,恐怕实在是难以接受。罗伯逊大致可算是在“文化研究”纲领下探索全球化的问题的。在他看来,全球化体现为世界的压缩和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即全球相互依赖性和全球整体意识的增强。具体而言,则是全球人类状况的四个要素的相互渗透的增强。所谓“四个要素”,即个体“自我”(selves)、“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由民族社会所构成的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以及“人类”(humankind)。要素间的一体性的增强,具体又体现为“个体”和“民族”的参照点的相对化(relativization)(注:Robertson,Roland,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显然,罗伯逊最终还是试图立足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来提供一幅全球化的图景。所以,他用来批判别人的一段话,好象特别适合于他自己:“许多社会学家乐于同意社会学应当‘国际化’和‘去种族中心化’,但他们显然并不怎么想对经验的、历史地形成的全球场域本身,进行直接和认真的研究”(注:Robertson,Roland,"Globalization: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in M.Featherstone,S.Lash and R.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London:Sage,1995,p.26.)。
应该说,赫尔德(D.Held)和麦克格鲁(A.McGrew)等人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为复杂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分析全球化的框架。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即是“全球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以及加速”,具体表现为:“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国民经济和社会卷入国际活动强度的不断加强,因此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事情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距离遥远的行动”(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社会能动者行动的方式,一个地方的能动者的行动对于距离遥远的其他人能够产生有意或无意的重要后果)、“时空压缩”(全球化似乎缩小了地理距离和时间,在一个即时沟通的世界中,距离和时间似乎不再是人类社会组织或者交往模式的主要制约(注:[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他们又认为,“全球化处在一个具有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的连续统一体上”。其中一端是在本土和国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另外一端则是在区域和全球交往的更广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越边界。因此,相较于“全球化”而言,“本土化”、“国家化”、“区域化”、“国际化”就属于更具空间界限的过程了。但就根本而言,它们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复合和动态的关系。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在当代才出现的崭新现象。所以,他们提出了区分全球化历史形态的时空维度:“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注:[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其中广度、强度和速度相对比较容易衡量,而所谓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所以他们又分别从“决策”、“制度”、“分配”和“结构”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决策影响”是指受全球力量和条件影响的政府、公司、集体以及家庭所作的政策选择带来的相对成本的收益程度;“制度影响”是指组织和集体日程反映有效选择或者选择范围的方式;“分配影响”是指全球化塑造社会中以及社会之间的社会力量的方式:而“结构影响”是指全球化限定了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与行为的模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四种维度来勾画全球化的组织轮廓,即:“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全球网络和权力实施的制度化”、“全球分层化的模式”和“全球交往的主导方式”(注:[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9页。)。
如此,他们能够对全球化作出类型学的区分,以避免主张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极端全球化论者”和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并未带来任何新鲜东西的怀疑论者的各执一端,尽管他们未能对全球化由“稀疏”(thin)到“密集”(thick)的划时代转变,提供首尾一贯的解释。而且尤其值得称许的是,他们借助于这种复杂的模型,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多面或者分化的进程,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不再将全球化看作是单一的状态,而是“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注:[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当然,不同领域的联系模式可能大不相同,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全球相互联系。另外,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权力关系深深体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权力关系的扩展意味着权力地点和权力实施不断远离体验这种结果的对象和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涉及相距遥远的权力关系的构建和再构建”(注:[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
全球化的“话语爆炸”,在不少人看来,其实是误入歧途:因为整个现代世界就是在一个全球体系中出现的,“西方的兴起”和后来的殖民扩张,本身就是全球体系内部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但无论怎样,我们不应否定“全球性”(globality)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全球时代,我们又应如何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呢?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明确表示过:“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但是,尽管米尔斯也注意到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趋势,也强调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应当“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但米尔斯的视野,依然主要还是落在社会之中:“社会学的想象力,能使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biography)以及二者在社会中(within society)的联系”。在具体展示社会学想象力“最有成果的区分”,即“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时,在所列举的例证中,米尔斯虽曾提及诸如“民族—国家的体系”与“世界上不平等的工业化”之类超越传统社会观的结构(注:[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一章“前景”,引文中参照英文版增添了若干关键词语。),但其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还主要是限定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
其实,在阐述“人类的多样性”时,米尔斯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通常是在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从权力,以及其他令人关注的方面来看,社会结构中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注:[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5页。)。其实,选择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作为一般性的研究单位,米尔斯是经过权衡的:大于民族国家的单位,比如“文明”,就因为“过于庞杂、含糊”而无法成为一个“研究的概念范畴”;小于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尽管可以满足“收集资料”的偏好,但难以“严肃地考察重要问题”。所以,他认为“适当的概括层次”是“国家的社会结构”,因为“这一层次使我们得以避免脱离问题,同时又能包含在当代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明显体现出的结构性力量”(注:[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6页。)。另外,从具体操作来说,“凡是对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经验丰富的人,都可以获得大量有关民族国家的经验证据,于是这一研究单位自身展现出其可取之处”(注:[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7页。)。
就当时社会学界的状况来说,米尔斯提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针对由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费尔德构成的铁三角所主宰的美国社会学,提出了正视和透视现实问题的替代方案,至少是不再让人能理所当然地忽视国家权力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变迁,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对有些问题来说显得过大,而对有些问题来说又显得过小的单位。
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还有一个平行的个体化趋势,即原先作为个体的行动框架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变动、松动乃至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之类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甚至当代许多社会制度的设计,就迫使人类的存在采取个体化的生活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和决定性,可谓是受到上下两个方面的侵蚀。所以,在当前状况下,再以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作为施展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已经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了。在有关“风险社会”的论述中,贝克已经非常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点(注:Beck,Ulrich,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
我们可以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为例。传统社会学历来将社会不平等视为一个特定社会内部的问题,无论是阶级、性别还是种族的不平等,其实都属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但是全球化与信息化,不仅改变了金融与资本市场,也重塑了社会体制及其交互关系,从而也使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与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譬如,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精英”(global elite)的群体正在悄然崛起,他们的特权和优势并不仅限于一个国家,而是从许多国家抽取和积累资源。他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极为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进行效率更高的投机。而同时,与之相对的穷人,则仿佛是马拉松赛中被甩掉的人,成为“结构性的多余”。他们之间不再具有直接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成为不同时空中的存在。对于精英们来说,空间已经相对失去了制约的性质,他们可以轻松地穿越,无论是在虚拟还是真实的现实中。而穷人们,则既不能乘着超音速飞机云游四海,也不能点击鼠标在互联网上冲浪,他们总是被栓在特定的空间。在时间上,他们也有不同的体验:对精英们来说,是应接不暇的现在的片断的接踵而至;而对穷人们来说,则是沉重、缓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无用的时间之流。“全球化富人”和“地方化穷人”,大概将是我们这个世界社会的最大分化,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迥异于以往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注:参见Bauman,Z.,The Bauman Reader,Vintage Books,2000; Walby,S.,"Analyzing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Restructure Inequality",Contemporary Sociology,2000,Vol.29,Iss.6,pp.813-819.)。
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并不仅是指要关注超越民族国家的结构性力量,而且还指在不同层次之间的视角的转换,特别是要将社会学的触角深入到原先并不认为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个人领域。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个人性即社会性”(the personal is social)的主张,这种观点太过“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了。但是,在原先确定的制度框架变得模糊以后,我们确实难以清楚地区分“个人的”和“公共的”了。或许,探索的重点不应再是区分,而是交互联系了。从分析单位来看,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活跃在全球舞台上的各类行动者,它们实际上也构成了层次不同的认同单位——都可以作为我们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分析单位的选择,要依所欲透视的具体现象而定。事实上,就连当年米尔斯并不看好的“文明”,如今也在方兴未艾的“文明分析”(civilizational analysis)中显示了自身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重要性(注:有关“文明分析”的研究,参见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6,No.3,September 2001.)。
除了分析单位需要重新定位外,社会学探究的方式和目标也需要重新反思。我们知道,现代民族国家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打破各种特殊主义,消除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力量和抵抗,将普遍的观念在物质和符号上强加于地方共同体而完成自身的整合。而在目前的全球化话语中,有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以及同质化与异质性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延续着这种思路。而从目前形形色色的地方性反应中,其实我们不难觉察到现代性和全球化背后的阴影。追求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必然导致对于异己的排斥和压制,而这种排斥和压制,势必导致形式多样的抵制和抵抗。近来在不少地方盛行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只有放入全球化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不过,不无悖谬的是,各种“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潮流本身,无论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在形式上又必定是全球化的。
根本而言,我们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概念范畴去把握当今的全球性格局了。在这个体系中,既有霸权势力欲图凭借着普遍主义的理由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实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沿着它们所谓的现代化路线前进的,因为发展的全球背景已经迥然不同),又有地方进行抵制、创新和寻求自身认同的冲动。“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词虽然道出了全球性和地方性相互依存和强化的辩证关系,但毕竟还是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对峙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今天,如果我们要以一种适合地方状况的全球视野来看待一切,则就意味着应当更多地强调全球体系内在的“联系性”(connectivity)、“多变性”(variability)和“反身性”(reflexivity),而不能片面地关注和追求所谓的普遍性。
当然,这并非是要宣告作为现代性之产物与反思的“社会学革命”(sociological revolution)的终结,而是探询将这种革命进行到底的可能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我们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上需要作出哪些调整和扩展。其实,图雷纳早就说过,“如果现代性就是变化,那么一种稳定的现代社会如何可能呢”(注:Touraine,Alain,"The Waning Sociological Image of Social Lif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xxv,1-2,1984,p.36,p.)?如果没有稳定的现代社会,又何来稳定的社会学呢?在此意义上,韦伯称社会学是一门“永远年青”(eternal youth)的科学的说法(注:Weber,Max,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Free Press,1949,pp.104-5.),在全球化时代益发显得准确!
标签:社会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世界体系论文; 沃勒斯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