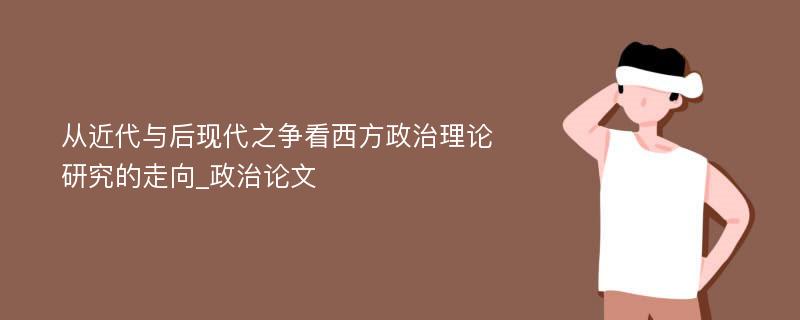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视野下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之争论文,视野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后,一股反主流文化和激进政治的热潮首先在法国掀起并迅速蔓延到西方其他国家,标志性事件即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此,20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批以福柯为代表宣称后现代来临和历史断裂的领军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抨击近代启蒙传统。相应地,也有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否认现代社会的任何断裂,并强调现代性与当前阶段的连续性。后现代理论内部虽然杂乱无章,但对传统和现代基本假设的挑战却体现出一些共通的特征和不足,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90年代的学术繁荣作了积极的铺垫。
首先,用微观政治学挑战宏观政治学来确定其方法论基础。古典和现代政治学多以宏观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观念等,但上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理论却张扬现代政治作用的微观层面,从而开创了微观政治学的先河。以福柯最为典型,他运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新史学研究方法,采取一种“由下而上”的微观分析方法,考察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以及各种规训机构的形成过程,以此论证现代社会发展其实是在压制社会和政治领域原本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现代意义上以主权统治为核心的宏观控制,而是在组织和管理人们的规制性制度中不断繁殖的运作关系,同时,权力运作的条件、方式和技术都与知识和真理存在密切关系①。
其次,用欲望政治学挑战理性政治学来建构其研究主题。现代政治理论强调欲望和激情服从理性的秩序,政治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为过好群体生活而设计更好的秩序。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则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运转的主轴已由生产关系转向消费关系,从而压制性的理性政治学也要为满足性的欲望政治学所取代。比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欲望视为颠覆一切社会形式的创造性力量,指出理性主义对激情和欲望的破坏性作用,并认为以消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使欲望脱离理性制度的控制而发挥作用;鲍德里亚更是以消费社会、媒体与信息、现代艺术、当代时尚等问题为分析对象,突出消费欲望征服理性的积极作用②。欲望政治学的视野虽然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问题,但却为90年代之后思想家因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而提出的生活政治观奠定了基础。
再次,开启了当代政治伦理学的复兴,并拓展了其分析空间。政治伦理学在现代政治科学化进程中逐渐边缘化,而后现代理论却试图从这一领域来反思现代政治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伦理—政治观一度成为福柯和德里达的研究重点,福柯“所真正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伦理,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伦理的政治”③。但这里的伦理已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规范,而是作为社会个体反对各种权力统治的方式;德里达则倡导一种以解构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政治观,强调伦理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的道德责任感。
尽管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视角指责现代社会和政治,但这种后现代立场在70~80年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反而遭到许多理论家的坚决拒斥。以哈贝马斯最为典型,他从80年代开始介入与后现代的争论以来,就一直坚守现代性,并视之为一项许多解放潜能尚未实现的未竟事业,认为所有反启蒙的思想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④,最终只会陷入非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现实政治的改造提供规范、基础和立足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捍卫现代民主、伦理和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但他的交往行动和共识理论还是存在某种缺陷,还无法解决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差异性和个体性问题。这是因为哈贝马斯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及其所受到的社会限制。共识要实现其“达成理解”的理想状态,就可能对个体实行操纵并压制差异,而且常常是把强者的意志强加到弱者身上。他的理论一味强调要获得理解,形成一致意见,达成共识,而很少指出和维护差异性的价值。
我们看到,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视角强调后现代的来临,而哈贝马斯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捍卫现代性的连续性。如果超越这场学术论战的立场,我们只从政治理论的层面去理解和比较他们各自的研究主题和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上述理论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首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后现代理论,思想家们都必须放弃或跨越19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的既定界限,用一种新型的跨学科话语,才能形成彼此对话的机制和平台。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与全球社会大变革和大转型的境况相一致,与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政治学相比,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体现为明晰化、碎片化和杂交化的特征日益突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也愈来愈明显,甚至无法区分学科之间的界限⑤。
其次,上述思想家们关注的依然是马克思、韦伯等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家们曾经论述过的问题,如理性化、个体化和总体化、商品化、大众化、异化等等。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理论所阐释的是那些被前人所忽视的微观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宏大理论所压制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但正如凯尔纳所总结的那样,福柯虽然开辟了重新思考权力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的空间,但却没有为此提供任何积极内容,也很少分析国家和资本等宏观权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如何把现代理论家研究的宏观因素和后现代理论家关注的微观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个体如何更好地生活在某个特定的空间,这些问题可能是这场论争之后留给其他思想家思考和解决的理论空间。
再次,20世纪70~80年代欧洲思想家对后现代性的宣扬或批判都有其特定的叙事背景。他们只能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境况作理论上的某种反应,无法从全球视野来观照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无法把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行逻辑结合起来。所以,这一时期的后现代理论几乎没有具体的社会与政治分析,他们更无法直面一些关键问题。由于无法得到现实的支持,那些宣扬进入后现代时代的理论家们后来也只能承认论战的失败。
苏东剧变是20世纪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90年代以后,西方维护现代性的学者重新调整立场,认为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对后现代理论也持更为包容的态度。思想家们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和概念框架,试图更合理地分析苏东剧变所导致的困境,并开始对全球变革的未来提出各种设想。所以,西方学术界尽管继续争论“高级现代性”、“晚期现代性”、“激进化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等概念,但宏观上关注全球化趋势和微观上寻求新的伦理和批判模式,却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达成共识的关键主题⑥,而且,他们都认为仅仅依靠微观或宏观的理论和方法论无法解释全球变革带来的现实问题。“我们相信微观理论与政治同宏观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结合可以提供探索当代社会的最佳框架,有利于实现激进社会变革”⑦。所以,捍卫现代性的思想家转变立场并宽容后现代理论的繁荣,后现代理论家也不再只局限于学院式的争论,而是立足于全球视野解释现实困境并探求新的出路。具体言之:
1.在宏观方面表现为反思民族国家面临的危机及其走向。民族国家面临的困境是指80~90年代一系列事件使民族国家的地位受到全方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1)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建构出现严重分野,使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国家建构不能为民族认同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和活动的领土场所,民族建构也不能为国家的运转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证明和资源支持。相反,民族主义运动却往往溢出国家的管辖范围并成为世界性现象。(2)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现代国家构成的三要素即领土、主权和人民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主要表现为:固定的疆域与政府权力的缩小,“个别民族国家正在丧失,也终将丧失对其经济政策基本要素的掌控”⑧;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世界市场超出国家主权的范围;民众淡漠了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3)国家能力的削弱导致政府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分离,使各种社会保障政策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9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国家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后民族国家时代全球变革的出路,学者们则从不同视角提出各种世界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1)主张建立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主导的全球秩序。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多来自美国、日本。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完全终结,全球变迁应遵循哈耶克关于扩展秩序完全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观。全球市场经济正在按单一的竞争原则形成,通过跨国生产、贸易和金融网络的建立,经济全球化正在摧毁一切制度障碍。所以,全球秩序的治理机制,也应该遵守世界市场规则,并建立成本最小化的国际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这一理论90年代后呈现从主流到边缘的发展趋势,因为,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人们逐渐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不能解决后民族国家出现的问题。这样,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设想日益遭到学术界的斥责,并逐渐为其他更有说服力的主张所替代。(2)主张以帝国的主权形式建立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削弱,但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及其管理机制仍然在支配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交换,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终结状态。帝国的主权是由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按照政治统治的逻辑来构成,并将利用全球政治权力最终驾驭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⑨。这种乐观的主张虽然得到欧美学术界部分学者的支持,但它仍只是一种设想,也无法解决当今的民族冲突、宗教纷争和文化矛盾等现实问题。(3)主张建构世界主义的民主和福利体系。这种观点在90年代后期的欧洲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赫尔德、吉登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支持这一设想。他们主张,原属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民主治理模式和制度秩序,可以扩展到区域和全球的水平,而且,全球秩序背景下民主理论的核心原则并不会改变⑩。同时,积极的福利开支不完全由政府创造和分配,而是与社会企业和国际组织合作完成,并可在全球范围推行这种社会福利模式(11)。在他们看来,这种世界主义可以使国家放弃民族本位至上的观念,进而成为一个没有敌人的民主国家,即世界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最终包含一种伦理和政治的空间,为保障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和尊严提供了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
2.在微观方面表现为对生活政治的展望和对伦理—政治的探询。民族国家在90年代出现危机后,西方思想家在宏观层面设计各种世界主义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的同时,还从微观的生活和伦理层面考察个体处于后民族国家时代的状况。这是因为,伴随着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出现危机之后,许多靠国家权力来组织和维系的地方性团体和制度也面临瓦解,从而出现了一种没有社会化的个体化形式。也就是说,个体脱离社会和国家的控制后无法再融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中,只能依靠个体自身的能力维系社会关系。在这种境况中,不仅“由国家政治腾出的公共领域被生活政治占领”(12),而且,赋予伦理责任的道德关怀对象是微观的个体而不是国家等组织形式。对于吉登斯来说,生活政治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重建晚期现代性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13)。而生活政治的主要使命是个体追求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成为一种未来的社会蓝图和与全球政治相对照的一种微观政治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寻求新的伦理的思想家有鲍曼、贝茨、波格和巴里等。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出现危机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为保持社会稳定而建立的规范伦理学也要受到质疑,而且伦理的坚固基础,如教会、传统或对乌托邦的信仰,具有更少的确定性和更多的复杂性。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生活的流动性、碎片化和私人化的性质,消解了我们思考公共利益和命运以及对政治行动负责的能力,而脱离共同体的制约和使命则成为主流观念。这样,道德就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从而失去了传统的确定性特征。他们关于个体伦理学的贡献,并不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蓝图,而是思考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的新伦理。而这种新伦理需要有一致的新政治形式,即自主的、道德上自我维系和自我管制的公民,与一个成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矫正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联。这样,道德与政治就能重新超越“政治无道德”的现代观念而结合起来。
3.在中观方面表现为寻找政治共同体。在宏观上探究各种世界主义方案和微观上寻求与之相对应的伦理—政治观念的同时,西方学者也试图超越现代理论宏观和微观的二元对立而构想一种中观要素:政治共同体,以便能联结世界主义理念和伦理—政治理念,调和公共与私人、道德与政治的分野(14)。比如,哈贝马斯试图重建与生活世界相一致的公共领域;麦金太尔、泰勒等试图发展超越现代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痼疾的共同体主义;还有鲍曼的“新部落主义”和贝克的“风险共同体”等等。但他们对于具体的政治形态仍然各执一词,还没形成基本共识。
90年代欧洲社会出现的危机是全方位的,学者们对传统观念、制度和行为的理论反思相应也是全局性的,所以,学术界对宏观、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反思和未来设计所运用的各种研究范式、分析视角和概念框架呈现多元化、碎片化、交叉重叠的特征。
按哈贝马斯的理解,进入全球化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在全球市场的压力下,福利国家出现危机,民族国家逐渐成为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15)。由此观之,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争论与全球化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上述争论对西方政治理论研究转换理论视野、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体现在理论视野的扩展。在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政治学传统中,政治主要是国家的活动,而政治学也主要是研究现代国家制度和行为的构建和运作,其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主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理论研究的视野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并放大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背景。因为,当代政治学中即使微小的研究对象都可能受全球化大趋势这个自变量所左右。
其次体现在分析视角的延伸。当代西方有不少政治学者支持以民族国家为分析视角,但也有学者呼吁放弃民族国家的视角并代之以世界主义。还有学者从伦理个人主义或宗教的世界共同体或公民资格等方面进行探讨,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公域—私域等现代政治学传统的分析视角受到质疑。此外,从学科发展来看,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已经完全突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几乎横跨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视阈。视角的扩大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空间,更有利于解释现实世界变迁的不确定性。
最后体现在理论范式的转换上。虽然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范式仍有较强的解释力,但面对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其中之一就是后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后现代政治学并不是主张与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决裂,而是着重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衰微的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如何才能对复杂、无序和不可预测的结构变迁具有新的解释力,如何将政治学的关注对象由民族国家转向更宏观的全球变革与更微观的个体生活世界,以及如何架构全球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的桥梁。
注释:
①Robert E.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89.
②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③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④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⑤Robert E.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97—109.
⑥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⑦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第380页。
⑧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⑨麦克尔·哈特等:《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⑩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2)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3)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14)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5)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