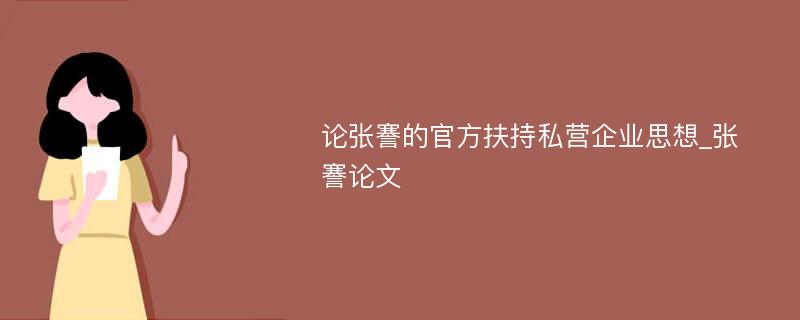
论张謇的官助民办企业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张謇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商关系的协调与否对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折时期,当时张謇提出的“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注:“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首次完整的提出是在张謇的《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该文《张謇全集》和《张季子九录》均署为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但依据该文中的“日人挟持新约”和“户部有二百兆赔款”等判断,该文实为甲午战败初期,即1895或1896年的作品,至迟不超过1900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早期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官商关系
所谓官商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近代中国第一次官商合作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洋务派基于对富强关系的认识及其早期创办军事工业的困境,迫切希望得到民间资金和人才的支持;而早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力量弱小、数量不多,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与倾轧,而且要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侵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正常发展,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以减少威胁其发展的阻力。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要求,近代中国开始了首次官商的合作,同时也开始了双方的初次摩擦。
官督商办是近代中国首次官商合作的基本形式。它师法中国传统的招商办法,又有所变更。其具体方法是先由官方提供部分官款作为垫借款拨给企业,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和作基建经费之用,同时指定官僚或与官方有某种联系的商人出面承办,向民间募集资本并经营企业,待企业经营有所得后,再陆续归还政府垫支的官款。1872年开始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80年代前后官督商办企业普遍发展起来,至甲午战败(1895年)以前,中国共有官督商办企业30余家,主要集中在采掘、航运、保险等方面。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方针一般公认是李鸿章在倡办轮船招商局时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卷39页。)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 与官无涉”(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0卷33页。)。前者是企业经营管理原则,后者是利润分配原则。官督商办企业在其创办初期除得到政府部分垫款外,还曾得到减免税收、贷款补贴、加工订货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顽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他们竭力阻止近代产业的开办。开矿,他们说“破坏风水”;架设电线,他们说这是“断绝地脉”;等等,不一而足。传统势力的阻挠,土豪劣绅的破坏,加上衙役胥吏的敲榨勒索,遂使当时的商人把经营新式产业视为畏途。官督商办的出现在早期适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有助于中国近代产业摆脱创办时的举步维艰。对于它早期的历史作用,郑观应当时评述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存心隐漏,官稽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全集》(上)第704页。)。官借商资, 商倚官助就是官督商办形式的基本内涵,也是其创办初期官商双方的理想。
官督商办企业是近代中国带有一定官办色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上引郑观应的评述既是对早期官督商办形式的肯定,也包含了早期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官督商办的理想界定。但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沿着郑观应的理想发展下去。说它没有,是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洋务派官僚明显地改变了初期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扶掖、保护,背弃了七十年代初提出的“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官为扶持……以助商力之不足”(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6卷35页。)的承诺,加紧了对企业的控制。官方专权,排斥压抑商贾,“无事不由官总其成”(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203页。),企业越来越背离原先的商办意识而趋向于官办,官商矛盾日益激化。说它不可能,是因为官督商办说到底就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和体,它介乎官办与商办之间,介乎封建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可以说是由封建国家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尽管它的产生在初期适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它毕竟是在封建之体嫁接资本主义之花,这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并无二致。“官借商资,商倚官助”,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设计,而实际是决不会达到的。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因素——商办,时时刻刻企图突破封建之体,更多更快地发展自己。而以官督为表征的封建主义又时时刻刻企图规范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使其为封建之体服务,使其不致越出封建主义之轨,不与封建之体相冲突(尽管为了适应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封建之体也有所调整,但这只是零星的变更)。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冲突决定了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商之间的合作最终必然是同床异梦。当时,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集中在不合理的总办、会办制度上。这是官督商办企业在“由官总其大纲”的原则下实行的具体的管理办法。它由政府派出大员充当企业的总办或督办,以“亦官亦商”、“半官半商”的身份代表政府全权管理企业,再由总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几人为会办或帮办,协助总办管理企业。总办、会办的任免概由政府。广大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对企业只有投资权,绝无管理权,“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否,司事之当用否,皆不得过问。”(注: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26卷第6页。)在这种“官有权,商无权”的体制下, 企业的发展与否广大投资者无权过问,完全取决于由政府任免的总办、会办的优劣,而这正是与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背道而驰的。官督商办这种形式在后期越来越成为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桎梏,同是一个郑观应,他在洋务运动后期批评官督商办是“名曰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1页。)。他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前途是“商可自办,官却不必督”。伴随着甲午战败,官督商办企业纷纷瓦解。
二、商自经营,官为保护
官督商办形式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官商之间不再需要发生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从此放弃了获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希望。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微弱,传统的保守势力仍能任意摧残新式企业,而企业经营者却得不到国家政治、法律的保护。“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正是张謇对甲午战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官商关系的构建。它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由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加上经济、军事、文教发展方略的一系列失误,它没能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对于洋务运动,张謇早在1879年就批评说:“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他指责洋务派官僚的做法是“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耗于无用”,认为“过此以往,虽更十余年,其又奚从而自强也?”(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1页。)尽管张謇此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比洋务派更高明的方针和政策,这种批评却是尖锐的。甲午战败给清政府的洋务政策致命的一击,同时也给了张謇进一步审视洋务运动的机会。同年,张謇代鄂督张之洞撰写《条陈立国自强疏》。该疏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该疏要求变革的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是一篇较为完整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与洋务派过去的零打碎敲、走一步看一步相比,显示了对整体与全方位变革的关注。(二)张謇批判了外洋以兵和以商立国的“皮毛之论”,指出“外洋之强由于学”,“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中国倘若真能“广开学堂”、讲求人才,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则“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该疏实际开张謇以后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之先声。(三)该疏不仅要求“以公正均平”为原则,对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选任董事,速加整顿”,而且建议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工政局”、“商务局”,对商民“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5-38 页。)。该疏是张謇甲午战败初期最重要的一篇历史文献。以上三点表明,对晚清洋务运动的理性反思,直接导致了张謇以“商自经营,官为保护”为内涵的官助民办思想的提出,引发了他本人由状元到实业家的历史转变。
官助民办的基础首先是“商自经营”。鉴于以往官督商办企业在后期官督有名、商办无实,形成“名为提倡,实为沮之”的景况,张謇提出今后中国实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商办。国家“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5页。)
“商自经营”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不再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官为保护”是与“商自经营”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謇指出“听商自便,官为保护,是为商办”。官不仅不能退出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相反,只有一方面允许人民自由经营农工商各业,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给予保护、支持,实行“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官助民办式的新型官商关系,才能达到“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械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注:《张謇全集》第2 卷11页。)的积极效果。官助民办式的官商关系在积极的方面体现为“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在消极的方法体现为“监督、限制以防其害”(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6页。)。官助民办就是提倡、保护、奖励、补助、监督、限制这六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官助民办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兴办农、工、商会:农、工、商会分别是农学会、工学会和商学会的简称,是一种研究如何改良、推动农、工、商业的机构。张謇主张在各府、州、县设立农会,“辨土质、考物产”、察“农事得失”(注:《张謇全集》第2卷10页。);在上海设立全国农会总会, 总会有学堂一所,有田四五十亩。总会除“译东西洋农报、农书”外,还可“分别兴办树艺、畜牧、制造诸事,以为乡民倡导”(注:《张謇全集》第 2卷14页。)。在各省设立总商会,在各府设分会,“考府辖之县最王之产、最良之产,与风尚之华朴、民俗之勤惰、工作之精粗、市情之消长,各列为表,度其所宜兴、宜革、宜变之故,斟酌其如何革、如何兴、如何变之办法”(注:《张謇全集》第2卷11页。)。待商会、 农会兴办之后,国家再在每省设立工会一、二处。
建立、健全经济法规:法律是社会的准绳。制定与实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经济法规,“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张謇认为近代中国的新式企业屡兴屡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律之导之故也”,企业“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不可复起也”。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经济立法。他在就任农林工商部部长时强调说,“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2页。),并在1913年9月——1915年9月短短两年的任期内主持制订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商会法》等各种经济法规二十余种。这些经济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规范近代中国的经济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改订平等税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海关不仅不能起到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反而成了替外国资本家向中国推销商品的工具。张謇指出协定关税对中国有“辱国病商”(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4页。)之危害,它“纯利于进口之货物”(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5-386页。)而大不利于出口之货物, 只有“从世界通例,改协定税为国定税”(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77页。),实现关税自主,“则国际市场上,庶有我国商人容足之地,而国民经济或可渐有生动之机”(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84页。)。在实现关税自主的方法上,张謇比较温和,主张由政府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力争,并希望各国政府给予体谅,“舍弃其条约上之权利”(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7页。)。
废除厘金:厘金是长期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一种国内税。厘金制度“百里一税,一二里再税,道途梗阻,节节为厉”(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严重阻遏了商品流通和正在萌发中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了抵制外货的倾销,推进国内实业的发展,张謇屡次呼吁裁厘。他说厘金“不利于商、不利于国”(注:《张謇全集》第1 卷第158页。),“厘捐之为弊也,贤者为之,下出三而上得一; 不肖者为之,下出五而上得一”(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 “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注:《张謇全集》第 4卷511页。)。厘金是当时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为了使它的废除不致影响财政,张謇先后设计了“行印税而裁厘”和“裁厘认捐”两种方式。遗憾的是这些设想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挠,没有得到施行。
减轻税收:在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上,张謇认为经济是根与源,财政是叶与流,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国家的财政收入“实基于生产,苟产殖日臻繁富,斯税源日益扩充”(注:《张謇全集》第2卷266页。)。鉴于当时实业“尚在胚胎”,他主张走减轻税收、推进实业发展之路,反对“纯然以收入为目的以为征税之标准”(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工业上,“凡工商机械制造之货,创办之始概予宽免捐税三年”,并实行“税生不税熟或者税熟不税生”的赋税制度,避免原材料和制成品重复纳税。产品若“就本地零销者,酌减捐之半”,价值不满万者,“免捐免税”。农业上,凡属开垦荒地和滩涂者,水田“免赋三年”,旱田“免赋五年”。(注:《张謇全集》第2卷12— 13页。)。对于各地农会创办的“树艺、畜牧、制造诸事”,以及带有试验性的“新生之物”,“一概宽免捐税十年,以为乡民示劝”(注:《张謇全集》第2卷14页。)。商业上, 凡属有关对外贸易或能为国堵塞漏卮之物,均给予运销之便,“务其负担可以稍轻”。不竭泽而渔的轻税政策有助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建立银行,改良币制,统一度量衡:金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针对清末民初“国家金融基础不立”,“金融家无吸收存款之机关,无以供市场之流转,遂至利率腾贵,企业者望而束手”(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2—273页。)的困顿局势,张謇强调“银行为各实业之母”(注:《张謇全集》第2卷60页。),“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注:《张謇全集》第3卷762页。),主张“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 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币制不良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桎梏,本位不善和货币紊乱是其两大主要弊端。对此,张謇主张,以金本位制为核心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他说:“金钱行而镑价均,银元行而市价平,铜元行而私毁清”(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55—56页。)。对当时和币制一样紊乱的度量衡制度,他主张首先划一本国旧制,以统一的旧制与国际通制并用,“俟数年以后,风气大开,科学日进,再改从通制”(注:《张謇全集》第2卷257—259页。)。
财政保育:就是由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某些与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幼年产业”实行扶持。张謇认为中国实业还很幼稚,“急宜采保育主义”(注:《张謇全集》第2卷168页。)。财政保育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为奖励,一为补助”。对于奖励和补助这两种办法,张謇都主张采用,但限于当时政府财力,他更看重属补助之列的保息法。他说“保息之法,需费无多而收效甚大”(注:《张謇全集》第2卷200页。),主张“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集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注:《张謇全集》第2卷168页。)。国家保息期以“以三年为限”,三年以后保息之费由企业分期偿还。财政保育有助于企业摆脱初期本小、利薄、力弱的困境,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政府干预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有条件的、适度的政府直接干预有时还可能引起经济空前的飞速增长。但一个落后的、成员整体素质低下、缺乏现代化意识的劣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只应永远限定在间接干预的框子里。这样的政府对经济直接的干预总以越少越好。综观以上张謇提出的官助民办的各条措施,不难看出,他的这种设计是在努力避免当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用心良苦的设计是与当时中国政府在张謇心目中的定位以及他对清末官营企业失败的感悟密不可分的。
三、绅通官商之情
政治的改良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前提。这是晚清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张謇指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1页。)。“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可忧方大”(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作为一个实业家,张謇对政治的热情明显没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那样强烈,但实业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联系迫使他在近代中国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关节点都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倾向。甲午战败的当年,他就代鄂督张之洞撰写了九条带有明显检讨洋务运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戊戌维新时期,他虽然嘱康梁等人“勿轻举”(注:《张謇全集》第6卷858页。),但其基本倾向是赞同维新变法的。1901年,张謇从“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76页。)的变革观出发,作了长达两万余言的《变法平议》,系统地涉及了清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变革。《变法平议》诚如大多数研究者所评述的那样,是重弹康、梁变法思想的老调,并且比康、梁的维新思想更温和,但如果把《变法平议》与康、梁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措施相比较,张謇的改良主张显然比康、梁更成熟、更全面。《变法平议》的各条措施如果能全部得以实施的话,起码和戊戌维新如果能获得成功一样,可以把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1905—1911年,他积极策划和领导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立宪运动,成了清末第二次改良运动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张謇“环观世界,默察人心”(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183页。),拥护共和,并一度出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虽曾对共和以来的政治紊乱颇有微词,并把它和孙、黄等人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但对共和国体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毅然辞官南下,加以抵制。晚年的张謇以村落主义自诩,在军阀的混战中折冲樽俎,力图创造出一个局部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综观从甲午战败到1926年去世期间的张謇,缓慢稳健地追求进步是其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而通过渐进的、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设一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开明、立宪的进步政府,是其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官为保护、官助商办在张謇的思想意识中又可以明确地表述为在一个开明立宪的进步政府领导下,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
官助民办是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比较理想的官商关系。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政府的主持下就曾以官助民办——“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大力扶持民间工商业者,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日本的成功向近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研习的范例。比较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张謇认为,日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有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以有今日”(注:《张謇全集》第6卷491页。)。反观中国,“中国之政府殆远逊于日本之政府”(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599页。);“大官蔽于昏庸不职之监司,监司蔽于因缘为奸之弁吏”(注:《张謇全集》第2卷76页。)。腐败、守旧、 顽固的中国政府造成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政府是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张謇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得到完全、合理的改造之前其充当国家工业化引导力量的能力是微乎其微的,更多的只能是阻力。中国“上下之势太隔……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7页。), 要有效地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必须一方面以渐进的手段把现政府逐步改造成为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另一方面在对现政府的改造实现、完成之前,必须有一种积极有效的力量能联结官商、通官商之情。比较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张謇认为绅“介官商之间”,最宜“通官商之邮”,充当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官商之间的联结者。
绅通官商之情是张謇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官商关系设计的最大特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已大大有利于新式企业的经营者,但商品经济不发达、资金难以流向产业、狭隘的小农意识、苛捐杂税,以及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等等,仍给新式企业的经营者以极大的困扰。欲克服这些困难,单靠商力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然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失败的教训告诉人们,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新式企业一旦被官方直接插手,必然会带来官僚式的工作作风,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甚至导致企业的破产。洋务派官办企业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官府直接插手,官商之间“不当通而通”(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招致的失败,使得商人把与官府打交道视为畏途, 商之视官“已几几乎望影惊心,谈虎色变矣”(注:陈炽《庸书·外篇》。)。一方面需要官方保护,另一方面又害怕官方直接插手的矛盾局势,使得在社会上具有双重身份、双重人格的士绅阶层介入企业在一定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工业化,官商关系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商不可日受官之激刺,官亦何可日与商为仇雠”(注:《张謇全集》第3卷780页。)。绅“介官商之间”,相对于商,绅近乎于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封建官府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相对于官,绅仍属于民,他们比封建政府更了解商的苦衷、困难和要求。绅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以“绅领商办”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兼官商之任”(注:《张謇全集》第3卷15页。), “通官商之情”,既能避免当时社会“官尊而苦商”、官商不通、“不当隔而隔”的弊病,又能避免类似于洋务运动过程中的“官皆商也”,政府直接插手企业事务,官商之间“不当通而通”(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 )所带来的恶果。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推进早期的中国工业化。
“绅通官商之情”是张謇创办大生集团的思想基础。早在1885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甲午战败以后他弃官从商,开始了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张謇在大生集团中的地位就是他所说的“通官商之情”的绅。大生集团创办时,张謇并无许多原始资金,其原始资金“不过一、二千元”(注:《张謇全集》第4卷147页。)。其真正的信用或原始资本是状元这一头衔,状元的头衔使他有了与官府直接对话的身份,而守制在籍、处于乡绅的地位又使他比当时的官僚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与信赖。张謇这种介官商之间的特殊地位使他具有了兼官商之任的特殊身份——张謇实质上是以官府代理人和商股代表的双重身份从事企业活动的。对于官,他是商股代表;对于商,他又是官府代理。张謇就这样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上承官责,下任商保”(注:《张謇全集》第3卷6—7页。),“下为商苦,上与官谋”(注:《张謇全集》第2卷53页。), 承担着“通官商之邮”的重任,同时也找到了一条甲午战败以后易为民间一般投资者接受的官商合作的新方式。大生集团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扎根、发展,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辉煌,这同样与张謇以其特殊的身份“绅领商办”、为大生集团创造出适于发展的有利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摆脱对洋务集团的依赖,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迫切需要检讨前一阶段的官商关系,同时从理论上重新构建、确立新的官商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张謇提出了“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并在其以后兴办大生集团的过程中实践和丰富了这一方针。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看,这一方针在总体上还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张謇对这一方针的提出及实践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标签:张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甲午年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