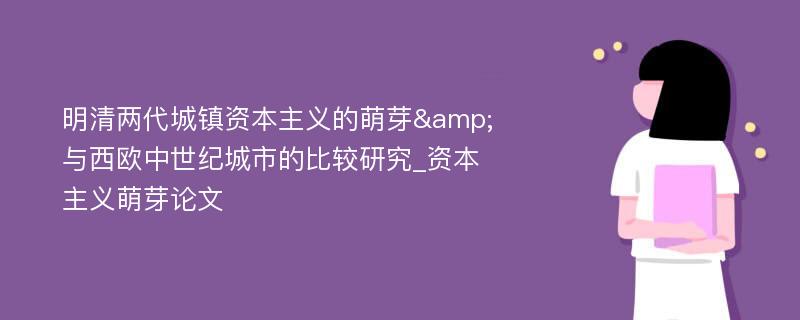
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不存在论文,中世纪论文,明清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欧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实为其社会所孕育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式完整基因在内的有机胚胎,主要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载体。或者说,西欧中世纪城市在建立、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内在素质和传统文化诸关系,逐步培育出这一有着细胞系统构造的胚芽,且在有关历史条件下茁壮成长。而中国古代乃至明清时期的城镇基本不存在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相关基因,那种主要将当时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雇佣劳动的数量和规模状况作为萌芽单一标志的研究方法,其萌芽认定概念本身就是极为片面的,所以问题讨论了数十年,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非但得不出什么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结论,结果却是长期争论不休,进行着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本文将萌芽认定为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组织齐备而发育全面的社会系统构造,把中世纪城市整体发展的主要特点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进行中西比较论证,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直至明清时期的城镇基本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胚芽,因此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一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一、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
西方中世纪所谓自由城市,它首先意味着其居民是自由人。许多城市在斗争中获得的特权证书明确给予市民以人身自由,而取消作为农奴的一系列束缚。“确实在原则上,依照每一个都市团体的原来的法律,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其次,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日耳曼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得一个人自由。’”(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1。)尽管它只是一个法律原则,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远没有解决,然而这一法律原则却成为城市日后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石。
其中下层民众(主要是雇佣劳动者)具体的社会地位如何呢?“在工人即所谓帮工与行东之间,除了由于在财产或地位方面的小小的并且常常是暂时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别以外,再无其他的差别,两者都受过相同的职业训练。工人在与他的行东的女儿结婚的那一天,以及在他聚集了自行开业所必须的小量资本的任何时候,他就可以成为行东。帮工可以自由地从事工作;他仅仅受一个具有一定期限的契约的约束。”(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6。)就是学徒,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法律地位。十三世纪的《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规定:“如果学徒由于匠师的过失而离开其匠师,他自己或他的朋友应到织工行会会长面前,说明这件事的情由;会长在两周之内应召唤学徒的匠师,对他训戒说,对于学徒他应该供应适当膳食,像对上等人的儿子一样,并应给予衣屣。倘使他不遵照办理,学徒可以另找匠师。”(注: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6页。)
同时,西欧许多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习惯法,即一个农奴如逃来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期间其领主并没有提出异议,即取得自由身份,过去的主人再也不能迫使他返回。如英王享利二世给予林肯城之特许状中写明:“任何人在林肯城之居留期已达一年零一日,且已照章纳税,任何具有申请权之人亦未提出要求,而此人能按照本城之法律与习惯证明此具有声请权之人在此期间确在英格兰国境以内,但并未提出不利于彼之异议,则予亦将准许彼等与过去一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于予之林肯城中。”(注: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4页。)
这样,西欧中世纪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乃至从农村逃来而住满期限的农奴,尽管财产方面存在差别甚至是鲜明的贫富对比,然而在法律身份上应都是平等的自由人。市民已初步取得选举市政官员及法律诸方面的有关保障,不负担沉重的封建苛税劳役、不发生与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因此,他拥有从公民而来的一切权利。他可以自由结婚,并让他的儿女自由结婚,他可以随便迁出,随意往来,可以自由支配他的财产,如同自由支配他的人身一样,可以取得、占有、让渡、交换、出卖、馈赠和遗传他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不受领主的管制。他的土地可以转让,可以租出和抵押,可以典当,一句话,容易变成现钱,以便促进商业的一切活动。”(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2~203。)
而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中下层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自秦、汉以来,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压抑而相当低下,尤其是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更为卑贱。唐宋时期,雇佣常常与劳役、奴仆混为一谈,甚至与被典当、鬻卖的人口相提并论,如“差雇”、“雇鬻”、“雇买”、“典雇女奴”、“典当雇工”之类,史不绝书。明清时期的“雇工人”在法律上决不是平等的自由人,“雇工人”称雇主为“家长”,双方是“主仆名分”。明清法律条文中,“雇工人”地位虽略高于奴婢,但要低于凡人,在犯罪量刑时,等级定在奴婢与凡人之间;而在实际生活中,则近于奴婢。其区别仅在于:“雇与奴虽同隶役,实有久暂之殊。”“雇工人者,雇请役使之人,非奴婢之终身从役者。”然而两者“盖亦贱隶之徒耳”。(注:张楷:《律条疏议》卷20。)即受雇期间雇工人与奴仆被同样役使,雇佣期满离开雇主方为平民。
雇工人在被雇期间,必须遵守雇主的家法,如受虐待也没有告发的权利,甚至雇主几乎可以任意处罚雇工人。《大明律》卷20、21规定:“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可见,雇工人稍有过失,或雇主略有不满,即可棍棒相加,甚至被官府法律处以刑罚,其中已没有什么生命保障,更何谈人身自由。周良霄先生经详尽考证后指出:“明律雇工人这一法律概念,其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了城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这种佣雇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毫不相干的。”(注:周良霄:《明律“雇工人”研究》,《文史》第十五辑。)
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雇佣双方绝非劳动力买卖的平等关系,而是雇工人无以为生,来受主人家的豢养。如北宋仁宗时,“上封者言: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以自处,望听其便。从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宋代对社会上的雇工已普遍歧视,而元代驱奴盛行,进一步扩展了雇佣奴婢的队伍。当时,“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驱口,南方以受雇者即为奴婢。”(注:《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明、清社会“雇工人”其低于凡人的法制状况,便是这一传统之继续。直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朝廷才补充规定:“有受值微少,工作只计月日者,以凡人论。”(注:《神宗实录》卷194。)也即一些短工不在佣奴(雇工人)之列。一般认为,明朝后期自由佣工之情况在社会上已为数不少,然而不要忘记,有关“雇工人”之法律规定并没改变。总之,“在商业上,到明代还主要是使用奴仆。手工业的雇工,则多属师徒关系,也有身份限制,并多属辅助劳动者,业主掌握主要技术劳动。”(注: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大清律》对“雇工人”身份所订条款,基本沿袭《大明律》及有关新题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万历年间的题例有所倒退。如乾隆年间改订的律文谓:“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内,或有寻常干犯,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以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止是农民雇请亲族耕作、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注:《大清会典事例》卷810,《刑部,刑律斗殴》。)总之,“清代法律所定的‘雇工人’包括‘长随’、‘典当雇工’、‘一切打杂服役人等’(如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店铺小郎),一般‘素有主仆名分’的雇工等各种佣工。清代‘雇工人’的法定地位与白契购买的可以赎身的家奴相仿。‘雇工人’犯案定罪亦在世袭家奴与凡人之间,有时亦与旗地上的庄奴同判,总体上仍属贱役阶层。”(注:黄冕堂:《清代“雇工人”问题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1期。)
其次,对所有的手工业匠户(多为自营谋生而有技艺之匠户),明代前期用匠籍制度对其进行掠夺性的奴役,将其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当时名列匠籍的工匠近三十万,其中有二万七千户为京城住坐匠,还有一部分在地方官工业中服役,其每年要为官府服役120天,并须连家带小迁至工场所在地,虽官府按月补助粮、盐,但在自营期间,维持生活还是很艰难。轮班匠每三年服役90天,“从服役时间看,只有住坐匠的四分之一,但他们须奔波往返,荒废时日,对自营事业冲击极大。又他们完全是无偿劳动,往来须自筹旅费,在服役期间也不给报酬,要自带薪粮。往往两年的自营,只是弥补当班年的亏空。实际上,它比住坐制度,扰民害民更甚,而工匠的失班、逃亡,也更为剧烈。”(注: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尤其是在籍工匠几乎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世代沿袭处于工奴一般的悲惨境地。明朝中叶以后,虽逐步改为征银代役,但始终是广大手工业劳动者的一项额外负担。时值明朝末年,景德镇民窑工匠仍必须列入班匠役、编役或雇役,为官窑劳作。其中编役与班匠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分毫雇值”。(注:《浮梁县志》卷5。)
再次,是对所有商家的“市籍”制度,亦即至官府完成登记手续,以取得营业的合法许可,即所谓“占市籍”。然而一旦“占籍”,就要承担各种繁重的税收和差役。各种商税,其名目之繁多,税率之加重,令人瞠目。如“榷取之课始不过四千两,渐增为一万、二万,而(正德时)及三万七千有奇。”(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23,杂税部引张秉清《芜湖榷司题名记》。)尤其是为官府承担“当行”这种差役,“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给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无不供役焉。”(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名义上是负责承买官府所需的商品,而官府往往拖延付款,折勒物价,甚至不付款项,逐渐成为套在工商业者身上的沉重枷锁。所以,一般没有背景之商家,“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注:《明世宗实录》卷306,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
许多学者认为,清代“雇工人”之外,大多数都是“无主仆名分”的自由雇工,而这平等的雇佣关系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在“雇工人”法律关系的笼罩之中,在君主专制官僚政体的统治之下,清代的一般雇工同样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平等”的权利。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令江南苏州踹坊,设立坊总甲长。南北商贩青蓝布匹,俱于苏郡染造,踹坊不下万有余人。时浙江总督李卫节制江南,因陈地方营制事宜,言此等踹匠系单身乌合,防范宜严,请照保甲之法,设立甲长,与原设坊总,互相稽查,部议从之。”(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3。)官府用保甲法对工商业者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和监督(后面还有铁冶业实例)。
总之,对明清工商业者而言,尤其在西欧城市市民所享有权利的比较之下,其依然处于一系列封建束缚之中,要负担沉重的苛税与差役,人身受一定程度的控制,不存在有关法律的保障,实际上就连罢工歇业的权利都没有。如清雍正年间,苏州府长洲县一些丝织业工匠“叫歇”,对业主提出增加工资诸要求。官府出面弹压,“勒石永禁”谓:“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官审明,应比照把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注:《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很清楚,对其冠以“自由”之词,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
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歧视,而明清法律同样没有明确过工商业者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当时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给予民众这些权利,而统治当局可任意进行为所欲为的奴役,还有明朝万历年间种种骇人听闻的矿税掠夺等等。这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法律明确保护市民的人身自由、工商经营诸权利是绝然不同的,两者的社会法律地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二、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
城市一般市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不仅要有法律上平等自由的身份和权利,而且要取得实实在在的参政权,就是说,城市政权只有在不断向民主共和制的道路上迈进,这样工商业者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发展自由的商品经济。
西欧中世纪城市从封建主那里取得独立自治权的程度各不相同,其统治政体也差异较大,不过大都已产生在选举基础上的地方行政官员体系和议会机构。“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兰西南部和北部以及低地国家,早在十二世纪,在德意志的莱茵河与多瑙河各地,从十三世纪起,都出现有共和国、半独立的国家、自治团体、执政官制城市、自由市镇,它们都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这些城市自治团体,通过一般的议会、代表机构、上议院、大小议会、长老法庭,和他们选举出来的县知事、市长、郡长议员和长老管理它们自己。它们形成了集体的权力。”(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0。)所以,尽管可以说城市也是当时封建割据势力中的一员,但就其政治制度的内核而言,它已开始与封建领主分道扬镳。
当然,在中世纪城市建立前期,其统治权力常常被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城市贵族所把持。尽管他们为城市的独立自治以及有关城市建设有所贡献,但越来越迈向专制统治,“他们窃取了议会、长官职位与法庭的控制权,并且总是要把市政官职变成世袭的封地。”(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以至压迫一般的工商市民,“他们不仅力图从公共生活中排斥这些小人物,并且还利用他们攫得的权力,去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自己。他们禁止工匠们结社,不许他们联合罢工,违者放逐或处死。”(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贵族的独裁终于激怒了市民群众,他们开始组织起自己的团体,选出领导人和草拟有关章程,开始进行反抗斗争。“所以,从十三世纪起,一种常常具有革命性质的民主运动,开始以日趋剧烈的程度在公会中出现。它的目的是要摧毁贵族阶级或行会在政治上的垄断,而它的方案就是取得市政权力的一部分,或者垄断全部市政权力。”(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221。)
经过数十年的英勇斗争,在贵族乃至国王的残酷镇压下,市民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强,直至采用激烈的暴力手段,最后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在法兰西,如同在西班牙和英格兰一样,皇室权力……它对平民阶级给予保证,以发展结盟行会来支持他们的奢望,并且(如在亚眠)让他们参加市议会和担任市政长官。”“在低地国家,贵族阶级的垄断被取消了,同业公会的代表和领袖可以进入议会和担任长官职位。他们制止了行会滥用的特权,并宣布了贸易自由。它们取得了经济管理的充分权力。”(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5。)当然,其中各国和各城市情况并不划一,但这一发展势头却是无可怀疑的日益趋向一致。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府,由一个执政团包括六至八名执政官组成,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行使最高管理职能。其执政官是从城市七个最大的行会如制衣行会、呢绒销售商会、丝绸商、银行家、法官、公证人、医生等协会所决定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往往采取轮流执政的办法,每人执政期只有两个月。一些小的行会如工匠和小作坊主行会,后来也有了参政权。1293年起,佛罗伦萨实行了限制贵族的政策,官员只从行会中产生,贵族不能充任执政官。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民在法律原则上可以通过举行公民大会来改变政府结构。再看威尼斯的政府,其最高官员称为道奇,是由男性公民选举产生的终身执政官。一个由六位大臣组成的小会议,负责处理、协调有关事务,并有一个十二人组成的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有三百人,是最有权力的立法、行政机构,议员负责制订法律,指导财政、外交等事务。威尼斯也保留有公民大会的形式,其可以选举产生政府官员,而一半议员就是由各部门官员组成,另一半议员是在一定范围中选举产生。威尼斯还有一个十人会议,由议员组成,负责监督宪章的执行和惩治内部的腐败。(注:参阅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2页。)从中可见,城市市民与工商业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从而把握着自己的命运。
中国明、清社会的城市市民,在君主专制的残暴统治下,也时有反抗斗争,一般形式有歇业罢市、群起闹事、武装私营、沿海为寇等。如清代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于官衙差役织造,且时无偿取用,而朝廷派造额又高,织工苦不堪言,遂“焚烧绸机,辞行碎碑,痛哭逃奔。”(注:乾隆《潞安府志》卷34。)有的还出现“抄打包头”、“倡聚抄抢”等激烈场面。很多时候有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注:《虔台倭纂》卷上。)引人注目的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在朝廷所派矿监税使的残暴压榨和疯狂掠夺之下,许多城镇都发生了颇有声势和规模的“民变”,《明史》中有关太监的传记和《神宗实录》中都有详尽记载。
万历末年,全国重要城镇连续爆发“民变”,其规模都相当可观,一些城镇运动高潮时达数万、数十万之众,甚至一些官僚士大夫也参与其中,市民斗争的激烈程度可谓史无前例。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场市民运动,其斗争目标仅仅只局限于少数太监使臣和贪官污吏,并不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斗争方式主要为鼓噪、殴击、焚毁诸示威式的城市骚动,运动零星分散,互相没有联系,更谈不上联合,处于一种不满经济掠夺而自发反抗的状态。结果朝廷撤换了一些地方的矿监税使,斗争即告平息;在朝廷追究责任之际,一些稍有首领嫌疑之人便诣官府自首,以示不敢与王法相抗而被杀害。其自主意识与抗争能力的局限,与其原生的乡族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西欧城市成熟的市民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其既缺乏明确具体的斗争纲领,更没有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表现出相当原始和幼稚之状况。
在西欧市民运动中,行会组织更发挥了它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组织武装斗争取得城市自治,到控制城市议会进行市政管理,它的规章一般还具有法律性质。“商业和工业阶级所组成的自由同业公会和结盟行会,……它们教导劳动群众懂得了团结一致和纪律,怎样在自由选出的领导人的指导之下,和在它们自行起草并经都市团体修改的法令与规章之下进行活动。”“在斗争中,贵族阶级最后被迫把城市的统治让于行会。”(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它不允许其成员有不均等的生产条件,禁止来自外部和起自内部的各种竞争,对劳动时间、产品规格和数量、商品价格、帮工和学徒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在前期为稳定城市经济运作起了相当的作用,到后期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这里主要指出的是,行会在帮助工商业者如何通过斗争,最后执掌市政权力,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方面,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然而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基本不见有上述一系列政治方面的职能。拙作《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指出:宋代的工商行会,它不是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而是官府为了便于对工商业者进行科索、派役乃至掠夺,强制工商业者参加,主要为官府服务的组织形式。(注:拙作《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代承元遗制,厉行户籍制度,商人的行业组织便于其中:“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使役,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或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注:沈榜:《宛署杂记·铺行》。)说明该铺行组织也是官府从户籍制度中派生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官府提供科索和征调差役,所以在万历年间的市民运动中,也完全不见有行会在行动的影子。上述情况与西方中世纪城市工商行会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到明朝末年至清朝,这一状况略有改变,就是当时商人会馆和工商业公所的兴起。商人会馆的职能,除联乡情、祀神、义举之外,还有通行情、计盈亏、评价格、讲商术、联同业诸目的。然而它与官府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需得到官府批准立案才能成立,并时常仰仗官府的力量对帮工、学徒进行压制。“而清代的工商业行会与官府结合,则是在他们彼此利害得失一致的前提下,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所以清代各地行会的创设和行规的制订,一般都要经过当地政府的批准。”(注:参阅刘永成、赫治清:《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清朝中期出现的工商业公所,开始订立行规,主要为约束本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一些规定,包括划一业务规程、统一货价和工价、限制开业和收徒等。其目的在于防止行业内外的无序竞争,这点与西欧城市行会的有关职能颇为相像,然而西欧城市行会那些要求市政权力的政治职能,在这里却始终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西方工商业者积极夺取城市的有关管理权力,最终执掌城市的政权,并在其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民主共和政体的雏形,应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而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权始终在朝廷官府的牢牢控制之下,一直是其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堡垒,绝不存在西方中世纪城市的相关情况,实际上就连追逐这一目标的思想要求都没有产生。
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开拓
西欧中世纪城市大多建筑在工商业经济之上,“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1页。)特别对大一些的城市来说,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粮食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的来源,它们往往必须用商业手段从远方市场取得这些物品。而工商业者执掌城市的政权,其必然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市场经济,可以说,重视开辟市场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特点。“城民们像把竞争者从旧市场上赶走那样勤奋劳作去开辟新的市场,像与商业对手斗争那样艰苦地与地理障碍、道德顾忌、技术缺陷、组织欠佳等作斗争。”(注:波士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剑桥1966年版,第169页。)如以德意志北部70多个商业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拥有自己的商船队和执行机关,并在各地设有商馆,其商船队主要从事欧洲北部各地区出产物的交易,如把俄罗斯的毛皮、蜂蜜,普鲁士的谷物,波罗的海的鲱鱼,斯堪的纳维亚的铜铁矿石,东欧的木材,贩到西欧,再把西欧的毛织物、葡萄酒、食盐、金属制品等运到北欧和东欧。而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商人,主要控制了连接欧、亚、北非的地中海洲际中转贸易。
14至15世纪,一般认为是西欧行会走向封闭性和城市失去进步性的时代,其实它正是城市生产力增强,而市场又很有限,以至造成城市间及城市内部竞争激烈之反映。也正是这一时期,一些城市的市民发起了伟大的地理探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开辟世界市场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开辟新航路的明确目标和技术手段,是在长期努力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1277年,热那亚人开通了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佛兰德的航线。1291年,热那亚人进行了寻找经大西洋去亚洲的航线的最初尝试,但船进入大西洋后不知所终。13世纪末和14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加那利、亚速尔等群岛。有人还继续沿西非海岸往前走。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王子亨利开始有计划地勘探西非海岸;下半叶,在意大利城市的资金、技术协助下,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先后到达了美洲和印度。寻找和控制新的市场、交通线、航线,可看成是这两个世纪西欧城市发展的一个总趋势。”(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从中也可体会到当时争夺市场斗争的激烈,而促成西欧城市向世界经济扩张的决心。
在不断向外开辟新市场的过程中,使得一些城市的大商业公司勃然而兴,且迅速成长,公司在各地设立分部、代理处。如佛罗伦萨一些商业大公司的分支机构网络几乎遍布地中海沿岸,乃至近东各口岸,资本实力也因此大增,同时还产生了类似股份制运作机制的公司。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信用业也发生了一系列革新,“意大利实力雄厚的银行和贸易公司在欧洲所有的重要经济中心设立永久性分支机构。14世纪时这个趋势在大规模贸易组织中开始一个真正的新时代。……与这个趋势密切有关的是采用了不少更为高级的技术,如在社团组织的方法上、代理和通信方面、保险方面、付款方法上、汇兑、信贷、银行业务和会计制度等各方面。”(注:奇波拉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9页。)如1338年,佛罗伦萨有80家商号经营银行业务和货币兑换,其业务几乎涉及全部地中海和整个西方。信用业的发展并伴随着利率的降低,又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也是城市经济的基础之一。随着商业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大,个体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大商人开始向工业投资,建立起手工工场。14世纪时,佛罗伦萨约有300~200家生产呢绒的手工工场,年产呢绒10~7万匹,雇工达3万余人,平均每个工场有100~150个工人,而全市总人口才10万。根特至少有4500名织工,其他漂工、染工、修剪工等的总数大体与织工相等,而全城居民不超过5万。到16世纪末,佛罗伦萨的7万居民中仍有2万人以生产呢绒为生,丝织业还有1.3万名雇工。(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2页。)可见当时城市手工业之重要地位,尤其是手工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城市工商业的拓展,还有力地帮助了农村经济的变革。可以说,中世纪后期乡村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是主要靠城市商品经济的带动。当乡村工商业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际,还引起了一些城市与乡村竞争的局面。
这段时间,西欧城市发展出现了有盛有衰的情况。在如此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根据其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加上饥荒、黑死病、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生产萎缩、经济萧条等因素,一些城市的衰落是很正常的。应该看到,有些重要城市依然发展很快,如伦敦、巴黎、威尼斯、热那亚等。“正在酝酿的近代性质的国际、国内商业网中的地位,恐怕是决定这时期城市兴衰最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时期,不然就可能没有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6至18世纪),因为这个商业网不能凭空产生,而是在14和15世纪一系列深刻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商业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所以14和15世纪时商业网的酝酿也应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商业网通过地理大发现成为现实,它以大西洋为中心,一边伸向世界各地,一边伸入西欧各国,特别是伸入各个城乡生产中心。”(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在上述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和重要发展中,我们看到在市场的不断开拓,特别是海外市场和远距离市场的形成之中,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大商业公司、手工工场和金融信贷银行的出现,它使财富集中于中心城市,集中于少数大商人、大银行家之手,而其商人与银行家一般都是城市的执政者和主要参政者,这样又能更好地扩大投资能力、协调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和整治地区经济,以便于城市经济的进一步自由扩张。……这些经济方面的表现内容,加上前面阐述的市民拥有基本平等、自由人身权利的法律地位和工商业者执掌城市政权诸政治条件,及城市大学教育、罗马法研究、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文化内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便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而中世纪初步完成共和自治体制的主权城市大都已具备这样的有机系统结构。
上述这种有机系统结构,在中国古代直至明清时期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首先,其大、中城市是在专制王权统治之下的政治中心,并非工商业经济运作的产物。尽管宋代以降,城市工商业经济也时显繁华,但其经济职能始终只是政治轴心的运作附件。而且,城市市场并不以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为主,却是以满足达官贵人诸城市居民的消费性经济为杠杆。就是存在有些小城镇政治色彩略显淡薄而以经济职能为主的情况,也不能改变当时整体城市的性质特点。而在专制王权统治之下的整个国家,依然固守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它对市场的开拓诸经济发展要求并不迫切。尤其是海外贸易,受到统治者海禁关闭政策的压抑,几乎谈不上什么稳定的海外市场。
其次,对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来说,谈不上什么政治地位,没有自由发展、自主经营的权利,而要受官府的严密控制,就是国内市场的开拓也是存在种种无法跨越的障碍。其中主要是官府的禁榷政策。明清政府对盐、酒、茶等传统禁榷商品及金、银、铜、铁、锡、硝、硫磺等矿冶产品继续实行不同程度的专卖和控制,有完全官办官销,也有官府不同程度利用民间商人经营的。如当时多数大商人资本的积累,靠的是经营盐、茶之类官府专卖的商品,尽管方式时有变化,“都是将民商变成官商,私营变成国营,使商人成为身份不自由的禁榷制度的附属物。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大为不利。”(注:曹三明:《明清封建法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2期。)当时最为民众需要而具有广大市场的商品部门,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或间接垄断,而给民营工商业所剩的可自由经营的市场空间就很有限了。
再次,明清时期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展,但非常有限且存在各类的狭隘特性。比如由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交流,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范围十分狭小。而某些局部市场的繁荣,还主要与官府的商业政策存在因果关系,如广东的佛山。“封建官府视佛山为‘货泉之渊薮’,十分关心这一重要赋税征收地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其实施的各种工商管理政策,如‘官准专利’等,有利于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比如规定全省的生铁只准运到佛山铸造。非此,即属私铸,与私盐罪同论。这就保证了佛山原材料的供给,也给佛山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易致富的条件。这说明佛山工商业的发展与封建官府的支持有一定关系。这种关系,暂时遮蔽了佛山商民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封建官府榨取赋税的实质。”(注:黄建新、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另外,明清时期的官府手工业规模庞大,机构种类齐全,主要有织造、陶瓷、建筑、军器、铸钱及盐、铁诸方面,工匠经常保持有数十万人之众。当时国家官府、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僚,其消费物品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由市场购买,而是由官府手工业供给,其中有些物品甚至禁止民间手工业生产。如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下令:“禁私造黄、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论死。”(注:《明英宗正统实录》)同时,统治者又把技术最好的工匠征为“匠户”,而官工业的技术严禁外传。这样不但妨碍了民间手工业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更是显著缩小了商品经济的范围,严重影响了当时民营工商业市场的开拓。而当时朝廷官吏大规模经商和官商勾结狼狈为奸的情况已相当普遍,这些官商和半官商资本的兴起显然没有多少促进再生产和扩大市场的作用,反而常常对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有所阻碍。
城市手工业情况以苏州丝织业为例。乾隆年间,城内民机有1万张以上,估计从业人员有数万人,可能超过佛罗伦萨14世纪的织工人数。虽然雇工现象已比较普遍,有关史料不胜枚举,但其中稍有规模的手工工场却寥寥无几。据1913年的一个调查材料,当时苏州“轻造纱缎帐房”中,只有11家是鸦片战争前开设的,开设时间分别是1702、1767、1768、1792、1802、1810、1837年各一家,1793年开设了4家,其中乾隆年间共有8家。这11家在1913年总共雇工1840人,可以肯定其在18世纪的雇工人数要少得多。就是假定当时有几家已先后倒闭,其雇工数与佛罗伦萨14世纪手工工场达3万之巨的雇工数相比,实在是众寡悬殊。而所谓“帐房”,实际上只是发料收货的纱缎铺庄,亦即包买商而已,与佛罗伦萨有一定规模的数百家手工工场的状况无法相提并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商业资本进入手工业生产过程,与手工业结合并加以控制的现象,寥若晨星。在苏州地区众多的手工业行业中,简单协作的作坊和独立的家庭手工业汪洋大海般地存在。”(注: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23页。)
以明清时期最著名也最有财力的徽州、山西商人而言,傅衣凌先生指出:“促成徽州出现有大量的经商者,则系由于封建的低下生产力所造成的人民生计难题;为弥补农民家计的不足,维持高额佃租的存在,依这历史条件的决定,遂使徽商的发展,渐带有一个极落后的性质,把他们对于商业行为的扩大欲求,限于糊口,而不在经济扩张;换言之,只是消极的谋乡族集团的利益,维持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不热心于商业来控制生产的活动。……不仅徽商如是,清代的山西商人亦同。”而对于那些依附于官府而独揽对外贸易的行商、洋铜商来说,其“大半都是靠着政府的特权,而坐得厚利;并且因为他们同政府关系甚深,许多有利可图的独占事业,都容易有插足的地盘,这样,促使他们在商业过程所积累的巨额利润,用不着急急于寻找出路,尽可在有利的场合待机而动;只是做着媒介商品交换的业务,便可立致巨富,而不必把他们的资本投放于生产事业上面。”(注: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193页。)有着半官商性质的盐商、茶商等亦同样。
而且,官府对各类手工业人户的控制极为严密。以所谓部分“开放民营”的广东铁冶业为例,明代“定山主以为炉首,立炉首以为总甲,收土民以为丁伴,择荒郊以为冶所,严巡捕以为约束,明保勘以为清查,时启闭以为聚散,定丁数以为撙节。”(注:戴璟:《广东通志初编》卷20。)当时官府对开矿设炉如何呈报、勘察、批准,及其雇工人数、籍贯、里甲编制、生产时间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一有违反便要从重治罪。(注:曹腾騑、谭棣华:《关于明清广东冶铁业的几个问题》,《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一般认为,清代的矿禁比明代松弛,其实“清承明制,对铁冶控制得更严,措施更加慎密。”“从清代有关铁冶案例中,可清楚地看到建炉必须报官,不得私铸。道光二年河源县曾茂南只不过私开土炉打制农具,便立即遭到封炉捉人的处置,私人开大炉就更可想见了。”(注:曹腾騑、谭棣华:《关于明清广东冶铁业的几个问题》,《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乃至对出海商贸船只也规定:“出洋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法,一船为非,余船并坐;余船能将为非船户捕到官者,免其坐罪。”(注:《大清律例》卷20。)
我们不否认当时有少数的平民富商巨贾,尤其在井盐、矿冶、制瓷、木材诸行业中出现了一些大作坊主,其手工作坊规模十分可观,而且当时雇佣关系也已相当普遍,但这些情况在上述社会条件下,尤其在专制政权的严厉控制之中,究竟有多少意义?当时民众所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被朝廷、官府以及达官贵族所吞噬,极少能被积累为工商业资本而投入再生产。各地首富中,大多为官僚贵族或有官府背景者,或者带有半官商性质。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代表着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内涵的制度结构与文明精神,资本主义萌芽根本无法在明清城镇的发展中诞生。学术界最近出现一种尽量缩小中世纪中西方城市性质特征差距的倾向,然而这一做法是不科学的。近代世界绝非靠乡村经济的变革就能开辟出来的,而主要应是城市综合力量的推动所致。中国古代就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这种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系统结构及所表现出的综合力量。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堡垒和政治的及教士的管理中心这个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确实出现过城市。但在统一的共同体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明显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参与选择行政官员的意义上,个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之外没有城市。”(注:《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0页。)
顾准也早就指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真是梦呓!”(注: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 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可以说,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机制中也包含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只能是一种阿Q式的梦呓!
标签:资本主义萌芽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明清论文; 欧洲城市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