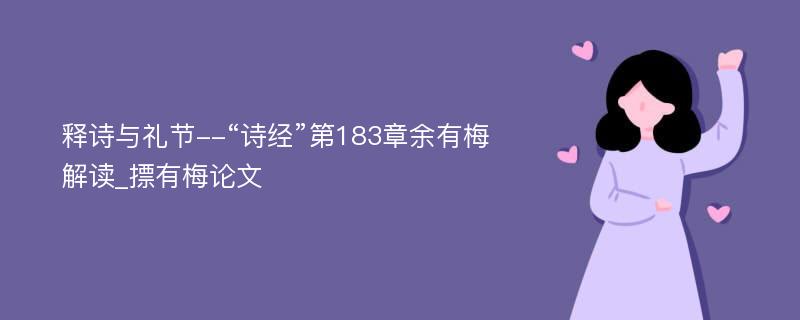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183;摽有梅》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摽有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1-0061-04
在《诗经》产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阐释者为考据、疏解其诗句背后的名物制度而皓首穷经,为辨诘其诗句的寓意指向而猜测纷纭。对《诗经》中《摽有梅》一诗的阐释,由于其背景涉及《周礼》,于是出现了解诗与解礼的交叉与冲突。
《诗经》中的《召南·摽有梅》是一首女子求偶的诗:“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摽有梅》与《诗经》中的其它作品一样,都曾是配乐的歌词。这是一个女子大胆的歌唱,没有忸怩作态,也没有假装羞怯,毫无掩藏的求偶心声中熠烁着后世无法重复的坦直和纯朴,悠久地盘旋于民族记忆的回音里。
两千多年前的女子早已化作飞烟,而她倾诉衷怀的歌诗却留下了千古难解的悬谜。“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句引出后人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摽有梅》传达了国君思慕人才的寓意,中国诗有以男女喻君臣的传统,同时,在中国文人的观念里,国君求才比男女求偶堂正得多,女子主动求偶则更难令人正视,而大多数阐释者仍认同这是一首爱情诗。
倘若承认《摽有梅》表达的是女子求偶之情(从不厌重复、层层递进的简短诗句来看确实如此),古代阐释者便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说清的问题:女子急切地求偶,呼唤“求我庶士”,这种行为方式有违礼教。古代阐释者不敢批评《摽有梅》这首诗和诗的无名作者,因为谁也不能撼动《诗经》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的地位。《论语》记录了孔子对《诗经》的崇高评价,并且认定了包括《摽有梅》在内的《诗经》作品的“思无邪”,尊奉儒家经典的阐释者们还能说这首诗“有邪”吗?然而诗中女子的主动态度又确实有违于“礼”,也逾越了儒家价值体系中道德观所标明的界限。孔子将《诗》与“礼”相提并论,“诗”、“礼”、“乐”三位一体。“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泰伯》)而《摽有梅》却显明地表现出《诗》与“礼”的相悖。持守儒家立场的古代阐释者既不能以《诗》否定礼,又不能以礼否定《诗》,更不能承认二者的相悖。面对两千多年前女子大胆唱出的“摽有梅”,阐释者们几乎被挤到了死胡同的尽头,于是,他们只能或巧妙或笨拙地做些对接粘合的工作,力图使本不合“礼”的女子盼嫁的呼声与“礼”接榫。由于预设了阐释目标,对《摽有梅》的释解中不乏强词夺理的猜想论证。
现存最早的阐释《诗经》的著作《毛诗》对《摽有梅》一诗的阐释已开牵强附会之先河:“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郑玄《毛诗传笺》云:“女年二十而无嫁端,则有勤望之忧。不待礼会而行之者,谓明年仲春,不待以礼会之也。时礼虽不备,相奔不禁。”孔颖达等人的《毛诗正义》认为:“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2](卷一)在毛、郑看来,“不待礼会”是很不体面的事,最好在期限到来之前完婚,所以女诗人语气急切。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对《摽有梅》的解读,也认为歌唱的女子在期待一个“及时”的婚姻,而这种期待,已经比纣王时代的男女遵守礼法了,他解释说:“纣世男女,常是先时犯礼为不及时;而被文王之化者,变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礼,待及嫁娶之年,然后成婚姻为及时尔。”[3] 为弥合《诗》与“礼”的矛盾,古代阐释者苦心孤诣地把女诗人求偶的心声牵拽向“合礼”的方向。
然而,《摽有梅》中所表现的女性求偶的大胆、主动毕竟让历代解诗家难堪,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又是不可指责的,于是他们设想出各种理由为女诗人开脱。例如,当理学家朱熹被问道:“《摽有梅》之诗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他只得支吾回答:“此亦是人之情。尝见晋、宋有怨父母之诗,读《诗》者于此,亦欲达男女之情。”[4](卷八十一)但男女之情如此急迫,毕竟有违诗教。朱熹在《诗集传》里又为女诗人设想出一个理由:“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也。”[5](卷一)一个女子主动求偶的歌唱竟被说成贞节守礼,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晚清学者方玉润作《诗经原始》,提出不少迥异前人的创见,除认为《摽有梅》的主题是国君求贤而非女子求嫁外,对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也嘲讽了一番:“夫女嫁纵不及时,而何至有强暴之辱乎?……曾谓文王化行俗美之世,而犹烦贞女之亟亟自虑如是耶?”[6](P109)方玉润的质疑巧妙而尖锐,朱熹的阐释确实存在着社会道德水准(文王之化)与女子惧怕强暴之间的自相矛盾。
在古代《诗经》阐释者中,清代学者戴震对《摽有梅》的见解独到。戴震的研究领域涵盖算学、经学、文学,他不仅有发现问题的敏锐眼光,更具有一个数学家逻辑严密的头脑。他对作品的阐释,主张“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7](《与是仲明论学书》)。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杲溪诗经补注》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摽有梅》,后收入文集另题为《〈诗〉摽有梅解》[7](文集卷一)。戴震面对的问题仍然是《诗》与“礼”的矛盾,他从研究上古三代的婚姻制度入手,力图使诗的本义得到合理的阐释。戴震的独到之处在于解释了古代婚姻制度的“杀礼”现象,揭露了儒家崇尚的“礼”的随意性。他注意到《周官经》中的规定:“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称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这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的一套制度,更重要的还是对这制度的补充性措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戴震解释道:“中春‘令会男女’者,使其属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贫不能婚嫁者,许其杀礼。杀礼则媒妁通言而行,谓之不聘,不聘谓之奔。故曰‘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奔之为妻者也。”“奔”是西周婚姻制度为“贫不能婚嫁”的男女所设置的补充方案,谓之“杀礼”,但“杀礼”性质的婚姻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戴震据《夏小正》、《荀卿书》、《韩诗传》考证出每年“杀礼”的期限须避开农忙时节,这样,“贫不能婚嫁”的男女可以通过统治者允许的“杀礼”嫁娶与自己同样地位低下者,而当事人的无奈,以及可能产生的自卑感与可能遭到的歧视就不在统治者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贫不能婚嫁者”在礼教允许范围内的“奔”毕竟不同于淫奔,尚未违背社会规范。
戴震把“杀礼”解说成“礼”与“权”的结合:“凡婚嫁备六礼者,常也,常则不限其时月;其杀礼不聘者,权也,权则限以时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礼备,则礼教不行、夫妇之道阙,而淫僻之罪繁。不计少长以为之期,则过其盛壮之年,而失人伦之正。不许其杀礼,则所立之期不行。既杀礼而不限以时月,则男女之讼必生。”戴震认为“杀礼”是对婚姻制度的补充,可以使所有人,包括“贫不能婚嫁者”组织起家庭。这种从权的解释符合传统文化认可的中庸心态,看似神圣的礼教其实都有可以通融的例外情况。例如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8](《离娄章句上》)中国传统文化在“礼”和“权”之间找平衡,形成的制度当然会是矛盾的综合体。然而造成这种矛盾综合体的原因,却未必仅仅是戴震所说的中庸之道,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发展国力是更重要的因素。周代对男女结婚年龄的规定是从优生学出发的,统治者把青年男女视作繁衍种族的生育工具,并不顾及男女双方的婚姻质量。班固《白虎通义》:“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故礼内则曰:男三十壮有室,女二十壮有嫁。”[9](卷下)《太平御览》也说:“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长也。”[10](卷五百四十)清代学者方苞认为仲春大会男女是“圣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斗辩也”,因为民间男女再婚很容易引起诉讼:“每见甿庶之家,嫠者改适,猜衅丛生,变诈百出,由是而成狱讼者,十四三焉”[11](卷一)。然而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民财富很少,由再婚而生出“狱讼”的事会像清代那样多吗?方苞是把自己见到的社会现实套用到古人身上了。
《周礼》讲到“杀礼”的“中春之会”时,用了十分严厉的措辞:“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12] 从维护礼教的角度出发,该罚的是“杀礼”之人,而官方却要惩罚不参加大会、独身不“奔”的大龄男女,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制度是为了“止佚淫”。杀礼制度透露出周代礼教的两条规则:一为无论男女必须结婚,不允许有独身或其它不合社会规范的选择;二为“贫不能婚嫁”的男女,须通过官方组织的“中春之会”结合。也就是说,那时代的青年男女,只要在官方的监控下,“奔”也仍然算得虽“杀礼”而实守礼的行为,而如果在“中春大会”之外自由恋爱,就是淫。“礼”的地位仍然至高无上。统治者垄断了“礼”的解释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礼教为其统治需要服务。然而,“杀礼”毕竟为个人自由提供了某种逃逸的借口,因而戴震这样阐释《摽有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即过二十,亦未遽为年衰,则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梅落非喻年衰”是戴震通过研究“杀礼”制度得出的结论。既然有“杀礼”制度,且女子二十“亦未遽为年衰”,女诗人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坦直地咏唱出“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的急切心声,表达了珍惜青春的求偶愿望,并非盼望完婚而守婚。
戴震由解诗而解礼,又由解礼而解诗,将解诗与解礼相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崇尚考据,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戴震,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避免想象和成见的干扰,去求解诗的本义。强调“杀礼”的影响,说明戴震已看穿礼教的虚伪,也对《诗》与“礼”的矛盾有所辨察,但在受到理学强大制约的学术氛围中,他以近于繁琐的考据作铺垫,包含着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见容于世的良苦用心。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东原以考核为通达义理的手段,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而汉学家末流以考核为目的,段玉裁、王念孙莫不如此。”[13](P166)
上古三代,人民的私生活已经被官方控制,被剥夺了自由恋爱或独身的权利。虽然也有人不甘受礼法的压抑,唱出《摽有梅》这样“急迫”的诗歌,但最终被郑玄、欧阳修、朱熹等学者曲解。而戴震的《〈诗〉摽有梅解》通过考据暗示了上古人民缺少个人自由的事实,打破了中国人景仰的上古三代的美好幻象。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自汉至清,《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备受尊崇,而在自晚清至“五四”,以至20世纪后期的“反封建”时代思潮中,《诗经》不但未被当作儒家经典遭受批判,人们反而从中解读出自由恋爱、反抗压迫等反封建内容。《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歌,兼具“五四”以后新的文学观念所认可的“白话”与“人民性”两大优势,因而成为论述中国文学反封建传统和民间传统的证据。
闻一多以新的文学观念审视古代的《诗经》研究,明锐地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14](P356)这真是一语中的的批评。自解诗成为一门学问后,《诗》便不被当作诗,而被视作经——“六经”之一。在古代阐释者看来,这是对《诗经》的抬举和尊重,而闻一多则视作对诗的贬低和亵渎。
闻一多的《诗经新义》据《说文》、《公羊》、《孟子》解“摽”字为“抛”义,并援引《木瓜》、《女曰鸡鸣》为例证,由此产生一系列的联想:“《摽有梅篇》亦女求士之诗,而摽与投字既同谊,梅与木瓜木桃木李又皆果属,则摽梅亦女以梅摽男,而以梅相摽,亦正所以求之之法耳。意者,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报,即相约为夫妇焉。”[15](P88)闻一多并且在《〈诗经〉的性欲观》里描述了“仲春之会”的具体画面:“《周礼》讲‘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这种风俗在原始的生活里,是极自然的。在一个指定的期间时,凡是没有成婚的男女,都可以到一个僻野的旷野集齐,吃着,喝着,唱着歌,跳着舞,各人自由的互相挑选,双方看中了的,便可以马上交媾起来,从此他们便是名正言顺的夫妇了。”[16](P171)闻一多发挥着他作为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在他的描述中,周代青年竟会这样无拘无束、自由浪漫。
闻一多对《摽有梅》的读解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对这首诗的阐释有了契合时代思潮的方向和路径。闻一多的阐释富有创造性。不同于古代文人以解经的方式解诗,他力图唤回诗的精魂和生命。然而,在富有文采的生动描绘中,他对《摽有梅》的内容做了有悖历史真实的引申和发挥,他对“仲春之会”的描绘充满随意性,也混淆了统治秩序已经成型的周代与原始社会的区别。
那么,是否可以把闻一多对《摽有梅》的解读,视作现代阐释学的一次实践呢?——虽然在闻一多生前,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尚未建立。到了21世纪初,面对现代阐释学所带来的阐释态度和阐释方式的变化,我们是否该高度评价闻一多对《摽有梅》富有想象力的解读呢?现代阐释学不是强调理解行为的主观性,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可以在被阐释过程中无穷尽地不断生成吗?我们能不能以现代阐释学理论为依据,判断闻一多对《摽有梅》的解读超越了戴震呢?——并不能。
闻一多与古代阐释者持有相同的阐释目标:求解诗的原义。他曾在回答求教者有关《诗经》解读的信中说:“要解决关于《诗经》的那些抽象的、概括的问题,我想,最低限度也得先把每篇的文字看懂。”“一朝你能把一部《诗经》篇篇都读懂了——至少比前人读得稍透些——那时,也许这些问题,你根本就不要问了。”[14](P339)所谓读“懂”读“透”,即是去接近诗的本义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角度说,闻一多的阐释有违他解读《诗》的初旨,虽然他的描述那样生动而富有兴味。闻一多想象周代青年享有无拘无束的自由,与郑玄、欧阳修、朱熹等将女子求偶解释为“守礼”,同样为一厢情愿的误读。
闻一多试图把对《摽有梅》的解读引向文学的方向,专注于文本而忽视文本后面的背景,他得出的结论竟不如戴震由解礼而解诗更贴近诗的本义。阐释者有理由以想象拓展作品的内涵,却没有理由以想象虚构如“中春之会”这样的史实。通过比较不同时代学者对《诗经·摽有梅》的阐释,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坚实的学风能给我们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