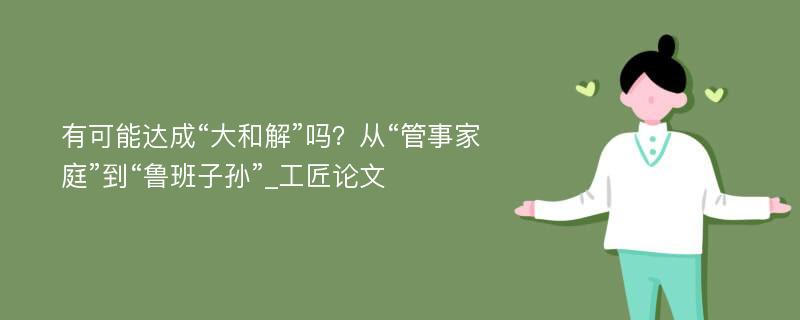
“大和解”是否可能?——从《内当家》到《鲁班的子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当家论文,子孙论文,鲁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83年,王润滋发表了小说《鲁班的子孙》,旋即争议四起。虽然早在两年前,王润滋就以一篇《内当家》名声鹊起,但引起轰动的《内当家》却没有像《鲁班的子孙》那样,引出一场巨大的争论。关于小说本身,关于老木匠和小木匠孰对孰错的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未见结果。
这场争论在漫长的将近三十年中始终未曾中断,并且这些争论每一次出现都显得那么激烈,彼此之间的冲突又似乎完全不可调和。究其原因,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阶级斗争停止,国家重新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几乎成为了普遍共识,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财富”的增长上。但是,这一共识同时引起了更多的围绕着“财富”的各种不同想象的分歧。比如,财富增长要通过何种方式?共同富裕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这种富裕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平等?将经济发展、致富放在首位,会不会导致人生价值的庸俗化?活着还需不需要别的意义?这些批评几乎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展开的,在80年代早期,其中一些是延续了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另一些则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问题有了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可以理解为,前半句是针对承认改革的现实,后半句则指出如何克服这个现实所生产出的种种问题。《鲁班的子孙》正处于这个争论的核心,小木匠的致富道路究竟是什么?它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究竟要怎样克服?相关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批评家为小木匠辩护,或指责王润滋的作品只有对客观的描绘而缺乏理想的品格(认为小木匠不是改革者的典型形象,作者刻画出这样一个人物是对改革缺乏真实的认识)①,或认为小木匠作为改革者即使存在缺陷,这缺陷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它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其理论基础乃是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要扫平一切古老文明和传统道德);②而另一些则站在老木匠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无论是否认同历史中的那个老木匠),或为美德的沦丧、或为社群的破裂忧心忡忡③。然而,在这种争论的背后,小说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被人忽视了。也许是老木匠和小木匠的象征意义过于重大,批评者急于或站在老木匠的立场上,或站在小木匠的立场上,来重述和评判小说中的冲突,而忽视了小说存在本身是各种冲突的第一次整体解决。忽视这一点,小说本身就成了个未解之谜,小说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何理解作者最后让木匠铺“渐渐恢复生机……虽说不能发财,却也生意兴隆。活儿多得做不完……”的情节安排?如何理解老木匠最后那句自信的“离了黄家沟,没他立脚的地场”?小说的叙事本身并非自然主义的描写,其结构也不是摊开一场或几场冲突,而是高度完整,指向了明天,是“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明天的故事谁来讲下去”,这是我们进入小说的一个线索。按照王润滋自己的说法:“有人问我是倾向老木匠还是小木匠,我说我是作者,不是老木匠也不是小木匠;问我寄希望于谁,我说寄希望于老木匠也寄希望于小木匠。两代木匠各自走过了他们不同的悲剧道路,还都要走向明天,但愿明天的故事不是悲剧。”④
小说的情节安排及其结尾提醒我们,这是一篇形式上高度完整的小说,小说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这意味着,王润滋在文本内部已经解决了父子冲突,并且实现了和解。从第一个小标题“陈年往事”到最后一个小标题“明天的故事”,小说就历史性地呈现出老木匠以及他念兹在兹的“良心”、美德怎样与他人发生冲突。这段冲突史不仅仅是和小木匠发生的冲突,还包括了和书记官、木匠铺的其他成员,此外,还有和小木匠的亲生母亲的冲突。小说讲述了“良心”的起源这一传统故事,继而叙述了毛时代的危机、终结和新时期的开始这一急遽变动的历史过程,并在经历了种种冲突后,小说以老木匠对于“良心”的满怀自信而告结尾。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的许多同样指向明天、结局更显光明的作品相比,这种面向未来的乐观并不是建立在呼唤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即使在小说中也明确提到个人财富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一步迈向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那个有深度的现代个人。一方面,使小说成为小说的不是纯粹“个人”,不是现代性世界中那个没有家园的原子式个人;另一方面,如果说“只有当我们与精神家园失去联系时,时间才能成为结构的因素”。并且,“小说……是唯一将时间采纳为结构原则的艺术形式。”⑤那么,恰恰是老木匠遭遇的精神危机,才构成了小说中的冲突在历史中的展开,而小说的结尾又预告着在历史中冲突如何被和解,在这个高度完整的叙事中,老木匠才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良心”的故事才可以永远讲下去。
于是在这里,一方面,是文本内部达成的和解;另一方面,是一直持续到今日的争论。这意味着,王润滋在小说中所设想的和解,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需要追问的问题就不单单是冲突本身,而是说,小说内部的和解是如何可欲的?需要哪些明显或隐含的条件和解才是可能的?这些条件是否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研究这些问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理解80年代历史进程的逻辑。
二
要厘清这些问题,我们最好首先退回到王润滋的成名作《内当家》,因为寻求和解的意图在《内当家》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王润滋的《内当家》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老地主在改革时代重回故土,过去受老地主欺压的贫雇农不计前嫌,为了改革的大局着想欢迎老地主的回归。《内当家》这篇小说基本上可视为响应国家政治号召的创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小说本身不是作者有感而发之作),一方面是要求阶级斗争的和解或者说呼吁安定团结,一方面则强调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国家、社会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领域。但是,这样一种和解的期盼,在《内当家》中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解只是发生在空想的层面,这样说是指,老地主归来以后的故事,《内当家》完全没有展开,老地主回来帮助发展经济,是否必然带回老地主在经济或者生产上的逻辑,以及随即可能出现的剥削、新的不平等的产生等诸多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内当家》实际上是通过不在现实层面上展开难题而回避掉了,但其难题性依然存在,当年毕竟是苦大仇深,亲手赶走的老地主,如今再回来,和解要如何可能呢?《内当家》虽然没有铺展开这一难题,但也并非对此完全忽略,而是进行了非常抽象地处理,在文本中,这种抽象表现为叙事的诸多含糊。首先是,李秋兰和刘金贵的和解是在老支书的劝服下进行的,党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功能。正如李秋兰自己所说:“就说俺李秋兰还有副中国人的心肝,俺不会给共产党丢人现眼!”但另一方面,老支书在进行劝服时说的却是:“就说刘金贵吧,他爱国,是个中国人哪!”⑥同时,老支书是一个典型的形象,他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村长的形象,他的权威并不完全来自于革命中国给予他的身份,这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叙事中较为常见。在80年代初期,这其中隐藏的矛盾并不必然构成冲突,因为在当时,党的领导,或者说在政治领域实现整体性和解,还是被普遍相信的。科学技术进步、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文化、伦理、价值、美等等由此不必然构成冲突和分化。但是,也许是过度阐释,随着《内当家》的最后一章里老支书的缺场,地主和贫农在感情上的和解,最终只能依靠一碗家乡的水,而进一步我们发现,到了《鲁班的子孙》中,老支书这样一个形象索性彻底失了踪。
这种隐含着矛盾的抽象处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和解的难题都尚未充分展开,而这恰恰是《鲁班的子孙》讲述的故事。如果将《鲁班的子孙》看做《内当家》的续篇,我们就会发现,小木匠所引发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老地主回来后的故事。王润滋试图重新开启在《内当家》中被抽象解决的冲突,让这一难题在现实中完全地展现出来。关于两篇小说的差别,王润滋说:“我做小说向来都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苦恼的是:多数篇目都表现得直露而且浅薄。《卖蟹》的思想倾向是明显的。《内当家》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的。我不满足一直这样写下去。我努力想提高自己的功力,以描写更复杂的生活、塑造更复杂的人物,从而也能够将思想倾向埋藏得深些,让读者寻觅和挖掘。”⑦因此,当《鲁班的子孙》实际上提出了老地主回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时,老地主的回归要求的就是切实可行的而非空想的和解。也就是说,《内当家》中那样抽象的和解是建立在难题没有展开的基础上,而在一个充分展开的过程中,小木匠揭示出和解之种种艰难,随着老地主(小木匠)及其逻辑的回归,人与人的关系变质了,亲情和爱情的纽带不断经受考验,共同体变得脆弱不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王润滋把两篇小说的差距理解为文学创作水平上的差距,似乎在后一篇作品中,这一难题的展开确实也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更妥帖的说法是,在《内当家》中,未展开的难题使得政治和解似乎还有可能,而在《鲁班的子孙》中,难题一经展露,则立刻暴露出政治领域内完成和解的不可能,所以,王润滋根本无法想象一个老支书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隐射或者预告了改革开放的整个后三十年里政治想象力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小说如此强调老木匠的“良心”,如果两篇小说表面存在着续集的关系,那么在其核心部分,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故事。《鲁班的子孙》是真正属于80年代的小说,从中我们也能窥探出,为何这个十年常常被指认为文化热的年代。
《鲁班的子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良心”上,文本内完成的和解,是所有人通过老木匠共同与“良心”的和解,或者说在“良心”上的和解。小说一开始便说道,良心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存在的,是“世世代代以来”尊鲁班为师的木匠们要上的“第一课”,这些都告诉我们,在小说里“良心”不仅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而且是一种起源性的文化认同。“良心”并不实指某些道德条律,而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既可变又不变,好像涵盖了许多内容,但所有这些内容又可以被明确无疑地归于“良心”这个概念之下。老木匠的“软性子脾气”,那种坚毅的性格是“良心”,人情滋味也是“良心”,看不惯“这年头儿,净兴坏规矩”的“规矩”也是“良心”,特别有意思的是,一直是“良心”的承载者的老木匠,在遇见了小木匠的亲生母亲后,为什么会“忽然觉得自己也有罪”?而有罪的人为何在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后,反而“自那以后,人们发现老木匠的心境好多了”,为何意识到有罪并不是否定了“良心”,而是能再一次回归到“良心”,只有经历了这一次同时意识到有罪与“良心”的戏剧冲突后,老木匠才得到那份自信,认为小木匠一定会回来。相信小木匠必然会回到黄家沟与老木匠清楚地意识到“良心”具有某种同构性,在这个意义上,《鲁班的子孙》提到伦理、文化认同的问题,要比寻根文学更早。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也许有人说王润滋是一个农民意识的卫道者,也许有人会反驳一两句:不,王润滋捍卫的是民族的美德。只要这么一两句,我就足矣。也许我所捍卫的东西被毁灭了,那么让我的灵魂同她一起毁灭吧。”⑧在此处,可以较明显地看到,正是依赖于伦理,或者说一种文化认同,和解才获得了它的可能性。
在政治认同不可能之后,如何实现和解,这是文化认同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但需要追问的,也是小说本身继续处理的一个问题便是,这种新的和解是否可能?原本涉及的是阶级斗争的和解问题,但由于“良心”在小说中的出现和所处的关键位置,冲突产生与和解的空间转而变得不同,从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转移到了文化、伦理的空间内。但把《鲁班的子孙》放回到文学史脉络中,它与寻根文学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与寻根文学相比,小说又没有完全放弃或者退出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也有不少观点认为《鲁班的子孙》在艺术性上尚有缺陷,在形式和技巧上也不圆熟。但这种笨拙可能恰恰来自於小说本身内含的矛盾,新时期以来,这种笨拙使得我们可能是第一次也是预先认识到,依靠纯粹的文化认同来重建共同体、依靠伦理传统来实现和解之不可能,这一点我在下文会谈到。相形之下,寻根文学往往拥有一种成熟得多的形式,但这种过分成熟与精巧却是以退出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代价的。
所以,更细致地来探讨老木匠的伦理关怀与小木匠的冲突关系的话,不难发现,和解仍然存在困难。相比于起初还期盼儿子回家一起重开集体木匠铺,老木匠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巨大财富面前完全无法再设想一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存在,从最初的希望重整旗鼓到最后连拉富宽一把的希望都无情地破灭,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这是一次惨败,也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内,“资本主义”成为普遍性的,无法选择的必然。但由于小说将伦理的问题与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转变拧在一起讨论,老木匠的这种选择余地的失去其实是一种双重失去,因为这里同时包含了“良心”的失去。这意味着,小木匠带着普遍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家后,“良心”在现实生活中迷失了自己,“良心”找不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方式,老木匠坚持的伦理道德无法在普遍性历史的现实中找到自己。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面临危机的一次症候,因为“惟有在西方,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是结合起来的,一体的,没有时空上的断裂的。因为我们不用改变宗教信仰,事实上,正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这个世界上才有了资本主义。而在非西方世界,传统、信仰、价值,由于和资本主义不合拍,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糟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要么留在过去,做一个中国人,……要么跨过资本主义的门槛,做一个现代人,……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两者兼得。”⑨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将老木匠在小说中的出现理解为纯粹的伦理、道德关怀,那会让我们过快地将问题置于文化领域内,过快地将之与文化热、寻根文学联系在一起。老木匠焦虑的是,无法不接受小木匠,同时无法抛弃“良心”。无论是王润滋还是老木匠,至少在姿态上从未置政治经济学领域于不顾,从未无视这样一点,即面对着小木匠,在伦理、文化上的大和解随时面临着在现实中失败的可能。
对于社会主义,老木匠偶尔会表露出怀念之情,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虽然在一方面,“鲁师像”在“解放以后说这是迷信,就不再供了,却舍不得丢掉,藏在箱子底下”,但另一方面,从文本的细节处我们同样得知,老木匠的“良心”在社会主义现实中曾经得到过某种程度的满足,社会主义从“良心”中获得力量和支持,并且重新叙述和创造“良心”。可以想象老木匠在合作社的制度下“帮乡亲们干点零星八碎的活儿……都不肯收工钱”,可以想象“五十年代那个人帮人哪……六十年代那个人学人哪”的社会实践,可以想象老木匠内心曾经的满足。但他所怀念的是一次本身充满危机的过程,小说也是从危机谈起,从滥用权利的书记官谈起,从富宽和李忠的埋怨自己的无能谈起,从黄兴的“干活不尽力”的检讨谈起,社会主义的危机就是“良心”的危机,面对这场危机,老木匠虽然还有所怀念,但一旦接触到回家后的小木匠,就再也无法幻想重回过去,他只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就是这样艰难、这样乐观地向前走啊走”。书记官与小木匠争执之后就再也没有登场过,富宽、大忠、黄兴和小金子各自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良心”也要找到自己的现实存在,这是一种无法选择也无法逃避的担当,所以才说是“不管命运安排在你前面的是幸福或是苦难,走上去承担它就是”。
但直到目前为止,老木匠在冲突中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失败,这表明着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当小木匠在历史现实中发挥自己的能量时,“良心”才刚被作为大和解的可能就立刻展现出它的不可能,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由于某种转折,在小说的结尾它又是如何重获可能。
三
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触及到小说本身的局限性。如果说“良心”从“很多很多年以前”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在老木匠的自信,在木匠铺的恢复生机中得以向未来传承,这构成了小说的完整性,那么这种完整性首先依赖于小木匠所代表的并非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其次就在于小木匠亲生母亲的登场在文中所具有的含混意义。无论文本内的人物,或是文本外的作者,都将小木匠的出场理解为资本主义,甚至小木匠自己都认为“俺这儿是资本主义”,但小木匠身上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一方面,在劳动或者说生产方式上他至多只是一个小生产者;另一方面,他与老木匠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作为一个小生产者,如果老木匠关心的是“生产”,小木匠关注的则是“交换”,即如何通过市场流通领域获得利润最大化。这样说的意思是,小木匠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者说至多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与改革开放的早期自我理解相关,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在此无非是为自己的私利干活,以及所谓技术革新,“机器化”、“置上电锯、电刨子”。但小木匠对于财富的渴望与他的劳动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木匠铺只是个小作坊、小木匠也只是个小手工业者。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对小木匠的劳动的最好诠释:“这哪里像一只小伙子的手:又粗又短的手指,简直象一排磨凸的石钻,每一道指节都凸起老高;虎口间堆了重重叠叠的老皮;手掌几乎全是一块硬茧;拇指让锤头或者釜顶打过,指甲死去了,只留下难看的一团……”,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联想到浩然在《艳阳天》中对于富裕中农“弯弯绕”的锄头的细致描写:“那锄杆磨得两头粗,中间细,你就是专门用油漆,也漆不成这么光滑。那锄板使秃了,薄薄的,小小的,像一把铲子,又像一把韭菜刀子。”小木匠考虑的就是通过自己辛勤的手工业劳动积累起财富,而当积聚起财富之后,他所能想到的全部就是“往后的日子是我们的,盖新房子,结婚,电视机,录音机,‘嘉陵’摩托……”。⑩80年代的改革开放逻辑并不是一路直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鲁班的子孙》仅仅是想象和解方式的一种,比如,在文革结束后,重新激活这些小生产者也曾意味着一种延长、接续新民民主主义道路的想象。因此,老木匠所可以想象的全部成功——通过扬弃小木匠的生产方式,妥帖地让“良心”在现实中实存——只是对一种小农经济、小生产者的克服。与此相关,在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中,劳动力尚没有成为抽象物,劳动力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比如说,李忠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老木匠也认为只有黄家沟才是立足之地。所有这些条件,构成了大和解可能的前提,而当真正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来临时,不难预见,无论是老木匠还是小木匠,谁都抵挡不了这种冲击,当所有的人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人”之时,老木匠的“良心”又将再次失去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于是和解又再一次回到了抽离于现实的空想层面。
至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木匠亲生母亲的出场。因为在小木匠逃离黄家沟以后,老木匠处于一个长时间的心情低落,对生活不再抱有希望的状态,只有在与小木匠的母亲相遇后,老木匠才重获自信,“从箱子底下拿出那尊格木雕刻的斑驳碎裂的鲁师傅,恭恭敬敬地放在小炕桌上,长时间出神地凝望着,心里说着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话”。在此之前是“人们都惊讶而悲哀地发现,老木匠不再是过去那个老木匠了,他真的老了,人老了,心也老了”;之后则是“自那以后,人们发现老木匠的心境好多了。脸上偶尔露出些淡淡的笑容来,眸子里有了光亮”,这转变过程中的关键就是小木匠母亲的登场,她使得老木匠“忽然觉得自己也有罪,觉得自己不如这个跪在地上的女人——儿子的母亲”,她的品行和道德使得老木匠震惊,“心颤抖了”。老木匠感到愧疚和自责,并且“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人都有罪”。这场戏剧性的冲突安排堪称绝妙,原本浑然一体的老木匠和“良心”——老木匠就是“良心”,“良心”就是老木匠——在此处由于小木匠母亲的出现被打破了,但这种打破并没有让老木匠否定“良心”,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让老木匠肯定了“良心”。小木匠的母亲有抛弃亲身儿子的罪过,但老木匠面对她“不是要领走儿子,是来报恩报德”的行为,自我反省过去又何尝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每个人都有罪,但“良心”依然是“良心”。在每个有罪之人的身上,都透出着那个永恒的“良心”的光芒,老木匠就是在一个有罪过又有“良心”的他者身上,看到自己与“良心”的分离,既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性(我也是有罪的),又恰恰通过这种分离同时看到了“良心”的无限性。
正是经过了这一场冲突,故事才被作者讲圆满了,老木匠才能在重重受挫后仍保持对“良心”的一种绝对肯定的态度。“良心”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保存还是抛弃,即使危机四伏,我们也只能接受这坎坷的命运,并义无反顾地担当。但是,老木匠和小木匠以及他的亲生母亲发生的冲突的性质,又有本质上的不同。比如说,老木匠在面对儿子那个两毛钱的镢扎和面对小木匠母亲的忏悔时,都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惊,而仔细比较会发现,这两种震惊又是如此不同,因为前者与劳动、生产直接相关,是老木匠在自家木匠铺生产出来的“两毛钱的镢扎”这个劳动产品里无法发现自己,这个劳动产品的生产与自己的“良心”有天壤之别,而这个问题在文本内部的和解,则恰恰是通过后一次震惊来实现的,而这后一次的震惊与劳动毫无关涉,直接是伦理内部的问题,是“良心”遇到了他者之后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确认,与生产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当王润滋在小木匠身上充分地展开和解难题的时候,他秉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品格,然而在最终实现和解的那一刻,他还是脱离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因此,老木匠所寻求的整体性和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幻相,在文本内外都不真正存在。或者说,即便人们真的憧憬这种和解,它也必然充满了危机。
四
《鲁班的子孙》这样一篇小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许在于以下两点:首先,它预言了新时期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在此之前,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展露其本性残忍的一面;其次,与《内当家》不同,小说寻求一种全新的和解的可能,并且,这种伦理的、或者说文化认同在之后几年的寻根文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鲁班的子孙》更为深刻之处则在于尝试为这一种“理念”找到当下的“定在”,而这种尝试在文本叙述中得以成功的条件,恰恰在于它完全身处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或者说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自我理解中。倘若果真如此,则有许多问题是可以由此文本引出,而又不能单纯依靠这篇小说的解读充分解决。如前所述,倘若老木匠和小木匠的争论仅仅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新自由主义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远远不同于小木匠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后者按照黄亚生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另一条道路”,老木匠和小木匠必须共同面对这个他者,这个已经成为现实的真正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于,两者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在一个理想状态中,或者说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中,小木匠的自然成长,是否就能使得中国积累足够大的能量,从而避免被动地陷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11)研究这一点,即是研究中国后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改革逻辑的一次巨变,同时为理解中国80年代与90年代的截然不同打开一个渠道。倘若“中国的另一条道路”真是一剂灵丹妙药,为什么中国非要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呢?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仅仅是中国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中国改革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国家内部,还是来自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循环?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论述是否根本上只是陈词滥调的反复?“中国的另一条道路”确实是一个精到的描述,但是它的全部能量是否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过后就不再存在,即使我们不能贸然称其为失败,可是寄太大的期望在这个“中国的另一条道路”身上,在多大程度上,这又只不过是充满浪漫色彩的怀旧热的一种变形呢?
注释:
①张达:反映变革中的真实——有感于《鲁班的子孙》,《山东文学》,1984年第8期。
②雷达:《鲁班的子孙》的沉思,《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
③秦晋:也谈对《鲁班的子孙》的评价—致雷达同志的信,《当代文坛》,1984年第10期。
④王润滋:《从〈鲁班的子孙〉谈起——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山东文学》,1984年第11期。
⑤卡夫卡:《讲故事的人》,《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9页。
⑥王润滋:《内当家》,《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
⑦王润滋:《从〈鲁班的子孙〉谈起——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⑧同上。
⑨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⑩关于《艳阳天》、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文学与劳动关系的解读,参见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2期。
(11)黄亚生:《中国的另一条道路》,王哲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