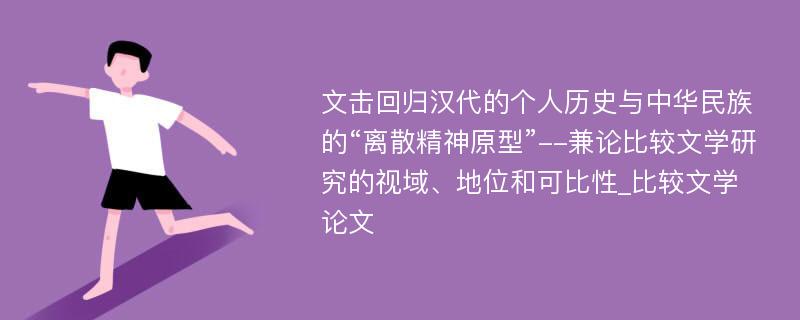
“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兼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立场与可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比较文学论文,华夏论文,可比性论文,原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8-0093-12
2003年,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长文中陈述了比较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转型。她认为,21世纪的比较文学正在经历的转型呈现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比较社会科学研究”(comparative social studies)。①这种现象最为恰切地呈现在福特基金项目官员托比·福克曼(Toby Volkman)所撰写的一本当时流行的小册子中。斯皮瓦克曾为这个小册子撰写了一个章节,就是“Crossing Borders”(跨界)。福克曼在这个小册子中具体描述了六个标题下的规定研究计划,其中第二个标题下规定研究计划就是“Borders and Diasporas”(边界与离散)。②
的确,在当下学术边界无际的研究视域下,比较文学的跨界性质适应了全球化时代对人文学科研究提出的前沿性要求,所以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敞开中最终走向了比较社会科学研究。但是,比较文学在研究的多元文化选择中也给自身带来了诸种困惑,其中一个重要的困惑就是由于研究视域在跨界中的敞开,从而导致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消失,比较文学在一种佯谬的姿态下走向学科的“死亡”。关于这一点,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长文中曾给予了详尽的论述。
于此,我们在逻辑上希望递进一步言说的是,学科边界的消失的确又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定位带来了困惑与焦虑。可以说,这种选题的困惑与焦虑长久以来直接困扰着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的培养及学位论文的写作,同时,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指导教授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科研与博士培养两个方面,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是一个让国际学界所瞩目的学科点。我们注意到,这里以往培养的比较文学博士其选题绝大多数是定位于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或日本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这些选题方向与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设在外国语学院有着直接的学缘关系。然而其中一部命题为《文姬归汉离散精神原型的跨艺术论述》的博士论文,却把研究的选题定位于中国传统文化,把“文姬归汉”及后世文学艺术以诸种不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③实际上,这一选题的定位不仅对台湾学界形成惯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对国内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因为,国内的比较文学是设定在中文系的,因此由于语境的不同,比较文学研究在国内与台湾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蔡文姬是一代大儒蔡邕之女,她博学多才且妙于音律。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战乱中,文姬遭遇了多舛的命运:夫亡守寡、掳掠离散、异族逼婚、边荒思乡、别子归汉、再嫁董祀及为董祀死罪蓬首跣足哭请赦免等,她个人饱经离乱的忧伤经历在生存的境遇中本身就是一段哀怨惆怅、感伤悲凉的历史叙事,而才女文姬又把这种忧伤寄托于文学书写,她以两篇五言、骚体《悲愤诗》及一篇《胡笳十八拍》,在历史上收揽了后世文人与民间读者关于离散与归汉主题的全部情思。
从东汉末年以来到当下后现代文化构建的全球化时代,以“文姬归汉”为叙事主题的个人历史,在汉语本土及外域的世界汉语文化圈被凄婉地讲唱了一千七百多年;的确,“文姬归汉”是个人历史,而这一个人历史被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所先后接受,他们借助于文学、音乐、绘画与戏剧四种审美编码在跨界中不断地呈现这一主题,在思念中以追怀悲愤来表达他们对“文姬归汉”的历史记忆,同时,他们也以此历史记忆呈现了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慨叹,也书写了对自身人格的期许。
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的维度提及“文姬归汉”的叙事主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这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作为四个叙事主题也曾被历代文学家与艺术家所敷衍、讲唱,并以此表现了草根族群用民间叙事的姿态所呈现的自我心理期许。然而,不同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是,“文姬归汉”不是从民族远古文化心理积淀下来的传说,其不是神话,也更不是巫术与原始宗教仪式,“文姬归汉”原是见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④当然,关于“文姬归汉”史料记载也见于残本《蔡琰别传》。
我们知道,在中国学术史上,关于“文姬归汉”及相关历史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方面。苏轼曾在北宋时期就文姬五言《悲愤诗》的作者身份提出过质疑,宋代学者车若水在《脚气集》对此曾有所著录,并且认为《胡笳十八拍》也非蔡琰所撰:“东坡说:‘蔡琰《悲愤诗》非真’,极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为之,其文辞甚可见。晦庵乃以为琰作也,载之楚词。”⑤关于骚体《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作者身份真伪的问题,一直是贯通中国学术史到当下被讨论的重要学案,可以说,关于文姬三部作品作者身份真伪的问题之质疑与考据曾吸引且成就了一批优秀的学者。
相当一部分学者往往习惯于从“比较文学”这个概念的字面上提取一种误读的意义,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比较”,并且错误地认定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多是把中国文学与外域文学进行“比较”,或更多地介绍外域的主流文学现象、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比较文学什么也不“比较”,而是对中外文学及中外文化进行整合性的汇通研究。我认为,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在把外域的学术背景作为自己知识构结的重要构成时,应该能够有效地研究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课题,以此使比较文学这个学科能够得到本土从事国学研究之学者的尊重,在本土学界安身立命,同时,其所依凭的研究视域及所形成的研究结论在国际性上又超越了国学,应该对国学研究者又获有一定的启示。无疑,这个要求使比较文学在研究的难度上加大了起来。
为了阐明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在当时所遭遇的困惑与焦虑,这里就《胡笳十八拍》作者身份真伪的质疑与考据罗列一个清单,展示一下在中国学术史上究竟有哪些学者曾经参与过这一问题的质疑与讨论。如参与和认同《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作的学者,有唐代诗人李颀、刘长卿,宋代学者王安石、郭茂倩、朱熹、王成麟,明代文人杨维桢、梅鼎祚,清代儒士沈用济、惠栋等;时至现代,文豪郭沫若曾连续发表7篇文章论证《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写,企图为自己在7天内创作完毕的大型历史剧《蔡文姬》力证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又如参与否认《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作的学者,从北宋朱长文的《琴史》以来,明代学者王世贞、胡应麟,清代大儒沈德潜都曾给予过质疑;现代学者胡适、郑振铎、罗根泽、刘大杰等都曾撰写了详尽的文章说明自己的质疑理由。关于五言与骚体《悲愤诗》作者身份的真伪问题,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与文史学家卞孝萱也参加了质疑性讨论。实际上,参与上述这些问题质疑与讨论的学者还远不止此。
我把这个清单陈设在这里是想告诉大家,关于“文姬归汉”及其作家作品身份的研究,其最有学术价值的讨论是集中在历史学界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界的,而那种把“文姬归汉”的历史降解为文学性故事的分析,对文姬三部诗作给予阅读者抒发个人才情的赏析性读解,其因缺憾学术价值且不足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而成立。展开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必须要对其所选题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解与反思。的确,从唐代以来,关于“文姬归汉”及其作家作品身份真伪的文史研究已经积累了诸多的学术成果,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介入这些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中国学术史上极具分量的著名诗人与优秀学者。可以说,如果执守一个传统的研究路数,“文姬归汉”作为一个学术选题实在没有给现下学者留下多少可以撰写博士论文的空间。再并且,关于“文姬归汉”一直是历史学界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重点,而学界都知道,学术研究绝对要规避那种对作家作品进行平面化的抒发阅读者个人才情的赏析性读解。也就是说,如果在文献的考据方面与出土文物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文姬归汉”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方面是一个无法出彩且被终结了的选题。
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角度来检视,历史上最早对“文姬归汉”在审美编码中进行敷衍的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蔡伯喈女赋》及《蔡伯喈女赋序》两部作品,据说前者是建安中为黄门侍郎的丁廙所撰,后者是曹丕为前者所撰写的“序”;而“文姬归汉”究竟是否是铭刻于历史本体的一件不可撼动的史实,这的确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争议,但是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至今也没有给出可靠的充足理由;当然,争议铸就了学术之间的质疑性张力,且推动了学术的前行。其实,《蔡伯喈女赋》是否为丁廙所撰,《蔡伯喈女赋序》是否为曹丕所撰,这两部作品是否是六朝文人的托名伪作,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界也都是有质疑的。丁廙及其兄丁仪包括杨脩都是曹植的羽翼,在曹植与曹丕的“继嗣之争”中,丁仪与丁廙是曹丕的政敌,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继王位后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家族男丁。关于这一史实,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⑥那么,无论是从政治逻辑还是从情感逻辑上讲,文帝曹丕是否可能为其政敌丁廙的《蔡伯喈女赋》作“序”?这是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学案。但无论如何,“文姬归汉”依然是见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
在我看来,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差异性在于,文学艺术这种审美编码的形式在虚构的敷衍中可以对历史进行再诠释,甚至是“过度诠释”(over interpretation),即历史脱离本体在文学艺术体验中走向审美化。这种历史的审美化可以投影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历代文学艺术家驻足于不同的时期与角度,面对同一件历史事件所完成的自我心理期许,这种历史审美化的再诠释、过度诠释与心理期许正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情结”(complex)的集体呈现。
从丁廙的《蔡伯喈女赋》及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始,一千七百多年来,“文姬归汉”已经敷衍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因离散而归宗的故事。从曹魏以来,文学艺术对“文姬归汉”这一主题已经构筑成多种审美编码形式,这无疑是文学家与艺术家写就的历史审美化的文学艺术发展史。这里有一个非常启智的理论思考,“文姬归汉”越不是本体意义上史实,越是一种依凭审美编码讲唱、敷衍及虚构的文学艺术现象,其越能够证明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沉积着一种因离散而归汉的血亲宗法意识。因为,成功的历史本体考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后来学者面对着历史不可给予误读性、过渡性与创造性诠释。也就是说,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可能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当人们借助于文学艺术在审美的价值期许中表达出来后,那就构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价值判断了,即历史在本体论的真实上不可再度言说的价值判断,文学艺术可以借助审美编码来坦然地呈现与扩张。文学艺术的敷衍、虚构与期许,无疑让历史现象在远离真实的本体距离中美丽且灿烂了起来。这是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在,也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
除去绘画之外,关于敷衍“文姬归汉”的主题见诸文学、音乐与戏剧三类审美编码形态。在建安的丁廙及曹丕之后,学界一般都知道有唐代李颀的七言古诗《听董大弹胡笳弄》、元代金志甫的杂剧《蔡琰还汉》,有明代黄粹吾的传奇《胡笳记》、陈与郊的杂剧《文姬入塞》、南山逸叟的杂剧《中郎女》,有清代尤侗的杂剧《吊琵琶》,1925年陈墨香编剧、程艳秋主演的《文姬归汉》,还有1959年郭沫若完稿,焦菊隐导演,朱琳、刁光覃、蓝天野主演的五幕历史话剧《蔡文姬》;1949年以来,“文姬归汉”的主题也曾被京剧、昆剧、吕剧、评剧、越剧、徽剧、粤剧及河北梆子等剧种移植而在中国本土频繁地演出过。
上述资讯是学界众所周知的事迹。我想陈述的是,时值20世纪70年代,“文姬归汉”的历史跨出了中国本土,被纳入美籍华裔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英语小说写作中,这一主题在她的小说《女勇士:生长在怪魔之中一个女孩的回忆》(The Warrior:A Girl’s Memorials Among the Ghosts)中被再度诠释,并且这是一次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过度诠释,也是一次极富异域想象性的“文化误读”(cultural misreading)。汤婷婷是美籍华裔女性主义作家,她在这部小说中关于“文姬归汉”的敷衍,是把这一主题从历史降解到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层面上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在最可能的虚构中表达了离散于故土的异域华人在文化心理上渴望归宗——归汉的心理期许。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汤婷婷这部依凭于“文姬归汉”主题的小说是如此的虚构,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非虚构”(nonfiction)类最佳作品的荣誉。我们必须承认,跨界所遭遇的文化误读恰恰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思考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在碰撞与汇通中生成了民族文化之间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杂混”(hibridity)现象,这一现象逼迫着国别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学研究转型,也逼迫着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社会科学研究再度转型,跨界成为当下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持有的立场。
从汤婷婷这部小说的个案,我们不难见出,一个主题从本土向异质文化语境传递时,这个主题在本土获有的历史性可能会降解为异域读者的误读性与猎奇性。的确,两个以上的民族文化与文学在碰撞、交流、对话与汇通中所产生的影响、接受、过滤与重构,这的确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到了21世纪,“文姬归汉”的主题被室内歌剧的综合艺术形式敷衍而再一次彻底国际化了。这就是中国著名编剧徐瑛、著名华裔女音乐家林品晶与美国导演林德·埃克特(Rinde Echert)三人合作的室内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Wengji:Eighteen Songs of a Nomad Flute,2001),这是一次让国际文学艺术界不可忘却的重大事件。这部作品曾于2001年在美国纽约首演,“中文的戏曲唱腔融合英文的西方歌剧演唱方式,中西乐器并置,让西方歌剧演员在具有中国戏曲身段和虚拟性空间的舞台上表演,编剧徐瑛是中国人,林品晶是生活在纽约和巴黎两地的华裔作曲家,导演则是美国人林德·埃克特,这三人的合作本身就是身份流动张力的实践”⑦。的确,“文姬归汉”这个主题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艺术审美编码呈现中,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进一步的国际化。
我想言说的是,一千七百多年前,“文姬归汉”是在胡汉两种文化碰撞与冲突之间所生成的一个历史事件;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至当下,“文姬归汉”这个历史事件被文学艺术的审美编码形塑为一个主题,在汉语本土、外域的世界汉语文化圈凄婉地讲唱,以此在民族文化的心理上铸就了一种因离散于故土而渴望归宗——归汉的思维惯性,并且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那么,追问这个主题背后的“离散精神原型”及其背后的因离散而归宗的血亲文化情结,就必然在最为恰切的学科逻辑上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
需要提及的是,“离散精神原型”在这里是于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个“源语概念”(concept of source language)。这个源语概念可以有两种方法翻译为英语目的语,第一种可以翻译为“the archetype of diaspora”,第二种可以在字面上直译为“the archetype of the spirit of diaspora”。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把用汉语表述的“离散精神原型”认同为一个源语概念⑧,这关涉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问题。从学科理论上评判,无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国际学界的平台上走向怎样的多元开放,但最终跌向了学科边界的无际,然而,我们必须界分出一位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据守的话语权力、文化身份及文化立场,我们是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大卫·达莫罗什(David Damrosch)等是美国学界英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汉语比较文学研究者与英语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语言持有条件与研究视域等是不尽相同的,一方对另一方以自己本土化的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给予苛求均是违背情理的。⑨所以对于英美学界来说,第二种翻译作为“目的语概念”(concept of target language)是在“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层面上完成的,因为,“离散”本身就是一种“精神”,“spirit”不必硬译出来。既然如此,离散——“diaspora”与原型——“archetype”这两个概念及在背后支撑这两个概念的整体理论体系,构成了研究者透视“文姬归汉”及其后世文学艺术以诸种不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呈现的研究视域,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学在这一选题的研究中遭遇了,并且形成了双向阐发的互文性思考及互文性研究。
思考到这里,还是让我们来阅读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所给出的一段陈述:“麻烦的是,霸权的欧洲语言(hegemonic European languages)只有几种,而南半球语言却不可胜数。惟一具有原则性的回答那就是‘太糟糕了’。老的比较文学不要求学生学习每一种霸权语言;而新的比较文学将也不要求她或他学习全部的下属语言(subaltern language)。”⑩尽管当下比较文学走向学科边界的无际,但斯皮瓦克一如既往地拥有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她把欧洲的法语、英语等看作为几种具有霸权性的主流语言,把除此之外的其他非主流语言称之为下属语言。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源于法国的一门学科,英文“subaltern”的语源即来自于法语“subalterne”及后期拉丁语“subalternus”,(11)“下属语言”这概念在修辞上本身就有着贬损性。斯皮瓦克在这里的表述是一个隐喻,也就是说,新老比较文学都是仗恃欧洲几种霸权语言而成立,且构建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地,所以,非欧洲国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也必须操用这几种霸权的欧洲语言。我担心的是,如果国际学界在这个意义上认同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因此,我在这里必须强调,我们从事的是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使用的学术汉语是我们在国际学界的文化身份所属,其截然不是下属语言。其实,法语与英语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应该是“下属语言”。较之于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我们就是强调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汉语中心主义”(centralism of Chinese language),这也不为过。也就是说,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进行学术交流时,要求双方都能够平等地使用对方的本土语言进行对话,而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及汉学家使用汉语的能力,较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使用外语的能力在水平上要低得多,而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汉学家正是以自己本土拼音语言的国际性霸权遮蔽了他们汉语能力及水平的缺席。
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因学科边界的扩张而走向了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等,宗主国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确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与冲突性,这是因为他们总是为了自己本土的利益与宗主国移民的文化主张而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
众所周知,“diaspora”是描述离散于巴勒斯坦故土在异域流亡与漂泊的犹太人族群,“diaspora”在修辞上沉淀着历史在记忆中描述犹太人离散于故土所遭遇的那些悲情,在《旧约》(Old Testament)的《申命记》(Deuteronomy)中,我们就可以提取到摩西告诫子民如果悖逆上帝即遭受“离散之咒诅”(Curses for Disobedience)的诸种相关修辞,我在这里仅著录《申命记》第20节的书写内容,就可以见出这是一些怎样的离散性咒诅:“The LORD will plague you with diseases until he has destroyed you from the land you are entering to possess.The LORD will strike you with wasting disease,with fever and inflammation,with scorching heat and drought,with blight and mildew,which will plague you until you perish.The sky over your head will be bronze,the ground beneath you iron.The LORD will turn the rain of your country into skies until you are destroyed.”(12)的确,仅在这一节的书写中沉积着太多的咒诅性修辞表达。把“diaspora”翻译为汉语“离散”之后,在汉语书写的字面上,一般汉语读者极少能够直接从这个汉语概念的字面上提取其源语背后的全部修辞性感情,而比较文学研究的要求在于,研究者在使用与阅读翻译为汉语的概念时,必须要把这个汉语书写的目的语概念在思考上回译于源语,以此提取源语概念背后全部的历史本质意义,否则对于那些从西方拼音语言翻译为汉语的理论概念,我们仅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往往获取的是隔膜且无效的误读。所以,我们在使用“离散”这个术语时,在学理的指涉上必然要回译于“diaspora”,用研究的比较视域网起沉积在源语概念背后犹太民族的全部流亡历史及苦难情愫。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概念所潜含的修辞情愫与全部历史意义,以此来研究文姬因离散于故土而归汉的遭遇,这样可以使“文姬归汉”及其文学艺术主题的研究获取了一个崭新的思考“维度”(dimensionality),从而给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更为丰富的诠释;同时,我们也需要把握汉语语境中“文姬归汉”的历史及其相关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以此来重新修订、改写与丰富“diaspora”这个概念的学理内涵。
的确,“diaspora”在汉语语境下被翻译为“离散”,由于汉语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使用,已不再是一个研究犹太文化的专有概念,而是一个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性的离散”(diaspora of Chineseness)概念了。也就是说,“离散”成为一个获有统摄世界性文学思潮的“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概念了。(13)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文姬归汉”及其后世文学艺术以诸种不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中,我们怎样追问一个贯通华夏民族文化历史的“离散精神原型”呢?(14)思考在一种追问的逻辑力量中必然把我们的设问与关注从“离散”导向“原型”这个概念上来了。
依然是众所周知,“archetype”这个概念是由希腊文“arche”与“type”两个词构成的。“arche”的原初意义是“first”,我们还可以把“arche”讨源到它的动词形态“archein”那里。《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关于“archein”的释义是:“from Greek:archein,to start,hence the starting point or beginning,first principle or origin”(15)。这部辞典的英语释义告诉我们,“开始”、“起始点”、“开端”,“第一原理”与“起源”是“arche”这个概念存有的全部内涵,学界一般认为,是希腊智者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最早起用这个概念把宇宙的终极命名为“原初实体”(first entity)。此后,从泰勒斯(Thales)等到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腊哲人依凭这个概念的操用在哲学本体论上完成了对宇宙终极的猜想,并构建了各自的“哲学宇宙论”(cosmology)体系。在学理上,哲学宇宙论是以思辨理性猜想宇宙的本原,企图为人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终极,因此,哲学宇宙论也被定义为“理性宇宙论”(rational cosmology)。
让我们的思考逻辑再度追问下去,把“type”这个概念讨源到希腊文“typos”那里。“typos”的原初意义是“pattern”(形式)或“stamp”(印记),当我们在词源的追溯上行走到这里时,“archetype”这个概念的原初意义清晰地出场了:“From Greek:arche,first+typos,pattern or stamp,the original model or pattern from which things are formed or from which they become copies.”(16)非常值得提及的是,英文的源语解释比汉语的译入语要容易理解得多:“指事物据以形成或变成复本时所出自的原始模型或形式。”(17)在柏拉图的哲学本体论体系构建中,理念即是被可感知的现象界所模仿并决定现象界生成的原型,即“ideas”就是“archetypes”。(18)
据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至少由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英语版《亚里士多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没有使用过“archetype”这个术语,但是其中英译本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第五章讨论“origin”(起源)的问题时,译者曾给出一个重要的语言还原性注释,以此把“origin”的释义追源到希腊文“arche”那里去:“‘Origin’ translates ‘arche’,elsewhere often ‘source’ or ‘(first)principle’.In Greek ‘arche’ also means ‘rule’ or ‘office’,whence the illustration under(5).”(19)从西方哲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逻辑上考查,从柏拉图历经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的古典哲学始终是在“archetype”所成就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思路上构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因此,从“archetype”这个概念的词源本质及其学理性来看,在相当的程度上,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承继的必然还是柏拉图主义。其实,我们在言说黑格尔于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上依然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时,言下之意的隐喻是:我们全然不应该忘却“archetype”这个终极概念的逻辑力量是怎样的强大,其推动着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在一种不变的思维“原型”惯性中生成与发展。
我们在词源上回溯“archetype”的原初意义,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荣格及原型理论。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构建原型理论时,是从哲学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而获得启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在译介与使用原型理论时,缺少更多的学者把荣格分析心理学的“archetype”这个概念在词源上追问到希腊哲人的本体论那里去,以至国内学者在操用这个概念对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民间传说及文学艺术的某些现象及主题进行追问时,缺失了这个概念于词源上在古希腊哲学本体论那里对终极追问的学理性感受。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比较文学方向下对“文姬归汉”这一个人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就是为了给华夏民族文化传统追溯一个“离散精神原型”,从学理上判定,这一“离散精神原型”必须是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的一种“集体无意识”(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比较文学研究把西方的原型理论带入作为一个透镜,准确地讲,是把原型理论及其相关背景学理与“文姬归汉”及海内外文学艺术对这一主题的敷衍整合在一起,最终给出一个崭新的结论性判断。我们在这里极度感兴趣且希望递进一步言说的问题是,荣格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那里承继“archetype”这个概念,以构建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他的原型理论构建是把“archetype”关于终极的思考从哲学带入心理学,以分析心理学(analytic psychology)的研究姿态把自己的研究视域投向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民间传说及文学艺术,企图在其中追问一个民族原始文化心理的一种终极,这个终极从远古的荒蛮时代在逻辑上链接于现代人的心理文化,并成为一种在历史中复踏回环的心理记忆,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复踏回环的心理记忆就是原型——集体无意识。
我们也知道,欧美心理学研究界更注重实验心理学,他们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缺憾实验的可能性持有质疑的态度;但是,这两位心理学巨匠恰恰以思想为文学艺术批评及文化研究提供了具有哲学分析性的心理学基础。在我看来,比较文学以“文姬归汉”为研究个案,这种学术跨界的交集性研究当然可以成为追问“离散精神原型”的理论分析依据了。
其实,西方哲学理论与文学艺术理论在其本土学术语境下的使用也特别注重在词源上的考据,以便把一个个古典、现代或后现代理论概念在词源上逻辑地链接到古希腊的历史语境中去,西方学者一定不是阻断历史而在当下凭空捏造一个概念,在学术的历史语境缺席状态下虚构一套理论。如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学在词源上把“dasein”(此在)追问到古典语言那里,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把“logos”(逻各斯)与“difference”(差异)等概念在词源上也追问到古典语言那里,然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再于语言交织于历史的发展脉络上逻辑地使用这些概念。当西方理论从本土源语译入汉语目的语时,中国学者往往习惯于望文生义地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而忽视了这些译入语概念背后的源语词源逻辑系统,这是非常遗憾的。
原型理论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那里,在学科发展史上经历了从哲学的终极追问到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的一个个终极原型的追问,(20)以此构建了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这显然已经是一种在哲学、心理学与神话等多种交集空间所完成的跨界思考与跨界研究了。实际上,在荣格之前,英国剑桥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他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中已经有类似的学理性研究。值得提及的是,弗雷泽也的确是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这些空间中,因为,这些空间是更具有原始性、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的文化形态。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把“archetype”带入上述空间中追问一个个“原型”,是把理性宇宙论的思辨逻辑在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空间中扩大化使用了,因为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是从史前原始氏族依凭口耳相传积淀而来的原始文化形态,其具有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所以,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为荣格及其理论的追随者在原型的研究上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与假设性。
荣格把这个本体论的哲学概念带入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中,重新赋予了这个概念崭新的学理意义,使这个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转型为一个分析心理学、文学艺术批评及文化研究共享的重要术语。为什么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如此晦涩?因为荣格是把哲学本体论关于终极猜想的概念带入心理学体系的构建中,让一贯崇尚实验性的心理学涂染上了哲学的思辨色彩,同时,这也使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抽象的理性追问一个民族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成为可能。一如我在前面所言,在中国学术史上,关于“文姬归汉”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是集中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文献辨伪方面,而比较文学研究把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带入,促使“文姬归汉”的研究在实证与考据的基础上介入了理论分析。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以“文姬归汉”为中心,在为华夏民族文化追问一个“离散精神原型”时,“文姬归汉”恰恰不是神话与民间传说而是历史,当然更不是巫术和原始宗教仪式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篇书写的开始处即强调:提及“文姬归汉”的叙事主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四大民间传说;四大民间传说被后世文学艺术在审美的编码上敷衍与讲唱为叙事主题,与历史事件的“文姬归汉”被敷衍与讲唱为叙事主题,两者在文化形态的本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无论如何,“文姬归汉”是见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的确,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存在形态截然不同于历史,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原始性、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为哲学或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带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猜想空间。
我们能否以一个历史事件为中心来追问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型?当然我们必须要在研究的思路与技术上给出重要的调整。从理论上评判,“离散精神原型”的提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一观点的提出把集体无意识的追问从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文化心理推衍到人类文化的自觉时代,无疑,两汉是华夏民族文化定型的自觉时代,以至于华夏民族文化可以在这个历史时期被称之为汉民族文化。如果说,文姬离散与归汉的历史事实被后世诸种文学艺术及民间叙事在复踏回环中进行审美编码,从而形成一种不可抵挡的主题陈述,并且最终走向外域,这也证明从历史的源头或早期以来,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确潜在地存有这样一个情结,这个情结作为原型一直期待着能够显现它的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叙事主题的发生与到来。非常有幸的是,或者说,非常不幸的是,历史选择了蔡文姬,蔡文姬以她孱弱的女性身体担当了这一切。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文姬的离散与归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与恰当的历史人物谱系中,恰当地成为“离散精神原型”的恰当显现,同时,也成为一个恰当的“离散精神原型”的叙事主题。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即便“文姬归汉”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然而后世的文学艺术在审美创作的编码上需要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积淀着对这样一种原型表达的期待。
当我们的思考行走到这里后,我们再来阅读荣格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ic Studies)一书中关于无意识心理情结的一段论述,或许会有着更为启发性的理解:“主体是一个确切的原动类型(motor type),通过对主体进行的试验,越发明确原动知觉(motor perception)显然控制着其它诸种感觉。原动倾向也是通过强大的运动活力而外在地呈现出来的,同时也呈现为一种强大的原动表现的发展力。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具有能动性的自动力(active motility)显然超越了意识运动感觉的界限,在原动的自动作用(motor automatisms)中传递,而原动的自动作用是通过诸种无意识的心理情结(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complexes)而促使活动的。在正常状态的反应中,存在着两种语言的自动作用,它们可以证明与无意识情结有着联系。这个情结与一个过去的约定有着紧密的影响关系。”(21)荣格在这里所论述的主体的原动类型及其无意识心理情结指涉的就是原型。
在此我们可以见出,从西方学界译入的原型理论在东方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获有一种终极追问的逻辑力量。当然,“文姬归汉”的“汉”,不应该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汉民族文化”,应该是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视域上理解为具有宗法血亲意识的华夏民族文化,只是在文姬离散与归汉的那个特定时代,华夏民族文化被称之为“汉民族文化”而已;时值全球化时代的当下,“文姬归汉”之“汉”被栖居于海外的华裔在他们的异域创作中,敷衍与尊崇为中华母语文化的原乡情结。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曾把西方分析心理学及原型理论译介到国内学界,他们的努力曾对国内学界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前瞻性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国内学者成功地操用原型理论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体系的构建上给出一个完整且自洽的原型个案研究并不多见。从学科理论的面相上分析,比较文学研究依凭其四个跨越的敞开视域,以“文姬归汉”为中心,从而展开关于“离散精神原型”的跨界研究,其最终是在汇通中对西方的原型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层追问的一个典型个案。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集之间,这一个案为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一方崭新的空间。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构建了“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的理论,文学艺术是一方公众审美空间,历代文学艺术对“文姬归汉”这一主题在叙事中的复踏回环,使“文姬归汉”的个人经验在历史的地图上,必然放大为整个民族所储存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种集体记忆也必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另外一种学理性表达,当然“文姬归汉”的历史记忆也是在一个面向上对沉睡于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血亲中心意识的唤醒。
哈布瓦赫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历史记忆的当下性,作者在历史记忆中借此对自身的期许实际上介入了对当下社会的期待与评价。公众都是依凭自身的价值评判在选择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同时,国家意识形态也依凭政治权力迫使公众选择历史记忆,这必然导致公众以反记忆来抵抗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历史记忆。曹操以君主的权力使用重金把蔡文姬从左贤王那里赎买回来后,她个人的经历却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公众在离散中期待回归故土的心理诉求提供了历史记忆,这种个人经历超越了政治与权力升华为一个民族公众的历史记忆,这在中国历史的图景上是为数不多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见出这一课题研究的价值。
由于比较文学不可遏制地呈现出研究的跨界性,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其必然成为一门全球国族文化、区域文化及国际政治批判的前沿学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皮瓦克在其比较文学学科论述中总是充溢一种国际文化的政治批判之偏激,如她的长文《一个学科的死亡》是从柏林墙的垮塌来论及比较文学对一个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到来的适应性:“从1992年以来,在柏林墙垮塌后的3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似乎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改革。这大概是在回应崛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大潮。”(22)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这里比较文学关于“文姬归汉”的选题及离散精神原型研究的结论接受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学科意识,但又没有像斯皮瓦克那样过多且敏感地把比较文学研究推到国际区域文化的政治批判中去,其选题与结论更多的是从纯粹文学艺术的学理角度以完成研究者的思考与写作,同时也满足了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设问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或者说,比较文学就是国际化的文学研究。
注释:
①按:“comparative social studies”是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我们可以见出本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转型,因此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国内比较文学研究者的
关注,并且学界不能把这个概念翻译为“比较社会学研究”,应该被翻译为“比较社会科学研究”。
②按:在福特基金项目这个小册子中,福克曼(Toby Volkman)在六个标题下设计了规定的研究计划,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出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比较社会科学研究的倾向性:“Reconceptualization of ‘Area’(区域的重新概念化);Borders and Diasporas(边界与离散);Border-Crossing Seminars and Workshops(跨界研讨会与工作坊);Curricular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课程的改革与整合);Collaborations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Activists,and the Media(与无政府组织、激进主义者与媒体的协作);and Rethinking Scientific Areas(科学领域的再思考)。”关于比较文学被区域研究与文化研究所取代,其最终被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称之为比较社会科学研究的论述参见[美]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一门学科的死亡》(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3.p.7)。
③按: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作者是台湾学者蔡明玲。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这部论文把“离散精神原型”溯源到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的诗性书写中,“文姬归汉”是以一个历史事件对先秦诗性书写中潜在的离散情结的呈现与担当;因此,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面向上来评判,“文姬归汉”是一个主题而不是一个母题,因为“文姬归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叙事表达了。在《比较文学概论》的《主题学与流变》一章中,南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者王志耕曾对母题与主题的区分给出过一个严格的界定:“母题是对事件的最简单归纳,主题则是一种价值判断;母题具有客观性,主题具有主观性;母题是一个基本叙事句,主题是一个复杂句式;主题是在母题的归纳之上进行的价值判断,因此,一般说来,母题是一种常项,主题则是变量。”(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④《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见《二十五史》,第2册,第1046页第4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据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影印。
⑤[宋]车若水:《脚气集》,第1页,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⑥《三国志·魏书》,见《二十五史》,第2册,第1133页第3栏至第1134页第1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据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影印。
⑦蔡明玲:《文姬归汉之离散精神原型的跨艺术论述》,第49页,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年定稿本。
⑧按:在这里,我们刻意强调研究者用汉语提出的“离散精神原型”是一个源语概念;在这种强调中,我们是在坚持一个重要的学术立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时,所操用的概念几乎都是从西方学界翻译为汉语的目的语。在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方面,我们把自己所操用的理论概念界分为源语与目的语时,本质上,已经凸显出我们在学术身份上屈就于学术从属地位的差异性了,即在学术研究的理论概念操用层面,中国学者永远是目的语概念的使用者,而不是源语概念的构建者。在《翻译、重写、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一书中,英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vere)曾讨论了翻译是重写的问题,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译者被他所生存境遇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给予的“操控”(manipulate)。我的观点是,无论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在怎样的理论力度上把翻译认同为“重写”(rewriting),西方理论的源语概念在学理的逻辑上对译入中国本土的目的语概念有着极为强制的操控性。因此,我在这里强调蔡明玲用汉语提出的“离散精神原型”是一个源语概念,这是在学术身份上凸显了中国学者在汉语本土构建理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⑨按:但是,我还是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在西方本土学界操用英语、法语或德语以陈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比欧美学者在中国本土学界操用汉语以陈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能力上不知道要强到哪里去了。当然,从这一点也可以见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依然属于弱式族群,他们必须操用较为流利的西方学界本土语言与西方学者对话,以便挤入国际学界。我们应该有理由要求西方学者操用起码的汉语与中国学者对话,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力不应该仅由西方语言来决定。让我最为欣赏的是康士林教授作为前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始终保持操用较为流利的汉语与中国学者交流。一位西方学者能够操用流利的汉语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这不仅说明他具有一门熟练的外语能力,也说明他在学术与文化姿态上的谦卑。在国际化的时代,语言不仅只是一种跨界交际的能力,而也是一种在处世姿态上让学者流露出傲慢与谦卑的界标;在国际学界,那些能够以一点较为流利的外语在西方学者面前小心翼翼表现出恭敬的非西方学者,往往归国后对自己故土的学者充满了傲慢,且端出一幅“学术买办”的架势,仿佛他就是西方学者的代言人,甚至仿佛他就是西方学者。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洋务运动”现象的确是值得讨论的。
⑩[美]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一门学科的死亡》(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3.p.10)。按:当然,这几门欧洲霸权语言对于西方本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本来就是他们的母语,所以用不着要求他们再学。从斯皮瓦克的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见出她是一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在“新的比较文学将也不要求她或他学习全部的下属语言”的表述中,她用人称代词指称上一句的“学生”时,刻意把“her”(她)强调出来,把“him”(他)放在后面。
(11)按:“sub-”是拉丁语的前缀,表示“在……之下”。
(12)《圣经》(和合本·新国际版),第334页,香港,国际圣经协会有限公司,1996。按:此段英语引文的汉译如下:“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的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在这里我引用英语是为了请读者直接阅读英语在这段书写中所使用的那些咒诅性修辞,这样可以获取不同的阅读感受。
(13)按:在国际学界,“总体文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少被中国学者带入使用,实际上,中国学界一直被总体文学现象所操控,因此我在这里愿意自觉地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我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曾对总体文学给出过一个界定:“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93页)
(14)按:严格地讲,我们在这里使用“汉民族文化”与“华夏民族文化”这两个概念,可以呈现出我们在研究中所表达的不同文化立场。
(15)(16)(17)[英]尼古拉斯·布宁著,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第68、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8)按:这里的“ideas”与“archetypes”应该使用复数,是指现象界诸种存在对本体界各自原型的模仿。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见《亚里士多德全集》(Aristotle,Metaphysics,s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Jonathan Barn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91.p.60)。按:《形而上学》第五章关于“origin”(起源)的讨论,是从六个层面展开的,从我引用的英语原文中不难见出“arche”在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思考中的终极指向性:"We call an origin(1)that part of a thing from which one would start first,e.g.a line or a road has an origin in either of the contrary directions.(2)That from which each thing would best be originated,e.g.we must sometimes begin to learn not from the first point and the origin of the thing,but from the point from which we should learn most easily.(3)That from which(as an immanent part)a thing first arises,e.g.as the keel of a ship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house,while in animals some suppose the heart,others the brain,others some other part,to be of this nature.(4)That from which(not as an immanent part)a thing first arises,and from which the movement or the change naturally first proceeds,as a child come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and a fight from abusive language.(5)That by whose choice that which is moved is moved and that which changes changes,e.g.the magistracies in cities,and oligarchies and monarchies and tyrannies,are called origins,and so are the arts,and of these especially the architectonic arts.(6)That from which a thing can first be known; for this also is called the origin of the thing,e.g.the hypotheses are the origins of demonstrations.(Causes are spoken of in an equal number of senses; for all causes are origins.)It is common,then,to all to be the first point from which a thing either is or comes to be or is known; but of these some are immanent in the thing and others are outside.Therefore the nature of a thing is an origin,and so are the elements of a thing,and thought and choice,and substance,and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for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re the origin both of the knowledge and of the movement of many things."
(20)按:这里的“终极原型”在语言的表述上是同义重复的,“原型”就是“终极”,但是一般学者无法从汉语书写的“原型”这一概念的字面上看视出它的终极性意义,所以在此我于汉语表述上强调性地使用一次“终极原型”这个表达。
(21)[瑞士]C.G.荣格:《精神病学研究》(C.G.Jung,Psychiatric Studies,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F.C.Hull,Second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55)。
(22)[美]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一门学科的死亡》(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3.p.1)。
标签:比较文学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姬归汉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文艺论文; 悲愤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