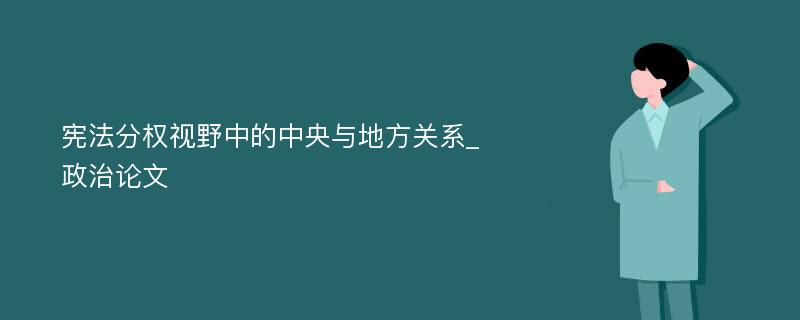
宪政分权视野中的央地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视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宪制建构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这样一个制度前提如何才能具备,确确实实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者、行政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如何才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探讨宪政分权视野中的央地关系,逻辑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区分宪政视野中的两种分权、一个指向。通常,论述宪政制度中的分权都只讲横向分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割的制衡。但实际上比宪政的横向分权方面更为紧要的一种分权,长期以来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宪政的纵向分权。横向分权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分权制衡的体制。因为在一个现代的国家体制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横向分权就可以解决好分权问题的。宪政制度当中的两种分权必须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并注意它们同时指向的控制国家、规范权力的目标。
第二,申述在宪政分权视野中,纵向分权对一个国家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如果不分权会怎么样,而分权又会怎么样,在比较说明中阐述大国的分权体制选择。
第三,把问题坐实到中国,如果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创新改革,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好的纵向分权,并为一个好的横向分权奠定基础。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宪政视野中的两种分权、一个指向
所谓两种分权,一个就是横向分权,这是我们比较了解的。所谓一个指向,就是不论两种分权的具体结构有什么差异,它们都指向限制权力的一个端点。这种分权的制度化安排是现代政治的独特后果。但是,在历史上有它的脉络可寻。我们不妨从古代中国的一统制开始寻找分权制的线索。
1、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制
在古典社会里,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最后、最高权力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帝王。基本上,在我们中国3000年的古典传统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安排都是一套中央集权体制。
在这种制度安排里,没有任何真正制度意义上的纵向分权或者横向分权,所有权力体系当中的人都是为皇帝尽忠的。
2、分权结构问题产生的背景
宪政分权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是可能的。
第一,在市场经济的情形下,这是经济基础。按照罗马民法的原则,作为一种扩展形态来说,当我有一笔私有财产,而又是在一个大型复杂社会里,我的谋生与他人、与高一级的官员、政府都无关的时候,我可以不听你的,我们才可以有一种理性妥协和相互协商的状态,不至于牺牲我的政治原则、正当利益和个人志趣,而被迫地服从。这就是经济学家们特别强调的私有产权在宪政结构里的基础性价值。
第二,在市民社会的局面中,这是社会基础。当国家对于社会处于一种古典情形下的通吃状态的时候,独断地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不会有丝毫尊重他人的意念的,他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治理国家的各种事务,有理性的时候,他成为明君;没有理性的时候,他就是恣意妄为的暴君。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才使得国家权力的内部分割与外部制约同时发挥作用,也才足以催生安顿权利与权力的宪政制度。
3、现代宪政的四大要素
从宪政的结构要素上讲,它需要绝对相互勾联在一起的四个因素支撑,才具有从可能性演变为现实性的动力。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现代宪政四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私有产权。因为只有统治者不能剥夺普通公民生存权利的时候,握有权柄者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讨价还价才有可能。
宪政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人权。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真正使它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权一定是至上的,它一定超过我们通常所谈到的国家主权。因为主权是为人权而设的,没有人权,主权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宪政的第三大要素是分权制衡。古典国家建构的合法性辩护进路几乎都是“君权神授”,但是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治建构是一种理性建构。就是通过人为的设计、契约的安排,通过组织架构的分割,通过组织职责的划分,把国家理性化。
立法权制约行政权,行政权必须依法行政,法律从哪里来,来自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提供的法律一定要是良法,而不是恶法。恶法是与宪法精神相冲突的。而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都必须按法律精神办事,宪法是神圣至上的。一个法律条规一旦合宪地制定出来,哪怕有缺陷,在没有修订这个法律之前,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文本来执行,而不能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来实施法外行为。法条主义与程序主义就此具有重要意义。
两种分权结构,有一个共同指向:使国家行为、政府行为,尤其是后者,作为配置日常资源、行使日常权力的、霍布斯所称为的巨无霸,能够被约束起来。国家权力、政府权力会自我膨胀。霍布斯写《利维坦》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国家是个巨无霸,它像一个巨碾一样,一碾过来,不仅自身无限扩大,而且吞噬力惊人。从权力内部结构上将权力做有效分割,可以达到有效规范权力的目的。于是,对于现代大型复杂国家而言,单一制的政治结构就不利于分权制衡机制的建立。而有必要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分解。联邦制的政治建构就具有了某种限制权力的重大意义。不把央地权力进行有效的划分,纵向权力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也就会影响横向权力分割制衡的效果。因为一个权力结构不清晰的央地权力结构,从中央权力到地方权力都会陷入一种各自为阵、争夺利益的状态。横向权力的分割制衡就会被这种政治紊乱所打破。
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使国家、政府规范化,不能滥用权力。政府太容易滥用权力了。两种权力分割都是指向控制国家、规范政府的。控制国家越有效、政府就越规范,政府办事的绩效也就越高。国家、政府的权限越有限,宏观控制能力在其应该发挥功能的领域里,也就越有效。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就此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关联是,如果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的规范建构,那么有效政府的建构就是一个海市蜃楼。
怎么控制国家、规范政府呢?这就是宪政的第四个要素法治解决的问题。法治,对中国习惯思维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法治的含义就是法律主治,就是以法律排开一切个人和组织的背景关系,而具有一种法律抽象统治的能力。法治,即现代形式化法律的统治,是没有例外法权的。只要有一个例外法权,而这个例外法权不是循法律的途径而得到的,那么,一切再严肃、甚至再完美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英美的判例法,经常有例外,但是这是循法律的途径得出的例外,那还是法治范围内的事情。一旦溢出法律的边界,一个例外,就是对法律权威性的颠覆。所以,我们说法治,不是靠法律统治,不是依照法律统治,而是以法律统治,是法律本身的统治。
中国央地关系的宪政安顿
确认了宪政纵向分权的重要性,我们就有了将之放置到中国处境中加以分析的理论理由了。在中国,宪政分权视野中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应当怎么处理呢?今天的中国要在宪政的层面解决央地关系问题,有很多环节需要具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首先,必须要做到三个避免:
第一,要避免央地权力博弈的崩盘。这不是危言耸听。一旦地方政府太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不是不可能出现。诸侯政治演变为全国政治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的。同时,一旦中央政府太过强大,也会造成地方发展缺乏活力,事实证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采取全国一刀切的政策,并对地方政府进行强势控制,会极大地限制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发挥其发展能量。最好的状态是中央力量布局和地方力量布局形成一个巧妙的平衡。否则就可能出现两个极端的痉挛症。国家没有统一的政治平台,国家就会崩盘了。现代民主国家特别强调国家平台的稳定建构。国家平台的稳定建构就是一个宪政建构。宪政建构就是一个分权制衡建构。所以,我们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崩盘,一定要走向宪政分权。
第二,要避免中央和地方政府双方的不信任。在自利的政府定位分析基点上看问题,一方面,具有明确的地方意识的地方政府,有一种恨不得把地方所有利益都留给地方的天性。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调整地方利益的政策或明或暗都有一种抵抗的冲动。另一方面,明确站在全国高度审视问题制定政策的中央政府,也会不由自主地采取“杀富济贫”的政治平衡术,从而对于不太顺从中央政府指挥的地方政府加以强力控制。于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此陷入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猜疑的局面之中。在宪政架构中,中央政府服从国家权力制定的规则,向全国人民负责。地方政府服从地方权力机构制定的规则,向地方人民负责。双方各自具有责任来源,也就各自具有工作动力。同时双方又具有双向的行政责任,不能以相互的推诿来回避责任。这样,双方必须以互信来支持各自的运作。
第三,要避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混用。从政治性权力的角度看,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全国范围的选举认可。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区域选举的直接认同。因此,中央政府不能随意支配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国家范围的事务上也不得随意对抗中央。没有这种政治性权力的宪政布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双方之间也就不会相互尊重。就行政性权力而言,财权、事权、人权都应有明确的划分,分级分层针对不同范围、大小、轻重、缓急、主次划分明确的权力处理各自的事务,就成为各级政府有效治理公共事务的前提条件。只有将政治对于行政的控制适度化,同时给行政以集权并追求绩效的空间,国家的整全治理和地方的区域治理才可能两全其美。
其次,要处理好央地分权关系,必须注意三个关键问题:
其一,国家基本法律即宪法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与有效规范。这是两个相互限定的方面。一方面,从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需要将国家层次的权力结构有效设计为分权制衡的架构,从而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安顿好。宪法有必要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及其职能、对于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以及职能划分、对于国家司法系统的构成及其职能有一个清晰明白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从地方权力机构的构成上分析,地方立法机构的组成与职能、地方政府的组成机构与职能、地方司法机构的组成与职能都仅仅停留在笼统的说法状态,没有能够将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与人员来源及人数加以明确规定。宪法对于抽象政治原则的重视远远胜于具体治国举措的设计。这就注定了宪法的纯粹文献性质。由于执政党的权力太具有同一性质,它对于宪法分权制衡原则的消解不容忽视。为此,真正要在宪法层次规定清楚国家与地方的权力分界,就必须真正将执政党也纳入到宪法的轨道。缺乏真正保障宪政的宪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处理好央地关系。
其二,将国家权力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作制度的切割与关联。这是在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外关乎央地关系的部门法所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其实,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进行清晰的划分,并将之制度化,只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地方的发展。在宪政制度中,中央权力得到了组成国家的各个地方的法律性承诺,维护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就成为各个地方的政治义务。非集权化就此成为国家政治共同体得以延续的条件。同时,在非集权化的政治状态中,地方政府只要服从国家宪法,就可以合法地开发合乎地方特点的政策和项目,从而对地方的发展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不至于使得地方的特性被中央的一致性要求所掩盖。
其三,把刺激地方活力与维护中央权威作为央地关系的轴心问题。刺激地方活力需要两个支持条件,一个条件是中央权力机构布局的时候给地方留下政治法律空间,另一个条件是地方权力对于地方责任的担当。前者是建立在国家权力的宪政布局基础上才具有的可能性。后者是建立在央地关系的法治状态下才具有的可行性。对于宪政布局中的央地关系而言,中央权威是地方之间具有弹性与活力的保障条件。
再次,要处理好央地分权关系,应当注意三个重要行为边界:
第一,央地两端应当各自谨守权力的边界。不论是中央的权力还是地方的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基本性质就是公权公用。掌握权力的央地两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都首先应当有一种基于公共权力的公共布局、公共使用和公共举措。因此,中央政府不是仅仅站在中央高层的角度考虑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问题,地方政府也不能仅仅站在区域利益的角度考虑地方利益的捍卫问题。各自必须承诺一个公正、平等、相互分割但互相制衡的权力体系对于国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宪法层次将中央权力体系与地方权力体系进行制度化安排之后,各自谨守权力的界限。有两个限度必须加以重视:一是中央权力不能随意根据国家全局来褫夺合宪地属于地方的权力。二是地方必须合宪地支持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行使的权力。促使央地两级权力对于宪法规定的权力格局的认同,对于宪法权力的尊重,对于宪法权力的遵守。
第二,央地两端应当各自尊重相互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权力代表了国家全局的利益,地方权力仅仅代表区域的利益。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是有的,但是差异性也是必须予以确认的。单一制框架中对于两者利益的一致性强调甚多。但是,基本上处于一种中央权力吃掉地方权力的状态。联邦制结构则比较弹性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中央权力代表的国家层面的利益,当然应当在各个区域的权力体系中获得响应并坚决支持。但是,这些权力与利益必须是有限度的,也必须是依据宪法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一个顾全大局就将地方利益调拨到中央或中央着意的地方。这个时候,合宪地区分中央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财政收益就是必要的。同时,地方不应为了地方利益而损害中央利益,即既不能多报地方收益而以上缴来获得中央的权力褒奖,也不能少报收益隐瞒中央来做大地方利益。这对于央地关系进入一种相互信任的状态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
第三,央地两端应当相互维护各自的权威。人们常常会以为,中央权力的权威性要大于并高于地方权力体系。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在宪政的权力制度安排中,中央与地方的两种权力体系对于国家的健康存在与稳定发展,具有同等的地位与功用,因此两种权力应当是平等的权力。国家权威来自权力的制度化安排,宪政是国家权威的最后与最高依据。只要在宪政的框架内,哪方服从宪政规则,哪方就应当获得宪政支持,它的权威性资源就应该更为丰富。哪方越出宪政框架,就丧失了权力成为权威的法理资源,也就丧失了合宪性地具有权威性的起码依据,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地保障它的权威性。一旦一个越出宪政框架的权力体系之不具有权威性形成为国家共识,我们就可以期待权力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可,其权威性资源的聚集也就达到令人们满意的状态。
一切宪政理念及其分权建构都是为了使权力运作规范化。这种规范化运作的整体状态就是能够达到三个三元共同存在的建构。第一个三元共同存在的建构是国家、社会、市场,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权力原则运转。国家以法律赋予的国家权力结构来运转。社会按照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机构,组织化运转。而市场按照价格原则运转。各自按照这三元建构的原则运行,国家就是最稳定的。第二个三元建构是国家权力建构自身要有一个三元建构,那就是立法、行政、司法的制衡建构。这也就是宪政分权制衡结构中的横向分权制衡截面。再一个就是中央、地方与基层的三元建构。这就是一个本文探讨的宪政分权制衡的纵向分权制衡截面。一个国家是不是宪政国家,是不是现代国家,就要通过这三个三元建构是否健全而能够相互制衡,又能够相互依赖,来加以判断。这种局面仅仅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宪政分权制衡框架内才有可能达到。
在一个国家的非宪政权力安顿局面中,国家是可以非常成功地控制住权力的。而且这样的国家运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空间条件下还会显得十分强盛。但是,这种权力控制,由于依靠的不是稳定和忠诚都具有保障的宪法,而是依靠权力之间的权术制约。权术的玩弄必定不是制度的延续。因为权术最后一定要落于阴谋的较量,而不会走向基于“阳谋”的沟通。久而久之,国家权力体系就会在阴谋的侵蚀下,丧失健全的权力心智,而难以维持下去,最终被权术阴谋断送掉国家的前途。这或许是一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史给我们最佳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