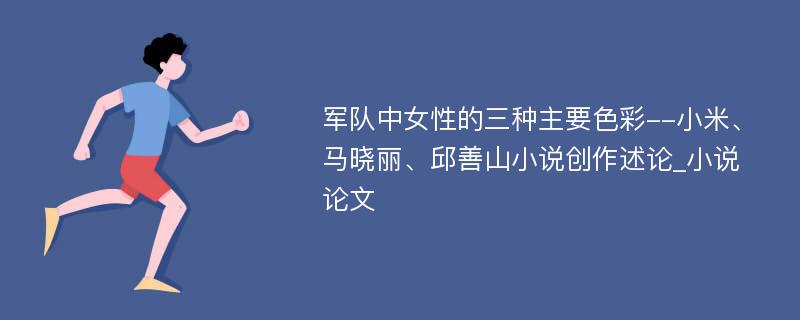
军旅巾帼三原色——谈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的长篇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色论文,巾帼论文,军旅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小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等为代表的女作家的崛起,无疑是最令人注目的亮点。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多年以来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鲜有女作家作品问世,她们的涌现就为军旅文学营建了别样的景致(虽然这也可以成为欣喜的理由),而是因为当她们刚刚迈向长篇小说领域的时候,就不动声色地显现出敏锐的思想和出色的艺术驾驭力,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乃至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质点。军旅长篇小说因之而霍然亮丽,她们亦因之而卓然有别。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和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为例,对其创作中所呈现的艺术新质作粗浅的勾勒,以期对当代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有新的认识。
一 项小米:革命历史与人性的拷问者
项小米从事小说创作始于1985年,但真正给文坛带来冲击力的还是1999年创作并出版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小说以“我”对从事特工的“爷爷”一生历史的追问,重新评价与审视那些被历史湮没的特殊英雄,以抨击当今市侩的功利主义哲学为表层,通过“我爷爷”与她的三个“奶奶”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以及名字叫每的女儿的悲剧命运反思,重新拷问革命文化中那些非人性的内容,以人性撬动历史,撞击灵魂。这里,革命历史的行程与事件已不是小说被动依赖的客体,而是她反思历史,张扬人性的载体,这使得《英雄无语》摆脱了历史本身而获得文学的灵动与飞扬。
项小米的“爷”是世纪之初就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工作的老特工,他传奇而神勇的一生却一直是一个无法知晓的历史之谜,这成为多年来萦绕在项小米心中难以释怀的症结。她迫切地希望能探究并破解这一历史的谜团,特别是当她知道故乡连城(闽西)与瑞金仅二百里之隔,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时,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冲击起她对历史言说的愿望。她四下龙岩体验这块圣土上的神圣与悲壮,感悟大山的伟力给予“爷爷”的抱负与活力(包括制约力),体察客家文化的底蕴给予“奶奶”的魂灵与依托。在一切烂熟于心之后,她冷峻而睿智地以人性为支点开启了尘封于历史深处的“爷爷”、“奶奶”和每的历史。
“爷爷”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一位曾在“特科”工作的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工作的环境与性质使他必须恪守组织严密的纪律和神圣的誓言,必须默默地独自承担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难甚至牺牲。这种面对组织,忠诚英勇,一诺千金,即便牺牲生命亦无怨无悔的近乎严酷的教义渗入到“爷爷”的血液中,使他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无言地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冷遇与不平,直至生命的最后消亡。但是,这种政治的悲剧并不是;“爷爷”悲剧生涯的全部,他更大的悲哀来自这信仰的背后人性的冷漠与无情。面对妻子,他简单粗暴,毫无信义,不讲道德心硬如铁,如同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面对子女,年轻时,他冷淡无语绝情绝义,任凭母亲心如刀绞亦无动于衷;年迈时,他渴望亲情,却又不通人情,难解人意,致使他的感情生活终生枯竭。更可悲的是,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意识。作为一个忠实的革命信徒,他收获了成功的果实,但作为一个丈夫,父亲,“爷爷”——一个应该有着丰富情感和责任感的男人来说,他品尝了失败的苦果。这位从闽西深山走来的农民,秉承了大山伟岸、坚强、粗犷的雄姿,也因袭了农民愚昧、粗暴和简单的因子。封建文化中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更膨胀了他恶劣的本性,催化了他畸形发育的精神世界。在“爷爷”的骨髓里,只有革命的需要而没有亲情的义务,晚年趋向众叛亲离的绝境也就在所难免。通过“爷爷”的形象我们看到:革命往往是伴随着某种缺憾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爷爷”就是带着浓厚的封建社会的投影和农民性走进革命队伍的。一部革命史的种种不足、甚或失误,可以说是与无数组成这支队伍的人们身上的缺陷紧密相关的。“爷爷”对革命忠诚无畏,对自己的亲人却无情无义,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革命者身上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但是,革命者也好,某种意识形态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一旦其脱离了人性的轨道,无论它曾经多么先进,都会走向其反面并为人们所抛弃。“爷爷”的形象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同样令人震颤的还有“奶奶”。这位生下来三天就给“爷爷”做童养媳的农村妇女,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一辈子含辛茹苦地操持生计,却遭受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她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想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将自己的孩子拉扯成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之路都几番走到了绝境。先是丈夫抛弃了她,唯一的儿子又被他派人领走而下落不明,之后又是唯一的女儿每也因丈夫的牵连在狱中染病,不久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奶奶”成了“孤人”。这是对“奶奶”最为沉重的打击(她只靠人求生的本能才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正是“爷爷”的冷酷破灭了“奶奶”生存的基本希望,“奶奶”失望——希望——无望——绝望的精神之旅就将拒斥两字深深地烙在了心上。尽管“奶奶”后来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但对于“爷爷”,“奶奶”所做的就是将拒斥两字再深深地烙进孙子辈的心上。这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不得不使“爷爷”终生郁悒独行在精神世界的赤贫国度里,至死方休。
“奶奶”之所以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抗拒“爷爷”的存在,完全是战争与历史的残酷性剥夺了“奶奶”长期的人性需要(包括肉体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所造成的。“奶奶”17岁圆房,19岁生下第一胎后,“爷爷”不屑与“奶奶”同房,每的播种也是一次极为偶然的心血来潮,之后,“爷爷”与“奶奶”再没有过任何的接触。这对于正处于情欲旺盛期的青年少妇来说,打击是极其残酷的。“奶奶”在上海那次对5岁的每,一改往日的温存,刹那间变形为魔鬼一般的妇人,涌动起恐怖的报复与残忍之心,丧失理智疯狂地暴打无辜的女儿,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肉体的拒斥尚可以忍受,骨肉的剥离是对精神需要最无情的打击。制造这一切的“罪魁”就是“爷爷”。实际上,“爷爷”完全有能力扶助“奶奶”并给予她精神的补慰,但他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根本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以一个绝对的居高临下的君主霸气,颐指气使地蛮横“奶奶”,从未有过丝毫的歉意,这就使“奶奶”的心凉到了极点,对“爷爷”复仇就成为“奶奶”心中根深蒂固的极致心理。
每的毁灭更让人心碎。她的弱小完全可以不计,她的生命也似乎可以不计。她没有任何可以抵挡的力量,如同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她娇小而孱弱的生命不幸成了政治势力较量与搏杀的牺牲品,脆弱地断裂如同一片羽毛悄然地飘落无声无息。历史的残酷,人性的悲哀在这里血一般地凝结。它向人们昭示:革命不单是荣光与自由,革命也不单是幸福与欢乐,它还包含着一种永远弥漫在几代人心中莫名的情结。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①项小米在重新解读与审视革命历史时,就包含着作者对历史、对战争的重新拷辩,包含着作者对妇女命运的更深的理解,对婚姻价值观念的多重探索,以及对人性历史与文化意涵的深刻批判与理性反思。作者从人精神的、本质的需要意义上去把握母亲的神髓,在历史、文化、人性的隧道中,去叩询革命的目的,去反省生存的意义与人的价值,这样,历史在这里就不是单纯的政治对抗和军事较量,而是包含着丰富生动的人性内容。作者以人性反思革命历史,不仅是创作视点和聚焦方式的转变,而且是历史观念和创作思想的革新。
二 马晓丽:历史化的革命伦理与现实功利哲学的追询者
与项小米相近,马晓丽虽于1987年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但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还是她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也许是职业的敏感与时代的感悟,她们的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将艺术的向度指向革命历史,指向社会现实,指向复杂的人性与伦理道德。所不同的是,项小米质疑的是革命历史的人性逻辑,马晓丽追寻的是革命伦理的道德准则。或者说,更令马晓丽饶有兴味的是历史化的革命伦理与现实功利的双重博弈,是人格精神与现实情境的两难选择。边防二团两名战士在检修电话线路时,不慎意外坠崖,一死一伤的结局是按“事故”处理还是按“事迹”上报,是托出实情还是造“势”出“机”,不仅关系到二团团长周东进的去留与升迁,还关系到军区组织部长周南征、边防军区司令员魏明坤等其他相关利害人的走向与未来。小说以坠崖事件为中心,以周东进痛苦而又矛盾的心灵抉择为主线,以红军油娃子的悲剧命运为辅线,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喻示下,展开了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局部与整体——理想构建与现实需要的较量与拼杀。
一般来说,在美学的层面里,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决然对立而不兼容的,而在现实的境遇里,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复杂。攻打395高地,孤高自傲的周东进没有料到自己的失误导致连队暴露主攻意图,瞬息万变的战情使自己作为主攻连非但没有首先占领阵地,反而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这使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中。更让他内心不安的是,部队对他的战斗作风表示满意,决定授予他军功章。一向人格率真、坦荡而自律的周东进决意推功揽过,托出实情。岂料,他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得到同事与战友们的谅解,反而使他与战友产生了更大的隔膜,他也因之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无奈,他自请调往边防部队而告别了野战军。理想的真情、善意与美德在现实面前黯然失色。现在,规定的情境再一次重现,荣辱相关的多米诺骨牌再一次叩击着周东进磊落的心灵:以“事故”报,全团再有两个月就唾手可得的“十年无安全事故典型”将化为乌有,全团官兵几茬人为改变多年受冷遇的努力将功亏一篑,曾经梦想过无数次的典型效应也荡然无存,自己当了七年的老牌团长的命运与十余年的军龄亦会就此而止,相应的,军区组织部长周南征的军人政治生涯亦可能就此封顶;以“事迹”报,整合的材料与事实的真相又明显相左!诚然,如果只是一次偶然的违心之举,良心的自责或许可以释怀人们内心的郁闷,但问题是,当我们抛开历史的表相切入本质时,往往会发现,历史是那样惊人的相似。当“势”与“事”的博弈以“事”取“势”占得上风时,当信念的操守最终失贞于功利的现实时,历史的又一个轮回开始了。油娃子的戏言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一次次被应验。
油娃子,本是团长的警卫员。在一次战斗中,团长被打废下身,悲观之极,饮弹自杀。在革命的年代里,革命的伦理只能认可英雄的壮举而不能认同懦夫的行径——只能认可团长的英勇牺牲而不能认同团长的自杀身亡。为了遵循革命的伦理,随同的警卫员油娃子便被指认为杀害团长的凶手,而另一位与他同行的警卫员周汉则在上级的强压下,以唯一证人的身份作了伪证。于是,油娃子被活埋。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的李冶夫、周汉、黄振中等,则在权衡“势”与“事”的利弊中开了窍,领悟了革命伦理与现实需要的辩证关系,并在日后的现实需要中驾轻就熟。他们的后继者周南征、魏明坤、王耀文等,虽身处和平年代但也很快在前辈的实践中秉承了这一要义,在将单一的事业追求变线为仕途、事业相辅的双线之旅时,自然而然地焊接了历史的法则。因此,周东进的人格力量在顺“势”则昌,逆“事”则亡的现实准则面前,无奈而悲壮地衰落,既是历史规定性的注定结局,也是现实必然性的命定结果。马晓丽将革命历史行程中历史化的革命伦理与现实化的功利原则相联系,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势态相结合,在纷繁的现实矛盾与复杂的历史纠葛中,状写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在历史的追思与现实的呈现中拷问灵魂。这样,历史就不是空泛的事件和单纯的背景,而是革命历史实践中人的心灵搏战与潜在动力,军人的行为也不是部队日常生活场景的机械再现,而是历史进程中无法屏蔽的鲜活的生活内容。这无疑强化了小说的历史感与现实性,也使作品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小说中黄振中的形象同样令人慨叹。这位聪慧的“识时务”者,以其过人的心计与领悟力成为革命伦理的顺应者与受益人。他如同一条训练有素的鹰犬,以其超凡灵敏的嗅觉敏锐地捕捉着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适时而又适势地出现在对手面前或给对手以致命一击。他应运而生的历史与苦涩黯淡的结局,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作者深刻地揭示了黄振中的思想行为与革命伦理的内在联系,即“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②这使得黄振中的形象具有更为深刻的警示意义。
三 裘山山:雪域高原圣情的守望者
裘山山的名字往往与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联系在一起。这部以崇高的人生信仰维系人生,锻铸军魂的长篇力作,将第一代进藏官兵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表现得激情澎湃,大气磅礴。在普遍回避信仰、躲避崇高的当下文坛,裘山山的守望显得尤为可贵。
裘山山的守望缘自军人的责任,也缘自内心的渴望。一次,她去采访一位首批进藏的老兵。已是花甲的老兵拿出了她当年与丈夫的合影,相片上的丈夫高大精神如首长,妻子瘦小稚气如通讯员。强烈的对比使作者在一瞬间产生感伤的思绪,她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一个那个时代虽不情愿却不得不如此的惯常组合。丈夫(老首长)也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伴的相片,情深意浓地回忆起往昔充满激情的岁月。那神情,使作者不由得重新细看那张对比鲜明的旧照,竟涌起了无限的温馨与感动。于是,她六进西藏所体悟的雪域圣情,所历练的道德精神,化作军人崇高的理想,化作青春无悔的选择,化作雪山不变的信念,化作高原神圣的责任,在心灵的天空自由地敞开。
人是要有崇高的精神的,人正是靠这种崇高的精神支撑起生命的质量。这是回响在《我在天堂等你》的最强音,也是欧战军、王新田、苏玉英、白雪梅等第一代进藏官兵引以为骄傲的人生信念。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利益冲突,却有战友间肝胆相照、生死相依的血肉之情;这里也没有舒适丰厚的物质基础,却有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间的温暖与至情。正是这种生死之谊与血浓于水的深情,使活着的人们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牺牲的战友和同胞的重托,将他们未尽的使命担在自己的肩头。因为他们是幸运的,比起众多将忠骨埋在雪域高原的先烈们来说,他们毕竟活了下来,他们可以在夕阳的映照下守望历史,守望那片神圣而震撼的天堂。如今,这种催人奋进的精神,这种勇担道义的责任,这种如山之挺拔、雪之晶莹的品格,这种在坚守执著中冶炼的崇高理想,已化作一代代军人的军魂血脉,在雪域高原上传承弘扬。
人还是现实中的人,军人也是现实中的一分子,军人的人性同样应折射出人性的普遍内涵。这是回响在《我在天堂等你》的又一旋律。戎马一生的欧战军,有着刚毅粗犷、吃苦耐劳、果敢坚定的军人作风,公而忘私、讲求奉献、甘为他人的高尚品质。这种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在当时的白雪梅看来,虽然少了许多生活的情趣,人性的关爱,却也增添了几分理想的光芒。他的一生只对白雪梅表达过一次爱的承诺,却令白雪梅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这不是说他不善于表达,而是长期的铁血生涯压缩了他内心的温情;也不是说他不懂得妻子的冷暖,白雪梅怀孕时的关爱和焦灼,同样体现了丈夫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只是说他更习惯于以军人的上下级的工作方式处理夫妻之间的情感事务,这使得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缺少人情。小儿子木鑫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这一论断虽然过于绝对,但欧战军常常从自己固有的甚至是僵化的观念出发,以己度人,居高临下,绝少换位思考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以家长制的方式包办木槿的婚姻,并自以为是为女儿安排的绝佳婚配;他冷眼旁观无助的木棉,却将有限的钱物捐给家乡的政府或他人;他更反对木鑫经商的选择,这使他与子女们的沟痕越拉越大。因此,当他再次试图以家长会的方式解决积蓄的子女矛盾时,其实是点燃了两代人战争的导火索,他也因之走上了悲壮的终点。作者以崇敬与理解的心情,抒写了老一代军人崇高而又悲壮的一生。他的告别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坚守固然重要,但在发展中坚守更为重要,因为行进在社会历史中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等为代表的女作家的崛起,是最令人注目的亮点。她们以崇高的信念为底色,或拷问革命与人性的历史脉象,或叩询历史化的革命伦理与现实的功利哲学,或追思雪域高原的神圣情怀,将军人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睿智、理性而又富于激情地镌刻在当代文学的殿堂中,大大深化了作品的审美意涵,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乃至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质点。可以说,《英雄无语》、《楚河汉界》和《我在天堂等你》等小说的问世,是当代军旅小说转型与创新的新起点,也是世纪之交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
注释:
①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②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958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4页。
标签:小说论文; 项小米论文; 裘山山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学论文; 我在天堂等你论文; 人性论文; 楚河汉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