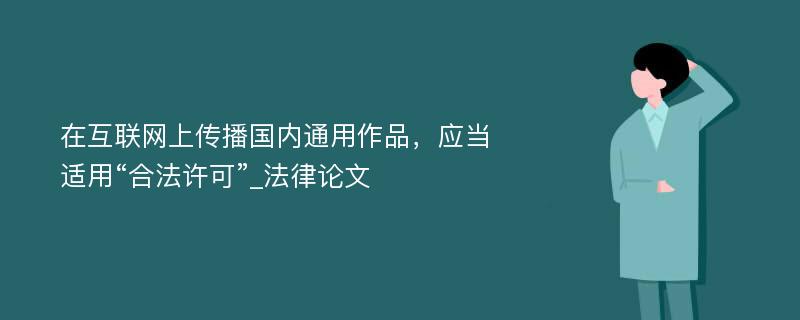
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应当适用“法定许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上传播论文,作品论文,国内论文,许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在我国网上传播作品能否适用“法定许可”这一问题,目前叠合着三方面的背景因素:一方面,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为代表的国际惯例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应当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另一方面,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在若干特定条件下传播他人作品可以适用“法定许可”,即只需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不必事先经著作权人授权同意;再一方面,为调制、衔接“授权许可”的国际惯例和“法定许可”的国内法律规定两者之冲突,当年在《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阴影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形成了“内外有别,外优于内”的“超国民待遇”。我国目前在网上传播作品究竟应当规制于“授权许可”还是“法定许可”?笔者认为,首先应着眼于维护我国利益,同时必须考虑无悖我国现行法律,衔接当前国际惯例。笔者认为在上述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应将网络媒体视为报刊;我国当前对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的规制应适用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 款“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规定,即对于无论是已在网络“媒体”上初始公开的,还是在传统报刊上首次发表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献、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即网上转载或摘编国内一般作品视同为“其他报刊”法定许可的转载或摘编;同时我国当前对网上传播外国作品的规制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42 条以及国务院《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的“授权许可”的规定,即“报刊转载外国作品,应当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是,转载有关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的时事文章除外”,即网上转载或摘编除时事文章外的外国作品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
一、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适用“法定许可”有利维护我国利益
网络科技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知识扩散、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密度,网络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将是新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必然,并且已经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全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又集中在网络的应用上。”(注:郑成思:《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网上传播作品之法律适用就是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新问题。网络一旦掌握了人群,就可能成为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商业资源;人群一旦掌握了网络,就可能成为最富有实力和威力的竞争力量。人群主要是通过文字语言去掌握网络和网络信息的。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英文从而涉猎英文网上信息资源;但我国绝大多数人仍将主要使用中文并籍此上网;在我国国内经贸、科技和文化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文字,包括网上使用的语言文字仍然以中文为主,仍将长期是中文。但是,据统计,在互联网络上的中文信息量迄今不及千分之一,这一比例与我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近千万网民(我国网民数量还将继续与日俱增)的记录严重不对称,势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发展,亟待迅速加以改变。因此,列入国家“863 ”高科技计划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与“中华文化信息网”重大项目已经实质性启动,正在北京图书馆等开展试点工程。其中酝酿着将近几十年来的中文报、刊、书所载的信息送上互联网,以拓展中文信息资源,弘扬中华文化和振兴中华经济。好几十年的中文报、刊、书的累积是海量的文献、海量的信息;站在这海量的文献、海量的信息后面的是海量的作者、海量的著作权人;如要取得这海量的作者、海量的著作权人事前的“海量授权”和“海量许可”绝非易事,甚至是不可操作的。面对这几十年来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文报、刊、书上的数以千百万计的“海量作者”,又如何能在茫茫人海中一一对号入座,一一请求授权许可呢?有人提出可加速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代表“海量著作权人”进行授权许可,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只能是“基于会员的委托,代作品著作权人行使有关权利,解决作品使用的许可和付酬问题”(注:国家版权局:《关于同意成立中国文学作品著作权协会的批复》,国权(2000)第5号文(2000年2月29日)。)的行纪组织,其进行授权许可的性质是授权范围内的再许可,其再许可的授权范围只能是著作权人已经委托的作品。著作权管理组织同样面对一个“海量作品”的“海量许可”难题。如果坚持要求“授权许可”,那么尤其是对于国内近几十年来刊载在报刊上的、依法仍在著作权保护期间的这些最可宝贵的,最需要交流的、最可能利用的海量的自然科学作品和社会科学作品、技术文献和艺术文献、科技信息和经济信息,都将因其不可操作的“海量许可”手续而无法上网,从而无法为我国各行各业所交流和利用。在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资源也将因此不能迅速增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面对互联网上仅占千分之一比例的中文信息资源的尴尬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如果坚持国内作品上网必须全面适用“授权许可”,势必严重影响拓展网上中文信息资源,阻遏我国的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不利于维护我国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也会因此诱发与刺激盗版现象和侵权行为的滋长和蔓延,影响知识产权之保护。如果在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就是将适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之“特别法”保护的计算机软件作品等特殊作品除外)适用“法定许可”的有关规定,那么,既保护甚至增大了著作权人因此而获得相应报酬的权益和机会,又能汇聚政府与民间的的各种力量迅速拓展网上中文信息资源,促进我国科技、经济、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还能有效阻遏盗版侵权,有利于建设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有益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二、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适用“法定许可”无悖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法定许可是指依法律直接规定使用他人已公开发表的作品只需付酬而不必先经著作权人授权同意。我国《著作权法》现行规定的法定许可实质上是“准法定许可”,全面的法定许可是使用者无论如何都不必经著作权人事先授权许可,只需付酬即可使用。“而我们的著作权法却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作者声明保护权利者除外,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法定许可就有较大差别,但它仍可以归纳入法定许可之列。”(注:沈仁干:《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析》中《关于对著作权的限制》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2月版。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营业性演出法定许可”、“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法定许可”共四种“法定许可”。
笔者认为, 网上传播一般作品应当适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 “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在于:1.转载及摘编的原有作品必须是已经在报刊上刊登发表过的。此处报刊仅指报纸及刊物,此外,即使在公开出版的书籍中刊登过的原有作品也不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2.著作权人并没有声明该作品不得转载、摘编;3.转载、摘编者必须是其他报刊,并且转载、摘编的报刊必须向著作权人按规定支付报酬,并且注明作者及出处。
网上传播网络原创作品是否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现行法律规定,这是当前争议焦点之一。譬如对于已在甲网站上初始刊登发表的原创作品,乙网站通过“从网至网”的途径将该作品转载刊登至本网站上向外传播,乙网站的这一行为是否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呢?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能否将在网络媒体上的刊登发表,视同为在传统报刊上的刊登发表?就是能否将其他网站“从网至网”或者“从网至纸”又“从纸至网”的转载、摘编视同于其他传统报刊的转载、摘编?一言蔽之;就是能否将网络服务商及其网站视同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报纸与期刊?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商及其网站应当视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报刊;在网站上初始刊登发表作品应当视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意义的“报纸与期刊”上初始刊登发表作品;网络服务商及其网站转载、摘编其他网站上初始刊登发表的网络原创作品等同于传统报刊转载、摘编其他传统报刊上刊登发表的作品。只要转载、摘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并未明确该作品“不得转载、摘编”,并且转载、摘编的网络服务商及其网络向著作权人按规定支付报酬,同时在本网站转载、摘编的作品上注明作品出处及作者姓名,则这类网上传播作品行为应当依法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为何只适用于报纸与期刊这类特定的出版物,而不能适用于书籍以及其他一般出版物。揣测当初立法之原意,之所以仅规定“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而并没有进一步延伸到“书籍转载法定许可”,这是否因为报纸、期刊相对于书籍来说,是信息传播的“快车道”和“轻骑兵”,具有信息传递快捷、及时、高效、组合、连续(定期或不定期地连续)的特点。那么,网络服务商及其网站的网上信息传播不正是更加增强了信息传递的这种快捷、及时、高效、组合、连续的特点吗?这样的网上传播作品为何不能视同为报刊传播作品呢?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认同,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也都已确认“网上作品”也是受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互联网上传播的原创作品和“二手”作品都仍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羽冀之下,都认为作品仍是作品,只不过作品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纸质化载体变成了网络的数字化载体,而数字化载体上的作品依然受法律保护。国家版权局“国权(1999)45号”文《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2 条也已明确界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若说将网上传播视为报刊传播是扩大解释,那么,将立法之初尚未涉及的“网上作品”认定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将立法之初尚未考虑的数字化复制等同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传统型复制,岂不也属于同样的“扩张解释”呢?反之,既然认为网上作品依然是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既然认同数字化复制行为是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那么,“网上报刊”为什么不能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层面上的“报刊”涵义所包容呢!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确没有明示其所称“作品”中包含了网络上的作品,没有明示其所称“报刊”中包含了网络上的报刊,因为立法伊始互联网还“藏在深闺人未识”,还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同样这部我国的《著作权法》也从未明示,其所称“作品”排斥网络上的作品,其所指“报刊”不包括网上的报刊。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有关“法定许可”的概念并非封闭性概念。现行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只要符合立法本意和法条涵义,就应当受到现行法律保护。对于现行法律的解释,不能仅拘泥于立法时的具体考虑和有限视野,而应当立足于立法本意和法条涵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动态性,应当容纳立法以后出现的既符合立法本意和法条涵义的,又没有现行法律规定明文禁止的新事物。在星驰斗转、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尤当如此。
因应知识经济,因应网络环境,法律的规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且要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也许知识产权制度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应当率先具备前瞻性、动态性和包容性。其实,这方面已有成例,如《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1款就采用了这样的表述:“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批准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实质上其包容了立约伊始已经存在和今后可能产生的任何复制形式。又如美国《版权法》中也有如下的表述:第102条述明:“(a)依据本版权法,对于固定于任何有形的表现媒介中的作者的独创作品予以版权保护,这种表现媒介包括现在已知的或以后发展的,通过这种媒介,作品可以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不论是直接或者借助于机器或装置。”第101条中还有对于机器、 装置相对应的专用名词释义:“‘装置’、‘机器’或方法是指现在或以后发展的装置、机器或方法。”可见其法条涵义包容了“现在已知的或以后发展的”任何表现媒介或任何装置、机器与方法。
至于另一方面,如果说报纸与期刊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要有资质审批手续,那么这种管理及审批实际上是另一种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网络报刊也可以建立相应的行政管理规制。当然,网络报刊的行政管理规范不但应当体现报刊行政管理的共性,而且还应充分适应互联网及网络传播的个性,应当更为机动、更为宽松和更易操作。
三、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适用“法定许可”无悖衔接当前国际惯例
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适用“法定许可”,网上传播外国作品适用“授权许可”并没有相悖于WTO构架下以TRIPS协议为最低基准线的当代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也没有相悖于以尚未生效的WTO 条约、WPPT条约为参照坐标系的将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标准与国际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8 条也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目前我国涉外知识产权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上,已经将我国缔结的、参加的双边条约或者多边条约转为我国国内法的一部分而直接适用。这一点并已为我国丰富的司法实践,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所体现和验证。所以,即使我国在报刊转载方面继续沿用对内“法定许可”和对外“授权许可”的双重标准,也是无悖于当今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规定的“授权许可”之国际惯例的。
“法定许可使用是各国著作权法普遍推行的一种制度,其所涉及的权利项目包括表演权、录制权、广播权、汇编权等,但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注:吴汉东等:《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实际上,在包括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中,不但广泛存在着各自相关的“法定许可”规定,而且还多有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未涉及的“强制许可”制度:即不管知识产权权利人是否同意,国家版权主管部门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与情由,将对已发表的作品进行特定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权利的申请者的强制制度。甚至《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中都有有关强制许可的条款。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都不是著作权人的直接意定许可,实质上都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实施的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合理限制。从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一个悖论:知识产权究其实质是一种相对的垄断权利。“知识产权可能特别脆弱,当其脆弱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同时,知识产权可能特别强大,这同样能抑制经济发展。”(注:帕梅拉·萨姆森:《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信息时代中国的机遇》,《面向21世纪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主办,1998年)。)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和保护智力成果完成人的知识产权,那么,作为科学技术智力成果与文化艺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要获得其智力劳动、智力创造的合理回报和要取得其创造的智力成果、智力信息的相应价值是十分困难的、是没有保障的,这时他们对发明创造、文艺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也是难以维持、难以再生的。另一方面,如果给予智力成果完成者以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则作为垄断者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有可能滥用其垄断性的权利,因谋取超额利润或者谋求不当效应而阻碍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影响或者破坏智力成果和破坏知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社会化利用。“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生产足够的信息,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能使太多的信息被使用。”(注: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经济学思考》,《法学》2000年第4期。)应当注意依法兼顾社会公众的利益, 注意有利于良性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不应造成“遍地都是知识产权地雷阵,到处都有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迈步就触雷,一举手准触电”的客观形势和社会效果。“过犹不及”,如果一味过于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而忽视社会公众利益,忽视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使得社会公众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其后果可能造成全面压抑智力创作和阻碍知识扩散,与知识产权保护之初衷南辕北辙。(注:陶鑫良:《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面向21世纪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主办,1998年)。)而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和合理使用等正是合理限制知识产权权利人之权利,追求利益平衡前提下的智力成果资源最优化配置和智力成果创造活动可持续发展的离合器,也是保护发达国家相对历史优势和保护发展中国家合理发展空间的调节器。法定许可与强制许可制度也有利于和保障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之效益。面对获取报纸、期刊上海量作品的著作权人之海量授权许可的不可操作性,网上传播其作品与其一味强调“授权许可”而作茧自缚,画饼充饥,倒不如合理选择“法定许可”而广种多收,得其实惠。徒法不足以自行,苛法更难于实行。对维护公共秩序和倡导善良风俗而言,与其制定一部保护水平高却没有操作性的“空头”法律,倒不如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制定一部保护水平适度但较有操作性的法律。与其苛求于法但却盗版猖獗、侵权泛滥,倒不如立法适当而力求法出规成,令行禁止。
从长远看,网上传播一般作品的全面法定许可制度应当成为和有可能成为今后世界通用的“交通规则”和新的国际惯例,这是由网络科学背景与技术条件下信息扩散与传播的新特点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或许并不是中国应当向现行的“国际惯例”看齐,或许是整个世界应当趋同建立全球性的网上传播一般作品的“法定许可”新国际惯例。
争取使网上传播一般作品(尤其是文字作品)适用“法定许可”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惯例是有可能的,或者说是可行的。强权规则下合理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必须考虑“授权许可”的可操作性和发展中国家的忍受力之极限。如果几无操作性的“授权许可”制度形同虚设,只能引发盗版猖獗与侵权严重;甚至引爆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反弹和对抗。那么,发达国家一味坚持“授权许可”岂非是买椟还珠,饮鸠止渴,很可能成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所以,网上传播作品适用“法定许可”不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不但是利益平衡,也是利益趋同。一方面,网上传播一般作品适用“授权许可”的不可操作性,及其如果强行实施后极易引发的大面积破坏性对抗行为之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之间在解决国际知识产权贸易冲突中达成此类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曾经有在为教育目的而翻译、复制作品的“强制许可”方面达成妥协的先例;那也完全有可能在网上传播一般作品方面达成适用“法定许可”的妥协和谅解,形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认同的、人类在新世纪进程中利益平衡、利益协调、利益趋同的合理方向和优化方案之一的新国际惯例。从根本上讲,这一新的国际惯例的形成和成形不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应该并且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国际“交通规则”和“游戏规则”。
标签:法律论文; 著作权法论文; 法定许可论文; 知识产权法院论文; 知识产权管理论文; 知识产权保护论文;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