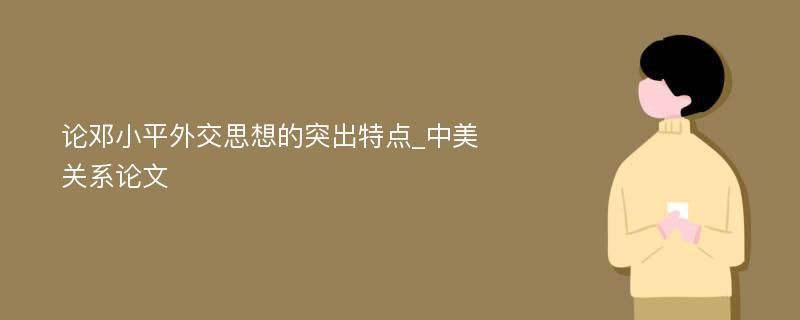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突出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富睿智、最有个性、最具魅力的华彩篇章之一。基于对当今世界国际局势的独到观察和深刻认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一二十年,甚至可以避免的科学论断,强调真正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据此指导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鉴于此,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于正确贯彻邓小平外交战略,服务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毫无疑问,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改变。本文着重探讨其带有鲜明个性印记的突出特征。
一、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外交政策有一条鲜明的轨迹,这就是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可以说,无论其中的哪个阶段,我国都基本上奉行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冷战氛围、中苏分裂以及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也时有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的倾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埋葬帝修反,永远闹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媒体上充满了对与我们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不屑、敌视、怀疑、猜忌与偏见。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口号,在当时却是我们外交思想的最直接最生动的写照。上述倾向固然有某些不得已的苦衷,但同我们在外交指导思想上的不成熟无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我们树立和面对了太多的敌人”。[1](P241)
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认为这实际上是自设障碍,自我封闭。在邓小平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众所周知,中苏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苏联作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之强可想而知,中苏两国又有着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线。因此,中国要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苏关系的状况。但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和双方各自战略利益选择的差异,中苏关系却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一直致力于中苏关系的缓和和改善。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就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无自责地称自己作为那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回过头来看,中方同苏方一样都讲了许多空话。强调此次会谈的目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再申明他所讲的中国人、中国党对过去中苏关系中是是非非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认为这将有利于双方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邓小平还不无幽默地告诉戈尔巴乔夫,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过去就结束。并郑重建议在发展交往时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邓小平再次告诫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要同苏联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所有这些,都为中国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外交空间。
不难设想,如果我们仍然斤斤计较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两国就绝不可能在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使本来在西方制裁下已经严峻的外交局势雪上加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美关系处于严峻局面。对此,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为修复中美关系投石问路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讨论和处理问题的,强调中国欢迎美国商人对华进行商业活动;并且高度赞扬尼克松1972年中国之行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行动。这种坦率和开诚布公的会谈使双方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妥和可靠的基础之上,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今天,中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总体上良好发展的态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最具建设性的时期”。[2]这一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得益于邓小平的这种远见卓识。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发展关系和处理各种分歧时,再也没有以往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篱障,而是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从而为建立和发展健康的双边关系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如果再回顾一下距今不远的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意识形态相同的西方国家挑起的严酷事实,就更能体会这种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做法的正确了。
二、突出实力外交,既量力而行,又有所作为
“弱国无外交”。这一古训已为千百年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也是近代以来饱受列强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的血泪控诉和无奈叹息。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同样未能超越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的冷酷断言:“基于权力的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本质。”[3]这一断言的底蕴与弱国无外交的古训实无二致。邓小平在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同时,并没有认为天下从此太平。他指出,国际局势虽然正由缓和代替对抗,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竞争已由军事实力的竞争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中国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开展实力外交。这样,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其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内政外交等一切问题的基础。离开经济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
1982年9月,闻名世界的英国首相、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来北京就香港问题与邓小平进行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针对撒切尔夫人坚持中方必须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否则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影响的讹诈和恫吓,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表示中国会勇敢地面对灾难,作出决策,并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此后,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立场,致使从1983年7月12日开始的四轮会谈毫无进展。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总理受权发表声明:如果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底前仍然不能达成有关香港问题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迫使英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显然,无论是邓小平的谈话,还是中国政府总理的声明,其语气都是居高临下、不容商量的。这不是无视对手的傲慢态度,而是对自身力量充满自信的十足底气的自然表露。事实上,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邓小平耳闻目睹了许多重大事件。邓小平应该不会忘记袁世凯政府代表在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病榻前谈判的屈辱一幕;不会忘记在抗日战争中标榜支持中国抗战,放弃在中国治外法权和租借地的英国政府却断然拒绝讨论香港问题时国民党政府的忿怒和无奈;不会忘记刚一建国就奔赴苏联寻求支持的毛泽东在莫斯科遭受的冷遇(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仍然对这一冷遇耿耿于怀)。所以,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香港问题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4](P85)
当然,中国毕竟是一个初步走向繁荣的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中国的国力还远远没有大到足以使别的国家围着自己转的地步。成堆的国内问题(很多是属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使中国根本无力也不应该过多地关注与己牵涉不多的事情。正是基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最基本的国情,基于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清醒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所会议访华团时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的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世界上都说美、苏、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有足够份量的。
苏联解体后,国际局势由过去的美苏两霸主宰世界转变为一超多强的较量,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收拾这个摊子,人们一时拿不出成熟的意见。对此,邓小平说,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出面当头,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我们千万不要当这个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只能广告天下,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应当指出的是,强调量力而行,决不意味着无所作为。邓小平指出,现在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4](P353)因此,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即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灵活务实,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中国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目标。
1989年10月底,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100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的谈话诚恳、务实而不自卑。承认自己是弱者,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种以实力决定地位,以地位确定扮演角色的做法,无疑是符合国际政治现实而又残酷的逻辑的。
反观改革开放前,中国时常自觉不自觉的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力图充当世界思想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支援亚非拉人民,自己却仍然处于所谓“忿怒的孤立状态”的尴尬处境,其得失实在值得检讨和反思。
三、把高度复杂的外交战略变得更易感知更易操作
如前所述,我国实行的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使这一政策更易感知更易操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多次就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外交政策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纲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心中有数。针对当时国内刚刚平息政治风波的小气候和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大气候,针对西方对苏联和东欧咄咄逼人的渗透和苏联东欧国家已显端倪的动乱,针对国际上所谓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战而胜”,于2017年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社会主义灭亡展览的叫嚣,邓小平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务必做到冷静观察,冷静,冷静,再冷静。因为,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不确定、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一些深刻的矛盾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其中有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有我们可资利用的矛盾和千载难逢的机遇。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而冷静观察则是利用矛盾、把握机遇的前提。邓小平指出,苏联、东欧肯定要乱,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关键是我们自己首先要稳住阵脚。并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表明,中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知识分子,都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制裁和威胁,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的态度:中国反对制裁,但不怕制裁。坚定地表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同时,反复强调尽管苏联、东欧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仍要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美国、日本、欧洲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不要动摇。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处之泰然,沉着应付。显然,沉着应付的核心就是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最高民族利益,又要避开锋芒,不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形成对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才能继续发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的应有作用,彻底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现实处境,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反复告诫第三代领导集体,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改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因此。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譬如中美关系,邓小平告诫中美双方不能打架,即不在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4](P351)我们只管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战争时期领袖的品质更易于衡量,因为战争时期的危难局面为人民提供了比平时更多的考察领袖的机会(大意——笔者注)。在1989年风波以后那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中,在中国外交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他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为我们制定了这十六字纲领。不着意修饰,不大肆渲染,不板着面孔训人。生动,具体,实在,它是伸手可以触摸的,然而又是意蕴深厚的,给人以极大的启迪和教益。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富于想象又脚踏实地;着眼本国情况又面向世界;立足当前又兼顾未来;既高屋建瓴又易于操作。一句话,理性、务实而且冷静。今天的中国外交在国际上越来越树立起理性和自信的形象,不仅为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营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诸如“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这些成果无一不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之树所结的硕果。因此,深入贯彻这一外交思想,中国外交无疑将拥有一个更加辉煌与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