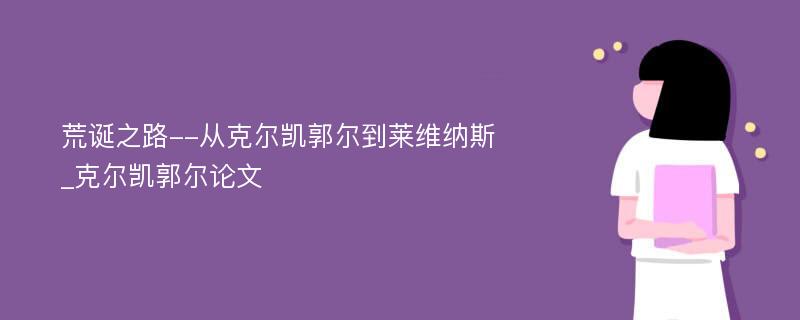
悖谬之路——从克尔凯郭尔到勒维那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尔论文,维那斯论文,悖谬论文,之路论文,凯郭尔到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活跃在从克尔凯郭尔到勒维那斯这条精神线索上的,是一些像赫拉克利特那样的隐晦哲学家。这些“隐晦”哲学家的思想长期被排斥,没有被真正的理解。但是,正是这些隐晦的思想酝酿着传统哲学家们没有想到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口,是“隐晦”一词表面含义上的一种极具挑战意义的思想延伸。人类思想界已经并继续在爆发一场挑战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后现代的精神运动,这场精神运动的旗子上书写着两个大字“悖谬”。
一
克尔凯郭尔与尼采是同一类思想家,俩人的思想具有浓郁的文艺气质,一直被保守的学院派哲学家所排斥。但正是这种艺术气质的哲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整个西方的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现象学。必须破除把现象学研究“经院哲学化”的倾向,我这里主要是批评中国国内目前的现象学研究特别是海德格尔研究中的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好像重新把哲学抬到天上。事实上现象学的精神气质是亲历的、活生生的、极具想象力的、属于生命本身的,一句话,是“近”而不是“远”。那为什么还说“隐晦”呢?因为这些“近”的心情,是以悖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虽然“近”却因其不可理解性而显得“远”,而真实的情形却在于悖谬之“远”同时就是“近”的。悖谬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心情、行为举止,却被我们视而不见。现在,这些隐晦却并不来自天上的哲学家,正是想唤醒沉睡在每个人身上的这些心情。这是一些新的“想到的能力”,新的启蒙。克尔凯郭尔的全部著作都与悖谬心情有关,他的思想之魅力,来自这些同时是近和远的心情:“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相信一个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她,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相信她,还是不相信她,你都会后悔。”①这“后悔”与否的叙述,很像一个关于悖谬的函数句式,他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如果你从原则出发,后悔;不从原则出发,你也后悔……如果你停下来,后悔;不停,你也后悔。不一而足。为什么称“悖谬”呢?因为悖谬与矛盾有微妙而根本的差别,悖谬的情形与黑格尔所谓矛盾双方由差异到对立面的斗争导致的转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上述情景中的心情抗拒选择,既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亦此亦彼”;因为选择遇到巨大的尴尬,就好像心境因不选择而停顿下来;因为心情遭遇不透明性、死胡同,就像没有爱也没有恨,内心却充满着悲伤。这导致一种抽象的心情,平面的心情。心情的平面抗拒选择,就好像在抗拒具有思辨性质的传统“深度思维”。但这种平面的抽象心情却另有一种“深刻性”,我称之为“横向思维”或“横向的心情”。其特点,就是分裂性,强调破碎的关系,非中心。
为什么事物一定要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呢?对这种精神束缚最有敌意的,是我们真实的心情。心情或独白最具有分裂性或破碎性,表现为抗拒以being作为精神支柱的选择判断,这些判断也是传统哲学的根基。克尔凯郭尔揭示出悖谬的心情,在于想极力摆脱而又无法逃避判断(或选择)这样一种尴尬的场面。他想从“对立统一”中脱身,寻找精神的其他可能性,而他确实找到了,这就是悖谬。“悖谬”在他那里的待遇不像“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因为沿着“悖谬”的死胡同前行,可能带给我们新的精神幸福。悖谬是属人的或属精神的,它在本性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既不痛苦也不快乐,既绝望又希望等等),却又不可简单地斥为“非理性”的,这使我们的分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所有这些,与现象学乃至德里达等有何关系呢?关系就在于“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拆散范畴双双对立统一的精神框架,精神还有其他多种连线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也堪称最为微妙的精神,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从宗教感情或信念寻找突破口的。他从灵魂深处的绝望中寻找希望。
把人家让我相信的一切,那些关于“是”与“否”的判断,暂时搁置起来,只相信亲历的只属于我自己的心情,即使别人往往感到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这又是一种悖谬,即剩余或多出来的,非实用的精神。像只有提问没有答案的精神,处于焦虑状态的精神,反复无常,在气质上是忧郁的。什么是克尔凯郭尔的悖谬心情呢?他在《非此即彼》中描述说,忧郁的气质最具有喜剧色彩,最丰富的心思淳朴安详,放荡的念头经常是最符合道德的,怀疑一切的态度本身最具有宗教性。克尔凯郭尔这些话,是对“非此即彼”这种精神习惯的消解,他把被哲学死板地竖立起来的精神结构“摊平”了,从而暴露出精神的更多触角,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平面的精神中含有我们尚不清楚的“深刻性”,理解的线索在于其中隐蔽地搁置了being类型的判断。如果把是非判断理解为有根据或有原因的判断,那么,对“悖谬”的描述,就是试图逃避这些原因或根据而导致的一种抽象的心情,而此抽象区别于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之抽象。搁置原因乃在于忽视原因,因为任何东西可以产生任何东西。比如,厌倦不期而至。这种无法知晓其原因的厌倦,是抽象的厌倦。悖谬或抽象的心情中,发生了心情的奇迹。这个世界并不曾真的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对心情而言,发生了不曾发生的事情,只属于精神个体的事情。悖谬因其个个特殊而显得精神“不正常”,这些“不正常”的心情常为灵感的源泉,却被公众舆论所忽视甚至鄙视。难以被人理解或说不出口的心情,竟然是最强烈的心情,也是最抽象的。不是没有勇气说,而是没有能力说。从心情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但没有隔着万里长城,而且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心境,就这样僵住了,由于无法前进一步而化做永恒,化做诗一样的语言: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只是选择。同样,全是后悔,也就没有后悔。后悔,成了多余的心情。选择的一生也是后悔的一生,而所有这些在临死之时都成了废话。
失去原因与失去对象,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当快乐与痛苦、愿望与信仰的对象模模糊糊,难以证明时,心情往往导致抽象的悖谬。其表述为“没有X的X”,例如“没有痛苦的痛苦”,这可能是最大的痛苦,悖谬对人的严峻性就在于此。再如,既然欲望的落空是人生常态,悖谬引导人们把失望当成一种乐趣,就如同沉醉于爱而不是被爱。精神与其说是飘逸的不如说是突兀的。精神高处不胜寒,在于精神总在异域,这使得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很像诗句。具有创造性的句子在于不断推迟词句含义的实现。刚一开始就停,念头刚萌芽,“后悔”已发生。还没有等一个句子落地,就见异思迁了。就宏观世界而言,不断转向的、微观的心情世界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悖谬的心情发生在精神之微观或基本粒子层次上,要用显微镜观察“没有X的X”现象。
关于信念领域的悖谬,克尔凯郭尔引述了《旧约》中一个感人的故事,亚伯拉罕对上帝有无坚不摧的坚强信念,甚至当他受到上帝的欺骗,牺牲掉自己的儿子以撒,仍旧不改对上帝的一往情深。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精神内涵,它影响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真实的类似事件。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服从全能的上帝统治,做上帝的工具,而在于他在经历信念的考验过程中,所受到的磨难。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战胜了自己的人。“信仰”是一种历经磨难的心情,要相信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的做法是对的,这就是信念上的悖谬。放弃却永远在想,永远在想却永远没有准确答案。这“没有放弃的放弃”就是折磨人的悖谬。从这里萌发出一种荒谬的精神力量,它引导人们朝不可能的方向“妄想”,它是人身上一种同时令人讨厌和陶醉的天性。当人们谈及“相信”时,很少想到这个层面,也就是相信不能相信的东西:相信就是放弃,但又不是放弃一切。亚伯拉罕放弃了心爱的儿子,但没有放弃上帝,这很像是一种没有希望(因为孩子肯定不会回来了)的“相信”。能让孩子回来的力量,肯定来自神,而不是人,这里暗含着一种高于人类能力的可能性,一种悖谬的可能性。这里的悖谬还在于,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行为同时是他痛苦(因为要失去儿子)和减轻痛苦(奉献儿子的行为是为了神)的原因。这两者之间能相互补偿吗?这里没有天平,只有内心的磨难。
绝望的时候,信念在发抖:“每个人按照他的期待有不同的伟大,有因期待可能之事而伟大者;有因期待永恒之事而伟大者;但是,期望不可能之事者,乃一切伟大者中最伟大者……每个人是因其奋斗献身的事业而区分出伟大程度的:与天地人奋斗者因其征服世界而伟大;与自己搏斗者因战胜自己而更伟大;但是,与上帝搏斗者乃一切伟大者中最伟大者。”③精神上的高难动作,就是精神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与神过不去,却又不是无神论,这才是精神的真正奇迹。但不是精神悲剧,因为“一个能放弃自己愿望的人是伟大的,但更伟大的,是在放弃后还能坚持这个愿望的人。”④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一个人有信仰,它的含义就是决不放弃最虚无缥缈的可能性,即使对那里的情形一无所知;就是相信绝处逢生,精神越是接近顶峰,就越是有怪石嶙峋,越是充满悖谬。信念是悖谬的代名词,这样的悖谬,显然是对哲学的超越(哲学不相信悖谬,因为悖谬相信不可能性)。悖谬不是以哲学方式而是以思想的方式出现,故曰之隐。它是一种极具精神个性的孤独的力量,却是精神之原样。最丰富最有灵感的思想,往往是在精神孤独中想到的,就像笛卡尔的沉思。孤独的精神之所以具有纯粹性和无条件性,在于它不是与人照面,而是直接与“神”对面——这里有精神之间的不对称性,要完成这样的沟通,要借助超越的一跳。
二
很多资深的哲学研究者,就是进不了现象学的大门,因为现象学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不仅隐晦,而且悖谬。现象学最大的精神“拐点”,也是怪点,在于非人类学的思维——破除人类中心论,认为人不是万物的尺度。现象学的“精神拐点”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强调不断超越的思维。也就是说,虽然思维是在人的心理活动中构成了,但是,纯粹现象学的意向活动是一种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活动”,是“非心理活动的心理活动”。胡塞尔坚持说,思、概念、意义本身不应该以人的标准为标准,是在人的想象能力和范围之外的东西。明明是我在想问题,但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我”不是一个“人”。现象学思维具有“非实证的实证性”,即它的纯粹性。它们是一些感觉不到的感觉、经验不到的经验、直观不到的直观、想象不到的想象——普通的或者自然而然的思维为什么达不到现象学思维呢?因为没有掌握现象学还原的方法。⑤
现象学的“现象”为“隐”而不是“显”,胡塞尔反复提到现象学的纯粹性和无前提性。现象学是一门绝对“不切合实际”的学问,这来自它对“自然态度”中的世界,也就是对“显现”的世界持一种加括号的态度。也就说,眼前的世界当然还是这个世界,但是,因为我坚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我所看见和想到的一切,意义便大不一样了。这里的意义,就属于我这里说的“隐”。一切理解的关键,都在于对现象学还原能有多深的理解。“还原”,就是撤退到“隐”,不断还原,就是不断地撤退。每一次撤退,都像是再次经历类似从“自然态度”中还原的情形,是与从前肯定的“存在”状态脱离关系(“脱离关系”不是否定。“否定”仍旧是在旧的舞台上的对立统一关系,比如唯物主义否定唯心主义,用黑格尔的“有”否定“无”等等)。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也就是说,有两种“无”,一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它并非真的无;另一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无”不是在自然态度上的。胡塞尔所谓“无”,意思不是说“没有任何东西”。东西是有的,但是,我不从功利的角度利用这些实在的东西,我绝对与这些东西“脱离”关系。我也不利用前人关于这些东西的任何理论判断,即使这些判断曾经是或者现在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这就涉及对胡塞尔一个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超越性”,也就是在哲学描述过程中的无前提性,并没有一个事先的概念、理念、计划、目标,总之,“无前提性”的本意,就是搁置以往任何形态的理论知识。
最能迷惑人的,就是现象学的“我”。这个“我”不是一个人,不是胡塞尔,也不是笛卡尔的“我思”,不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自我意识”。现象学的“我”只是在经历了还原之后的一个纯粹的象征。胡塞尔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即使是现象学领域,要“看见”或“想到”什么,总要有一个意向行为的“发射口”,作为对事物的存在状态不感兴趣(不介入)的旁观者,它不是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我”。
现象学的一切概念,都隶属于“纯粹”。越是纯粹的东西,就越是不实际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我们不要以为现象学的纯粹现象是绝对“非现实”的。从一种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能刺激出自然的态度,也能刺激出现象学的态度。胡塞尔说,你不能固执地认为“自然态度”中的观察所得才是真实的,即便事实果真如此,即便这个自然判断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然态度”下的判断不是一个哲学判断,而只是一个常识判断。哲学上的“真”,应该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胡塞尔说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开始者”。他做了一辈子的“导论”,不断寻找新的出发点,就是继续澄清出发点中那些尚不十分纯粹的部分。这种不停顿地“原地踏步”的哲学姿态本身,就是现象学的“现象”特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总是新的东西。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著名哲学箴言的道理就是,虽然生活本身貌似重复,但实际的情形是,每次重复都是一次重新开始。至于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判断究竟是诡辩还是蕴涵着更大的真理,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束”或者说“目的”的实现,所有的愿望,都是以“非愿望”的方式被实现的,你第一次入河时,就已经走了岔路。
胡塞尔的方法特征,除了“还原”和“意向性”这些研究者们熟悉的字眼,还在于不停顿地“细致区分”和“加宽视野”,它们是胡塞尔更实际的操作方法。要不停顿地打开眼界(horizons),就要不断地变化观察的角度。“变化”(modifications)当然是意向方向的改变,它本身已经包含了“区分”的意思。
“区分”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变化”。胡塞尔很喜欢“流”或“河流”这个词,他甚至使用了“意识流”这个说法。“流”总有像一条线的嫌疑,但胡塞尔又把这条线解释为杂多的串联起来的网状结构。他把现象学之“现象”的起源问题,与时间性联系起来思考。这条现象学之流,确实有很多条支流,思之路上的大转向。其中,视野在不断地加宽,新意迭出。从前的非哲学地盘,被哲学殖民化了。哲学在自然科学中失去的地盘,在更为广大的生活世界中重新找了回来,并且最终改变了整个哲学的面貌。“一个新世界顷刻间就敞开了。”⑥接下来,就是惊奇,因为全是新的:多样性、差异性,且相互之间是无法公约的,在结构上是一种并列关系。怎么得到的呢?来自内直观。
最直接影响现象学的概念,是布伦坦诺的“意向性”。布伦坦诺肯定“意识总是针对某个对象的意识”(意向性)——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对胡塞尔以及后来的现象学家们,具有异常深刻的启发作用。简单地说,总要有“被感觉到的东西本身”。胡塞尔说,意向就是要有一个瞄准点,要描述这个点在还原的状态下是如何出场的。重要的是要有意向“关系”。
意向性强调意想因素的“方向”和“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就方向而论,在纵的方向表现为“历史”或“发生学”,事物或事件是如何出场的,这与时间性有关;在横向方向,则表现为意向结构,比如感觉、判断、愿望、审美等等,各有不同的意向结构;就关系而论,胡塞尔甚至认为,意向要素的连接是任意的,很像是一种自由的联想。空间的位置关系,只是这种任意联想关系中的一种。这种自由联想关系,恰恰要破坏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因为前者试图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或事件连接起来。
意向方向的转移不但有后撤方式的(比如现象学还原),还有横向的,这就涉及现象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边缘域”(horizons)。当意向性瞄准某一个点时,那个点的周围领域是模糊的,与其他事物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一直可以延伸到经验的眼界之外。眼界之外的经验是我们看不见的。在这里,意向的辐射范围有限。要延伸这个有限,需要与时间连接起来。可能的经验是以不可能的方式到来的,它们不断地变化着意向的方向。我们必须以不断超越“眼界”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总是生活在别处,或者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或者甚至连一次都进不去同一条河流。
如果说时间现象学的意向性基本上是一种横向因素之间的贯通关系,那么,还有一种静态的或者共时性的现象学。在这里,胡塞尔发明了超越论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想象”:“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在想象中完全任意地变化事实,随心所欲地想象。以某种面对事实的方式,靠纯粹想象虚构事物和世界。”⑦“纯粹想象”的奇妙之处在于,可以大胆地在想象中变化可能经验的方式。比如,把事实因素扩大或延伸、设想看不见的情形、变化颜色声音位置关系、转移与替换等等。这是一种超越论的——超越自然经验的——直观,它破坏现实经验世界的因果关系。胡塞尔强调放宽眼界(比如本质直观),已经包含了“解构”的意味,因为这意味着观察者上了一个精神层次,就好像做梦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本不过同时也是别人的梦,他自己的存在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真实。现象学的解惑,打开眼界,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在地平线之外增补很多新的可能性。“没有经验”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经验。
胡塞尔独创的现象学方法处处都有悖谬,他晚年借此研究历史或事物是如何发生的。几何学观念第一次被发明出来的过程,出现在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发明者的“主体”之中。那几何学的意义,也在他的意识空间里;可是,无论怎样,几何学的存在不是心理的存在。几何学不是作为某种个人的东西,存在于个人意识领域。几何学观念是客观地对“所有人”(所有的几何学家,所有具有几何学知识的人)存在的。就是说,从一开始悖谬就出现了:在现实时空的大脑里跳出了不应该属于这个大脑的观念,创立了第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观念,一个对所有时代有几何学知识的头脑的公共场所。这是一种纯粹观念的对象性。精神的“肉身”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口语和书面语,精神的内容却只能是“观念的对象”,这又是一个类似上面的悖谬。所以,观念应该在非心理学维度的反思过程得以实现,这才是哲学。就此而言,第一个几何学家一定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的反思不是在心理学维度中。与此同时,更有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反思,它有一种与几何学的哲学反思不同的非心理学维度。
三
就像胡塞尔晚年对几何学起源的分析一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Dasein也充当着一个重新激活“点”的作用。就此而言,把Dasein⑧解释成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在”或传统逻辑学含义上的“是”都是错误的。Dasein者,吊诡也,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按照传统哲学的目光——或者说,它是一个悖谬词语,它一开口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却又不得不开口说话。就像此刻我说“我死了”,在这个语境下我滔滔不绝,但我说话的前提,却是一种不可能性。于是,我的口若悬河,就成了不可能的可能性。我把这称作“超越性”,这是Dasein最基本的说话或行为方式。一个不能传达其恰当含义的词,在天性上就拒绝翻译。不是翻译没有水平,而是先天地没有翻译的可能性。Da-sein之Da,就是汉语中的“那儿”或“这儿”(法语的—là或英语的there)。在哲学史上,这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因为它在德语中太普通不过了,充斥于日常生活。所以,Dasein为“近”,但又不是“这张桌子”或“张三李四”之类的“存在者”,甚至可以说,它不存在,所以,亦为“远”。有一个熟悉且莫须有的动词,以不确定的方式活动着,它的在场等于不在场。为什么不用动名词呢?因为一旦被命名,就要固着于某物,就有了总体性或整体性,就成了“存在者”。海德格尔的Dasein,不是指“存在者”意义上的实在。
以西方哲学传统不熟悉的方式说话,以一种不可能的智慧方式说话。它的要害,是以形不成观念的方式说话。Dasein中有一种没有观念的智慧,这个词没有或没有能力表达它企图表达的念头。一种不可能的“表达”,也是表达,就像从来不以观念形态出场的Dasein嘴里念叨着“在”呀“是”呀,其实是与概念形态的“在”或“是”完全隔离的(因此,也不能说Dasein为“非在”或“不是”)。结果,首先是“表达”然后是“翻译”都遭遇到绝境。20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最终在悖谬中找到灵感的根源:它以不可能的形式“表达”不能表达的意义。
这里也上演了现象学的“心情”,“从本体论上说,这意味着当Dasein以空置的方式说话时,就离开了其朝向世界的原初真实的关系。”⑨于是Dasein变得轻飘飘无以附着,它以无根的方式说话,就可能说出从前不可能说出的话语——去除了“存在者”之根以及只对“存在者”才显示的可能性。话语处于未使用状态,丧失了习惯的根基,其中暴露的焦虑表现了别一种理解的可能性——它没有把所谈论的对象占为己有,无论对象是否就在眼前,它与我现在的心情或话语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海德格尔把哲学史上最普遍最抽象的“存在”概念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这儿”与“那儿”每天遭遇的事儿。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正在沉睡的“事儿”唤醒。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地上。
海德格尔一般不直接说“人”,因为人只是“存在者”。Dasein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在”或“缘在”形态。这些形态是以可能性的方式显露的,如同道路是开辟出来的。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本体论,其实不是“存在”而是可能存在。比如,这种可能的缘分活在其特定的时间中,不是实际经历的钟表刻度上的时间,而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反思心情。它是对时间本身的思,让“缘在”感到焦虑或厌恶(注意,这区别于人类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焦虑或厌恶,而是一种隔离的效果)。犹如我在等待中反复看着手表⑩的举止已经不是作为利用或消磨时间的方式,而是注视着时间之空闲——因为“太久”而显得闲置,时间好像被杀死了——如同勒维那斯所说,海德格尔从死出发思考时间。时间不再是“存在者”,而是“非时间”或“超时间”。别一种时间,绝望、焦虑、厌恶、走神、陶醉的时间,全神贯注而忘记了时间在流逝之情形下的“时间”。时间的确像一条一去不返的河,但是在时间这种习惯性的流淌过程中,任何一次波澜都可能开辟一条时间的岔路,从而改变未来的生活。
“异在”尚不能被“看见”,乃在于还没有揭露它的显示方式。这种“看见”与康德的经验直观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就需要从“逻各斯”现象中解脱出来,实现一种“看见”的跳跃。就是说,“现象”不再是作为看得见的或想到的对象——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对象——彻底摆脱对象型的思路。于是“现象”躲藏起来,后撤再后撤,玄奥而无光,这才是现象学之“现象”,没有面孔的面孔。“‘异在’(Dasein)的现象学是解释学的,是在解释学的最初意味上的……”(11)这种解释超越了存在者的眼界,是一种关于“异在”之各种可能性的解释学。应该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本体论”解释为现象学之“现象”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可能的呢?关键是切入现象的方式。“异在”不是“存在者”,而只能是“可能存在”,它是以悖谬的方式显示的,因为“距离最近的与最熟悉的就本体论上说是最远的最不熟悉的,它在本体论的意味中通常是从视线中消失的。”(12)这就使“异在”显得更加匪夷所思。现象学家用一双陌生的眼睛看周围熟悉的事物,就是说,发明了显示或揭示(解释)事物的新方式。在接近中保持距离,越远的与越近的之间不但没有相隔万里长城,而且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受开辟了新体验的可能性。
四
如何评价勒维那斯的建树?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一切以往精神成果的正义性,都要重新估价。精神与创伤遭遇,人道主义固执于人的主体性概念,因而遗漏了很多人性。勒维那斯说,比如不与“是”连接的人性。这当然与海德格尔不一样,因为时间没有与存在连接,伦理学也不与“是”连接。他者的权利就好像是异域中的权利,别一种权利。并不是说being这个动词的词义还有某些深刻之处没有被挖掘出来,而是立刻停止这种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自我挖掘。停下来,是为了质疑这样挖掘的合理性,因为要来的线头不连接“to be”,而是与之无关的“别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不是本体论性质的。
在对一切本体论问题加上括号之后,精神活动的正义性何在?什么是他者呢?一个第三者。“第三者”问题与勒维那斯所说的“正义性”有密切关系。我注意到这里的“正义性”之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谬。他者究竟是“你”还是“第三者”呢?无论怎样,“你”向“他”的过度模糊不清。是更远吗?勒维那斯所说的“正义性”既不在于我,也不在于你,而在于“两个面孔”之间的“关系”之中。“关系”不等于“to be”,不让“关系”有一个说法,否则就成为“to be”。“关系”之真谛,乃在于切断关系。从“to be”出发之真谛,乃在于从“to be”撤退,且不停顿地以一再超越的形式一再撤退。语言只是貌似以“to be”的形式说话,但这个过程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就像德里达说的,这个实现过程被一再推迟,于是,只留下一些迹象,或者像勒维那斯说的“有(il y a)”,但与“to be”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也不是“not to be”。像一些多出来的……渴望。
为什么勒维那斯在表述中宁可使用“有(il y a)”,而不是“to be”?因为being这个动词往往连接主体与客体,而勒维那斯想制造一种非主体的或说不出来的气氛,以找不到说话源泉或终止以判断真假的方式说话,就像克尔凯郭尔那样以匿名的方式说话——他面对上帝,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的面孔。从那里发射出冷色的光,有点恐怖。与康德的“自由”概念相比,勒维那斯所谓自由是“困难的自由”。勒维那斯认为“有(il ya)”的状态,就像海德格尔说过的“天下雨了,”——这里并没有人什么事,人只是自作多情。想想吧,这世界有你没你,“雨”根本就不在乎——“有点恐怖”,但是“恐怖”之声来自人而不是天,是人类自己对那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东西,感到恐怖。“有(il ya)”既不是存在也不是虚无,即不属于存在与虚无的序列(或分类方式)。于是,像是瞬间发生了精神的创伤,是灾难,也是黑夜。是无我之境,没有任何机会说“我”。走出being的判断,“我”不仅无所适从,简直就要发疯。简言之,任何选择都失去了根据。找不到选择的原因,是无所谓的选择,好像就不能再被称作“选择”。勒维那斯想象人可以走出“主体性”——一心想控制一个对象的主体性、与对立面你死我活的主体性。在“奥斯维辛”,在这一象征着人类(以各种“整体性”为特征的政治口号下)自我灭绝的战争事件之后,劫后余生的人类在思考。从此,人类的哲学与道德再也不会像从前的样子了。人类面临着“困难的自由”,在没有了黑格尔“总体性”的哲学与政治之后,通向未来的路还怎么走?
勒维那斯多次引用海德格尔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人一来到世界上,就衰老得要死了。”这句话和“人一次也踏不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是一句类似诡辩的话谜。“要存在”与“要死亡”之间没有距离,更没有万里长城。并不是说,时间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者死是时间中发生的某个事件。不是的,勒维那斯说,最原始的时间是非存在。或者说,“存在”的“存在方式”是死。你要亲自死,死只有出发,没有回头,不可度量。人有两样事情注定一辈子也想不明白:在生前的时间,在死后的时间。这是一样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时间?同样都是“漫漫长夜”,绝对没有任何希望。同样都是死寂的时间,生前的“未曾活过”与死后的“曾经活过”能是一样的吗?可以把Dasein翻译成“异在”,也就是走出存在吗?因为Dasein是向着漫漫长夜走去。生前与死后的时间,比长还长的长,不像可以度量的日常时间。可以说得出的时间或可以区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或所谓的线性时间,是可以度量的时间。在可以度量的线性时间背后,还有无法度量的生前与死后的时间,可以说后一种时间更为深刻更原始吗?
勒维那斯问道,语言和思考是否可以摆脱being这个最大的精神负担,这个支配者。“说”永远比“被说”更丰富、更原始,具有不可还原性。“摆脱”不是否定“是”与“非”的判断,而是扭转方向。去哪?去那人未曾到过的地方,还没有地址的地点。为什么一定要沿着“是”与“不是”的方向做判断呢?这样的判断遗漏了人的绝大多数心思,那些既不“是”,也不“不是”,甚至也不同时“是”与“不是”的心情。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行为的原因和根据呢?这些原因总被说成“being”的各种变形形态。能否用非being的语言反抗being的语言?反抗语言的语言是怎样的语言?能否在反抗语言的语言中不说“是”与“不是”?——如果这不太可能,那语言本身是怎样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谬事件啊,我们完全有理由不相信任何语言。把不相信语言的意思写出来,还是得用语言,就像不相信being的哲学还得使用“是”与“不是”。哲学与心情一样,不该躲避而应该迎接悖谬现象。“悖谬”不可以说成“现象”,因为“悖谬”为隐,它的显示意味着破碎。“显示”,就是给了一个说法,能被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是非”判断。“去哪”也是“连接关系”的方向,现象学的意向。“是”与“不是”的判断,根源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传统。“是”生硬地打通不一样的东西,名为逻辑判断实为想象中的类比,是人生来就有的形而上学天性。
勒维那斯说,康德提出的4个具有悖谬性质的二律背反中的反题,就是这样一些不可能想的想——我这里接着勒维那斯说,在不可能之处继续往“前”想,是疯狂或精神分裂。思想怎么成为疯癫了呢,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想,在那些什么都想不起来的地方,继续想,从而打通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在那些什么都想不起来的地方,继续想,与在什么都没有说的情况下继续说,情形是一样的。这很像是一种从来不显形的、绵延着的时间、没有指针的时间、超越时间的时间。去那去不了的地方与回想那任何记忆都追溯不到的瞬间,情形是一样的。异乎寻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这里走出来没有精神负担的自由,像一种异域的博爱。一种困难的自由,与我的选择无关,不是以我为中心的任性。去那我选择不了的地方,想我那从来都不能预先想到的事情,一切都在我的能力之外,“哪儿”与“何时”都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哲学听到这些很不满意,因为哲学不喜欢轻飘飘地说话。五
属于我们以上提到的这条精神线索的代表人物,当然还包括了国内学界熟悉的当代法国那些重要思想家们,比如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尔、德里达,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他们的思想。总之,19世纪后半叶以来,精神上的这条悖谬之路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了哲学的“死亡”。它指的是旧哲学的死亡还是哲学本身的死亡?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不死的,生活的意义来自知道事物是“要死的”。更鲜活的思想从哲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最为彻底的解放思想。为什么说哲学要死了呢?因为“哲学”精神已经延伸到哲学接触不到的范围,延伸到哲学所能理解的界限之外,延伸到悖谬这个死结。也许我们可以照样把“哲学”的标签贴在这里,说“悖谬的哲学”。但是,这根本于事无补,因为严重的问题只在于,“悖谬”的或“他者的智慧”在以往的所有智慧之外。
作为极其特殊的“疑难”,悖谬是无解的,它并不属于现在还没有认识,将来就会知道的事情之列。对此,哲学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疑难”也不是宗教问题,因为悖谬为传统的“相信”概念设置了巨大的障碍。“疑难”就是不可能回答,它和悖谬一样,是朝着不可能的方向去的,属于超越哲学界限的问题。比如,对于悖谬的问题,不能用being及其变形的方式提问,无法询问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为什么,等等。哲学一直是以being的方式提问的,影响到人类传统文明的各个领域都以同样的方式说话。以往所谓学习哲学,不过是记住了传统哲学的提问或说话方式,与其说它们是一些真正的提问,不如说是一些套话,因为它们属于封闭式的提问。开放式的提问,是无法预设可能性的提问,它对问题有些无从下手,问题太多且一个套着一个。没有“问题本身”,因为“问题本身”意味有答案。纯粹的问题,是无解的问题。
因此,悖谬是不属于哲学的另一精神层次的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告诉我们,精神在自己的旅途中最终会得到满足的,尽管得到满足的道路曲折而漫长。从一开始就不以满足为目的的精神“欲望”,显然摆脱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作为一种有别于辩证法的微妙精神,精神“悖谬”现象告诉我们,能够被满足的只是需要,而不是欲望。“欲望”和“需要”之间有细微且本质的差别。欲望的天性就是不能被满足,它只是摆出一副想要满足自己的架势。欲望总是与摆脱需要(或者摆脱得到“满足”才幸福的念头)连接一起的,就像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相信”总是与放弃“相信”后“心满意足”的心情在一起,这当然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精神上的悖谬乃心情上的悖谬。悖谬与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矛盾只是精神自我同一性的满足,即能够返回或者还原出事物本身(即所谓辩证法的“圆圈”)。这种建立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的自我满足的世界观,又是以线性时间为基础的历史哲学之独断结论。但是,悖谬之“诡辩”却认为,由于精神或心情的本质就在于不能满足,精神刚一萌动就已经开始走了岔路。时间、文明、历史其实都是以这种没有满足初衷的“岔路”方式实现的,所以精神应该像心情一样呈“网状关系”,而不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变相直线。
悖谬与不相信语言连接在一起,因为悖谬是难以表达的,当它说出某一词语时,同时意味着没有利用这个词语的使用价值,摆脱这个词语的表面含义。悖谬的心情,就是无限地接近一个非常遥远的他者,越是有接近的欲望,就越没有满足。欲望是满足之外的剩余心情,一种心情的悖谬。这又破坏了《精神现象学》的精神大团圆。作为一个缺憾,不完满是悖谬的常态。缺憾是精神的创伤,它强调“分”而不是“合”,强调不幸而不是幸福。悖谬比“矛盾”要复杂得多,犹如精神的不幸比精神的幸福要复杂得多。精神的不幸是以“精神的分裂”为特征的。这里的“分裂”不是指黑格尔式的“对立统一”,因为精神的分裂或不幸,不是想在“彼”与“此”之间做出取舍,而是在这种取舍面前不知所措:因为悖谬的“精神”从“彼”与“此”中都得不到满足。它不得不在注定无法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做出痛苦的选择。
作为一种微妙精神,悖谬反复提醒我们,不要把不一样的东西混淆起来,看成一样的。悖谬的思想之所以显得晦涩,就在于哲学思维的习惯无视“悖谬”所描述的精神或心情之细微差别。也就是说,悖谬表现出一种哲学所不熟悉的智慧能力。“悖谬”放弃了哲学的说话方式。但是,放弃了哲学的智慧仍然是智慧,尽管是与哲学不同的智慧。这智慧让精神延伸到哲学之外,不啻为一种新的精神启蒙,因为启蒙的光不可能是一样的。
注释:
①S.Kierkegaard,Either/Or,Volume on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37.
②《圣经》中说,上帝许诺亚伯拉罕一子,许多年月过去了,上帝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但是,亚伯拉罕丝毫没有改变等待孩子的初衷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经过了漫长年月的期盼与折磨,他得到了他的爱子,并取名叫以撒。然而上帝却让这个美好的结局有一条很不吉利的尾巴,他叫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来献祭。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又将失去自己多年期盼的儿子。亚伯拉罕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的一个考验,他只是默默地执行这个命令。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还没有人能像亚伯拉罕这么伟大,有谁可以理解他吗?”
③④S.Kierkegaard,Fear and Trembling,Penguin Books,1985,pp.50,52.
⑤因此,一切现象学术语,尽管表面上和形而上学或心理学的术语相同,但都是在“隐”而非“显”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像感觉、想象这类思是可以分为“显”与“隐”分别描述的。进一步,即使是洛克意义上的“外感觉”与“内感觉”,在胡塞尔看来,也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学的感觉,甚至也不是洛克的“内感觉”,也不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⑥E.Husserl,Psychologie Phenolmenologique(1925-1928),vrin,2001,p.32.
⑦E.Husserl,Psychologie Phenolmenologiqu(1925-1928),vrin,2001,p.70.
⑧德文Dasein在中文中多翻译为“此在”。我认为也可以在远与近的含义上,翻译为“缘在”(张祥龙教授的译法)或“异在”(我的译法),意为:近的事件同时就是远的事件,能否相遇全看缘分或灵感。Dasein在《存在与时间》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或者干脆保持德文原词,或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办法,即把这个词中间用—隔开(Da-sein),法文翻译为être-le-là,英语翻译为Bing-there。无论是“此”、“缘”还是“异”,都与意向之特殊方向有关,强调“难得”与“不一样”。但是,我在阅读后发现,英文翻译中的“there”与法文翻译中的“là”都指“那儿”,其实,海德格尔的Dasein之“那儿”,同时也包含着“这儿”。或者说,远的就是近的,在这个意义上,“此在”的译法也是贴切的。但我认为,Dasein一词根本不可能有标准的汉语对应词,得用一组汉语加以描述,所以以“缘在”与“异在”等等增补“此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丰富了对Dasein的理解。
⑨(11)(12)Martin Heidegger,être et temps,Traduit par Francois Vezin,Gallimard,1986,pp.214,65,75.
⑩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1929-1930年的讲课稿《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更集中地讨论了“厌恶”这个在传统上不是哲学概念的“哲学概念”。为了描述“厌恶”状态(萨特写过的最好的小说《厌恶》肯定受过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竟然用了整整100多页的篇幅,好像在讲述一个焦虑者在等待中反复看手表的荒诞故事,它完全可以作为荒诞戏剧上演。海德格尔的解释,则像是这独幕剧的旁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