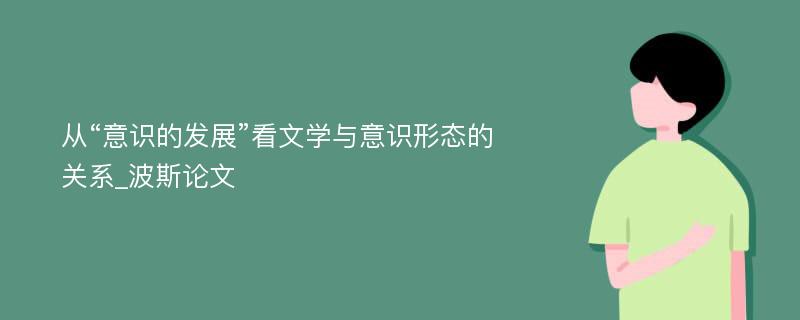
从波斯彼洛夫的“意识发展”看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波斯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意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8)02-0153-04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占有重要的位置。钱中文于1984年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时,是在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中译本前言中提出的。波斯彼洛夫提出了文学与社会意识发展相关联的命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钱中文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启发,新创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所以,分析波斯彼洛夫的观点,对于认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乃至更进一步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是有帮助的。
波斯彼洛夫的观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借鉴了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著作的思想,他既将文学视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充分地看到了文学与人类意识的发展关系,从而从不同的意识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观察文学艺术的特征,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看法,富有启发性。但他的结论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在保留对于“象”的第一性质的认可基础上,才能成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学独特性的支撑资源。
波斯彼洛夫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而发展的,他指出:
文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内容上划分得越来越细了,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除艺术之外,社会意识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科学、哲学、道德、法律,政治理论。不过所有这些形式都在一点上不同于艺术,这就是它们都用抽象的概念表达自己的内容,而艺术则用富有表现力的形象来表现内容。[1]71
这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波斯彼洛夫分析了文艺不断趋向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提出了划分社会意识发展的标志,认为它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向阶级的国家制度转变时期产生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就从其他的社会意识中分离出来,成为精神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但同时艺术在改变了其形式和新的作用中,仍然保留了社会意识发展早期阶段的某些特征”[1]71。于是,在他看来,艺术的发展其实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社会意识没有分化的阶段上的“原始艺术”,第二阶段是在社会意识发生分化的阶段产生的“真正艺术”。
社会意识没有分化的阶段可称为“混合阶段”,神话与巫术的观念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占有统治地位,既没有产生作为道德理论的伦理,也没有产生国家法律与国家观念。此时的仪式歌舞、仪式短剧、雕塑、洞穴绘画等,作为一种集体创作,表现了原始人的生活哲学。
而就思维特征看,“原始人的思维不是根据抽象的特征把各种生活现象联系起来,而是根据现象之间的相同、类似和对比去联想,因此它是一种联想的思维,同时它还是一种混合性的思维……原始人也不会明确地区分生活现象的共性和个性、单个和多数、生灵性和非生灵性、现实性与虚幻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的接近”[1]72-73。所以,原始思维也是一种表象思维、类比思维,是在极度低下的狩猎生产方式和对自然力的依赖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思维结果,并不具有后来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因此它具有集体意识的性质,在同等程度上它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且它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某一个有目的地努力想象的结果。它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意识的创造因素。它的感情色彩是集体思维的夸张的万物有灵论本身造成的,所以并不带有任何的思想倾向性。感情色彩在后来——在艺术现象中,才具有思想倾向性”[1]76。据此可知,在人类意识发展的混合思维阶段,出现了原始艺术,这被波斯彼洛夫称作是“艺术前的艺术”,但这毕竟是艺术,因为那时的社会上还没有形成意识形态,所以,那时的艺术也就与意识形态无关。这表明,艺术的出现,是人类意识发展与审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却是在不必沾染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自然分娩的,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必然关联。
按照波斯彼洛夫的观点,只是到了氏族贵族政治出现时,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特权,社会意识的一致性才遭到了破坏,“每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意识都带有强烈反对另一集团的生活和活动的倾向性”[1]88,社会意识的发展才从统一的状态演变成分化的状态,社会的意识形态才出现了,并深刻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混合性的仪式创作思维才被真正的艺术思维所取代。所以,波斯彼洛夫指出了新的“真正艺术”的特征是与阶段与社会矛盾相关联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社会意识发展形式的艺术,是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阶级国家制度以后,在其深刻的社会矛盾所形成的新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产生的。”[1]94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艺术创作是有倾向性的、具有思想深度的,体现了阶级矛盾与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波斯彼洛夫在分析这一时期的艺术特性时,才用“艺术的意识形态意义”加以概括。由于要求这一概括具有彻底性与单一性,他对艺术的说明也就力图彻底摆脱“原始艺术”的特性,因而使得意识形态性成为“真正艺术”所具有的唯一属性。
这样一来,反对艺术创作的其他才能的重要性,否定艺术创作与混合思维的深层关联等,成为波斯彼洛夫的论证重点。他说:
自然赋予人们的才能在程度上是不同的。但是任何才能,只有在社会提出了任务,需要相应的才能来完成它时,它才有可能得到表现和发挥。艺术创作是一个独特的任务,它需要专门的才能来完成。这种才能也只有在真正的艺术从混合性的创作中产生出来之后,才得以表现和发挥。这就是说,不是人的才能造成了艺术创作的特点,而是艺术创作的特点把相应的才能引向生活,促进了它的发展。而艺术创作的特点本身又是某个国家和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需求的特点所决定的。[1]106
波斯彼洛夫的结论是:艺术,如果说原来曾经体现了混合思维特点而没有意识形态性,那么,在阶级与国家出现以后,它就以其意识形态意义而存在了。波斯彼洛夫通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意识的发展,到头来论证了艺术在进入阶级与国家阶段以后,只有意识形态性。但波斯彼洛夫的观点,也许只是一种单一推进的进化论,并简单地运用人类社会意识发展的模式来概括艺术创作活动,不能周全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再讨论:
其一,波斯彼洛夫关于社会意识发展过程的描述,尽管借助于一些人类学的成果概括了不同阶段的特征,但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从社会意识谈起,分混合阶段与抽象阶段来谈,还不足以全面清晰地反映人类认识活动与精神活动的全部已有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可作三个阶段的划分:混合思维与类比思维阶段、抽象性思维阶段、有鲜明的倾向的思维阶段。这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在第一个混合思维阶段即诗性思维阶段,主客体不分,人处于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还没有从自然中清晰地分离出来,因此人还不是后来所说的主体,这是一个“象”形的阶段,对世界的认识是“象”形的,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象”形的。这个阶段产生了艺术,哪怕称它为原始艺术,可毕竟是艺术的产生。在第二个抽象思维阶段,主客二分,人开始脱离了自然界而建立一个人所创造的社会,人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开始以一种概念的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思想与理论开始出现了。这个阶段产生的是宗教、工艺技术、契约、哲学性的思想等。第三个阶段是意识形态的阶段,也就是不同社会主体之争的倾向思维阶段,不仅主客是二分的,人是主体,人群之间出现了极其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人群间的统一是通过分裂的方式来实现的,各种理论产生了。这个阶段产生的是意识形态,包括各种严密的法律体系、政治观点、军事思想等。尽管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的,但第三阶段的真正成熟,依然是在第二阶段之后的,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部分地出现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总之,三个阶段的前后连续,正是人类意识发展的完整过程。所以,从混合性的诗性思维阶段发展到意识形态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在没有到达意识形态阶段之前,人类的艺术早就诞生了,这一事实表明,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要远比人们想象的晚得多,远得多。
其二,文学艺术早在意识形态形成之前就已经产生,但它与后发的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里主要涉及对于先发性质与后发性质之间关系的观察与评价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因为学术立场相异而给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波斯彼洛夫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和其他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往往执行的是一条用后发性质取代先发性质的研究策略,强调经过社会意识的发展与变化,文学艺术也随之发展与变化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波斯彼洛夫的观点在注意了发展变化时,忽略了事物性质的稳定性,是在一种近乎进化的单一发展观的思维中完成自己的论述的,用后一阶段的性质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性质,未能看到事物性质的根本性及其整体性。如果我们从维柯的“起源即性质”的观点来看的话,原有的第一性质的获得,因为是自然生成的,往往也就是这个事物的根本属性;而后发的第二性质尽管对于事物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是人为的性质,也就只是事物的附加属性,附加属性不能否定事物的根本属性。因此,波斯彼洛夫是用附加属性取代与否定了根本属性,这是不利于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
其实,在波斯彼洛夫所分析的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他所说的原始氏族阶段的混合思维对于整个的社会意识发展来讲,也许确实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但也是一个基础阶段,对于艺术来讲,只要具有这个初级或基础阶段也就足够了。因此,混合思维阶段的意识活动所体现的“象”形特征,正是产生艺术的情感与思维的温床。即使人类的意识没有向阶级的国家的阶段发展,没有出现后来的意识形态,艺术也已经产生了。所以,混合意识是艺术产生的母体,而意识形态只是艺术产生以后所经历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艺术不得不意识形态化了,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却无法彻底改变艺术的原有的混合意识特征。正是在这个方面,钱中文试图用“审美意识形态”来修正波斯彼洛夫的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在我们看来,钱中文的修正还不够彻底,仍然带有波斯彼洛夫的思想印痕,是在意识形态的樊篱中兼容了审美,审美还不是独立的,主导性的。只有将混合思维看作是艺术的母体,艺术在这里孕育诞生了,才能界定艺术的基本属性。意识形态好像给艺术披上了一件外衣,艺术因为活动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不能不披上这件外衣,可这件外衣,并不能改变艺术的胴体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与呈现着。因此,艺术在受到社会意识发展的影响后,不是仅仅如波斯彼洛夫那样轻描淡写地说着“保留了社会意识发展早期阶段的某些特征”,而是深刻地烙有着社会意识发展早期阶段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基本特征,决定了艺术永远具有了其产生时所具有的那些基本性质,从而与后起的其他社会意识保持了鲜明的区别性征。若是艺术最初的基本性质是可以在后来的社会意识发展过程中因为受到其他意识形式的影响而简单地趋同的话,艺术就会消失。波斯彼洛夫没有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制约力,故他在论及艺术的意识形态意义时,就不自觉地遗忘了艺术的原始起源性质。正是艺术的这一起源性质的永不消退,才使艺术永远保持了它的基本特性。
其三,波斯彼洛夫在谈到艺术的特性时使用了“形象”一词,这是过去的苏联文艺理论家常常谈到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意在维护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他们认为文学艺术区别于意识形态其他范畴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形象性,其他的意识形态均是抽象思维的活动领域,而惟有文学艺术是以形象的方式存在的,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创作活动。波斯彼洛夫指出:
每个达到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民族,除了有自己的科学和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之外,还有艺术。而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对生活的社会特征表现出富有感情的思想认识。艺术的特征无疑使艺术属于社会的形态的思维范畴。但是艺术的内容,它的艺术性的内容,却是不可能用理论,即借助于抽象的概念来表现的,而总是通过把生活创造性典型化的生动形象表现出来的。[1]102-103
但我们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不可否认,形象性确实是艺术的特征,但仅仅只是艺术的特征之一,对艺术只作这样的肯定,还只是在艺术创造的手段、方法层面上来研究艺术的独特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区别艺术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不同点,从而也无法厘清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界限。就波斯彼洛夫的原意来看,他本来就没有彻底区分这种不同的意图,所以,如此要求他是没有理由的。但就我们而言,接过他的理论,若只是肯定形象是文艺的重要特征,那就意味着文艺除形象外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没有区别。如果说文艺是用形象来表现意识形态,或者称作通过“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来表现意识形态,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是用抽象的概念来表现意识形态,二者在表现意识形态这一目标上没有区别,只是途径、方法、手段不同,那这两个事物之间也就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了。所以,从形象的角度肯定文艺的特性,掩盖了从本质的角度肯定文艺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没有区别这一最严重的假定。
我们记得胡风在讨论到文学的性质时,就非常激烈地反对将形象化视作文学的本质,其担心与此有关。胡风反对的理由是:形象化的观点将会割裂人的存在,以为一边是思想,一边是形象,让思想穿上形象的外衣,结果创造出了只是一种傀儡,不是活的人物。胡风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这就非得在作家底意识上‘再三感觉到’不能胜利。”[2]613这“再三感觉到”说明艺术创作不是遵循理性的规律,先有认识,形成概念,再进行形象化的处理,而是只能在完整地把握感性世界的基础上去创造它的果实。胡风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前苏联持有的与波斯彼洛夫相近观点的一种否定,说明仅仅突出形象性,不足以维护文艺的独特性从而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用形象性或形象化来说文艺,难以完成规定艺术的本质特性这个任务。当然,胡风反对“形象化”,只是不自觉地感觉到了形象化在理论上的严重不足,他没有意识到在反掉形象化以后,应当大踏步地后退,后退到原始时期,才能真正找到文艺的本质特性。在这一方面,维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与原始时期的混合思想即诗性思维相关的是艺术其实正来自这个整体性的感觉与思维的温床,不是艺术在形成了概念以后要形象化,而是艺术在其起源上就本来是形象化的,只有将手段意义上的形象化转化为本体论上的形象化,形象化才与揭示艺术的真正本质相关的。
为了避免形象一词的流行用法可能造成对于论述的模糊影响,我们认为应当用“艺象”来取代“形象”来说明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形象与艺象的基本区别在于:艺象即艺术形象的缩写,与宗白华的“艺境”即艺术境界的缩写相近,它强调通过“象”来自发地反应及认识世界,或者说是情感地表现世界。通常的形象化一词,仅仅强调其作为一种手段而被用来包装概念。由于认为“艺象”就是一种诗性思维,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功能,所以,它也是人类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定形态,可以称为“艺象形态”。它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是它以艺象的表现方式存在并表达着人对世界的最初反应及体识,这种最初的反应与体识构成了人类的第一个反应模式,在这一个反应模式中,人类的艺术第一次自然受孕而成功诞生了。于是,带着这个母体的血脉遗传,无论文学艺术日后如何幻变千万,也改不了它不变的“精神基因”。
收稿日期:2008-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