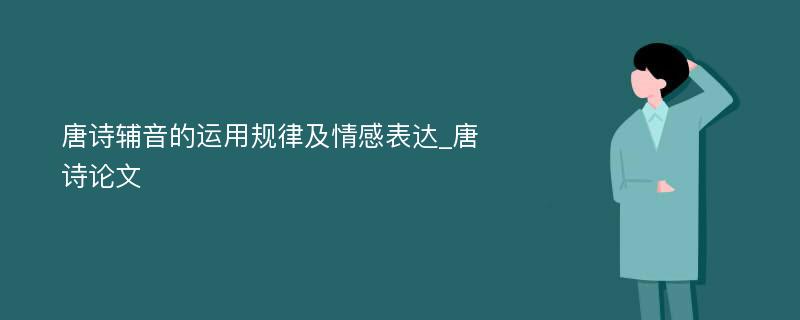
唐诗中声母的运用规律及其情感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母论文,规律论文,情感论文,唐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5)02-0134-07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将声母简称为“声”,又叫“纽”,或者合起来称作“声纽”。这里的“纽”就是“枢纽”的意思,可见古人认为声母在一个汉字的音节里面,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实际的情况是,有的汉字字音里面根本就没有声母(“零声母”)。这样看来,在汉语的每一个音节中,真正必不可少的成分还是“韵”和“调”,这也是古人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为什么特别强调押韵与平仄,而不太注重声母的一个客观原因。尽管声母在汉语音节中的地位不能与韵母和声调相提并论,但优秀的诗人,凭借自己对汉语言文字天才的敏感和独特的认知,总是尽可能地在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开发和利用汉语音节的各种有利因素,以追求音律谐美、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这里面自然也就包含对声母的关注和运用。 在我们所考察的唐诗中,即存在着大量的诗作,它们利用相同或类似声母字在诗句中的反复出现,一方面与同一诗句中的其他音节形成错综对比、和谐呼应的美感效果;另一方面又配合诗人主观情感的表达,以声摹境,达到了声情谐和的艺术至境。如王维《渭城曲》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与“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一句七个字中竟然叠用了五个齿头音的声母字,如“舍、青、青、色、新”。齿头音在发音上具有一种尖锐清厉的感觉,这无疑从诗歌的音响上增强了送别时凄怆惨恻的气氛。后一句中的“劝君更尽”与前一句中的“客”前后呼应,是一连串的舌根塞音声母字,也即古人所谓的“牙音”字,在音响上具有一种浊重质实的效果,形象地表现出了送别者内心的沉抑痛苦。这一点在杜甫的诗歌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是他“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一个具体表现。比如著名的《登高》一诗中的第六句:“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一句七个字中,除了“年”之外,其他六个字全部是塞音声母字,且其中的“多、独、登、台”四个字又都属于舌尖塞音,诵读起来犹似一连串的啧啧叹息之声敲击在我们的心坎上,造成一声痛似一声、无限凄楚的音响效果,这和诗歌内容所要渲染的孤独、多病、衰老等情感在气氛上是一致的。[1](PP.129—130) 唐诗中诸如此类的诗例非常丰富,这也就告诉我们,让相同或相似的声母在一句中有规律地反复出现,以营造出一种“声情并茂”的音律效果,这对于早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或许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在唐诗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诉求。因此,借助声韵学的知识,探讨唐诗中声母的运用规律及其审美效应与情感表达,对唐诗语言学批评来说,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须。 一、声情谐和的语言学理据 从前面所举诗例的分析中可知,相同或相似声母字在诗句中有规律的使用,能增强诗句的节奏感与音律美,但它与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是否真的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着某种关联?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声母的运用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虽然不可能是一一对应、固定不变的关系,但声母在诗句中有规律的使用有助于某种情感的传达,则是肯定的。换句话说,语言中一切音律技巧的使用,除了给诗歌带来音响上的美感效应之外,更为重要的,其实都是为了集中而有效地凸显某种情感。这从古人关于五音与情感表达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如清人王德晖与徐沅澄合著的《顾误录·五音总论》中就提到: 刘向《五经通义》云:闻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角声使人恻隐而好仁,闻徵声使人恭俭而好礼,闻羽声使人乐养而好施。《白虎通》云:宫者容也,含也,商者张也,角者跃也,徵者止也,羽者舒也,此通乎性情也。[2](P39) 所谓“宫音舌居中,商音口开张,角音舌缩却,徵音舌挂齿,羽音撮口聚”[2](P40),说明这里所说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声韵学上根据声母发音部位的不同而区分的“喉、齿、牙、舌、唇”五音是一一对应的。虽然我们对五音的音质所产生的情感联想可能与上面所说的并不十分一致,但这里所提出的五音“通乎性情”的观点,仍然对我们具有启发与参考的价值。黄永武先生就曾对这一观点作过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人情的喜怒哀乐,或奋或郁,为求宣情达意,在发音时,借着喉、牙、舌、齿、唇诸官能姿势的辅助,造成发声气流的委直通塞,表现出清浊、高下、疾徐不齐的声音,赖此声音,以宣达其奋郁惊喜的情绪。所以,在五音之中,不同的音质,自能表现不同的情感。”[3](P174)这也就是说,汉字的声母在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上具有高低、清浊、轻重、洪细等各种音质上的区别,而优秀的诗人往往能根据汉字在音质上的这些不同,配合表现自己各种不同的情感,以追求“声”与“情”的内在谐合。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将五音与情感联系起来的观点,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一种主观的感觉与模糊的印象之上,并没有十分谨严的科学依据与学理参证。唐诗语言学批评要通过“声律”来发掘语言形式当中深隐的情感内涵,就必须找到这种可靠的内在理据。 语言学家从语音的角度考察不同词汇之间意义联系的研究,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知道,在人类创造语言的原始时代,语音和词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等到词汇初步形成以后,旧词与由它所派生的新词之间,往往因为声音的相似,意义上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第四章,在专门谈汉语词汇的发展时,就主张从语音的联系去看不同词汇之间意义的联系。他为此列举了丰富的实例来进行说明: 以明母字为例。有一系列的明母字(唇音)表示黑暗或有关黑暗的概念。例如:暮、墓、霾、昧、雾、灭、幔、晚、茂、密、茫、冥、蒙、梦、盲、眇。(当然还有一个“明”字作为反义词而存在,但在上古时代,反义词也是有语音上的联系的。) 再以影母字为例。有一系列的影母字(喉音)是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的。例如:阴、暗、影、荫、曀、翳、幽、奥、杳、黝、隐、屋、幄、烟、哀、忧、怨、冤、於邑、抑郁。 再以日母字为例。有一系列的日母字(半齿音)是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的。例如:柔、弱、荏(弱也)、软、儿、蕤(草木花垂貌)、孺、茸(草初生之状)、韧、蠕(昆虫动貌)、壤(《说文》:柔土也。)、忍、辱、懦。[4](PP.534—536) 其实,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之前,传统的训诂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朱骏声、章炳麟、刘师培等人,都曾从汉语语音的角度去追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联。然而,真正将这些训诂学、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的研究当中去的,其实并不多。今人傅庚生先生曾经做过大量的尝试,他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中专门谈到声母的发音部位与诗词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他说:“音阻分喉、牙、舌、齿、唇五种。喉音、牙音,皆浊重;舌齿唇诸音则较清利。”接着便以韦庄的《荷叶杯》一词为例,认为其中“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两句,“情意寄于文字者十分,不难明白;寄于声韵者亦十分,缘多用唇齿间字,单单藉声音即可表示宠姬曼倩之姿质,真才人呕出心血之作也”。下又举《西清诗话》所举王晋卿一诗为例:“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认为其中以牙音字为韵,便见浊重,与晋卿感叹爱姬不可复得的怆然心境正相吻合。[5](PP.209—211) 除了傅庚生先生之外,郭绍虞先生也提出了“声随情转,情由音显”的观点。在《中国语词的声音美》一文中,他不仅列举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而且还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语音之起,本于拟声与感声。拟声是摹写外界客观的声音,感声是表达内情主观的声音。拟声语词既善于摹状声貌,感声语词尤足以表达声情,所以只须巧为连用这些拟声或感声的语词,就足以增加行文之美。……陈澧《东塾读书记》根据子思、程子诸人之语,首创“声象乎意”之说。他以为“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他再举其例云“声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气象之也。《释名》云: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而高远也。风,兖司豫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此以唇舌口气象之说也。”后来刘师培《原字音》篇也有这种理论。他们以声象乎意之说解释一切语词,固然不很妥当;但若用以解释比况形容之语,则大都适合。[6](PP.137—145) 正因为“声象乎意”,声、义之间即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郭先生据此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为例,他说:“《上林赋》写灞、浐、泾、渭、酆、镐、潦、潏八条水道之混流而下,称其‘赴隘陿之口,触穹石、激堆碕,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沸宓汨、偪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这一节文连用了好几个双唇阻的破裂声,如‘暴’、如‘澎湃’、如‘滭沸’(音毕拨)、如‘宓’(音密)、如‘偪’、如‘泌’(音笔)、如‘潎’(音撇),这一些字的发声状态,都是口程鼻程同时闭塞,阻遏气流,然后骤然间解除口阻,使气由口透出,所以才成为破裂声。这正像灞、沪八川之赴隘陿之口,触穹石、激堆碕,受到阻碍,而成为一种沸乎暴怒的情形。”又以李清照《声声慢》一词为例,认为此词之所以“创意出奇”,就在于“她注意到字音与字义的关系,能运用适合的语词以从声音中表现出神思而已。即如她所用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中,以齿上音占大多数,就可知此词运用之妙,全在这些声母相近的字联在一起,于是读来也觉声情中所表现的兼有凄清惨凄之感而已”。[6](PP.142—145) 傅、郭二位先生所举的例子虽然都不是唐诗,但就文字本身的音响效果与情感意义之间的关系来说,用在赋或词里,与用在诗中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所以,以上这些对声义相关、声情谐和的理论探讨,一样也可以应用到唐诗的阅读、欣赏与批评中来,给我们唐诗语言学批评提示了一条通达的蹊径。那么,在具体的唐诗中,其声母的运用规律呈现出什么样的形式呢?声母的构成形式与诗歌的音律美感、诗人的情感表达之间又是如何建立起谐和一致的关系的呢?我们在下文中一一予以阐明。 二、唐诗声母运用规律之一——双声的连用 所谓双声,即是指语言中连结在一起的两个汉字在声纽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近似或相同。在诗歌的音节组合中适当地进行双声的配置,不仅能够增强语言的音乐性,而且还能辅助诗人的情感表达,以臻于声情谐和的艺术至境。 如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一诗的首联:“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其中“演漾”二字,同属喉音喻母字,是典型的双声连用。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与“演”声音相近的字,如“衍、延、引”等,都属于同源字,皆有“长远”之意(四字同为喻母,且在韵部上,“引、演”与“衍、延”为真、元旁转)。[7](PP.692—696)“漾”字也是“水流长”的意思,如王粲《登楼赋》:“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与“漾”声音相近的“瀁、泱”等字,都有着“水深长而动荡”之类的含义。[8](P577,P622,P642)所以,“演漾”二字在诗中串读起来,由于声纽相同,连绵婉转,音响上自然就更给人一种水波泛溢、摇曳动荡的感觉,这与诗人在诗中所着力描摹的城东清溪波光潋滟、充满生机的春日情境,是非常切合的。“演漾”二字的双声连用,在唐诗中表现得极为丰富,如“危昂阶下石,演漾窗中澜”(沈佺期《绍隆寺》)、“清辉淡水木,演漾在窗户”(王昌龄《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深林秋水近日空,归棹演漾清阴中”(王昌龄《送十五舅》)等等。“演漾”之所以被如此频繁地使用,恐怕与王维的诗句一样,都是要在诗歌语言的音响效果上借助于双声连绵的前后推转,展现出波澜“流动起伏”[9](P1865)的景象与诗人开阔健朗、物我相融的澹然情怀。类似的还有“萧瑟”一词,在唐诗中也经常出现,如“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张说《幽州夜饮》)、“苍茫秋山晦,萧瑟寒松悲”(岑参《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阎防》)、“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等等。这些诗句中的“萧瑟”二字,在声母上都是齿音心母字,显然也属于双声连用。诗人在诗句中使用这样一组双声连绵字,除了它本身在词汇意义上具有“秋风貌”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寂寞凄凉”之意以外,在音响效果上也有它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作用。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齿音心母字一般多数都具有“尖细分碎”的含义,如“细、小、纤、碎、散、撕、澌、嘶”等[10](PP.124-154)。这与一些曲学家对声音的感觉也是不谋而合的,如汪经昌在《曲学例释》中就认为,相对于喉音的深厚、牙音的豁显、舌音的和平、唇音的柔微,齿音有一种清厉的感觉[3](P175)。曲学家所谓的“清厉”,与训诂学家的“尖细分碎”应该是同一个意思,都指向一种细碎、稀疏而又枯落、凄清的意象。这从与“萧瑟”有着音转关系的其他几个同源连绵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如“萧索”、“萧萧”、“萧屑”、“骚屑”、“肃霜”等,它们都属于一个以声纽“心·心”为格局的同源双声联绵词族[11](P37)。由此可见,“萧瑟”一词除了大家熟知的基本词义之外,它在诗歌的音响上通过双声的连用,实际上也起着一种“以声摹境”的作用。 以上讨论的还只是双声的单用,唐诗中更多的是双声的对用,即在上下联相对应的位置上,运用双声词以为呼应的一种声律现象。如“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上句中的“寥落”与下句中的“流离”都是来母双声,且都处在诗句的第二个节拍上,构成了声律上的对仗与呼应。唐代诗人中积极运用这种声律技巧,以营造一种顿挫的音律节奏,并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效果的,当属诗圣杜甫。尤其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双声的对用随处可见,且不仅限于双声的连绵词,有的甚至还打破了诗歌节律的界限,在两个相邻的词组之间形成双声连用,如下面这些诗例: 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九日诸人集于林》)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八首》之三)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秋兴八首》之五) 上面这些诗例中,不管是连绵词还是复合词,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叠用了双声。其中最为奇特的是最后一例,上句中的“宫阙”与下句中的“金茎”相对,声母全属舌根清塞音,这毋庸细说。而且,在“莱宫”与“露金”之间也有一种突破词界的限制而形成的音素对应。这在杜诗中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就如本诗的颔联:“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其中“降王母”(k—r—m)和“满函关”(m—r—k)在声母上也形成颠倒对应的关系。再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秋兴八首》之七),上句的前四个音节中有三个唇音,下句中在相同的位置上则有三个半舌的边音与之相对,并且两句的最后三个音节在声母的发音部位上也是相互对应的。这些都表明了杜甫杰出的建构诗歌语言声律的能力,他能够通过改变诗歌语言中相同声母的密度,以加快或放慢语言的节奏。而这样做在诗歌语言的审美和情感表达上的作用在于:“语音相似的音节互相吸引,特别是一行诗中出现几个相通的音节时,它们便会形成一个向心力场;同时,如果一行诗中重复了前面出现过的音型,前后的相同音型也会遥相呼应。这两股力量无论是单独或共同发挥作用,都会为它们影响所及的诗行提供聚合力,并使这些诗行有别于其他诗行。”[12](P3) 当然,除了相似音型之间前后呼应所形成的向心力场、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烘托与强调的作用之外,构成声律并在诗行中对应的双声,其本身在音响上也起着描摹情境的作用。就以杜甫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这一联来说,“萧瑟”二字声母同属心母,是双声;“江关”二字声母同属见母,也是双声。再往深一层去看,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齿音从听觉上来说比较尖利,而同属于齿音心母字的双声连绵词“萧瑟”,本用来形容“秋风之貌”,便已将凌厉的西风刻画得刺人心坎,再引申以刻画人生之处境,更让人顿感寂寞与凄凉。同样,牙音见母字,从发音上多有屈曲、钩折的意味[3](P187),所以唐代的诗人常用同属见母的双声连绵词“间关”来描写莺啼或鸟鸣,如“春晚群木秀,间关黄鸟歌”(孟浩然《晚春题远上人南亭》)、“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白居易《琵琶行》)、“莺啭才间关,蝉鸣旋萧屑”(喻凫《惊秋》)等等,这是因为“间关”作为双声连绵词,在音响上不仅能摹状鸟鸣的优美之声,而且还将其婉转、流滑的声音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与此类似,“江关”一词虽然不是属采附声、写气图貌的连绵词,但在声音效果上与“间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在词义上指明了庾信暮年诗赋名满天下的卓越成就,也在声音上与上联的“萧瑟”形成强烈的对比,一改之前的凄厉、悲凉,而变得优柔、婉转,既表达了诗人对庾信晚年文学成就的崇慕之情,同时也寄寓了深沉的自我人格的坚守与对未来人生的自信。 三、唐诗声母运用规律之二——双声与叠韵的互相配合 双声与叠韵,本来就是汉语在构词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唐诗除了在诗句中连用双声之外,还经常配合叠韵词的使用,以进一步形成声韵谐合的音声之美,并以此达到声情相切的境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叠韵”,与前面所讨论的“双声”一样,指语言中连结在一起的两个汉字在韵母的构成上相似或相同。这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指那些语言学上所谓的单纯叠韵联绵词(如“窈窕”、“蹉跎”之类),同时也包括诸如“涕泗”、“寒山”之类的叠韵复合词,甚至像“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杜甫《秋兴八首》之五)中,与上联“南山”相对应的下联中的“汉间”二字,尽管在实际的语言中不一定都构成独立运用的语词结构,但由于它们之间音韵的蝉联,对诗歌的音律美感与情感表达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我们也将之看作叠韵。总而言之,只要是在声母或韵母的读音上相同或近似的诗语建构,都可以称作“双声”或“叠韵”。 双声与叠韵在音节的构成上,本身就具有一种声韵之美,而双声与叠韵的配合使用,对诗歌整体节奏与音律美感的形成,就更能起到加强作用。这是由于中古时期的汉语词汇,大多以单音节或双音节为主,而唐代的五七言诗基本上又是以两个音节为一个音步,所以双音节的双声或叠韵词汇刚好能各自构成一个音步,在实现自然谐和的音律美感的同时,又对诗歌音步的节奏性有所增强。对于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就已经谈过,他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13](P639)即是说,双声叠韵如果不是处在同一音步的位置,而是“隔字”或“离句”,则不利于诗歌音律节奏的形成。清人周春对刘勰的论述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双声隔字而每舛者,双声必连二字,若上下隔断,即非正双声。叠韵杂句而必睽者,叠韵亦必连二字,若杂于句中,即非正叠韵。双叠得宜,斯阴阳调合,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者,总指不单用也。”[14](P184)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唐代诗歌中的大部分正是借助于双声、叠韵与诗歌节奏的同步吻合,以及在声、韵上的这种“辘轳交往,逆鳞相比”的配合使用,从而巧妙地强化了诗歌语言内部的节奏和音律美感。宋人魏庆之就曾指出:“李群玉诗曰: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诘曲、崎岖,乃双声也。钩辀、格磔,乃叠韵也。”[15](P40)清人邓廷桢亦云:“义山《异俗》诗: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猪、都叠韵,獭以赖得声,古音在祭部,獭、祭亦叠韵也。下文: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点、对为双声,搜、求为叠韵,亦云密矣。……义山诗双声叠韵最多,人所易知,子美诗双声叠韵则融去迹象,尤为精妙,如: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细、写双声,匀、圆双声兼叠韵。”[16](PP.389-390)清人洪亮吉也曾指出杜诗语言上的这种特点:“唐诗人以杜子美为宗,其五七言近体,无一非双声叠韵也。”[17](P2)清人周春更是撰写了《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一书,专门阐明杜诗在语言上的这一特点,略举数例如下: 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春日江村》)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南极》)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宿府》)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秋兴八首》之五) 在这些诗例中,双声与叠韵有在一联上下句中的对用,也有在一句之中的连用,有单纯连绵词,也有复合词,形式多变,不拘一格。周春对杜诗中的这些双声叠韵及其运用方式展开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将之总结为“正格、借用格、广通格、对变格、散句不单用格、古诗四句内照应格”等多种类型,并称之“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14](P5)。后来王国维进一步指明:“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多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18](P34)前人关于双声、叠韵的这些论述,大体上来说是不错的,但进一步考察唐诗中的具体诗例时,我们发现有时双声与叠韵的安排,打破了原本固定的声律节奏,在诗句中分散开来,遥相呼应,也别有妙用,如李端的《听筝》: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这首诗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了丰富的双声与叠韵字。首先来看双声的配置:首句中的“粟”与次句中的“素”都是齿音心母字,属于同纽双声;次句中的“手”(齿音审母字)与三句中的“周”(齿音照母字),属于同类双声;再加上一个叠音词“时时”(齿音禅母字),本诗中一共有六个字都属于齿音的同类双声。其次,再来看看叠韵的使用:除韵脚“前、弦”二字押先韵外,“鸣筝”二字,在《广韵》中虽分属庚、耕二韵,但在唐代是同用的,因此是叠韵字;次句中的“玉”与三句中的“欲”,同属入声烛韵;二句中的“房”与三句中的“郎”,同属平声唐韵;二句中的“素”、三句中的“顾”以及末句中的“误”三字,同属去声暮韵;倘若再加上既双声又叠韵的“时时”,共计有十三个字运用了叠韵。在这首短小的绝句中,如此密集而错综地使用双声与叠韵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前呼后应的丰富音型的展示,对“筝鸣”之声作一种语言声韵上的相应模拟。正如黄永武先生所言:“本诗不仅在开端处用‘鸣、筝、金,三字拨动了筝响,录下了筝声,而这些双声叠韵字,遥隔呼应,成为和声,使整首诗竟像一条协奏的曲谱,充盈着音响的美。”[3](P191) 借用双声叠韵(包括叠音)在发音上所具有的参差错落、前后呼应的特点,来模拟一种音乐的听觉效果,几乎成为唐诗在语言技巧上的基本套路,白居易《琵琶行》中对琵琶之声的描摹就是一个显例,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每一句中都用到了叠音或双声叠韵词。再有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前二句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其中“昵昵、儿、尔”以及“女、汝、语、怨”诸字,或双声,或叠韵,或双声兼叠韵,读起来给人一种轻柔、圆滑而又十分和谐的感觉,与小儿女私语呢喃的情致十分吻合。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字在声母上没有一个是摩擦音或爆破音;在韵母上,除“相”字以外,也没有一个是开口呼的音强比较高的字。后二句说:“划然变轩昂,猛士赴敌场”,情景突变,语言在声韵上也随之而变。第一个字“划”,在发音上就来得非常突兀斩截;韵脚也由首二句闭口的上声韵转换为开口的平声阳韵,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而这与“猛士赴敌场”的豪情胜概也正相一致。 不管是与诗歌节奏的同步吻合,还是打破原有的节奏在诗歌中的分散妙用,双声与叠韵的配合使用,对唐诗音调的婉转铿锵、对偶的精工细巧,乃至声情的妙合无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前人对双声叠韵在语言形式、诗法技巧上费心甚多,而对于声情关系的探讨则用力稍浅。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将双声与叠韵的配合使用作为一种声律现象来研究,就不仅要探讨其在语言形式上的构成对诗歌音律美感的作用,而且还要深究其是如何借助于自身的音响节奏,而达到对事物之意态、人生之情感惟妙惟肖的象征与模拟。关于这一点,前面的论述其实已多有涉及,下面再举一例以进一步阐明。杜甫《野人送朱樱》一诗的颔联:“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关于此联,前引清人邓廷桢之语中即提到:“子美诗双声叠韵则融去迹象,尤为精妙,如: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细、写双声,匀、圆双声兼叠韵。”[16](PP.389-390)他的确看到了杜诗双声叠韵安排之精妙,至于诗人为何这样组织语词、搭配声韵,并没有进一步给予深入的解释。高友工、梅祖麟在《唐诗的魅力》一书中就曾说过:“如果不能有助于诗歌的欣赏,音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12](P4)同样,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津津乐道于杜甫诗中双声叠韵的“融去迹象”,而对其中所暗含的事物意态的描写、诗人情感的传达没有丝毫把握的话,这样的诗语解读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借助于前面屡次提到的声韵学知识,我们可以对这两组在一联诗语中对用的双声和叠韵词语,做一番细致的分析:“细”字,苏计切,属齿音心纽;“写”字,悉姐切,亦属齿音心纽,故而“细写”乃双声。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齿音心纽字多数都具有“细小分碎”的含义,在发音上又给人一种清厉的感觉。因此,同为齿音心纽的双声词“细写”,在这里不仅将西蜀樱桃颗粒细小、但筠笼溢满的意态写得极为贴切,而且还非常生动地刻画出杜甫将它们从一只筠笼倒入另一只筠笼之时内心的倍加珍爱与疼惜,后面的“愁仍破”三字也进一步点明。再看“匀”字,羊伦切,声属喻纽,韵在十八谆;“圆”字,王权切,声属为纽,韵在二仙。由于中古音中喻、为二纽不分,同属喉音,所以“匀圆”二字亦为双声;而谆韵与仙韵,在《广韵》中虽分属二韵,但音转最近,故而“匀圆”在双声之外又兼叠韵。“匀圆”二字叠韵,在发音上给人一种圆滚、滑动的感觉,用以描写倾泻而出的一笼樱桃,万红攒动,圆莹可爱,最是自然而贴切。所以黄永武品读此联说:“写樱桃芳润匀圆之状,摹写物状极巧肖。”[19](P65)经过这一番声韵学上的分析,我们才真正明白杜甫在诗歌语言上的“精妙”,“细写”与“匀圆”在语词构建上的好处,不简简单单在于“融去迹象”,而是借助于双声与叠韵的配合使用,在声韵效果上就把樱桃从筠笼里倾泻出来之时,那细小玲珑的样子给予了生动细腻的描摹,并且深刻地传达出诗人由衷的珍惜与惊喜之情。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汉字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在唐诗声母运用规律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双声”,即同一声纽字的叠用,以及它与“叠韵”词的互相配合,再加上双声叠韵的特殊形式——“叠字”的使用(因学界论述较多,故此不再赘言),则将这些因素集中组配起来,以形成一种节奏音响上的合力,不仅在摹声、状物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对情感的表达更具有一种突出与强调的作用。唐诗声母的运用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三种形式所建构而成的,它们不仅给唐诗带来了婉转铿锵的音律之美,而且还使得唐诗的对偶愈发的精工细巧。唐人在声母运用上的这种精雕细琢,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声情相切、摹景入神的艺术至境。标签:唐诗论文; 发音方法论文; 双声叠韵论文; 咏怀古迹五首论文; 读书论文; 秋兴八首论文; 萧瑟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