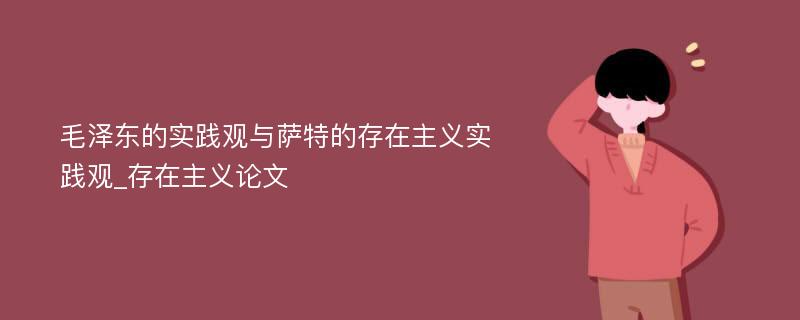
毛泽东实践观与萨特存在主义实践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存在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6—0080—06
一、萨特存在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分析
萨特曾经多次重申:存在主义就是一种行动的学说,“存在主义即是一种行动和卷入(involved)的伦理学”。(注:《存在主义》,纽约哲学丛书1947年版,第42页。)萨特认为,“人的唯一希望是他在他的行动内,行动是使人生活下来的唯一事情”。(注:《存在主义》,纽约哲学丛书1947年版,第42页。)因为单纯立足于行动,萨特拥有了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从而对整个世界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萨特说:“各派存在哲学也许只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存在不能归结为认知。”(注: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8页。)因而, 萨特的存在主义实质上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哲学以探讨认识为目的的模式。由此看来,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绝不能延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否则会误入歧途。
就知与行的关系来看,行有受制于知的一方面,所以单独考察行是难以实现的。但是为了单独考察行动,萨特首先对知即意识进行了现象学的处理。萨特一直认为,只有将意识虚无化,才能从?
绝对纯粹的意义上考察人的行动,由此所得出的才是真正关于行动规律的结论。
经过上述处理之后,萨特开始对行动的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即自由观。萨特说:“自由是我存在的要素”,“自由的计划是根本的,因为它就是我的存在”。(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455 页。)他认为自由等同于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则可还原为行动,或者说“做”。自由,必须在某种境遇中爆发,自由,就是去做(do),就是去行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萨特进一步强调自由是不被限制了,如果说它被限制,也只是被自由所限制——我的或他人的自由。萨特的上述观点确实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因为对待同一种环境和事实,相信有这种自由的人们和不相信有这种自由的人们行动起来是会有所不同的,而这种相信所包含和带来的精神力量也可能加入因果的链条,使局面得到改观。
在某种意义上,萨特也承认行动者是有意图的。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行动者要接受一个“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他唯一行动的条件,这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的东西,他缺少的东西。“事实上一旦我们把这种否定世界和它自身的力量归这于意识、一旦虚无构成确定一个目的的主要成分,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行动的独立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这行动者的自由”。(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436页。)因此,萨特主张的是“行动自律”。在他那里,人们自由选择行动,并不受动机和目的的制约,“动机仅仅是为了意识”,“原因不能决定行动”,“实际上动机和动力只是我们的计划所给予它的力量,所谓我的计划即是自由地产生有待于实现的目的和已知的行动。当我深思时,事情便已完结”。(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561页。)显然,萨特持有的是非理性主义的行动观。从本质上说,由于萨特的非理性主义行动观强调一个人的道德选择可以不经过思考,凭内心的意向,凭借本能便可以行事。这样的道德行为只能必然取消道德行为的客观标准。
萨特的行动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张行动就意味着选择。萨特认为,“对人的存在就是选择自己,它不接受从外面和内部来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永远地选择自己,否则就要变成纯粹的自在而非自为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这选择既具体又本体,“自为的选择总是在一个不可比的独特的具体境遇中的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本体论意义也是真的”。(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598页。)选择与有意识是同一的, 一个人要选择必须是有意识的,一个人要有意识必须选择。所以,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了不选择。因此,萨特主张的行动决不是那种躬行某种规范体系的道德践履,不是那种终生恪守一原则来砥砺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修养和磨炼,而是不断的选择和创造。这种选择既不遵循任何规律,也不遵守任何规范。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循规蹈矩已违背了自由。
二、毛泽东实践观与萨特存在主义实践观比较
不可否认,毛泽东实践观与萨特存在主义实践观之间有着某些相同的地方,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彻底否认“命定论”的存在,强调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环境。
如前所述,萨特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强调行动就意味着选择,认为自由是“人行动的第一条件”。萨特曾说:“假如我对于一种不仅涉及自己,而且也涉及全人类的选择,必须担负起责任,那末,即使没有先天的价值来决定我们的选择,那也不能任意妄为。”(注:W·考夫曼:《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页。 )他认为,一个人在行动时不仅要向自己负责,而且要向全人类负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把自己与这个责任脱开哪怕一分钟,正是这种巨大的责任感使人深深地陷入烦恼之中,就仿佛他每做一事,整个人类都用两眼盯住一般。因为我是孤独的,我是被抛弃的,没有上帝,或者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所以我对我行动的责任是不可逃脱的,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或他人,而必须自己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巨大重负。当然,我之所以要负起我的责任,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我是自由的,我既不受上帝的支配,也不受任何外部事物或内在本性决定,那伴同人的本质因素的必然联系只能在一个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自由都在它的存在中向全人类的存在负责。(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519页。)因此,萨特坚决反对“命定论”,他强调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选择中确定自己的行为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是绝对自由的,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甚至明确提出在人决定自己的行为的过程中“上帝死了”,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反抗环境的压迫。
就毛泽东对实践所持的观点来看,毛泽东一直积极主张“人定胜天”,他对人战胜自然和社会中出现的艰难险阻的能力充满信心。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勇斗的思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注: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以不断运动、 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反对“命定论”的信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时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272 -273页。 )这一思想更进一步说明了毛泽东主张人不是消级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安排,而是积极改变环境和改变自我。在他看来,人拥有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权力和能力。毛泽东还说道:“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实行自我改造的阶级,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注: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二,都强调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力提倡一种责任型的行动观。
萨特认为自由是“人行动的第一条件”,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又主张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责任型的行动观。萨特说:“世间并无人类本性”、“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生活,在你未出生之前,是一无所有。这时,给予生活的一种意义,乃是你的责任。所谓价值,也是你所挑选的意义。”在他看来,人是自己造就自己,人的生活的意义是由人自身所赋予的,人是自己行为意义的承担者,人对自己行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毛泽东那里,也非常重视人对自己行为所应承担的那份责任。他通过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勇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勇于去认识客观事物,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培养自己的反省意识等等,使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应担负的那份责任。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曾说:“因此,《实践论》克服了以前只考虑到集团在历史上被制约性、而回避个人在整个实践中的责任的想法,开辟了一条纠正把作风中表现出来的一切自觉的个人责任全部推给集团和‘无错的党’的倾向的道路。”(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高度重视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还在于他科学地解决了在集体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即个人推卸责任的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专门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以“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全党同志履行责任的自觉性提高,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认识了毛泽东实践观与萨特存在主义实践观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的同时,我们必须对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有所了解。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它们对行动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萨特那里,行动的意义是为了行动而行动,是为了自由而行动。他曾说道:“除行动之外,无所谓现实”,真理虽然无须实践来检验,但却要在行动中而得以显现。如前所述,存在主义就是一种行动学说,萨特强调行动,反对清静无为。因此,在一般人看来,萨特的行动观绝对是有为主义行动观。但是美国学者W ·考夫曼在《存在主义》一书中却写道:“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诱导安于一种绝对的无为主义(quietism)。因为如果每一条解决事物之道被阻断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视在这世界上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最后就会走到一种瞑想的哲学里去。而更甚的是,由于瞑想是种奢侈,因此我们的学说就不过是另一种布尔乔亚的哲学而已。在这方面,是特别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指责。”(注:W·考夫曼:《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1页。)因而,将存在主义简单地视为有为主义行动观是有失偏颇的,透过它的有为主义外表,人们应当认清它的绝对的无为主义的本质。
的确,在萨特那里,极端的主观主义导致了极端的虚无主义,有为主义最终变成了无为主义。萨特既然认为行动就意味着选择,并且选择是无章可循的,于是这里立即出现了一个矛盾:既然人没有任何标准可以遵循,他又怎么样能进行选择呢?如果他无法选择,自由又从何谈起呢?其实萨特本人也看出,这种没有任何选择依据的选择自由是一种难堪的矛盾,因而怀着绝望的心情写道:“自由即是自己的存在的选择。这个选择是荒谬的。”自由不是礼品,而是负担。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一切,但偏偏这种选择的自由不是人所自由地选择的。“事实上,我们就是进行选择的自由,而并非选择自由状态。我们被判决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注:萨特:《存在与虚无》,H·E·巴恩斯英译本,1957年版,导论,第XXXV页,第558—565页。)他还说,我们是被抛入自由之中。自由成了人的宿命,人的整个存在都不能摆脱这种自由,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放弃自由也是他一种自由。因此,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萨特的有为主义行动观却使人们害怕选择、自由和行动,有为主义最终变成无为主义。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人的行动的意义有三层:第一层是,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第二层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第三层是,为了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由。这样一来,人的行动的意义在毛泽东那里实际上被解剖开来,他在强调人的行动具有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意义的同时,把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由看作是人的行动的最高境界。进言之,毛泽东还认为人是在不断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由的。他说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单纯从自由的角度去理解行动、实践的意义,他所强调的是自由并非是人的行动的存在形式本身,自由是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中去获得的。单纯地强调自由是“行动的第一条件”,使得萨特陷入了矛盾困境,致使他由有为主义者变成了无为主义者;一种积极的行动哲学,在他手里最终演变成一种消极的行动哲学。但是由于毛泽东科学地理解了行动的意义,因此,毛泽东的行动哲学一直是积极的行动哲学,它不断地鼓励着中国人民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另一个方面是,对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理解不同。
萨特提倡的是绝对自由的行动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西方哲学史上通常占优势地位的决定论的哲学传统的一种抗议和反动。但是这种行动观毕竟是错误的,因为它彻底排除了客观因素对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萨特曾说了一个惊人的故事来解释他的立场。飞机场的地勤人员中有一个黑人,因为是黑人而被阻止成为飞行员。为了对种屈辱的歧视行为表示抗议,他偷了一架飞机,企图飞越拉芒什海峡。当然,由于没有任何飞行经验,他把飞机撞毁了,自己也丧了命。根据萨特的说法,这种悲惨的和绝望的无益举动是“解放的行动”,他的死亡“同时意味着他的人民的不可能的反抗,所以它也意味着他同殖民者的真正关系,意味着他的命运和抵抗的彻底普遍性,最后,意味着这个人的内心的计划——他对一种短暂的闪光的自由的选择,即对赴死的自由的”。(注:参见[英]约翰·霍夫曼:《实践派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不言而喻, 萨特确信自由是必然的对立面和任何决定论的死敌,它们之间是有你无我的关系。但客观地说,他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行动观只是一种书斋式的论调,人的行动受制于客观因素这一客观事实,是无法借助于主观想象、主观愿望就可否认的。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批判中国的主观主义者时就提到了人的行动是受制于客观因素这一论断,他明确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人要吃饭”、“打仗要死人”。这里,他不仅抓住了教条主义的要害,而且明白无误地点明了凡是不重视客观规律,否认人的行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就会陷入困境,遭受挫折,受到惩罚。在毛泽东看来,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并不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人们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人们必须承认决定论的存在。毛泽东提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此,他明确指明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在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过程中获得的;如果不对必然加以认识和对世界加以改造,要想获得自由是绝不可能的。
第三个方面是,对历史实践主体的理解不同。
萨特是个体主义实践观的代表人物,他刻意强调个体实践的存在是具有较典型的意义的。萨特认为个人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个体实践”(Person-Paxis)是历史人学的起点,只有从此入手, 才能把握辩证理性的运动。(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2页。)通过假借修正唯物史观的名义, 萨特极力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应当是个人的“实践”,只有把存在主义的“实存”思想合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才能说明“人们自己创造着他们的历史,但是在一种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条件之中进行创造的”(恩格斯语)。(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1年版,第466页。)因而, 为了坚持以个人的实践作为其历史人学的起点和对象,萨特剪栽了法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若干史料,仿造了一种近似于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三段式:把从“构成辩证法(个人的实践)-反辩证法(群集)-被构成辩证法(共同实践)”的逻辑递嬗,作为历史辩证法运动的基本程序。当然,尽管萨特的历史观点在总体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的剖析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个体实践作为代表人类实践向个体独自行动方向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发展拥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在关于历史实践的主体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强调“联合的力量”即集体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他明确将利用人民群众联合的力量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胜的法宝,并极力阐明应该围绕集体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毛泽东一贯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明确指出: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又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因此,他十分坚信离开组织起来的群众,中国革命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毛泽东并不否认个人及其实践在集体实践中的作用,但在建国后,他却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正当的个体实践(如勤劳致富活动等)在集体实践中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使个人的行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农民种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曾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予以坚决取缔,致使农民从事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