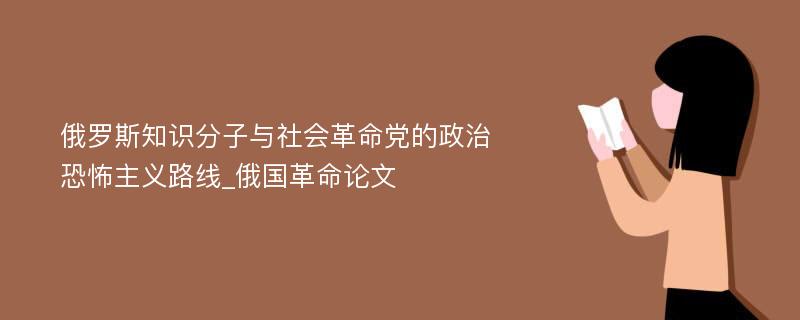
俄国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政治恐怖主义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革命党论文,恐怖主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4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21-(14)
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俄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独特的公共肖像。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和意识;他们同情劳动人民,怀有“为民请命”的永恒情结;他们善于总结和反思,具有难得的批判精神。这些知识分子的公共特质深刻影响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在漫长的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为了改善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推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过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命题,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近代俄国社会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恐怖主义是近代俄国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探索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失败的理论探索和行动尝试。社会革命党是近代俄国主要的民粹主义团体,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在策略上继承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手段。政治恐怖是社会革命党政治策略的主要特征。本文以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为切入点,根据原始档案资料考察近代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恐怖主义理论的思考和恐怖活动实践;探讨政治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常革命手段的效能问题;从政治文化视角,对近代俄国政治恐怖主义的失败进行探源。
一、知识分子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路线选择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并于1873-1874年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他们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鼓动农民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民粹派的名称由此而来。这是民粹派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拉夫罗夫(П.Л.Лавров)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将这次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人们不仅在努力实现某个实际目标,同时还在努力满足个人道德净化的深层需求。”①热情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次运动,到农村亲眼看到一直以来同情和感谢的人民,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他们以小组形式进行活动,通过印发传单,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社会的不平等,鼓动农民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由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基础薄弱,民粹主义者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再加上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此后,民粹主义者放弃宣传鼓动的活动方式,为尽快实现社会革命转而选择了激进的革命方式,慷慨激昂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道路。
1876年10月,“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成立。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米哈依洛夫(A.Д.Михайлов)、纳坦松(A.A.Натансон)等人成为该组织领导人。他们组织了各种宣传及罢工活动。“土地与自由社”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主张把全部土地平分给农民,村社应有完全的自主权。由于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土地与自由社”于1879年分裂成“黑土平分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л)和“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二者继承“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并在内容上进一步完善。“黑土平分社”主张进行宣传,民意党则转向了恐怖。
民意党将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发展了“土地与自由社”所奠定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民意党将推翻专制制度、将政权还给人民确立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在1878-1879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②。1881年3月13日(俄历3月1日),经过半年的密谋和跟踪,民意党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此举非但没有实现民意党人唤起人民觉醒和推翻沙皇制度的愿望,反而带来沙皇政府更加残酷的镇压,民意党组织遭到极大削弱,党的主要活动家先后被捕甚至被处死,执行委员会遭到严重摧残。1884年10月,民意党停止活动,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至此陷入沉寂。
19世纪90年代初期,民粹派运动复兴肇始。侨居国外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开始反思民意党的失败原因,总结民意党时期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和活动经验,宣传民粹主义中的激进思想和政治恐怖主义。曾被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В.М.Чернов)视为自己的老师、后来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成为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日特罗夫斯基(Х.О.Житловский)认为,“恐怖是民意党所有的纲领、目标、创举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它使民意党名声大振、强大并富有感召力”。③“民意党的恐怖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它没能成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恐怖主义。”④民粹派元老布尔采夫(В.Л.Бурцев)⑤认为,1879-1881年民意党的纲领已不合时宜,但民意党却留下了不变的信条——政治恐怖。“政治恐怖对于我们的国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影响是如此深远,革命者所有的意见分歧在恐怖面前都应该消失。重要的是,政治恐怖应成为确立和调整各小组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各小组应一致认可政治恐怖的重大意义。所有的政治恐怖卫士应不顾在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将自己视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无论如何要联合成一个政治恐怖同盟。”⑥
随着民粹派运动的复兴,一些宣称自己是民意党继承人的秘密民粹派小组逐渐涌现出来⑦。“社会革命者联盟”⑧是俄国第一个正式使用“社会革命”这一名称的秘密民粹派组织。该联盟的纲领《我们的任务》⑨(Наши задачи)在最后一部分“革命斗争手段:恐怖活动与群众革命斗争”中(Средств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масс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орьба)集中论述了革命政党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特殊作用。纲领指出,专制制度有百万军队保护,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创建群众性的社会革命政党。因此,“应当先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这一任务只能以‘社会革命党’之名完成”⑩。关于政治恐怖的作用,纲领是这样总结的:“政治恐怖是该政党最有力的斗争武器之一,也是指导过去和现今革命的有效手段。政治恐怖可以归结为消灭当下最反动、最有影响力的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物。系统的恐怖(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ррор)联合其他的群众斗争方式(工厂的、农业的暴动、游行等)瓦解敌人,这些斗争方式只有在恐怖中才能获得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在战胜专制制度并获得完全的政治自由后,恐怖活动方可停止。恐怖活动除了具有涣散和瓦解敌人的主要作用,还具有宣传鼓动的作用。……最后,恐怖活动还是所有地下革命政党保护和捍卫组织、防止奸细叛变破坏的手段。”(11)
1901年夏,在巴黎的俄国旧民粹派小组出版了第一期《俄国革命通报》(12)(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这正是后来的社会革命党机关报《革命俄罗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的前身。《俄国革命通报》的纲领开篇写道:“我们自认为是民意党思想上的继承者。”(13)对于恐怖的态度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忠实于执行委员会的传统,我们将恐怖视为必要手段。……我们认为,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系统的恐怖才是合理的。我们铭记,民意党的恐怖活动符合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能够完成尚未完成的推翻专制统治的历史任务,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14)
1902年1月,《革命俄罗斯》(15)(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第3期刊登通告,宣布社会革命党成立。这一期《革命俄罗斯》刊登了一篇题为《紧急任务》(Неотложная задача)的文章。文中关于恐怖的措辞十分含糊:“关于恐怖这一点,可以并应该以某种表达方式列入党的共同纲领……在承认恐怖斗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原则下,当周围的条件成熟时,党保留自己着手进行恐怖斗争的权利。”(16)三个月后,即1902年4月2日,战斗队成员巴尔马舍夫(С.В.Балмашев)刺杀了内务大臣西皮雅金(Д.С.Сипягин)。此后,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刊登了切尔诺夫写的题为《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二》(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无论党的教条主义者有多怀疑、多反对这一斗争方式,恐怖的生命力都将战胜他们对恐怖的成见。实际上,恐怖活动并不是简单的‘需要’或‘合理’,而是必要和必然。”(17)。《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在社会革命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社会革命党将政治恐怖主义纳入党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动员
社会革命党将政治恐怖作为争取政治自由、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斗争工具,必然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托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撑。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思想家在实践中创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学说,为政治恐怖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宣传鼓动。他们首先需对政治恐怖策略和一系列政治恐怖活动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辩护,一方面强调作为政治工具的暗杀不同于一般的杀戮行为,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消除社会民众对政治恐怖的心理恐惧和排斥,唤起革命者对政治恐怖的向往。
1、以武抗暴强调政治恐怖的合理性
社会革命党认为,在沙皇专制制度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并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恐怖是人民自卫的武器和安全防御体系。为了强化政治暗杀的特殊性,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以“武力”(сила)和“暴力”(насилие)的语义辨析作为切入点,回避了政治恐怖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宣传政治恐怖作为政治工具的合理性。
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政府对人民和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是“暴力”,革命者和被压迫人民反抗专制统治是“武力”,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武力是对个人及其权利的正当捍卫;而暴力是对个人及其权利的侵犯。武力完全是同恶势力斗争的手段;暴力则永远支持并服务于恶势力;应该以武力对抗暴力。1904年,第46期《革命俄罗斯》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革命斗争中的武力和暴力的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ле и насилии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е)。该文章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便是:以武力对抗暴力(18)。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恐怖组织——“战斗队”的领导格尔舒尼(Γ.А.Γершуни)宣称,“党难以忍受政府对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动用暴力,在这种压力下,党不得不以暴抗暴。……在社会舆论高涨的时代,反动势力的打击只会导致个人的绝望的顺从。坚定不移的反抗是必然的……”(19)
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企图除去政治恐怖的“破坏性”和“非法性”标签,用“合理性”和“必要性”来粉饰政治恐怖主义。这种粉饰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可以用来激发民众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革命激情。但是片刻激情过后,尤其是当革命的力量被专制势力打压削弱之后,人们看到的是这种理论对于改变现实的无助以及对于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灵的持续破坏。粉饰的外衣终究会脱落,理论的光环注定会消散。没有了粉饰的政治恐怖主义终将彻底丧失民心,退出历史舞台。
2、以“使命”强化的革命正义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认为,政治恐怖担负着执行人民和社会审判的使命。切尔诺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恐怖的一切意义在于,它要执行一个不成文的但却无可争议的人民和社会良心的审判。”(20)
1907年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政治恐怖策略的存废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争论焦点。格尔舒尼在这次临时会议上阐释了政治恐怖的意义。具体发言内容如下:“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不是对掌权者肉体上的杀戮和清除。恐怖对我们而言有另外的意义……当社会的愤怒和仇恨集中到某一类的政府代理人头上,不论职位的高低,当这些代理人成为独裁和暴力的象征,当他的行为对社会财富构成危害,在任用期间没有任何办法排除他所造成的危害,当他的存在成为对社会良心的侮辱,最后一扇门向恐怖打开,它为忧心忡忡的自觉的公民执行判决。当炸弹爆炸时,人们长出一口气。那时,所有人将明白,人民的审判终结了!无需任何解释,任何传单。国家期盼着这一审判,……只有杀戮能解救百姓。”(21)
格尔舒尼认为,当权者是独裁和暴力的象征,是对社会良心的侮辱,暗杀当权者的政治恐怖行为是在执行人民的审判,是在解救百姓。这种以“使命”装饰政治恐怖主义、遮掩恐怖主义的破坏性本质的理论,为革命者的心理塑造了强烈的正义感。但是,这种丧失科学性的非理性宣传势必导致政治恐怖活动的失控,逐渐偏离党最初设定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革命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3、以革命英雄主义动员革命者
社会革命党认为,执行政治恐怖任务的革命者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必须勇于承担恐怖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们借助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为政治恐怖制造特殊的光环。
津齐诺夫(В.М.Зензинов)既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理论家,也是“战斗队”的成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年轻的康德(Kant)哲学的信徒,我们认为人是最终目的,社会性的服务造就了个人的自我价值,对我们而言,恐怖问题是最危险、最悲惨、最折磨人的。……我们去暗杀是因为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可能让我们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纲领,为国为民造福。倘若在某种程度不能为暗杀辩解,那么唯一可行的就是主动地救赎,这必然会导致个人牺牲。从道德哲学的观点看,暗杀行为同时也应该是自我牺牲的行为。”(22)津齐诺夫认识到恐怖的一些负面效应,但却从人生观的角度用道德哲学论证了革命者自我牺牲的必然性和崇高性。
在赋予革命者自我牺牲的荣誉感和政治复仇的神圣使命感的同时,社会革命党还极力营造对政治恐怖顶礼膜拜的神秘氛围。社会革命党关于政治恐怖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中的一段文字渗透着一种宗教式的痴迷。“恐怖斗争能够提高周围人眼中的革命政党的威信,证明革命的社会主义拥有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尤其满怀奋不顾身的热情,渴望建立功勋,从而提升了这些真正的伟大烈士们的正义,使他们能够高兴地为(政治恐怖的)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23)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Б.И.Николаевский)的大量信件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英雄的个人”(героические одиночки)和“英雄突击队”(героические ударные группы)(24)。1907年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格尔舒尼在阐释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观时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убийца—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героем)(25)。
《革命思想》(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мысль)(26)第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的象征”(Mementomori)的文章,文中写道:“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俄国革命者手中……只有英雄的行动,只有壮士死前所唱的歌颂永垂不朽的理想之曲能够鼓舞群众参加战斗。这些令人敬畏的复仇者是即将出现的新人类雏形。对他们而言,‘我想’和‘我创造’是融合的。‘我’的涵义就是创造新的价值。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我’与世界是融合的。人们是带着对这种英雄的价值观就义的”(27)。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将政治恐怖视为政府残酷镇压下合理的政治复仇;自我牺牲是革命者执行政治恐怖任务后自我救赎的途径,是神圣而光荣的;革命者在政治恐怖活动中体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这种理论思想渗透着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式的痴迷,缺乏科学理性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社会革命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4、以群众运动为政治恐怖主义造势
受无产阶级工农运动的影响,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将群众运动纳入到党的工作范围,提出群众运动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理论,并着重强调:政治恐怖并不是要取代群众运动,而是要以服务为目的,对群众运动进行“补充”和“强化”,从而保护群众自身的权利,争取更多的政治自由。
在《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中,切尔诺夫论证了政治恐怖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恐怖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斗争体系,并非借助自己内部的力量就会必然冲破敌人的阻抗,使其投降……对我们而言,恐怖只是我们的部分革命武装所掌握的众多斗争方式之一。……恐怖应该与所有爱国主义群众斗争方式重新组织成一个体系,自然而合理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恐怖只是一种手段形式,只是一种斗争的技术方法,只有和其他斗争方式相互配合、协同运作发挥效用,才能产生我们所期望的影响”(28)。恐怖与其他斗争方式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但“绝对不是替代,我们只是想通过战斗先锋队的勇敢出击和对敌人心腹的有力打击补充和强化群众斗争……我们反对一切片面的恐怖主义特殊论。”(29)
“战斗队”成员杜列波夫(Егор Дулебов)暗杀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之后,切尔诺夫撰写《恐怖与群众运动》(Террор и массовое движение),专门探讨恐怖主义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在《革命俄罗斯》上,文中提到,“恐怖应该成为,甚至不可能不成为一种辅助的斗争方式;……恐怖行动应该与群众运动联得更加紧密,以群众运动的需要为基础并对其进行补充,在群众中唤起革命情绪,从而推动群众斗争。”(30)切尔诺夫认为,民意党时代的恐怖主义者的不幸在于没有支持大量的工人运动,但对社会革命党而言,工人运动“现在就有并日益高涨”(31)。
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们重新审视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政治恐怖的新任务,即: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恐怖主义游击战(массовая партизанск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1905年10月出版的《革命俄罗斯》(第59期)的社论《战斗时刻》(Боевой момент)明确指出:可以集合大批手中有武器的民众发动进攻,可以调动勇士对反动势力的台柱进行恐怖袭击,可以开展全线的群众性的恐怖主义游击战。1907年7月,民粹派元老柴科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写信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提议由埋伏在山间丛林中的流动的“匪帮”(банды)开展游击战(32)。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企图在政治恐怖与群众运动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恐怖发展群众运动,补充并加强革命力量;工农群众反过来积极参与政治恐怖活动促进政治恐怖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恐怖活动的成功实施,最终实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目标。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以群众运动作幌子,为政治恐怖主义造势,扩大其社会影响。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没有认识到政治恐怖作为一种革命手段的特殊性和政治效能的有限性,造成党在发展路线的制定中出现偏差,与党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严重误导了党的政治发展方向。
三、俄国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政治恐怖主义实践
在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和动员之下,“个人恐怖”(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террор)成为社会革命党策略的主要特征。社会革命党继承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手段,宣称政治暗杀是有效的革命手段,不仅可以威胁沙皇政府,迫使其进行改革;而且可以鼓动和唤醒社会、动员革命力量。1902年4月末,恐怖策略被正式列入党纲。同年,社会革命党还成立了恐怖主义组织——“战斗队”(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该组织购买武器,组建有针对性的战斗小分队,其行动不受党中央的指挥,独立执行暗杀决定。在1902-1907年间,社会革命党以暗杀(покушения)、爆炸(бомбометания)、政治性剥夺(грабежа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мотивам)、武装进攻(вооруженные нападения)和敲诈勒索(похищения,вымогательства и шантажа)为手段,制造了大量恐怖事件。他们特别推崇暗杀把持重权、极端反动的国务活动家的中央恐怖活动(центральный террор),并在实践中秘密策划并成功实施了多起对彼得堡和莫斯科政府领导的暗杀,掀起了俄国政治恐怖活动的高潮。据统计,1905-1907年间发生的恐怖行动中,有78.2%是由社会革命党完成的(33)。社会革命党实施的政治恐怖活动的涉及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会革命党191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02年到1911年(包括1911年),总共实施了213次恐怖活动(34)
在众多从事政治恐怖活动的革命者当中,不乏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革命家。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创始者,被称为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红色教父”(35)的格尔舒尼(Г.A.Гершуни)。
格尔舒尼(1870-1908),犹太人,化学家、细菌学家,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社会革命党恐怖小组先锋队“战斗队”(Ъ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的创建者。在警察局眼中,格尔舒尼是“恐怖艺术家”(артист террора)。在激进派眼中,格尔舒尼是“革命猛虎”(тигр революции)(36)。他在组织政治恐怖活动和挑选干部方面,对“战斗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02年5月,“战斗队”正式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构。“战斗队”在格尔舒尼领导期间共进行了5次恐怖活动:1902年2次,1903年3次(37)。
1902年4月2日,格尔舒尼成功策划了对内务大臣西皮雅金的暗杀。这是“战斗队”首次公开进行的政治恐怖活动。此次恐怖活动取得成功后,格尔舒尼迅速着手准备下一个政治恐怖活动计划:在西皮雅金的葬礼期间暗杀极端保守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由于执行者的临时失误,此次恐怖行动以失败告终。同年7月20日,由切尔诺夫挑选的木工卡丘拉(Фома Качура)实施了对哈尔科夫省长奥博连斯基的暗杀。此次行动虽然没有击毙省长,但省长和身边的警察局局长均被射伤(38)。1903年3月10日,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下令在兹拉托乌斯托(Златоусто)对不满工厂制度的工人进行扫射,打死69人,打伤250人。1903年5月6日,格尔舒尼安排铁路工人杜列波夫成功完成了对博格丹诺维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的暗杀。
继格尔舒尼之后,又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充当了战斗组织的领导。萨文科夫(1879-1925)是社会革命党著名理论家、活动家,同时也是作家,著有中篇小说《白马》(Конь бледный)和长篇小说《未曾发生的事》(То,чего не было)。萨文科夫出身世袭贵族,父亲是波兰的法官。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因参加学生动乱被开除。1903年5月,萨文科夫负责组织和领导战斗组织。上任后,他更换了一套全新的组织成员,在对具体恐怖行动的周密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与了对内务大臣普列维、谢尔盖·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 A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内务大臣杜尔诺夫(П.Н.Дурнов)、莫斯科省长杜巴索夫(Ф.В.Дубасов)等重要人物的暗杀行动。
1905年2月4日,萨文科夫派其密友卡里亚耶夫执行了对莫斯科省长谢尔盖·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暗杀计划。萨文科夫认为大公应对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Кровав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事件负主要责任。按照萨文科夫部署的行动计划,卡里亚耶夫向大公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大公当场被炸死,马车夫和“战斗队”成员身负重伤(39)。同年5月10日,卡里亚耶夫被执行绞刑(40)。
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1902-1911年间社会革命党所从事恐怖活动27人中,有20人是女性,均来自知识分子阶层(41)。社会革命党的44名女性革命家当中,11人受过高等教育,23人受过中等教育,6人只受过家庭教育,3人只受过初等教育。这些女性革命家中有9名老师,8名大学生(42)。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为她们提供了难得的受教育机会;贵族出身又能够使她们在接触穷苦的农民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强烈地向往社会公平;而较高的教育水平为他们阅读和理解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著作中蕴含的革命思想,为她们革命理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有助于形成更高的政治觉悟。
社会革命党战斗队的女性成员伊万诺夫斯卡娅·沃洛申科(Ивановская-Волошенко)(1853-1935),出生在图拉州一个穷苦的乡村牧师的家庭,幼年丧母。在一位十二月党人的资助下,她和妹妹得以就读于图拉州的一所宗教学校。1871-1873年,伊万诺夫斯卡娅去彼得堡,在著名的阿拉钦斯基女子讲习班学习,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她曾试图进行革命宣传,但迫于沙皇政府的抓捕浪潮,最终转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积极加入民意党。她先是在彼得堡一处秘密活动寓所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以掩护革命活动,后来又到民意党印刷厂工作。1883年,民意党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17人诉讼案受审,伊万诺夫斯卡娅被判死刑,后改服终身苦役。1904年7月15日,伊万诺夫斯卡娅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对内务大臣普列维(В.К.Плеве)实施的暗杀行动。一名恐怖分子跑向普列维乘坐的轿式马车投掷炸弹,普列维当场殒命。
亚历山德拉·阿多丽福弗娜·伊兹马依洛维奇(Aлександра Aдольфовна Измайлович)(1878-1941)出身贵族,190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实施对明斯克警察局局长的暗杀活动中,她当场将恐怖袭击对象射伤,被判11年监禁。
另一位社会革命党史上的传奇女性是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A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1941)。她出身贵族,中学辍学,曾担任省贵族会议的管理员。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组织战斗队,1月16日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Ъорисоглебск)车站射伤省参赞卢热诺夫斯基(Γ.Н.Луженовский)。此人曾因残酷镇压农民骚动成为社会革命党等组织袭击的目标。斯皮里多诺娃最终被莫斯科军事法院判处绞刑,后以终身苦役代替,被关押在坦波夫(Тамбов)市的一所监狱。十月革命后,她于1918年7月6日因积极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被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庭判处斯皮里多诺娃一年监禁,不久获特赦。此后伴随她的便是无休止的抓捕和流放。斯皮里多诺娃曾被流放萨马拉和乌法。后来,她放弃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И.A.Майоров)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夫妇二人被执行枪决。
有“社会革命党恐怖之星”之称的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比岑科(Aнастасия Aлексеевна Биценко)(1875-1938)在社会革命党中也有很高的地位。比岑科出身农民,中学毕业后在师范训练班学习。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先后在斯摩棱斯克(1902-1903年)、彼得堡(1903-1904年)和莫斯科(1905年)工作。1922年加入战斗队。同年11月22日,她在一次恐怖行动中将残酷镇压萨拉托夫省农民骚动的省长萨哈罗夫(B.B.Саxаров)当场击毙。比岑科被判死刑,后执行无期苦役。
四、知识分子情结与社会革命党政治恐怖主义路线的失败
知识分子作为俄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忠诚地扮演着“民族良心”的角色,对俄国人民怀有特殊情结。他们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热爱改变人民命运的解放事业,甚至不惜为人民自我牺牲。在一些革命者心中,人民和上帝具有同等地位。大批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不惜牺牲个人幸福和利益,完成了从社会上层到极端激进的社会革命者的“社会位移”。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以“为民请命”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试图代替人民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甚至从事最危险的、但在他们看来可以作为革命事业的政治恐怖主义。
然而在近代俄国,政治恐怖是一种暴力革命的非常手段。当社会处于无秩序的动荡时期,革命者通过刺杀、爆炸等极端手段制造恐惧,以相对来说最小的人力物力为代价,直接打击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代表,从而引起社会的震动和恐慌,威胁统治者。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角度看,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活动只是借助革命力量的高涨迫使沙皇专制政府作出暂时而有限的政治妥协。这种行为不但没能缓解沙皇专制政府对革命的镇压,反而使其变本加厉,结果适得其反。因此,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是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革命政党和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面对俄国落后的政治和经济现状,探索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没有认识到恐怖主义反人性、反社会的本质,企图以革命和正义来粉饰政治恐怖主义的非法性、犯罪性、暴力性、破坏性等特点,片面而偏激地宣传政治恐怖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向善耻恶的自然法。在理论上出现的认识偏差和局限导致社会革命党选择了错误的革命手段,并严重颠倒了政治恐怖与革命的关系,将本为革命非常手段的政治恐怖视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变成了为恐怖而恐怖,甚至不顾时局的变化和民心所向,坚持政治恐怖策略。社会革命党采取的革命手段本身与革命目标南辕北辙,又错误地将革命手段当成目的强行推行,这是政治恐怖主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俄国300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得以成型并且逐步稳定。在这个权力构架中,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受到严格控制,致使俄国社会结构发展缓慢。广大农奴处于社会等级的最下层,他们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最大,但在政治、经济、司法上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专制制度的长期运行和知识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广大农民形成了稳定的顺从型政治心理。他们热爱沙皇,从不反对沙皇,对于自己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剥削和压迫中的责任毫无认识。这种“政治自觉”的缺失,从根本上决定了广大农民无法担当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领导者。而城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才伴随着迟到的工业现代化而出现,年轻的政治力量尚不足以独立地诉诸本阶级的政治要求。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稳定的顺从型政治文化和有能力组织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抗争的社会阶层的缺失,促使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民请命”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试图代替人民与专制制度斗争。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走政治恐怖主义路线的社会驱使力量,同时也是近代俄国革命在斗争主体的选择上遭遇的困境。
再次,激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没有认清当时的俄国国情,过低地估计了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根基,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素养和革命力量,以及政治恐怖主义的历史功效。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家将沙皇专制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皇族后裔、政府的奸细以及所有专制政府的同谋者、帮凶统统列入政治恐怖打击的对象范围之内,幻想只要惩治和铲除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就能引起政府的组织混乱,消灭专制制度。但是,专制主义在俄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推翻根深蒂固的沙皇专制制度并不是只需对其统治者进行肉体上的消灭那么简单。人民对于自己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政治角色、决策过程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社会各阶层对于自己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剥削和压迫中的责任亦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政治恐怖可以消灭沙皇专制政府反动代表人物的肉体,却无法根除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本身;可以暂时满足人们的复仇和宣泄愿望,却无法激发人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自觉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头脑中的非理性和宗教式的狂热退去之后,在沙皇专制政治文化的强力作用之下,人民自然又回到专制制度的既定轨道中来。
尽管传统的知识分子情结催生了近代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美好的革命动机,但是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政治思维出现的偏差,造成社会革命党在政治路线选择和执行上出现错误。正是这种错误的政治思维所导致的错误惯性断送了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生命。但是,一种政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并未使革命停下脚步,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仍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注释:
①Ричард Стайтс.Жен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Феминизм,нигилизм и болюшевизм 1860-1930.М.,2004,С.199.
②其中包括:女革命家查苏利奇(В.И.Засулич)刺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Ф.Ф.Трепов),克拉夫钦斯基(С.М.Кравичинский)刺杀宪兵队长梅津佐夫(Н.И.Мезенцов)等事件。
③Григорович С.(Житловский Х.О.).Социализм и борьба 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воботу.Лондон,1898,С.58.Цит.по: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13.
④Григорович С.(Житловский Х.О.).Указ.соч.С.62.Цит.по: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16.
⑤布尔采夫是首批后民粹派小组(пост-народоволь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之一——“社会联邦制拥护者”(социалисты-федералисты)成员。
⑥Будницки 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ХIХ-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25.
⑦当时出现的秘密民粹派小组有:“旧民意党人小组”(Группа старых 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社会革命者联盟”(Союз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南方社会革命党(Южная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俄国政治解放工党(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农业社会主义同盟(Aграр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га)、社会革命党农业联盟(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等。
⑧“俄国社会革命者联盟”1894-1896年成立于萨拉托夫,随后其重心转移至莫斯科。在彼得堡、雅罗斯拉夫、波尔塔瓦、托木斯克等地有其分支机构和派驻代表。联盟以《我们的任务》(Наши задачи)为纲领,以《革命俄罗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报为理论刊物。成员由知识分子构成,人数少。主要领导人有阿尔古诺夫(А.А.Аргунов)、谢柳克(М.Ф.Селюк)等。1901年9月,第三期《革命俄罗斯》出版后,社会革命者联盟在托木斯克的印刷厂被查封。同年12月,莫斯科的中央小组以及其他城市的大多数联盟代表均遭逮捕。
⑨《我们的任务》于1896年初完成,由联盟创始人和领导者、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的阿尔古诺夫(1866-1939)起草,胶版印刷,原名《社会革命者联盟纲领基本原则》(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программы Союза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1898年,由阿尔古诺夫作序,纲领以《我们的任务》之名在莫斯科油印出版,此后,莫斯科成为社会革命者联盟中心。1900年,《我们的任务》在伦敦由侨民中的“俄国社会革命者联盟”印刷,联盟领导日特罗夫斯基(Х.О.Житловский)以格里高洛维奇(С.Григорович)之名为纲领作后记。
⑩Наши задачи//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 3-х тт./T.1.1900-1907 гг.М.,1996,С.24.
(11)Tамже,С.25.
(12)由民粹派侨民在巴黎创办,在日内瓦出版。1901-1905年不定期发行了4期。第一期问世于1901年夏,主编卢萨诺夫(Н.С.Русанов)。1902年2月,从第二期开始,该杂志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宣传喉舌,由切尔诺夫(В.М.Чернов)、郭茨(М.Р.Гоц)、卢萨诺夫、卢巴诺维奇(И.А.Рубанович)集体编辑发行。
(13)Наша программа//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901.№ 1.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 3-х тт./T.1.1900-1907 гг.М.,1996,С.51.
(14)Tам же,С.58.
(15)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1901-1905年共发行77期。由社会革命者联盟(Союз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创办并出版头两期,最后一期由切尔诺夫(В.М.Чернов)、郭茨(М.Р.Гоц)和希施科(Л.Э.Шишко)编辑,以文章单行本形式发行。
(16)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25,134.
(17)Чернов В.М.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 3-х тт.Т.1.1900-1907 гг.М.,1996,С.78.
(18)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56.
(19)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1904.№ 46.5.05.С.5-6.Цит.по: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56.
(20)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 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67.
(21)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73.
(22)Зензинова В.М.Пережитое.Нью-Йорк,1953,С.108.Цит.по: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ХIХ-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58.
(23)Чернов В.М.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С.84.
(24)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67.
(25)Там же.С.173.
(26)1908年-1909年由尤杰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和阿加福诺维(В.К.Агафоновый)在巴黎创办的报纸。总共出版了6期。《革命思想》报编者认为,首先应该争取政治自由,然后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对全民公开武装起义的想法给予否定评价。认为恐怖是俄国社会政治解放的唯一途径。社会革命党的守旧派认为《革命思想》中的观点带有“恐怖立宪主义”(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детзм)的特点;列宁巧妙地将该报纸更名为“不成熟的革命思想”(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едомыслие)。
(27)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86
(28)Чернов В.М.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С.84.
(29)Чернов В.М.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С.84,85.
(30)Чернов В.М.Террор и массовое движение//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граммы и тактики.Женева.1903.С.122.цЫт.по: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идеология,этика,психология(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ХIХ-начало ХХ в.).М.,2000,С.140.
(31)Там же.С.142.
(32)Будницкий О.В.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125.
(33)Леонов М.И.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гг.Самара,1992,С.23-24.
(34)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00-1925 гг.В 3-х тт.T.2.Июнь 1907 г.—февраль 1917 г.М.,2001.
(35)Городницкий Р.A.Г.A.Гершуни《Красный отец》эсеровск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Будницкий О.В.Eвре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1999,С.233~266.
(36)Гейфман A.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террор в России:1894-1917гг.М.,1997,С.73.
(37)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С.379.
(38)Гейфман A.Указ.соч.С.74.
(39)Там же.С.80.
(40)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С.379.
(41)Будницкий О.В.Введение//Женщины-террористки в России.Бескорыстны е убийцы.Ростов-на-Дону.1996.本文引自电子版全文http://www.a-z.ru/wоmеn/te xts/budniz1r-е.htm
(42)Там ж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