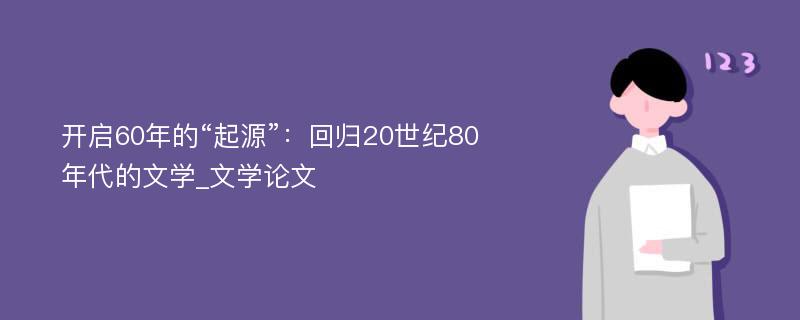
打开六十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点论文,六十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六十年”作为当代文学讨论的基本范畴时,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时间单位。在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整体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原点”式的阐释框架,这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时期”文学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当代文学的历史被理解为两个“三十年”、两种对立的文学规范乃至两种知识范式之间断裂和冲突的历史。新世纪语境中提出的当代文学“六十年”,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时间概念,而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这为人们去探讨、反省80年代的“新时期”意识与“新启蒙”思路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80年代却常常并不是作为“历史”而是作为“现实”,存在于当下的文学视野和历史意识之中。80—9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变,常被描述为与70—80年代的变化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一次转型,“后新时期”、“后现代”论述的提出和关于“80年代终结”的讨论,便是这种意识的呈现。不过,在更多的研究者那里,这次转型一直被理解为一种外在于文化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制性介入。它使得八十年代像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和一段“未完成的历史”,其历史价值和意义非但没有耗尽,反而正是需要在以后的时间中被延续的对象。也因此,关于80—90年代这一次转型在怎样的意义上发生、如何对之做出评价等,一直以来都是受到争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诸多思想与文化论争,比如“人文精神”论争、“学术”与“思想”之分、“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等,其实并不是90年代文化的内部论争,而应当被视为90年代意识与80年代意识之间的交战。这种种分化与论辩,有许多都并不是在对80年代历史做出有效的清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往往变成了各执立场的意气之争,或流于印象式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尽管对80年代的理解存在着上述种种争议,但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当代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又恰是把80年代形成的新主流文化观念和知识体系持续地合法化、常识化、特别是制度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寄身其中的整个知识生产体制,其实都形成于80年代。正是借助二十多年的学术规范、学科建制、学院制度等的重构与完善,80年代形成的文化观念、历史意识和知识结构已经成为了“自明”的知识,也成为了人们理解整个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合法性依据。文学研究界的状况就更是如此。80年代文学常常被作为“批评”而不是“文学史”,它的基本知识前提和文学规范仍旧来自与80年代同步确立起来的那些文学批评实践。正如程光炜形象地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文学类似于一个“认识装置”,通过它,“‘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被看作‘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八十年代”。而这样一套在80年代形成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不被反省的观念体制①。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当代文学的六十年历史作为整体提出,首先需要反省和思考的,正是80年代形成的这种关于文学的制度性知识。惟有如此,才能跳出80年代那种看似无色的“透视镜”,而在更开放也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观察整个当代文学历史。“重返八十年代”的初衷,也就是把80年代文学从一种仍在现实中发生作用的观念体制与制度体制中解脱出来,让它回到自身的历史语境和知识前提之下,并真正被历史化。
历史化的关键步骤,乃在于揭示这样一种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文学与知识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呈现其运作的历史轨迹。“新时期”文学知识与“新启蒙”式的文化观念之所以常常是“自明”的,是因为它们提出的总是那些看似具有普泛性的价值范畴、那些本体论式的文学知识,如“文学本体”、“人性”、“现代化”、“审美”、“文化”等等,而不是如50—70年代那种可以轻易地看出其“构造性”的特殊范畴,如“政治”、“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李杨在提及这一问题时谈到,对于50—70年代文学,人们总是可以轻易地区分出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尤其是文学制度、政治运动对文学的控制;而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文学制度”如何规约和控制文学的形态却被充分自然化和非历史化了。这也正是人们如此自然地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来描述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差异性的原因所在。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李杨提出,这主要因为两个历史时期通过文学而展开的“政治实践”的具体方式不同:“为什么一提起‘规训与惩罚’,我们就会想到50—70年代文学呢?这是因为50—70年代的‘规训’采用的都是看得见的外在的力量,比如开批斗会啊,把作家批评家投进监狱啊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暴力,一目了然。80年代的‘规训’为什么不容易辨析呢?那是因为80年代的‘规训’主要采取的不是这种外在的暴力形式,而是采取内在的方式实施的。……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化为你的内在的要求。”②显然,揭示出80年代文学实践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文化政治”或在“无意识”领域实践的政治,无疑有助于打破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框架,以及将80年代文学实践合法化与自然化的主流观念。呈现新时期文学自身的“政治性”,也就是显示它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权力机制的运作方式,从而把它从那种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层面,拉回到具体的、在复杂权力关系博弈中将自身合法化的历史实践层面。这无疑是把握80年代文学历史化的关键所在。
拆解80年代形成的文学知识体制,需要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三个层次同时展开批判性重读。从程光炜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这样一种整体的研究构想。这实则也意味着一个全方位地呈现80年代文学制度的解构工程。
在80年代的文学实践过程中,文学批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秩序正是通过批评实践而确立的。事实上,文学作品并不如“纯文学”、“文学审美”观念所理解的那样,是因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而获取其“文学性”;毋宁说,作品的“文学性”总是经由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论阐释、经典化过程和历史书写,尤其是文学批评的评价与筛选机制而得以确立的。也就是说,使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并支配其意义阐释方式的,是包含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的确立和文学出版乃至文学教育机构等在内的一套文学生产制度。而其中,文学批评又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将“文学”范畴历史化时指出的那样,正是文学批评的裁断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得以在西方确立,“因为此时它是确认‘文学’这种特殊的、带有选择性的范畴的惟一途径”③。也就是说,“文学”这一现代范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同与排斥机制,而文学批评则是其确立自身合法化的主要途径。在那些文学变革时代就更是如此。在80年代中国,当对一种理想文学形态的确立,乃是基于对另一种“非文学”形态的排斥的情形下,文学批评担当的就是极为重要的“鉴别”和“筛选”工作。它把一些作品确立为“文学”,另一些作品判定为“非文学”,把一些作品认定为“好作品”,另一些则认定为“坏作品”。许多经典作品,正是通过这样的批评实践,建立起与“时代”的历史性关联,并被纳入新主流文学秩序之中。因此,重新清理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尤其是文学思潮和重要文学事件,显示的就是新的文学规范如何通过批评实践而确立,以及在这一确立过程中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这种研究把新时期文学还原为一处处复杂的话语并置和杂陈的状态,以及其中的一种文学力量或文学规范如何凭借其知识/权力的优越位置,而将自己确认为“惟一”合法的形态,并由此获得讲述历史的权力。
这种经由文学批评而确立的文学观念、经典序列和美学准则,通过文学史书写实践而被制度化和常识化。因此,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呈现其历史“叙事”的特性,以及这种叙事与写作者的特定立场、身处的历史语境和基本认知框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呈现文学批评如何被作为“知识”而固定下来。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文学史写作及其流通总是与学科建制及学院体制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知识化的过程就与知识生产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这首先表现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间的关系。程光炜提出,“‘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意识是在‘当代’形成的,具体地说,它的所谓‘当代’实际上就是‘八十年代’”④。这无疑是一个极有见地的论断。应该说,这是现代文学在80年代作为“显学”存在的原因。而今天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与学科规范,也正是将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与知识体系持续合法化的结果。不过,因此就把当代文学“一直处在过分批评化的话语混乱状态”归罪于现代文学的压力,却并非必然的结论。一方面,以“左翼”为核心线索的新文学,作为学科方向,在50年代初期就确立了,并且正是为了确立“当代文学”的合法性,“现代文学”范畴才在50年代后期被发明出来⑤;另一方面,80年代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化与现代文学的“重写文学史”,依据的是同样的文学规范,完成的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实践,可以说就是“新时期”历史断裂论造就的同一问题的两面。因此,惟有超越了“新时期”意识及其历史断裂论,当代文学形成某种“自我统一性”而超越“过分批评化”的状态才会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重返八十年代”也是当代文学确立其合法的学科地位所必需的步骤。
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或许是“重返八十年代”最需要倚重的路径。如果说“重返”历史常常也就是研究者基于其特定的现实诉求与文化视野而进行的历史建构行为的话,那么,正是文学文本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生态”。作品自身的复杂性,使得这种“重返”与“重读”必须在对话的关系中展开。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总是经由特定历史语境中的阐释机制而获得的,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品本身,常常具有着体制性的文学知识所难以捕获或驯服的内涵。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总是“敞开”的。任何阐释都无法将其穷尽,也因此,“重读”始终是可能的。重读意味着文学作品被放置在重新建构的历史语境和意义的关系网络中而得到重新定位,更意味着文学作品中那些曾被新时期主流文学所遮蔽或边缘化的文学因素、那些因为过分地认同于“新时期”意识而“看不见”的历史经验和文学内涵,都在这种新的历史视野中得到彰显。如果说对文学批评实践的追踪与对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所显示的是80年代的主流文学观念如何形成并被制度化,那么,对文学作品的重读,则将在被拆解开来的认识装置的“裂缝”中发现更别样更复杂的历史,尽管这同样是不得不借助另一种现实透视镜下的“洞见”与“盲见”。
通过对文学批评事件和文学思潮、文学史研究和文学作品的解读,将会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新时期”文学如何作为一种包含了复杂的排斥与认同机制的运作过程,也展示了一套在今天仍旧处于主流位置的文学制度如何形成。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实践中,新时期文学才得以被“还原”为在80年代发生的历史。
把80年代文学还原为一种历史实践过程,首先改变的将是我们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基本认知与判断,乃至重构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阐释模式。程光炜是把80年代研究作为“方法”来对待的。他写道:“借‘八十年代’,既能够发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也能够充分地把‘九十年代文学’的问题打开。把它当作漫长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制高点’或‘瞭望塔’,重新理解、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学史的问题,并做一些方法论的探讨。”⑥这也就意味着,拆解80年代的文学实践过程和知识制度之后,打开的是整个当代文学历史的新视野。其原因显然在于,“新时期”形成的有关文学的那套知识的“自明化”,使它事实上成为了我们观察历史和现实的透视镜。我们所看到的“十七年文学”以至“文革文学”,都是透过“新时期”的透视镜而显影的;而我们对今天的中国现实的判断,事实上也潜在地在一种“新时期”和“新启蒙”式的思路上展开,这种思路决定了人们认为现实中何者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何者则需要推进和发展。指出这套文学知识是如何在80年代的特定中国语境中形成的,也就是指出这种知识的历史特性,指出它的充沛的历史批判能量的同时也指出它同样明显的历史有限性。在今天探讨这一问题,并不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评价“新时期”文学和“新启蒙”思路“好”还是“坏”的问题,而是这套在具体的历史针对性中形成的文学知识,如何把自己变成了一种超越性的知识/权力,从而阻碍着我们更为准确深入地认知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它把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评价体系,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普遍标准,而遮掩了它自身造成的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现实,或许便是中国社会基于不同经济、政治、社会脉络上的“分化”及其文化表述上的冲突。正是这种现实,使得去细致地梳理、辨析和理解不同脉络上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关系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葛兰西关于“政治”如何同时作为强制与同意机制的运作、“去政治化的政治”如何得以实践的具体形态等论述,才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⑦。如果说,在80年代,“政治”是一个携带着过多粗暴、强制成分和过多暴力记忆的语汇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以来中国语境中浮现的“政治”,则与这种需要被正面处理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显示出80年代文学与知识的有限性。甚至应该说,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只有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才呈现为“政治”。这其实才是我们需要重返80年代的文学实践、需要把80年代形成的那套自明的知识历史化的现实动因。
这种将80年代历史化的工作,无疑将改变“八十年代”自身的历史形象。这里呈现出来的“八十年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在“新时期”文学与“新启蒙”思路中自我呈现的80年代。它被重构因而获取了别样的面貌,变得“陌生化”了。程光炜将那种由8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确立的“八十年代观”,视为“自我本质化”的一种代表思路⑧。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变革时代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自我本质化”的过程,比如“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正是通过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领袖们的阐释而获得其主流地位的。不过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更有意味的地方是,如果说将80年代历史化的研究者也是同一批将80年代本质化的研究者,比如程光炜所表达的那种“亲历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角色的体验,那么这种将历史“陌生化”的工作首先遭遇的将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乃至经验与理论、文学记忆与知识批判、历史体验与现实感知之间的张力状态。并且,正因为“新时期”意识和“新启蒙”知识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知识状况和知识生产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对80年代的历史化工作,就不只是针对某一知识群体而言,而带有对当下中国主流知识状况的自我批判的意味。如果说那种完全站在“新时期”与“新启蒙”意识之内的80年代文学研究(毋宁说“文学批评”),强调的是80年代文学价值的普遍特性和批判功能的话,那么这种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展开的自我批判工作则会更为突出80年代文学的有限性及其得以展开的历史的与知识的前提。不过,正因为关于80年代的文学体验与历史经验尚且如此鲜活地存在于许多研究者的记忆之中,因此需要被拆解与“陌生化”的,就不仅仅是以史料、文本、知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同时还有那些被积淀为“情感结构”的体验方式和身体记忆。在后一种意义上,被陌生化的将不只是80年代,同时还有我们借以观察、认知和表达世界的那个常常被称为“自我”的主体结构。
当80年代这一原点式的阐释框架被历史化之后,最需要被重新讨论的,或许是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实践。如果说“新时期”意识和80年代文学制度所力图压制的正是前三十年的文学实践的话,对那段历史的更为复杂化的讨论也显然只有在80年代认知框架得到反省之后才有可能。不过,显然并不存在不透过某种“镜片”而可以看见的历史,问题只在于,80年代形成的是“透明”而无色的镜片,它被充分自然化了。也正因此,关于“新时期”与50—70年代文学的断裂性叙述,才成为一种如此“自然”的描述。如何使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停留在一种政治/文学对抗性的评判,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侧面,是研究界这些年格外关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所谓六十年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其主要意图便在如何去理解两个三十年之间更复杂的关系。比如甘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便集中论述前三十年与80年代以来的历史的延续性,进而提出“通三统”这样的表述⑨。在文学研究界,探询比“断裂论”更复杂的历史阐释,更成为诸多研究者“重返八十年代”的初衷。其中,李杨关于两种文学时段的不同政治运作方式的区分,以此破解那种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来阐释“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的观点,显然是极富洞见的。不过这些洞见同时又带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强调50—70年代政治运动的外在暴力和80年代政治运作的内在规约,事实上又以另外的方式重新强调了这两段历史之间的断裂性。也许应该说,它们仍旧是在强调50—70年代与“新时期”的差异性的前提下,来讨论政治的文学性和文学的政治性的。它们在颠覆以前那种文学与政治的对抗模式的同时,或许对“政治”本身做了一种普泛性的非历史化的理解。如果说在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中,新的政治是透过个体“认同”机制、“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来进行的话,能够简单地说50—70年代的文学就仅仅是在一种“外在暴力”的形式下运作的吗?我们如何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广泛激起的热情、渴望与乌托邦冲动,更不用说那些政治运动常常是以“全民运动”的形态展开的。从来不存在任何超历史的个体的内在欲望,因此政治的运作也就从来不是在非历史的抽象空间里展开的。欲望自身的历史性,使得我们不能以80年代的欲望准则衡量50—60年代的欲望形态。因此,对政治运作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区分,仍旧包含了经由80年代形成而对50—70年代造成压抑的阐释框架的过滤。
这些或许过分抽象的理论问题,需要在大量艰辛而坚实的历史梳理工作中被纠正、调整并得到深入讨论。不过,“重返八十年代”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使许多我们曾经认为不言自明的观念、感受和记忆都在一种陌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别样的新面貌。它将拆解那些我们借以透视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观念制度,并使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更多的侧面和新的阐释与想象空间。
注释:
①程光炜:《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前面的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李杨:《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80年代文学”研究与人大研究生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③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④⑥⑧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第78页,第81页。
⑤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⑦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⑨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2007年第2期。他在《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提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当代文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