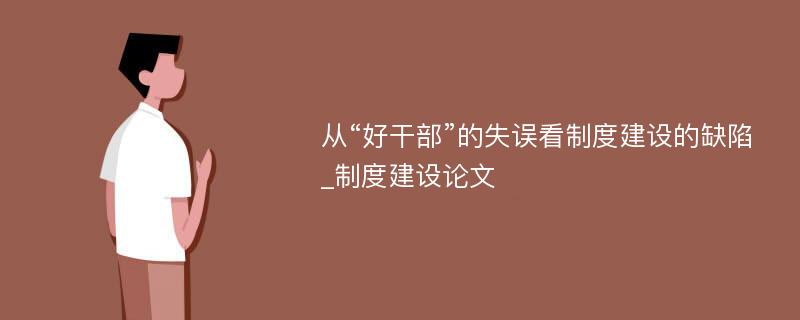
从“好干部”犯错误看制度建设的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缺陷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些貌似清正廉洁、作风朴实的好干部,或者工作表现积极、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并有显著政绩——即媒体所说的“工作并腐败着”的干部,最后却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被发现是腐败分子。这不由得使人产生种种疑问:各级党组织都制定了那么多的反腐倡廉的制度,为什么发挥不出原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假象为什么能迷惑住党组织?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权力运作过程中存在某些制度缺陷。
一、“无赖原则”是确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不可忽视的原则
党内好干部居多数,这是事实,但从制度建设的视角来看,这不能成为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起点。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重心是防范,既然是防范,防错纠错,所遵循的就是“无赖原则”。“无赖原则”是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说,在设计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这种人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而且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都必须让他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一条正当的政治准则。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党内很多人对上述观点并不以为然,在制定制度的时候往往先确立一个前提,就是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权力行使者是好的,职务越高其素质越高,特别是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其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自觉性——因为是经过组织筛选提拔的干部,所以素质是靠得住的。由此导致制定制度时往往针对下级较多,防范性较差。再加上某些封建主义的为尊者讳的意识,就会出现一些监督的空白点。胡长清曾说,当官当到了他这一级,就如同羊进了牛栏。羊进了牛栏,其栅栏缝隙对牛而言当然是小了,但对羊而言自然是太大了,用牛栏防范羊是防不住的,所以“无赖原则”是有道理的。
凭心而论,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是无赖,党的领导干部确实是经过考核、层层选拔才进入到“领导”序列的,但不能排除下列情况:一是当权力运作过程缺少民主化科学化的体制性制约时,即使是素质较高的领导干部也难免牵连到一些属于滥用权力的事端中;二是人的素质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在长期掌握权力的情况下,在客观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行使者自身的素质就成为非确定因素;三是用人制度还不完善,导致少数有问题的干部能够得到提升。还有其他种种因素,都可以导致权力行使者出现问题。这证明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是准确的: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
笔者无意纠缠人性善与恶的问题,只是从反腐倡廉的视角来看,主张“无赖原则”应当得到重视。这是由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的。制度是对人的行为最低限度的要求,比如,制度只能规定领导干部不许贪污受贿,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守法的领导干部,但不一定是优秀领导干部。然而,制度却不能规定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做到焦裕禄、孔繁森所做的事情,只能提倡向焦裕禄、孔繁森学习——因为这是高标准,是优秀领导干部才能做到的,而列宁说过,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用制度化的形态规定其必须做,那么制度就会失去其刚性的特点,成为纯粹字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既然制度只是对人的行为最低限度的要求,那么,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其预设的前提,就是“无赖原则”。以这一原则为起点并不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的不信任,而是制度的内在要求。对于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领导干部来说,制度的最低要求已经内化为其道德和行为的底线,对于精神品质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说,则可以防范各种问题酿成大祸。
按照这一原则,就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反腐倡廉、防止干部犯错误最重要的途径。以权力制约权力,本质上是权力配置问题:一是要有体制性制约,即从领导体制上,保障不同类型的权力有相对独立性,既可在权力行使范围内有效地运作,又可防止滥用权力。即使对同一类型的权力如决策权,也应根据决策主体的不同,界定其行使权力的边界,明确界定其承担的责任,不能权力无限而责任有限。二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强化监督权力,这既是由于现有的防错纠错机制本身较弱的缘故,也是由于社会转型期易于出现各种问题,需要有较为强大的监督力量的缘故。有人提出,监督机构权力加大了,谁来监督监督机构?这还是一个权力配置问题。监督机构也不能权力无限,当然也要受到被监督的权力机构的制约。权力配置是科学性问题,不能有游离于规则之外的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
二、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制度是揭露一切假象的最好办法
“好干部”犯错误,如果仅仅以“假象”迷惑人为理由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无论这些人以什么样的外观出现在众人面前,其错误都是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人们就只能注意其外在的印象,诸如是否朴素、平易近人等等。归根结底,出问题还是出在权力运作领域中。从权力运作的视角看,上述问题都可以找到根源。离开了权力运作过程这一领域,上述问题就带有偶然性;而事实已经证明,“好干部”犯错误一再出现,这就不是偶然性的问题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权力运作过程公开,这是不被少数人的表象所迷惑,使各种问题暴露于阳光之下的最好办法。
需要指出,公开化问题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有了重要进展,一些地方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特别是有的政府部门在制定行政法规时,通过互联网颁布草案,欢迎市民提意见,并且真正吸取群众的意见,甚至将原法规否决。这是权力运作过程公开的重大进步。只有公开,人民群众才有可能介入权力运作,所谓政治参与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公开,才能使监督不至于落空;只有公开,才能减少干部犯错误的概率。列宁曾说,没有公开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同理,没有对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所谓监督制约就是很可笑的。
公开,关键在于权力运作“过程”公开而非结果公开。所有的腐败行为,无论发生在哪个环节,都与形形色色的私下的“活动”相关。比如,在招标投标问题上,在政府采购问题上,如果把私下的“活动”全部公之于众,就会大大减少腐败现象成功的机会。再如,在用人问题上,虽然有了许多关于选拔任用干部的程序规定,也有了用人失察、失误追究责任的制度,但某些关键环节不公开,或者在投票的具体操作规则上做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规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以民主之形式体现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意志之实,依然不能解决“边腐败边升迁”的问题。当所有享有监督权利的人最后见到的只是结果——既成事实时,监督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并且,在监督权力较弱时,也不可能推翻既成事实。
建立权力运作过程公开制度,需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公开制度建立于人民是国家权利主体、党员是党内权利主体这一最基本的理念之上。所有的制度固然都是特定社会种种因素促成的,但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这里不来探讨时代理念、价值取向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比如,在君权神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专制制度,在人民主权论基础上建立的就是民主制度。如果制度的价值取向倾向于反映少数人的意志,所有的规则就有利于体现少数人的意志,反之则会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因此,没有对权利主体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推行公开制度的。第二,公开制度应是双向度的公开,即需要公开的事项不能由权力行使机构单方面决定,愿意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如军事、外交、重大商业机密等外,均应公开。第三,权力行使者因其行使的是公共权力,事关公共利益,因此其隐私权应有所“减损”,权力越大其“减损”的幅度应越大,如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应当公布于众。财产申报制度在海外被称为“阳光法案”、“终端反腐”,可是来到中国却失效了,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失效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却是不公开不透明,其申报只能是形式的。
当然,公开制度并不能直接遏制产生腐败的根源,但可以减少腐败行为成功的机会,是任何领域的反腐败都不可缺少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