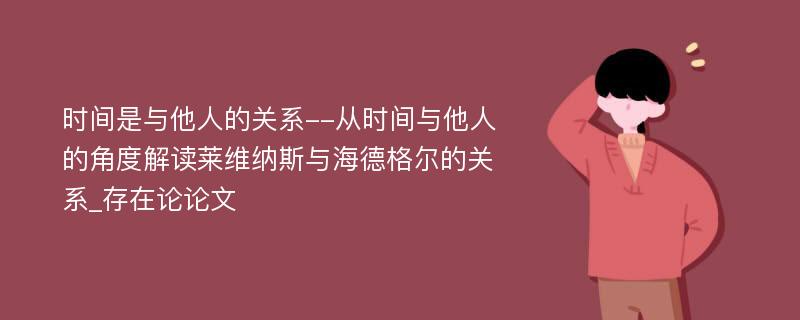
时间是与他者的关系——从《时间与他者》解读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他论文,海德格尔论文,关系论文,时间论文,纳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列维纳斯是最早向法国引进海德格尔思想的哲学家之一,甚至在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之后,列维纳斯也仍然把海德格尔置于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列,但与此同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又对海德格尔进行了最激烈、最尖锐的批评。因此,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成为“后现象学”领域中最困难的课题之一。这个课题意义深远,它不仅关涉“走出海德格尔如何可能”这个所谓的“后现象学”问题,而且关涉“后现代伦理如何可能”这一“社会正义”问题。对此关系的探究,研究者多以列维纳斯1961年的《总体与无限》为起点,这对阐明二者的对立立场无疑是关键的,但是要阐明二者在学理上更深层面的复杂关系却必须从列维纳斯的早期著作开始考究。本文尝试以其早期作品《时间与他者》为解读的个案,在现象学内部具体而微地铺陈和思考这个话题。
一、由对反而出离
对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的关系,Manning 深有体会:“正是海德格尔向列维纳斯显示了现象学方法的真正的哲学意义”,列维纳斯的现象学就是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之内,而又总是给予另类的诠释(对此种关系本文称之为“对反”),虽然列维纳斯早就有自己的一套对存在和人类存在的观点,即要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但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教他往那儿看的”。[1](pp.6—8)
在列维纳斯的第一本原创性专著《从实存到实存者》中,这种对反就已经开始了,其核心概念“位格”(hypo-stase)就是在与海德格尔的绽出(Ek-stase)相对反的意义上提出的。要而言之,如果说海德格尔是用“绽出”表示从“现成在手状态”朝向存在本身的超越(trans-cendence), 那么列维纳斯恰恰是要从纯粹存在状态中挣脱出来(ex-cendence)。海德格尔把他的这个超越作为“出神”的轻舞加以倡扬,而列维纳斯却分明在位格中感受到“负担”和“责任”。但是,列维纳斯同样认为位格是一种存在论事件,一种存在者的呈现过程。作为“不愿意去存在”的疲乏和“不可能开始”的懒惰恰恰证明了作为一种负担的那种瞬间所意味的“开始存在”,“瞬间才真正是存在的完成”[2](p.76)。列维纳斯甚至用烦(souci)——这本来是作为海德格尔的Sorge的法文对应词——来表示这种存在论事件。用列维纳斯的话说,瞬间就是“存在一般的极化”,而位格就是“因由这种瞬间的位置而发生的事件”。[2](pp.17—18) 不过,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不同的是,瞬间是先于与世界的关系的。而一旦进入世界,列维纳斯的烦就成为享受了,并由此把海德格尔的因由“向终结而在”的“将来取向”而绽开的(实际上是虚化了)的当下加以“落实”了,并且,在海德格尔那里,相对于超越和回归自身的“本真性”而成为“沉沦”的日常生活也被列维纳斯由此“正名”了,成为一种真实的、自由的“居家状态”。不过,列维纳斯真正关键性的进展却在于;与海德格尔的本性上就是时间性的、并有终结性(Endlichkeit)取向的“绽出”(注:以这种“绽出”作为“时间性”也是胡塞尔开辟的,其现象学要义在于时间之流的存在方式或其本质性形式是“现在一涌现”,任何有意或无意的河流之“整体”及其“流淌”的意象都已经是某种超越性的建构了。这种绽出性的时间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一路共同的基本视角,也是本文论述的基本背景。至于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则在于更深一层的、对“绽出”本身的不同理解。) 不同的是,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已经纯然是存在论事件的“位格”的呈现或在场,最多只是作为永远重复的不停的“开始”,是没有能力打开时间的。因为,这里发生的只是永远囿于自我之中的作为同一性及其运作的在场,真正“异质性的将来和过去”永远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在列维纳斯看来,“超越”永远只能是向自身的回归,它是不可能真正完成作为存在论本来所欲达成的存在(ex-ist,绽出性的生存)的。源此,列维纳斯提出了“出越”(ex-cendence)以代替超越(trans-cendence),不再朝向自身,而是出离自身,即朝向他人,并在这个意义上朝向“善”。但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列维纳斯又是在完成海德格尔所开启和欲完成的ex-ist(注:这也是列维纳斯要用existence而不是用être翻译Sein的真正原因,而决不仅仅是“出于谐音的考虑”。(Emmanuel Lévinas,Le temps et l'autre,Montepellier:Fata Morgana,1979,p.2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维纳斯恰恰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把时间性作为存在及其意义的根本境域的思路前行的,并正是缘此而把最关键的环节集中定位在了对时间的全新的界定上:真正的时间只能是与他者的关系——这就是其早期(注:在1975—1976年度的讲座《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列维纳斯又精致练达地演绎了这个主题。与之相比,这确实是其“早期”的作品。) 另一篇专著《时间与他者》的主题。
二、重构“存在论差异”
在《时间与他者》的开篇,列维纳斯就针对海德格尔明确提出:整本书的目的在于表明“时间不是独在主体的成就,而是与他人的关系本身”。[3](p.17) 不过,这里有一个进路,就是“他人”(autrui)首先出现(在正文第一句)。因为关注的主题就是主体及其独在(solitude)。而“他者”(autre )是在谈论死亡的异质性以后才引入的。他者控制的是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存在本身,但如何控制是一个不可能知道的谜。他者的整个存在是由外在性、异质性(altérité)构建的。只是在说到“那么死亡还是我的吗”时,即再次诉及主体性时,才又把他者定在他人上,“被承担的他者就是他人”[3](p.67)。早在《论逃避》中,列维纳斯就强调了从存在逃避的必要,但还没能提出全新的路径,到《从实存到实存者》,他更把这种逃避称为拯救和解放,并且认为个中关键就是“时间和他者”[2](p.99),把与他人的关系界定为是与神秘者、外在性和异质性的关系了。[2](pp.75—76) 至于时间和他者如何构建了从存在中的解放,这是《时间与他者》的主题。尽管强调了从存在逃避的必要,但列维纳斯也仍然明确他的分析是存在论的,他“的确相信存在论问题和结构的存在”[3](p.17),这一路的存在论确信或自觉的分析结构一直持续到《总体与无限》。对列维纳斯来说,存在不仅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还有自身的“辩证法”[4](pp.219—234) 和自身的一般家政学(l'économie générale l'être),《时间与他者》的关键词“独在”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范畴。[3](p.17)
列维纳斯认为, 在海德格尔那里, “本真的”此在是孤独的, 其“共在”(Miteinandersein )所描述的最多也只是一种“肩并肩”地朝向“共同的”目的(比如真理)而形成的团结,其中没有“面对面”的“源始的”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即便是绽出,也是要么在日常生活中散化,要么重又回到自身,其中都没有真正的“他人”的出现。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几乎相同的是,列维纳斯首先也明确要建立死亡对主体的肯定性意义,不过他重新界定了死亡现象,认为其中有一种神秘之谜,而并非必然是虚无,而且其中“不仅有与他者的关系,也有与时间的关系”。[3](p.20) 简而言之,列维纳斯就是要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根基中开辟出一条走出海德格尔,即走出独在、面向他人的道路。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正是我的存在决定了我的孤独。不可交流的不是在我之中的任何“内容”,而是“因为这种不可交流性就植根于我的存在之中”[3](p.21)。这是一种最“内在的”关系性,即我与我自己的生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说:“存在拒绝任何关系性和多元性。它不关涉其他的人而仅仅关涉存在者。”[3](p.22) 也就是说,存在与存在者是一个统一体,但若能打破这个统一体,就可以实质性地克服独在。在此,列维纳斯引入“位格”,即“存在者对自身的存在的承担”这个“存在论事件”。具体的进路是:
首先,在此存在与存在者“统一”的背景下,列维纳斯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他说:“对于我来说,《存在与时间》最有意义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3](p.24) 列维纳斯总的来说是支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之说的,但是他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有存在者才能现出存在,而这样的结果却又会使得存在者消融于存在,这样,差异就不彻底了, “在海德格尔只有差异没有隔绝(séparation)。存在总是在存在者那里被把握”[3](p.24)。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正表明了这种差异的不彻底性,即总是要由Dasein、甚至某人(quelquún)来拥有存在。
其次,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事实上却又表明存在是先行并独立于存在者的,因为存在者只能在存在中才得以呈现,而永远不可能成为存在的主人。因此就必然有没有主体、没有存在者的存在,列维纳斯称之为匿名的il y a。(注:法语il y a的意思是“有,存在”,列维纳斯用此无人称动词短语表示纯粹存在的无人称状态。当然,对于这种没有存在者的存在,不用说前期,即便是后期的海德格尔也是难以认可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海德格尔,存在本来就“总已经”是世界性的了,关键是应该如何“去存在”;而列维纳斯则认为世界性也有一个发生的过程,这就好像在表象意识之前有一个非表象、甚至非意向性的意识一样。列维纳斯要追溯它们的“源”,其宗旨只是要说明“世界性—存在”和“意向性”一样只是“流”,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分别把它们说成是独一的,就已经是落入了自我或自身性中心的“总体”之道,其中再不可能有真正的他者,从而也就不可能是道德的和正义的。)与《从实存到实存者》中进行的思想实验一样,[2](pp.57—58) 列维纳斯在对世界进行想象的拆解(destruction)之后,发现了这个剩下的“事件”(le fait):一种存在的无人格的“力场”,一种失眠状态中的黑夜;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实体,但却自我设定(se impose);它又是匿名的,即没有任何人和物将其承担。
再次,对于这种没有存在者的纯粹存在,即纯粹的动词状态,列维纳斯将其理解为“克拉底鲁之河”,即人一次也不能踏入的那条河流。它没有任何固定性,但这正是位格得以“产生”——具有“存在的效果”和“存在被暴露”双层含义[5](p.26) ——的地方。在此间,虚无是不可能的,所以列维纳斯认为,存在之恶(mal de l'etre)不在于它是有限的,而恰恰在于它是没有边界的。海德格尔将畏作为对虚无(即纯粹存在)的体验;而列维纳斯则认为,如果死亡意味着虚无,那么畏实际上表达的正是死亡的不可能性。死亡是对人的可能性的剥夺,“死亡是筹划的不可能性”,它所带来的不是人对自身的存在可能性的把握。恰恰相反,是人对自身存在把握的不可能性。死亡剥夺了存在(即可能性)。但是死亡并不是虚无,这里有他者和神秘,人不可能就此终结。如果说纯粹的存在不是虚无,那么死亡也不是虚无。在剥去虚无的相对于存在的所有依附性和对反性之后,列维纳斯就以最彻底的态度直面着死亡。
最后,就是从存在到存在者的发生,即“在场”了,列维纳斯将其称为“位格”。这是一种存在论“事件”。在《从实存到实存者》中,列维纳斯曾把匿名的il y a描述为一种失眠状态,在失眠状态下,意识向自身呈现(面向自身在场),仿佛意识到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换个角度,就是说某物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向意识呈现自身,而意识却无法将其同一化,其中的永远在场的只是纯粹存在的嗡嗡声,“有而不名”,却又挥之不去,因为根本就无“能”(注:这里的“能”(pouvoir)既指能力,更指拥有能力的可能性,即作为一个存在者的自身建构。) 去“挥”。因此,意识的“觉醒”(从失眠状态中走出来)就是意识觉知到它与存在本身的“隔离”。在这里,列维纳斯认为“在场”就是“永远无始无终的存在的结构的一次突然的撕开”,就是“位格”这个“事件”,“撕开”又合上,它只是“开始”本身,它的过去只存在于记忆中,“它有一个历史,但它不是历史的”。它不是现存的、已经被构建起来的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就是在场的那种功能(即撕开)。它像一种“存在论的安排”,就在存在与存在者的边界上:既是“必须由动词才能表达的纯粹事件”,又“已经是一种存在者”[3](p.32),所以,“在场就是完成那种总是昙花一现的‘出离自身’的一种方式”。[3](pp.32—33) 如果在场可以持续, 它就可以从先行的东西那里接受它的存在;但是它只是来自自身的东西,昙花一现就是这种开始的本质。这里,列维纳斯实际上已经是在说一种完全异质的“在场”了:(1 )在场是“撕开”匿名存在的一种功能;(2)没有过去,只来自自身, 不是线性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就是“开始”本身或“开始”的本质;(3)只是昙花一现, 没有绵延;(4)这种昙花一现的结果就是“自我”。列维纳斯说, 在场或位格实际上也就是自我或主体,表面来看,“自我(je)总是具有双栖特征:它不是实体,但又绝对是一个存在者”[3](p.33),要想理解这个悖论, 就必须把自我理解为存在自身的一种样式,甚至可以“准确地说它并不存在”[3](p.33)。而当自我或在场被形式化为一种时间时,这样的时间也就会成为存在者,从而失去“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构架功效”。[3](p.34) 列维纳斯认为,在寻找这个从存在到存在者的桥梁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超出了现象学的经验。因为从存在到存在者的过程不再属于“经验”范围,“而如果现象学仅仅是一种关于激进的经验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在现象学之外了”[3](p.34)。换句话说,位格实际上是前现象性的、前自我经验的,甚至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对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和海德格尔的此在—时间进行发生现象学的描述的意味。事实上,从位格、事件到后来的历时性,这正是列维纳斯出离存在与意向性现象学的轨迹。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独在”的复杂含义了。一方面,“位格”就是“存在者呈现”这个“事件”,其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存在者成为它的存在的主人。这是纯粹的自发性发生(sui generis),因而是纯粹“独”在的“主人”状态,“作为在场、自我,位格就是自由”。[3](p.34) 为了能有存在者并把握存在,独在就必须摆脱匿名状态,脱颖而出,成为“一”(存在者就是与自身相同一)。因此,独在不仅是存在主义所关注的一种绝望和放弃,也是一种生命力、一种骄傲和统治权。另一方面,位格作为在场的纯粹功能,既从存在出发,又牢牢地牵连于自身,对自身负责,而这就是列维纳斯思想中的关键词“物质性”(matérialité)的真切含义。物质性就是自我(Moi)与自身(Soi)不可分离的“锁链关系”:存在者不仅是出离自身、与过去和将来相脱离、重新开始的自由,一种脱出的自由,而且总是要回到自身,被自身所充满、占据,“这种被自身占据的状态就是主体的物质性”[3](p.36)。当在场从无限的存在中撕裂而出,在割断了历史脐带的同时,又是有重负的。自我并不是像一个精灵、一个微笑、一缕气息一样地存在,而是一种物质存在者,自我必须为自己负责。因此,列维纳斯说,物质性并不是精神向肉体坟墓或监狱的“偶然”“堕落”,而恰恰是与主体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那种高涨的自由相“伴随”的,“自我的自由与它的物质性是并行不悖的”[3](p.38)。换句话说,物质性恰恰是向存在论还原的结果,而“震碎这种物质的锁链就是摧毁位格的确定性”[3](p.38)。可以说,只要是在存在论中,位格就只能是同一性自身的锁链。
这样,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便被列维纳斯“解构”了,即重新理解、重新布展了。在列维纳斯看来,存在论差异作为对存在与存在者统一的打破,本来是可以克服独在与其存在的自身同一性的,但是在由此获取一种全新的自由的同时,又陷入新的自身束缚。而在场的“开始的自由”以及相应的“物质性的锁链”则是列维纳斯在海德格尔的境域内开展出的另类思想,其关键在于:此在的本真状态被转化为主体的独在;独在又被诠释为一种不断撕开存在、获得全新开始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又更深地被锁缚在自身的同一性中,这种同一性又是一种责任和物质性。列维纳斯以后关于主体的所有论述都是奠基于此。而在这个主题线索的一旁,一个方法论的奠基也同时开始,这就是列维纳斯对“时间”的立场性展示。正像在场的位格只不过是位格的一种,时间还可以指向存在与存在者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与他人(autrui)的关系,而独在只是一种时间的不在场。至于那种被预设的、被给予的、主体携其同一性在其中穿行的“时间”,也不能松开位格的同一性链锁。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就是“时间的时间化”,时间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理解,因而时间是存在论内部的问题或其地平(水平的context,而不是列维纳斯的上下垂临的context);而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时间却是超越存在论的,其基础不仅来自罗森茨维格,而且也来自胡塞尔。(注:胡塞尔在时间问题上与列维纳斯的关系可用“从被动综合的时间意识到异质触发的感性时间”作为理解的线索之一,详见拙文《解读列维纳斯的〈意向性与感性〉》,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
三、从“磨难—死亡”到“他者—时间”
依照列维纳斯的理解,“存在”就是行动,并且最终是以我们的存在本身作为此行动的对象。这也是《存在与时间》的基本宗旨:世界是工具的整体效果,相互指引的工具最终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存在之烦。对此,列维纳斯的诠释是:“在打开浴室的开关时,我们打开的是全部的存在论难题。”[3](p.45) 而列维纳斯出离海德格尔之路也是就此开始的。列维纳斯认为,在成为一个工具系统之“前”,世界就已经是一种“滋养”的整体(un ensemble de nourritures),就是说“我们虽然超越自身,是一种绽出性存在,却是被限制在对象之内的”。[3](p.46) 列维纳斯把滋养中的这种与对象的关系的特征称为“享受”(jouissance)。在位格的纯粹同一性中,主体是陷滞于自身的;而在享受的世界中,主体就从自身分割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从开始的物质性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方式”。[3](p.46) 这里已经包含了对自身的遗忘。海德格尔批评常人“遗忘自身”,而列维纳斯却赞赏这种遗忘,他认为,“‘世俗滋养’的道德性”是第一个道德、第一个自制(abnégation,自我否认),它是每个人都要经验的。[3](p.46)
享受使得主体生活在客体之中或被他所吸收的客体所吸收,这样与自身就有了距离。海德格尔对此距离是批评的;而列维纳斯则认为工作就是对此距离的征服,“工具或工具的制造就是对那种填平这个距离的幻想的追求”[3](p.53)。列维纳斯认为现代机器作为工具更多的已经不是海德格尔所考虑的“器具”的功能了,工具(机器)本身具有了压制劳动的效应,因此才有了列维纳斯的新主题:“独在最终被还原到的现象就是痛苦和伤心”[3](p.54)。这种痛苦和伤心真实地构成了独在的悲剧,而“享受的绽出性并没有能够克服这种命运”[3](p.55)。由此,列维纳斯明确以下两点是其独在分析的重点:一是“我对独在的分析,是在需要和劳动的痛苦中加以追求的,而不是那种虚无的焦虑中实现的”;[3](p.55) 二是这种痛苦是身体的,不是道德的,正是身体的痛苦才是存在所不可松懈的。列维纳斯明确排斥海德格尔甚至萨特的布尔乔亚作风,认为没有任何可以躲避这个磨难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磨难就是虚无的不可能性”[3](p.55)。
然而,在磨难中却有死亡的亲近(proximité)。死亡的不可知性是与对虚无的不可能性的经验(即磨难的经验)相关的。与死亡的关系是不可能发生在光之中的,所以它是不可知的,是一种神秘之谜。就光是智性的而言,所有的知识都是主动性的,“通过光的中介,在知识中的所有被动性都是主动性”[3](p.57),即使死亡宣告了有主体无法把握的事件,也没有阻止主体把所遇到的客体都理解为是自我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甚至把死亡作为存在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准确地说,它使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得以可能”[3](p.57),死亡由此成为主体自由的一个事件。列维纳斯则认为,死亡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之谜,是一种纯粹的被动性经验,“死亡从来就不是一种在场”。[3](p.59) 当死亡在此时,我就不在此,这不是因为我是虚无了,而是因为我不再能够把握了。就是说,在死亡到场时,不在了的那个“我”实际上是“我的主人地位”、“我的生力”、“我的英雄气概”;尤其是在磨难中,“我”似乎达到了可能性的极限而成为一种不可能性。此时,极端性假设的那些至高的责任(向死而在)就转化为极端的无责任能力,进入婴儿状态,“死亡就是回到这种无责任状态,像婴儿一样啜泣颤抖”[3](p.60)。这里,在与死亡相亲近的磨难中发生了从主动性向被动性的倒转,死亡从来不能被预设,它只是来临。可以使人们“预设”死亡的虚无是不可能的,死亡的临近尚还可以是一种“现象”,但是死亡本身却无从把握,不仅不是现象,甚至不能被预设。而虚无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只是存在的另类表达,即使非存在也已经是“要去”不存在,因而就已经是“去存在”。正如列维纳斯后来所明确的,to be or not be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6](p.40) 总之,在死亡面前,存在者不再有能力成为存在者,“我们不再能够‘能够’”(nous ne pouvons plus pouvoir)[3](p.63),因为我们不再有“能够”的能力。死亡就是筹划的不可能性,因此,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是,列维纳斯认为“死亡不再是肯定而是打破了我的独在”[3](p.63),在死亡中,存在者的存在被异己化了。依据列维纳斯的观点,死亡是无法与现在连接的,因此才引出了真正的将来,即不可化归到现在或在场的将来本身。所以,将来就是他者,而“他者就是将来。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与将来的关系”[3](p.64),对此,列维纳斯很明确“我不是用将来去界定他者,而是以他者去界定将来,因为死亡的那个将来就在于它的异质性之中”。[3](p.74) 这是以他者为起点的方向,而不是以时间中的将来为预设的方向。从柏格森到萨特都是把将来作为(将来的)在场(现在)了,这种作为预期性和筹划性的将来是列维纳斯所反对的,因为“将来不是在场(现在)”,“从这样的将来概念出发,人们就决不会把时间理解为‘移动着的永恒的形象’”,[3](p.71) 而“时间的真实性”就在于永远不能在现在里面找到将来。柏格森的作为绵延的自由本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他为现在保留了决定将来的权力,他认为“绵延就是创造”;而列维纳斯认为“创造”只是“重新开始”,时间的要义在于“新生”。时间的深刻意义就在于打开了主体的封闭性,这意味着主体在创造自身时就前设了对神秘之谜的一种开放,这也是列维纳斯坚持在存在者(主体)之“前”(其实是之“外”)要有匿名而又不可懈怠的存在(exister)的原因。因为在场决然不可能超越自身、侵入将来, 所以与将来的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面对面”的“关系”中才能完成。面对面的场域也将使时间自身整个得以完成,因为时间的条件就在于人们的关系或历史中。死亡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将来,它表明了与在场的断裂,因为我不能与死亡并存,所以将来就决非来自自我,死亡表明真正的将来是异质性的,他人就是将来。正是在与他人的面对面的关系中,在场与将来的“关系”才得以建立,“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他者的不在场,但不是纯粹的不在场,不是纯粹虚无的那种不在场,而是在将来的境域中的不在场,这种不在场就是时间。”[3](pp.83—84)(注:《时间与他者》的英译者Cohen在导言中甚至认为他人时间与我的绽出性时间二者本身之间就不是同时性的。相反,正是他人时间对我的时间性的中止或打搅才是真正的时间所具有的异质性。Cohen在其精彩的导言中有两处说法,一是将列维纳斯的瞬间等同于胡塞尔的原印象,二是把列维纳斯从前期“将来”向后期“过去”的转变更多地从列维纳斯要铺展开异质性的时间的所谓“三个维度”的角度加以解释了。我认为,列维纳斯的瞬间确实有胡塞尔的原印象的渊源,这在其后期特别明显,但在这里,还是放在海德格尔的“当下”的背景下可能理解得会确当些。而从将来到过去的转换更已经是列维纳斯本人以后新的时间性的引入了。总的说来,Cohen似乎有以列维纳斯后期的立场诠释其前期作品之嫌。当然,关于列维纳斯思想发展中有无转折问题学者中还有不同意见。) 也就是说,他者的不在场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纯粹虚无的不在场,而是在将来视域中的不在场,因为所谓将来(avenir)就是总是将要来临(à venir)但却从不会在场,在将来的视域中“呈现”的只能是“不在场”。“在场”的“时间性”的超越性所朝向的应该就是“将来”的神秘之谜,于是时间本身也不再是存在者存在的境域,而是存在超出自身的样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列维纳斯所说的“时间就是存在的事件”[3](p.88) 的真正意味。
这种异己的他者(l'Autre)对“我的存在”的控制不是主体式的拥有,而是一种谜,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可能知道。对于这种神秘之谜,列维纳斯引入了情欲关系:“我认为情欲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关系的一个原型。情欲,就像死亡一样强有力,将为我们提供对这种与神秘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3](p.64) 正如英译者Cohen在注释中所提示的:情欲像死亡一样强有力,这是源自《旧约》“雅歌”的传统,对列维纳斯影响至深的罗森茨维格在其《救赎之星》的第二部分的第二卷也是如此开篇的。[7](p.76) 列维纳斯正是由此开始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现象学描述,“欲望”成为中心“意向性”,“情欲的意向性是将来自身的唯一的意向性”[3](p.83),而其结果便是永远不能化归的、“在女性中方得以实现的异质性”。[3](p.81) 由此,作为“在生命中的”他者之他性的显现的爱人就被呼唤出来了,因为“爱”是生命的动力,并且像死亡一样有力,由此可以重新布展主体,这成为列维纳斯在此书之后的主题。
至此,我们可以在“存在与时间”的向度上简要梳理一下列维纳斯“出离”海德格尔的轨迹。列维纳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理解为虚无,“虚无化的存在”就是其il y a,这种理解忽略了海德格尔还有“无的运作”。海德格尔的虚无意义上的存在不仅可以被列维纳斯诠释为失眠与警醒,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无的运作”本来就可以直接为列维纳斯所说的位格的出现给予说明。不过,也可以说列维纳斯是以其特有的方式阐释了海德格尔这种“无的运作”的机制,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正是从独在的角度才有对本真形式中的Dasein的分析”。[3](p.89) 至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列维纳斯则是从对在场的批评开始的,他一直是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归为“自身指涉”意义上的“在场的哲学”,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烦和表象进行的都是自身指涉意义上的综合行为,这种综合行为是要使将来和过去聚集在当下的结构中得以呈现。列维纳斯要做的就是保持住过去和将来那种不可化归到在场的异质性,直面死亡和他者。在列维纳斯的思想逻辑进程中,先是“瞬间”,然后是“将来”,再转为“过去”,有真正异质性的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成为列维纳斯逃脱海德格尔阴影的主线,他自己的思想也在对时间一步步地完整型构中逐步完备。一句话,海德格尔的时间是存在者存在的境域;而列维纳斯的时间却是存在得以超出自身的境域,“时间不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存在论境域,而是作为超越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思’与他者的关系”[3](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