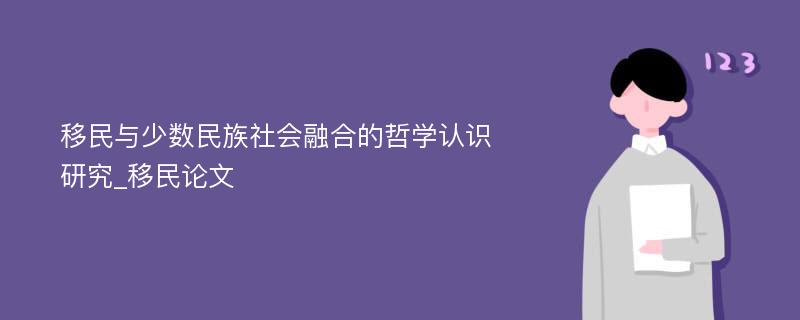
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哲学认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认知论文,移民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4)08-0062-04 一、移民少数民族的不同性质分类 (一)少数民族生态环境移民 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移民是指“生活在生态脆弱、资源贫乏、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少数民族通过迁移实现异地开发、脱贫致富的人口流动形式”,[1]因此包括了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生态环境的恶劣导致少数民族无法顺利生产生活,被迫迁离原地而成为移民人口。例如陕南安康等地的山体脆弱,常年发生泥石流灾害,陕南三地启动了回族移民工程,安康县江口回民镇整体迁出;又例如陕北榆林、延安等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干旱缺水,造成地下水盐碱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神木县、靖边县、洛川县的彝族、壮族少数民族整体迁出。第二是针对某地区生态修复而进行的少数民族移民迁出。例如为了保障黄河、长江、澜沧江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内蒙古、青海、西藏等传统少数民族游牧社会向城镇社会过渡,迁出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少数民族共计一万余户约七万人口。第三是国家为了建立生态保护区而主动采取的少数民族移民搬迁政策。例如贵州荔波县喀斯特生态区在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之后,当地居住的布依族、瑶族成为生态移民的对象,政府通过扶持和补助的方式进行移民安置。可见,无论是自愿移民还是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生态移民都是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选择”,[2]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 (二)少数民族商业经济流动移民 少数民族商业经济流动移民是指少数民族离开故土到经济较发达地区谋求发展,划分为城镇化扩建移民与雇佣关系移民两种类型。首先,城镇化扩建移民,例如龙潭水电工程的库区移民,为了实现城郊扩建,政府出台了针对当地壮族、布依族的一系列扶持照顾政策,从食品营养充分到公共服务恢复,从旧的乡村组织解体到社区重建,从失业代工到再就业保障,“体现了少数民族分化与整合的社会变迁过程”。[3]其次是雇佣关系移民,例如从西部地区到中东部地区务工的少数民族,即是依靠生存技能实现异地安居就业,代表少数民族如南疆维吾尔族,“因为工业基础的薄弱,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少,维吾尔族的农村中青年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4]包括喀什市和附近县城农村待业人员,主要流向北京、深圳、苏州等城市,成为当地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生力军。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商业经济流动移民是围绕异地就业展开的城市经济建设行为,一方面供应商品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促成商品经济形态的再创造,即少数民族利用自身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为迁入地的商品市场服务。例如少数民族异地创业或社会投资的移民背景,通常经由大杂居、小聚居的个体经营形式,联合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民族文化商业街,代表少数民族如城市散居回族,他们以清真寺为依托,打造各大中城市的特色清真饮食一条街,不仅丰富了现代城市商业综合体的业态组成 ,还吸纳了大量当地少数民族毕业生留居工作。 (三)少数民族跨族通婚性移民 少数民族跨族通婚移民是由少数民族婚恋家庭关系的明显变化引起的人口转移,相较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整体性与商业经济流动的异质性,跨族通婚移民受到的传统性制约较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少数民族跨族通婚背景下的人口移民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族、蒙古族、傣族、彝族、回族、维吾尔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群体,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差异。例如哈萨克族跨族通婚的人口迁出地一般是汉族、达斡尔族地区,多为汉族、达斡尔族男性娶哈萨克族女性,原因在于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体制。哈萨克族男性牧民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迁往他地成为上门女婿的情况较少,而傣族男性与汉族女子通婚则刚好相反,傣族社会重女轻男,傣族男性结婚要为女方家做三年苦工,与汉族女性通婚也大多迁入对方所在地。同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也影响着跨族通婚的人口移民倾向,例如新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受到民族传统婚姻习惯法的制约,很少与非伊斯兰教信仰的汉族通婚。综上可见,“虽然少数民族跨族通婚的移民现象是家庭关系变迁的结果,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成因”。[5] 二、移民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 (一)移民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融入 少数民族移民脱离原有的生产生活空间进入陌生的地方,首先面临的便是对新的经济文化环境的适应融入。一方面,少数民族谋求物质资料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生产方式差异”。[6]例如为了保障黄河、长江、澜沧江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五万藏民离开世代居住的草原,搬迁到城镇生活”,[7]藏民牲畜饲养繁殖的自然方式被人工喂养替代,饲养成本、手段、时间等技术性要求需要习惯了露天放牧的藏族人重新实践学习。同时,伴随经济方式变迁而来的即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诸如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各个生活领域的社会适应问题。例如饮食方面藏族人喜食酸奶、牛酪,蔬菜也以野生蘑菇、洋葱为主,城镇定居以后,奶食的比例急剧下降,藏民生活开始更多的摄入白菜、萝卜等大众蔬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移民容易阻断迁入对象与故土的文化联系,例如龙潭水电工程库区移民的城郊扩建,布依族移民与城镇汉族人口的社会整合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城郊乡农区文化”,[8]布依族向汉族农民购买草料常常需要连比带画,语言杂糅的沟通障碍造成了移民对象心理与精神的双重负担,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婚丧嫁娶,布依族人都需要进行对日常生活模式的文化调适,例如布依族招待客人不喜欢出现红布或火堆,那意味着家里有产妇或病患,而汉族人却偏好在热闹喜庆的场合挂红灯笼、写红对联等等,如何兼容两者的民族习俗,规避文化禁区是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重要课题。 (二)移民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融入 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关系融入指向少数民族移民主体的社会人际感受与人际关系适应。一方面,少数民族移民的人际感受是指社会交往感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交关系网络发生了空间位移”。[9]例如跨族通婚性移民,以蒙古族与汉族通婚为例,蒙古族迁出地的牧民社会交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成年蒙古族男性的社会交往行为多发生在家族与村落之间,蒙古族女性的外部交往联系更是局限于婚庆、祭祀、节日等大型民族活动之中,通过跨族通婚性移民进入主流都市社会后,牧区的“走篷串户”与草原生活互助体例变为了高楼大厦的业缘关系,无论是城市社区的物理空间,还是少数民族移民与当地人的情感沟通都透露着人际交往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移民基于交往感受的社会关系营建,主要体现为民族关系,“即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与相互作用”。[10]例如商品经济流动移民,以回族城市经营为例,回族人一般以清真寺为依托,形成“围寺而居”的商业居住形态,在强化自身族群特性的同时,铸造了与当地汉族社会鲜明的文化边界,对于此类商业文化多样性的调和,不仅需要求同存异的民族融合观,还有赖于经济贸易的民族平等竞争关系打造。可见,少数民族移民的人际关系适应既指向社会生活接触,又指向社会经济活动的良性交互,对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民族关系的意义重大。 三、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哲学认知 (一)“现成人”与“生成人”的辩证关系 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蕴含着“现成人”与“生成人”的哲学辩证关系。首先,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是少数民族处于新环境规定之中的再生产过程,无论是生态移民、商品经济移民还是通婚性移民都提供了与少数民族原生环境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而原生环境所孕育的少数民族“现成人”需要生成崭新的社会特质才能融入其中,例如饮食特质、服饰特质、习俗特质等等,因此现代哲学认为“人并非自由生成,而是社会的预成之物”,[11]即少数民族作为物质实体,可以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环境预料其生成路径。其次,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中的“社会关系”随着生存空间的变迁而变化,而人对社会关系的适应则是人的超越性的体现,即人有选择、谋划、实践未来的超越性,它促使少数民族“能从以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身而出,从而创造崭新的社会关系”,[12]例如藏族生态移民的草原社交被城镇生活的业缘关系代替,移民少数民族通过抽离原生环境与重建社会关系实现“现成人”到“生成人”的嬗变。 (二)对疏离与异质感的困惑 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是生存境遇转换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文化割裂性,使得身处社会融入过程的移民人口存在疏离与异质感的困惑。对此,马克思人学观指出:“人的处境构成人的存在”,[13]少数民族移民意味着历史生存处境的中断,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都必然面对原有历史文化抽离的分裂阵痛,它是移民对象疏离与异质感困惑的来源,造成了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不适应。其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适应是自然环境适应与社会环境适应的综合,包涵着“必然的规律”与“非必然的规律”两部分。必然规律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无法摆脱的“历史感”,例如少数民族语言、信仰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移民少数民族无法对“必然规律”不假思索地使用,被迫转向对“非必然规律”的使用。例如布依族移民与城镇汉族社会整合的城郊乡农区文化生存,布依族人无法发挥先天语言能力(必然规律),通过连比带画并夹糅汉族语音词汇的方式进行社交沟通,对非本族语言的习得利用即是布依族移民借由非自身自然的语言规律重新组织生存资源的表现。因此,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非必然规律既不是少数民族原始所有,对其产生的社会适应也并非一劳永逸,只要发生社会时空境遇的转变,社会适应的“非必然规律”便发生变更,移民对象的疏离感与异质感体验将再次出现,因此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是不断获得非必然规律,并经由非必然规律建立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 (三)民族性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是从现实性方面对人的本质加以确证,即少数民族移民的经济文化融入与社会关系融入都体现了人依赖于社会现实的本质特征,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主要指向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民族性特征,是差异化的民族属性在决定着移民对象的社会改造内容。一方面,人永远无法摆脱民族性的物质划分与关系划分,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融入行为是处于民族境遇中的自身创构。例如为了保障黄河、长江、澜沧江地区生态屏障功能的生态移民,五万藏民搬迁到城镇生活,藏民牲畜饲养繁殖的自然方式被人工喂养替代,其经济适应内容虽然覆盖了牲畜饲养成本、手段、时间等各个技术要求领域,但牲口饲养繁殖的民族经济属性并没有被改变。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移民的自我更新创造同时也为移入社会提供了可被利用的有价值的民族性元素,以商业经济流动移民为例,回族人异地创业,主要依托清真寺文化,以大杂居、小聚居的个体经营形式,联合打造各大中城市的特色文化商业街,其作为现代商业综合体的业态组成,不仅吸纳了大量少数民族毕业生留居就业,还树立了回族伊斯兰教信仰的餐饮品牌。因此,移民少数民族社会融入并非是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摒弃,其民族性特质反而被纳入移民城市发展的一部分,用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