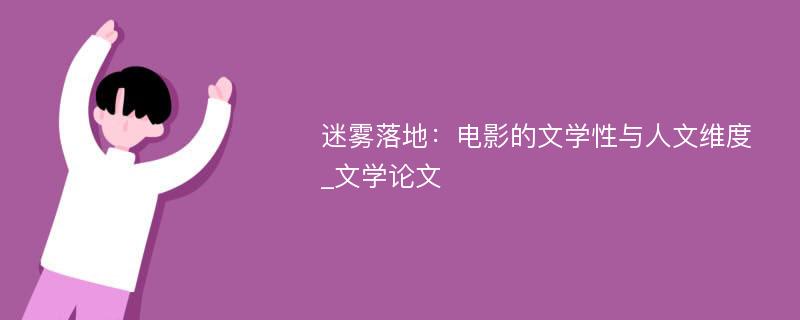
雾失楼台:电影的文学性与人文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楼台论文,人文论文,文学性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产大片,确实让人喜欢让人忧。一方面,国产大片吸引大量电影观众重回影院,让国产电影工业出现复兴气象;而另一方面,这些国产大片,如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等等,无论票房成绩如何,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部分电影观众的质疑和批评。
对于国产大片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即电影叙事的幼稚紊乱、人物形象的苍白单薄、影片的思想与情怀既不让人寻味更不打动人心,可以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进行讨论。放在文学性层面来讨论,当然是可以的。
若深究下去,应看到这些现象不仅是国产大片的问题,在其他各种类型的国产片中也一样存在。进而,这其实并非当下中国电影的新问题,而实际上是中国电影由来已久的痼疾顽症——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报纸上就曾公开讨论过“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这一问题,早就有传媒社论指出“大部分国产片的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① 可见类似的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在电影市场化的今天,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尖锐突出——在文学性的层面上,恐不易将这一问题说深说透。
深究下去,当涉及电影艺术的人文维度。
一
张艺谋的《英雄》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例子。这部影片的视听冲击力是第一流的,让观众享受一场视听艺术盛宴,正是作者主要创作目标。影片中场景恢宏、色彩缤纷、画面精美、新意淋漓,突出的缺点是它“目中无人”——首先,影片中的第一主角便叫无名,无名与他的几个看似有名的同伴如残剑、飞雪、长空,其实都不过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其次,作者的思想,说穿了不过是经过包装的犬儒哲学,片中的“英雄”竟是那杀人如麻的暴君。再次,作品中人物公然宣称“个人的痛苦不算痛苦”、“赵国的仇恨也不再是仇恨”,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个人情感和生命价值。又次,影片的叙事借鉴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罗生门》,但《英雄》的叙事变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说谎游戏,明显背离了黑泽明电影在叙事中做“人性的求证”这一深刻的思想主题。
上述问题,当然可以在商业大片的创作方法上去寻找原因,例如为了大场面而相对忽略具体人物,为了布局群星戏份而相对忽略叙事肌理,为了视觉冲击而相对忽略人文情怀等。深究下去,则是电影观念问题,张艺谋说:“我们有时候回忆一部好的电影,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过了多年一说起这部电影,你可能马上就能记得的是那些几秒钟的画面。基本上说的故事你肯定忘记了。这就是我们看电影的习惯,都是这样子的。”② 这一说法的要点,正是只见画面而目中无人,表明他并不真正了解、也不够尊重商业大片的广大观众。
商业大片的这种目中无人或“目中有人,心中无人”的创作观念和方法,正是这些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总是干巴发飘甚至发虚空洞的根本原因。张艺谋的几部大片是如此,其他导演的若干大片也几乎无不如此。商业大片的目中无人,当然与电影人缺乏文学素养乃至缺乏文学意识密切相关。
张艺谋等人的这种电影观念,直接来源当是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理论界关于“电影化”的讨论。当时,先锋人士鼓吹电影的现代化,电影视觉和音响意识的觉醒成为中国电影新时代的主潮流。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论文,③ 和钟惦棐先生提出的“(电影)与戏剧离婚”的观点,④ 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回归本体”的主流观念。这一主流观念不仅影响了第五代的电影观念,实际上也是由第五代导演付诸实践的。
这一思潮的背景,是此前中国电影的舞台化倾向十分严重,电影几乎成了舞台戏剧的简单记录工具——此前的样板戏电影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而那时的舞台化或戏剧化不仅体现在人物台词的舞台腔,更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和虚假做作,以及故事情节的概念演绎。如此,“丢掉戏剧的拐杖”、“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现代化”等思想观点价值凸现、共鸣强烈而成一时主潮,并最终载入中国电影理论史册。问题是,这些思想观点几乎不约而同地从电影的形式和技巧方面着眼,是否触及了中国电影弊病的根本所在?实在大有讨论的余地。
只不过,第五代电影视听本体舒张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文学叙事性的空泛与匮乏。虽然早有人指出这些作品中有许多“生吞活剥”且“偏重于画面造型,思想意念化,常常使人产生审美欣赏的困难,需要从外部对它进行解读”,⑤ 但在思变崇新的大环境下,出于对电影探索、电影艺术和电影新人的由衷热爱和珍惜,第五代的片面探索之作大多成了新时期艺术电影的宝贵珍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艺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第五代的另类,他表现得相对折中,证据是他在“丢掉戏剧拐杖”之后悄悄拾起了文学(小说)的拐杖。他甚至说:“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⑥ 实际上,新时期电影人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大多都没有当真丢掉文学拐杖,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黄健中的《小花》和《如意》、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吴天明的《人生》和《老井》,以及张艺谋转行导演之后的《红高粱》等多部影片,无不是根据小说改编。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的文学性问题自然被遮蔽,以至于被忽略。
直到电影和文学当真要分道扬镳,文学先锋愈走愈远,而电影则要开始面对市场面对观众,我们才恍然惊觉:太多的中国电影人不会讲故事,太多的中国电影缺乏文学性,乃至多数电影中的人物都“不说人话,没有人味”。即使如张艺谋、陈凯歌这样多次在国际影坛获奖,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优秀大导演所拍摄的商业电影也是如此。《英雄》、《十面埋伏》离开了小说,明显步履蹒跚,甚至连栽跟斗;《满城尽带黄金甲》照《雷雨》的葫芦画瓢,也不过人影飘忽。至此,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严重匮乏问题,才真正凸现出来。
早在十几年前,富有人文素养的名作家阿城就曾对张艺谋说过:“你们第五代导演,谁哪一天能跟侯孝贤似的拍自己童年的自传,我觉得你们干得也就可以了。”⑦ 我不能确定,张艺谋和他的伙伴是否真正懂得了阿城的话中之义。虽然张艺谋也承认自己的作品“缺少对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活生生的人的基本关注”,但却坚持“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台湾和大陆,一边以小开始,一边以大开始,都没有错误,我觉得都对”。⑧ 而实际上,从国家出发与从个人出发,不仅天差地远,而且南辕北辙。其间差距,恐不止是一个小小的台湾海峡,而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纪元。
二
在中国电影理论界,并非没有人关注电影的文学性。实际上,在新时期之初,针对电影本体化理论的片面性,张骏祥先生发表了《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一文,强调电影的文学性,甚至强调要用电影的特殊手段体现出文学内容和文学价值,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电影文学性的大讨论。⑨
张先生论文及其思想观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最主要的弱点是“电影即文学”的观点显然有些武断,甚至有些伤害电影人的自尊:正在寻找电影自立的电影人,如何能够接受电影不过是文学的手段或附庸的观点?
于是有了进一步的争议,郑雪来先生发表《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一文,⑩ 就明显要将电影特性置于优先地位。其后,余倩先生《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一文,(11) 试图调和双方矛盾观点;而谢飞先生的《电影观念我见——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则重申电影的艺术思想、艺术内容、艺术技巧三个层次不容颠倒。(12)
按照电影性与文学性调和论者的观点,中国电影大可建立影像形式和文学叙事的平衡双翼,进而健康地展翅翱翔。但结果却不幸并非如此。
在理论本身而言,无论是强调电影的文学性或是强调电影性与文学性平衡者,其立论虽也言之成理,其中却存在诸多暧昧与莫大难题。诸如电影的文学性与电影性的关系究竟谁主谁次、电影的影像性与叙事性的关系、文学价值及其思想价值有何异同、电影的思想性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若没有谈深谈透,而只停留在老生常谈,以至于了无新意,自难真正深入人心。
在理论上,对文学的两种界定几乎人所共知。即:其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二,文学是人学。这就是说,文学性要从两个维度去考察和理解,第一个维度即语言艺术的维度,文学性包括叙事性、戏剧性、抒情性。第二个维度即人学的维度,或者说是人文精神的维度,包括人文思想(价值观、思想内容及其想象方式与想象逻辑)、人文视野、人性经验和人文情怀。
一些人看到了中国电影中存在问题,多半从文学性的语言艺术维度去考察,认为电影的最大问题是叙事技术不过关,即不会讲故事,以至于故事情节漏洞百出,缺少戏剧性。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对文学的另一维度即“人学”维度的理解和实践方面。电影故事漏洞百出,其原因在作者忽略了人性的依据;而电影人物形象苍白单薄,则更是由于作者对个人心理与个性的蒙昧无知。按照“人学”标准,文学应该关心人、尊重人、探索人、表现人,而我们的电影大片最大的弊病恰恰是情节公式化和人物概念化,极端情况则是:不说人话、不做人事、没有人味、不通人情、缺乏人性,当然也就不能打动人心。长期以来,批评电影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中国电影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却依然如故。
当年钟惦棐先生提出电影与戏剧“离婚”,是希望电影不要舞台腔,不要装腔作势,不要弄虚作假。第五代导演之所以要蓄意创新,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前辈们的电影作品中存在虚假现象。而多年以后,更年轻的电影人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我的摄影机不撒谎》(13),言下之意,是别的摄影机会“说谎”——其实也未必是要说谎,而是其电影的故事和人物无法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空洞而虚假。
电影人物形象概念化痼疾根深蒂固,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电影作者对个人的存在缺乏知识、经验、想象力和创造性。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本位而至于个人的文化传统与革命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及典型化理论一拍即合,使得个人意识、个性价值及其个人情感欲望成为盲点,甚至禁区。因此,对个人的无知、无识乃至无视就成了中国电影的通病,甚至宿命。
前面所说的讨论电影的文学性所遭遇的莫大难题,就是流行了几十年的文学典型化理论。张骏祥先生的论文中说:“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写人,活生生的人。要有血有肉,不要概念。而且不是孤立地写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写,要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这些话非常正确,也非常中肯。问题是,这段话是在其所说文学价值的第二要点即“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这一标题下,它的前提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电影剧本必须首先提供的。”(14) 这样一来,想要创作“活生生的人”,就只能向理论云雾中寻。
典型化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被讨论了几十年,始终有人固守、有人质疑,似乎根本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典型论及其典型化规则曾被当成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不过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必然产物,即把政治性的话语理论当成了艺术的规则,进而把(政治)理论批评的话语当成了艺术创作的圭臬。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这一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在取消文学为政治服务义务即重建艺术本体的新时期,这一问题仍然说不清楚,人们对“典型论”的误解和误用却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界的莫大难题。
其中要害,与其说是理论家认不清,不如说是不敢面对政治与艺术的不同本位即不同的思维出发点。政治家、经济学家的思维和判断,以国家、集体为本位,总是要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出发,自是理所当然:而文学家、艺术家以人或个人为本位,总是要从个人的情感、个性、命运的认知和表现出发,更加天经地义。由于一元化传统,理论界对此不同本位或者无知,或者回避。似乎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根本无法共存,甚至势同水火。而不知道在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不同本位恰能组建成美妙的和谐结构。就连中国古人也知道君子和而不同,更不必说,个性的发展乃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其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说,在逻辑上有明显的薄弱环节。首先,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数量,无论多少都会存在逻辑问题。若是数量有限,即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算一个典型环境,每个阶级有一个典型人物,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都不过区区二种或三种(而“第三种人”或“中间人物论”在此前曾遭到无情批评),如此文艺创作的个性追求便成为空谈。而假若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可以无限量,即典型环境与假定情境可以相容、典型人物和个性形象可以一致,那么这一典型理论还有什么逻辑基础和存在价值呢?
典型化方法,说到底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思维的方法,也就是概括或归纳总结的方法。在这一方法之下,很容易会以“应该如何”取代“实际如何”,即用“想”代替“是”,用“理想”代替“真”,以至于艺术创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及其个人阅历会因为“不典型”而成为无用的赘物。从而实际切断或颠覆了“生活是艺术源泉”这一重要法则。如此,很难不出现概念化甚至公式化现象。
文艺理论界对“典型理论”的偏爱和固守,一方面是来自对经典理论的不假思索的信奉,即使明知是误解或误用也不敢越界寻求对经典理论的重新解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理论话语实际上成了许多理论批评家乃至艺术创作者对人性蒙昧无知的方便借口——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善恶区分始终压抑了真假识别,因而除了《红楼梦》等极少数着意于人性真实的凤毛麟角外,大部分文艺作品都停留在好人与坏人的脸谱化简单分辨,甚至固化为对善者(好人)神圣化与对恶者(坏人)妖魔化的简单模式。而典型化理论在中国,正是被极端简化成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人物识别模式,即将人物简单分为两类: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亦即道德的人物和不道德的人物。
无论典型理论原意如何,在中国都已经变成了蒙昧文化的精美包装。典型论中的先进阶级和落后阶级的典型代表,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好人和坏人的变相,或不过是中国传统民间“讲经文学”和“演史文学”的基本模式的简单推衍。而这种简陋的人学认知模式,其实不过是人类原始思维的遗传,即不过是5岁幼童的认知水准。由于缺乏现代化的人文教育,使得现代人仍保留了原始遗传的结构习性,而成年人的人性识别水准也大多停留在幼稚程度。这种状况,与文学艺术的人学要求,即追求活生生人物形象的艺术理想,实在是南辕北辙。
由于对典型论绕不开,说不清,或不敢说,以至于在当年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即鉴于“文学性的概念难于讲清楚、确定。语义学的争论无助于创作”,因而建议大家“少开药方,多开门路”。(15) 这一模仿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说法,本不无意义,奈何在混沌且最终走向封闭的语境之中,国人的思维已成定势,艺术想象不知向何方展开,“药方”固然无法治本,而“门路”也一样无法开通。
三
针对中国电影创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讨论电影的文学性,当然不无意义。毕竟,电影作为综合性艺术,其中当然可以有文学维度,正如电影中含有美术的维度、摄影的维度、表演的维度和音乐的维度。
然而,讨论电影的文学性也不无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容易模糊文学性与电影的关系,甚至可能异化电影的本体性。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没有任何理由将电影当成文学或其他艺术的附庸。
所以,中国电影中叙事不清、形象不活、人味不足等问题,与其说是因为电影的文学性贫乏,不如说是由于电影(应有)的第二维度即人文精神维度的麻痹或萎缩。文学有语言艺术和人学这样两个维度,电影当然也应一样,除了电影的视听语言技艺维度之外,也应该有其自身的人文精神维度。
在这一意义上说,在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人其实肩负了双重任务,其一当是重建电影的“电影性”即电影的视听艺术本体,即追求电影语言现代化;其二则是要重建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人文精神维度。
要建立中国电影的现代人文精神维度,须包括:第一,确立人文思想,首先是人文价值体系,即在社会语境中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即普遍尊重个人的独立、个性、尊严和利益。第二,拓展艺术家的人文视野,即站在人文的观点和立场观察和评价社会与人类活动,从作者或作品人物的个人角度表述其人文经验和感想。第三,丰富艺术家的人文经验,这包括重视并挖掘创作者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涵养,也包括借鉴一切人类人文艺术的经验和见识。第四,明确艺术创作的人文目标,即探索人性奥妙,讲述人文主题,丰富人类自我认知的资源积累。
只有在人文精神层面上,才能彻底说清楚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电影不仅有其独特的视听语言技艺维度,同时还有其人文精神维度。电影可以学习和借鉴文学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可以学习和借鉴文学的人文思想和情怀,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电影的独立性这一前提之下。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电影中存在的叙事方式简单、故事情节粗糙、人物形象苍白等等问题,与其说是文学性的欠缺,不如说是人文精神维度的欠缺或麻痹。也就是说,只有电影的人文精神维度真正舒张开来,中国电影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即不通人情、没有人味、没有个性等致命缺陷,才有望真正得到解决。
当然,有望解决并不意味着容易解决,更不可能立竿见影。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谈论艺术形象的个性与情感,艺术创作以丰富人文景观为目标,以及重视和培养创作者的人文经验,或许都不成问题;但到实际建立艺术家的人文视野,进而建立全社会的人文价值观念共识,则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理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艺术或文化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更大的语境中的社会理论与实践问题。所谓更大的语境,即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语境,亦即从传统的以集体为单元的家国社会向现代化的以个体为单元的公民社会的变革与进化语境。其核心要点,首先是要认识到个人的存在与价值——正所谓认识自己是人类最大的智慧,即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次,则是要让个人在所在社会中拥有合法的安置和发展的空间。
这一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上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完成的思想启蒙课题目标。(16) 新文化运动的要点,正是对人的启蒙,即个人价值的启蒙,亦即建立现代人文精神维度的启蒙。思想家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7) 因为人的现代化,正是文明现代化的真正目标;而现代化的人,则是文明现代化的真正动力源泉。(18)
改革开放新时期本是继续完成新文化运动启蒙任务的最佳机遇,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确实为此付出过智识与热情。新时期之初,曾有过一场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结果突然中止,不了了之。(19) 90年代初期,又有一场“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开始得热闹非凡,结果还是无疾而终。(20) 这一让人感叹且困惑的人文启蒙思想沉浮的历史,当然也可以从两方面看,积极的一面是无论如何总还是有人在思考并谈论人情、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这样一些话题,并且通过讨论和传播使得这些思想信息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历史影响。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人文思想屡受挫折,会使得人文精神积累和人文艺术创作在一个较低水准上徘徊不前。由于没有清晰的理论目标和明确的社会语境的支持鼓励,艺术家的人生经验和人文理想会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无所适从,因为找不到适当且通畅的思想渠道,部分艺术家的生活源泉甚至会变得干涸乃至堵塞。(21)
追思新时期之初的那场有关电影本性的大讨论,我们看到,电影界的前辈们曾为建立电影的人文维度做过艰辛努力。“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其实是新时期人性和人道主义讨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只不过,参与讨论的诸位前辈,不仅走不出典型论的迷宫,更不能(或不敢)提出电影艺术“思想性”的艺术家主体及其明确的人文精神价值目标,(22) 即没有人明确提出电影艺术要立足人文观点、发掘人性奥秘、伸张人文价值。如此主体模糊、目标模糊,在电影的学习、创作、欣赏和批评中,又如何能够建立起必要的人文维度呢。
在这样的更大的语境背景下,仅仅是进行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自然很难有真正具有建设意义的积极成果,电影的文学性或人文维度,也仍然只能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于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只能是“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单翅振动,而其人文精神之翼则在无形中悄然麻痹和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中国电影的先锋,也不得不倚靠着文学的(人文精神)翅膀,才能勉强平衡地飞翔。一旦离开文学的拐杖,电影的人文精神就立即捉襟见肘。这一问题,不可能在纯粹的电影或文学理论层面得到真正解决。
注释:
① 均见上海《文汇报》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1956年11月14日。
② 张艺谋答记者问,见佳明主编《笑论〈英雄〉》一书第120—12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张艺谋说看电影只会记得画面,而不会记得故事和人物,很可能是他的个人经验,因为他是电影专业人士即摄影师和导演;但他却说是普遍经验,认为所有观众看电影都是如此,未免大错特错。这就难怪他只重视画面,而不重视故事和人物。在该书的第122页,张艺谋还说:“坦率地说这个电影不是一个演员电影,可以说是个导演电影”,这就充分表明,演员(和演员表现的人物)都不过是导演的表意工具(传声筒),而不是电影的叙事重点,更不是电影的艺术目标。可见张艺谋其实是用“作者电影”即艺术电影的创作理念和手法来经营商业大片,进一步说明他对商业电影观众的不太熟悉、甚至不够重视。
③ 分别载《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和《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罗艺军先生主编的《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收入了这两篇文章,分别为第3—8页和第9—34页。
④ “与戏剧离婚”一说,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在一张开会请假条上写的,委托主持人在会上宣读,后以《一张病假条儿》为题,发表在《电影通讯》第10期;一段时间之后,钟先生又写了《“离婚”一案》的短文,发表在1980年8月6日的《北京晚报》上。这两篇短文后来都收入作者的电影论文集《起搏书》,前者在第232—235页,后者在第236—23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⑤ 见封敏主编《中国电影艺术史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485页。
⑥ 张艺谋语,见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2页。在同一社会条件下,文学的人文维度相对健全,而电影的人文维度则严重萎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可能的答案包括:文学毕竟是个体劳动,而电影则是集体劳动;文学创作无需审查报批,而电影则无此幸运;文学的人文维度已成普遍共识,而电影的人文维度则至今少有人论及。
⑦ 张艺谋转述,同⑥,第107—108页。
⑧ 张艺谋语,同⑥,第105—106页。
⑨ 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的发言》,原载《电影文化》1980年第2期,收入罗艺军先生主编的《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35—53页。需要说明的是,张先生并不是要用文学取代电影,甚至也不是要用文学性取代电影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曾著文要求编剧要掌握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而80年代则强调“电影就是文学”,只不过是希望电影不要“舍本逐末”。
⑩ 载《电影新作》1982年第5期,《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54—66页。
(11) 载《电影新作》1983年第2期,《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67—75页。
(12) 载《电影艺术》1984年第12期,《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103—114页。
(13) 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一版。收入章明、姜文,张元、王超、路学长、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先锋导演的采访录、创作谈和作品简介。
(14) 同(9),第42—43页。
(15) 于敏《少开药方,多开门路》,原载《电影新作》1983年第2期,见《1920—1989: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89—102页。
(16)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大课题,其一是文化工具变革运动即白话文运动,其二是文化精神变革运动即人文启蒙运动。前者圆满完成了,后者却并没有完成。李泽厚教授说“五四”人文启蒙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启蒙主题被救亡主题所阻遏,这一论断听起来不无道理,实际上有些似是而非。假如没有抗日战争,即启蒙不被救亡所中断,中国新文化启蒙就一定能够完成?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说到底都不过是蒙昧政治专制。而蒙昧的政治专制文化恰恰是个人解放和自由的真正阻碍。很难想象,在那样的专制而又蒙昧的文化条件下,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能够顺利完成人文启蒙的划时代重任。
(17)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31页。
(18) 人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真正基础,若没有这一基础,那么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即使能够建成,也不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现代化。因为没有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是畸形的现代化。正如没有人文精神维度现代化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畸形的现代化,否则,我们又怎么会回头来讨论电影的文学性或人文维度的问题呢。
(19) 中国文坛有关人情、人性等问题的讨论并非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即从1957年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等重要论文开始。这些观点很快就被批判,作者也都被打成右派。但在1960年、1964年的中国文坛,仍有人提出相关的问题,结果还是被批判。直到80年代初期,人情、人性被再度提出,并且与人道主义思想明确挂钩,三者联系在一起讨论,结果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被迫中止。
(20) 人文精神讨论的热潮是1993—1996年间,这一讨论难以深入,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参与讨论者思想理论水准方面的原因。例如将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发展对立起来这一虚伪命题,就证明一些论者根本没有将人文精神问题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和人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近年来,人文精神的讨论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但看起来还是难以深入下去。这一现象本身,就非常值得思索和研究。
(21) 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虽然没有接受完整正常的中学教育,却因为上山下乡或参军做工而富有人生经验,但由于找不到理论的框架结构使得这些经验可以发挥较大的艺术思想效应,因而在第五代早期的作品中,几乎与自己的实际人生经验毫无关联。对于中国电影创作而言,而无疑是一种重大损失和遗憾。“第六代”导演曾有所改变,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成长故事”,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投入艺术创作之中,但因为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处于“地下”状态,这一创作思潮自然就很少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第六代”导演何时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自我认识推广为普遍的人性认知,进而变成其创作的源泉,看来也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
(22) 在大多数参与讨论的论文中,都有“思想性”这一维度,但几乎所有论者对思想性的究竟都是语焉不详。在过去的30年间,思想性几乎等同于政治性,所以艺术思想也就几乎等同于政治思想,因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艺术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新时期之初,政治领导人主动提出废止“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之说,即将思想的主权交给艺术家,以便让艺术思想——在思想主体、目标和方法上——有别于政治思想。但我们看到,在电影理论界至今也没有人提出电影的“思想性”,应该沿着人文维度展开。所以,电影的思想性,至今是一个模糊概念。甚而,仍有很多新老电影人,仍习惯于服从甚至听命于领导的思想。
标签:文学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电影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艺术论文; 英雄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张艺谋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