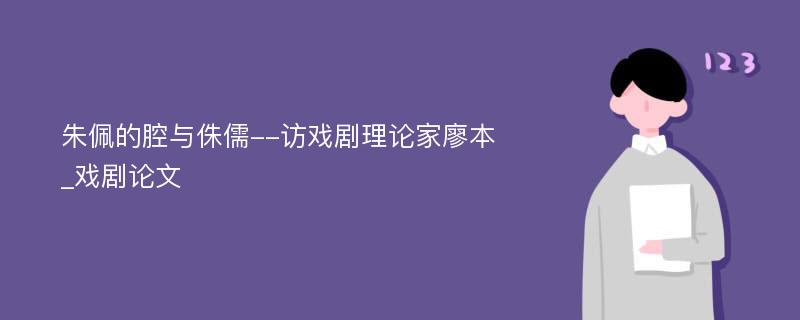
鞠萍腔与侏儒化——访戏剧理论家廖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家论文,侏儒论文,戏剧论文,鞠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些电视台的儿童节目里,幼稚病常常是普遍现象,如播音员装小儿腔,最典型的就是带有嗲音的鞠萍腔
记者:廖奔先生,你是一位研究戏剧多年的学者,又是2000年全国儿童剧会演的评委,今天的访谈话题可以宽泛些、随意些,当然尽量集中在有关少儿的话题上。结合长沙16台剧目的演出,能不能请你谈谈当前儿童剧创作或者说有关儿童题材创作演出中存在的问题。
廖奔:2000年全国儿童剧会演中,我感到我们的儿童剧观念真的比以前成熟多了。当然也有失败的作品,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创作观念的倾仄。
儿童剧创作的规律是要遵从儿童的思维特点。什么是儿童的思维特点?可以说出许多方面,幻想性、奇幻性、情趣性、情绪性、行动性、参予性、反逻辑性、反准则性等等。但在创作实践中,也容易加进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例如:幼稚性。虽然,低幼儿的行为包含幼稚成份,给他们看的戏也应充分考虑到对象的理解力,但幼稚性不是儿童剧的因素。作为艺术,儿童剧的立意和表现手法决无幼稚性可言。
最容易犯的幼稚病有两方面,一是将对象视作白痴、低能儿,而用十分浅显的道理来开导他,久而久之使他们向弱智靠拢。第二种幼稚病是表演的装痴卖傻。童趣和装痴卖傻决不能画等号。一个演员如果用装痴卖傻作为手段来扮演儿童,立刻就会给人厌恶感——儿童不可想象这是自己的伙伴,家长也不可想象这是自己的孩子。在一些电视台的儿童节目里,幼稚病常常是普遍现象。例如提问不具智慧性,常常是一般儿童常识性问题,角色装作回答不出,另一人再来一本正经地开导他。又如播音员装小儿腔,最典型的就是带有嗲音的鞠萍腔,这种腔调的前提是把对方当作仍在呀呀学语的低幼儿或者弱智,假设他还听不懂正常语速与腔调下的发音,即便如此,通常也只需要减慢语速或重复即可,而使腔调带有嗲音则是使人走向侏儒化的行为。在中央电视台宽广的播映范围和强大的收视率面前,真不知有多少儿童因此而被动减智。我的孩子上小学,见到这种情况我就坚决让他跳台或关机,不要影响了正常心智发育。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一点,儿童剧演员的形体年龄要与角色年龄尽量接近,如果不具备条件,最好不演。
与一切戏剧作品一样,儿童剧也要有智慧,要富有启示性,要带给人以聪明的愉悦,更要能够启发儿童心智的成熟。这次会演里的《少年华罗庚》,是在舞台上处理数学智慧的成功范例,因而受到中学生观众的热烈欢迎,它的前提是假设观众都是智者,戏剧是智者的对话,然后再来解释数学问题。
●今天一个中学生的知识积累,超过自己父母的范围常常大得惊人
记者:在家庭里,我们都承担着“父亲”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在社会上做为戏剧工作者,我们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呢?一部优秀的儿童剧应该具备哪些因素?中国有几亿少年儿童,怎样看待今天的他们?
廖奔:从智慧方面说,现代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早熟。科学知识的丰富和多种多样的现代传媒手段,促使这个过程大大提前和缩短。那些自觉进行优育的胎教和殚精竭虑的早期教育就不说了,一个最为直接有力的手段就是电视屏幕的影响,电视把全球和古今中外拉在一起,把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拉在一起,把教育和音乐、舞蹈、戏剧、诗歌拉在一起,把自然地理和环境保护拉在一起,成为一个最大的万花筒式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很快又要被电脑网络所补充和取代)。成千成万的城市和农村儿童,每日把许多时间消耗在电视里面,从中汲取的东西,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是成人往往想像不到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孩子说出来的大人话经常使你吃一惊。不要总是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我们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而已。平心而论,今天一个中学生的知识积累,超过自己父母的范围常常大得惊人。
我参加过一个儿童剧院的戏后座谈。一位中学教导主任提要求说,此剧很有教育意义,就怕同学们不容易理解,是否在开场前先给他们介绍一下剧情大意?紧接着一位中学生发言,说是这个戏太浅了,我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人物命运发展没有波折,剧情缺乏悬念——认识竟然如此大相径庭、针锋相对!而且很明显,后者在文学修养上远远高于前者。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成年人反思吗?
●儿童剧更为讲究艺术
●儿童之间信守诺言、不告密、不传话,这涉及到人类的信誉、承诺、尊严和隐私等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西方影剧中这时候常常支持儿童,而我们的影剧往往相反
记者:能不能进一步给儿童剧作一个界定?能否结合具体剧目谈谈?
廖奔:不要以为儿童剧就一定是小儿科。一部好的儿童剧,决没有观赏年龄的限制,不仅大小年龄的儿童都适应,成人也同样可以从中得到感染和启迪。儿童剧也是艺术,而且给儿童看的艺术,是更为讲究的艺术。
儿童剧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注意它的立场性。所谓立场性,就是站在什么基点上说话。首先要摆正观演关系,演出和观众双方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非对峙的,不是我居高临下地来教育你,就像在学校里经常看到的师生关系似的,而是让我们一起去剧作中进行体验和感受,这样儿童在接受时才不产生逆反心理。其次,在表现手法上应该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真情去感染儿童观众,而不是耳提面命式地向他们强迫灌输。许多社会普遍准则,成人自己往往不遵守,例如诚实、守纪律、维护公德等,但他们会要求儿童去履行。其实文艺作品的功能都是感染式的,其更直接的目的是美育而不是教育,在这里教育是通过美育浅移默化地实现的。看过一部戏,让师生开个座谈会,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最习惯性的词汇就是:这个戏非常有教育意义……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似乎戏就没有可谈的了。为什么成人可以娱乐,儿童就只有接受教育?儿童更需要娱乐,只要是健康的娱乐,就可以有益于身心发育。所谓“寓教于乐”,讲了几千年了。其三,立场还与观演对象的年龄段有关。对于低龄儿童,创作要强调想象力、神奇性、幻想性、童趣,适于采取童话故事、科幻故事的形式来演出,像这次的《寒号鸟》《想变蜜蜂的孩子》《白雪公主》等,但如果表现低龄儿童的现实生活则要慎重,因为扮演的难度过大,内容又容易走向幼稚。对于青少年观众要强调青春性、先锋性、独立思考性,这是一个强烈要求摆脱依附而在心理上充满反叛精神的年龄阶段,他们自认为已经十分成熟,最讨厌的东西就是幼稚和把他们当小孩,像这次的《月光摇篮曲》《享受艰难》都很不错,而一个最好的实例则是前两年出现的《未来组合》。
儿童剧的立场性,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它的实际立意上。我们说,一部好的儿童剧,它的立意应该博爱,给人以爱心和人间真情,应该以人类的基本准则为原则,如这次看的《春雨沙沙》《月光摇篮曲》等。有些儿童的立场总是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徘徊,最后以教师的立场为归宿,这是创作目光短浅的表现。克服这个矛盾的认识论基础在于:局部的行为规范应服从于人类的基本准则。举一个例子,儿童之间信守诺言、不告密、不传话,这涉及到人类的信誉、承诺、尊严和隐私等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西方影剧中这时候常常支持儿童,而我们的影剧往往相反。正面宣扬和表彰某人向教师的泄密行为,这种道德倾向发展的结果,我只能联想到汉奸。这个问题关系到民族素质,所托者大,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又如,儿童有许多活泼灵敏的天性,在单纯强调纪律和服从的时代往往就被扼杀了,但在强调素质教育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与旺盛的创造力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