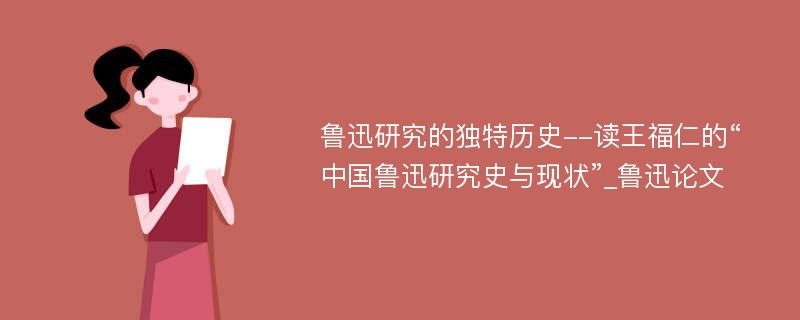
一部独特的鲁迅研究史——读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独特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富仁先生曾将他这一代学人与他的学术前辈及后辈加以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来,我们的爷爷辈和叔叔辈重视的是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我们重视的则是在各种主义背后的人。我们的弟弟辈和侄儿辈,则成了新的主义的输入者和提倡者,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宽广了,但讲的又是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至少暂时是如此。”(《王富仁自选集·我走过的路(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页。)在对人的问题的执着追问与审视中,王富仁带着丰富的生命体悟与深切的现实人生关怀,走进他的研究天地,奉献出一系列充满智慧、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成果,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不断地给当前有些沉闷、过于注重学理、有意无意忽略思想个性的学术界带来不可抗拒的冲击力。他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下均简称《中》。1994年《鲁迅研究月刊》分11期连载,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以其思考的深广与圆熟,在思想水准上甚至超过他的曾产生巨大学术影响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与汪晖的《反抗绝望》同为20世纪鲁迅研究领域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创意、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经典。在这两部优秀的著作之间,《反抗绝望》对鲁迅精神的复杂性进行充满哲理思辨式的探讨,而在语言风格上显得略有些艰深与生涩,给普通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中》对鲁迅研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评述,语言风格平易流畅,用纯熟的语言传达出深厚的思考,正如王富仁自己所说的:“当一个评论家的语言概念至少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时候,他才能够准确地掂量出它的分量并正确地使用它们,发挥出它们传达思想和感情的职能。”(见《中》第97页)
《中》给人印象很深的是高屋建瓴的气势与举重若轻的自信。鲁迅研究在长达80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显学,而对这门显学发展历史的探讨,无疑是踏入一座令人生畏的迷宫,研究者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材料面前,要么被它们淹没以致迷失自我,要么驾驭它们凸现出研究主体的个性。王富仁凭借他对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即文化由人创造,又制约、影响着人的各项活动(参见王富仁的《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4页),从文化心理这一独特视角观照鲁迅研究者进行鲁迅研究所依据的文化立足点,探索出不同的鲁迅观背后的不同组合方式的文化心理,这好比由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进一步探索出隐藏于水面之下的冰山主体部分,从而更通彻地了解整个冰山和浮出水面的部分。由于王富仁找到了文化心理这一他所擅长的切入点,故他在一大堆迷宫式的研究材料面前,丝毫不怵,具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从而使他的创造力轻松自由地释放出来。
首先,作者的创意在于根据在特定时期各个具体分散的鲁迅观所赖以产生的相近、相类似的文化心理,综合出不同的鲁迅研究派别:奠基期的对立批评、青年浪漫派、社会——人生派;形成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派(包括青年理论派、务实派、实践的政治革命家、精神启蒙派)、人生——艺术派、英美派;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国家政治派、业务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英美派。这些不同派别的概括,从纵横两方面简明扼要、立体式地建构出鲁迅研究史。
书中以文化心理为立足点,对各派的鲁迅研究给予宽容的理解和有力的评价。如针对奠基期以成仿吾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的鲁迅观,作者认为成仿吾等人对鲁迅小说误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理解、体会鲁迅所描绘的艺术世界,“他们没有感受到传统思想的压力并且也不想去感受了,他们没有陷入社会人生的旋涡并且也不必陷入了,因而鲁迅作品所描写的那个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只能用某些文艺理论的标准(如再现的与表现的,典型的与普遍的等等)对鲁迅小说的外观外貌进行衡量,从而失去了在鲁迅研究中做出有实质意义的结论的可能。”(见《中》第12页)在理解的基础上,作者没有苛责成仿吾,“因而我们不能把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视为他对鲁迅的攻击。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不是有意攻击便认为他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做出了什么贡献。”(见《中》第13页)
再如对形成期的英美派的鲁迅观的分析评价,过去学术界习惯于从政治立场上、将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作自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御用文人来简单地否定他们的鲁迅观,而王富仁认为英美派是以从西方学来的文化理论和自己当时自足封闭的学院式的人生态度来认识鲁迅及其作品的,难免有理解、沟通的障碍,所以他对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出现的迄今为止对鲁迅施行的最激烈、最全面的攻击也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并大胆地肯定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价值,“她的这些观点也正是不少同类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过她更真诚些、更不顾及自己宽容中庸的道德外表,因而她把同类知识分子的看法公开发表了出来,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多需要解决的有价值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对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见《中》第76页)
在我们的印象中,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收效甚微,充斥着对流行政治口号的诠释和对同行的异己的政治批判。而王富仁细心地发现当时业务派的存在,并揭开蒙在他们身上的流行话语的外衣,肯定他们对鲁迅及其价值的曲折阐释和认识,并大度地认为所有这些人的所有著作都应视为学术派的鲁迅研究,因为“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时流行的话语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的,这一点连鲁迅本人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重要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时代所作的严肃、有价值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程度如何。”(见《中》第142页)
新时期的先锋派鲁迅研究花样繁多、更新颇快,的确难以分析,作者在肯定该派为中国鲁迅研究带来种种活力的同时,也指出该派在对西方研究方式方法引进时,热中于追新逐异,忽视与国内鲁迅研究的对接,妨碍了自身以中国鲁迅研究的特殊实践丰富发展西方原有的方法论体系以形成自己独立学派的可能。作者的宽容理解和富有见地的评价来自于他对研究对象文化心理的熟稔,即他善于体察每一派鲁迅观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在领会到不同派别为什么如此评价鲁迅及其作品之后,自然不难理解不同派别的鲁迅观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其次,王富仁在对鲁迅研究不同派别的文化心理深入分析的过程中,生发出很多关于文化及知识分子命题的精辟见解,形成对20世纪文化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变迁史的自觉思考与阐释。这些议论似乎“旁逸斜出”,好像与鲁迅研究无直接关联,但仔细一想,莫不息息相关。对鲁迅进行评价与研究的正是各个时代颇有文化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不同鲁迅研究派别的生灭、分化与组合也客观地折射出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特点和命运变迁;而不同派别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正是参与和文化有关的活动,鲁迅研究逐渐成为20世纪文化中的显学,鲁迅观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思考本身也深化、丰富了对鲁迅研究的探讨,对鲁迅研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有了深入、明晰的把握,才会有对鲁迅研究的真正研究。
在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评价上,《中》以鲁迅为重要参照,将鲁迅与20世纪其他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如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代表着从文学革命的角度切入新文化运动的倾向,陈独秀代表着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切入新文化运动的倾向,而鲁迅是把这两种倾向最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最杰出的人物。在随后的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中,陈独秀、李大钊转入实践的革命政治;胡适为代表的一派知识分子走向重学理轻实践的学术研究道路;鲁迅、周作人坚持着中国社会精神改造的目标,但周作人因自身性格的懦弱和迫于日益险恶的现实环境的压力而渐趋温和、削弱叛逆性,以至堕落为民族的叛徒。只有鲁迅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仍坚守着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不断寻找着扩大自己思想影响力的空间。
又如与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鲁迅所追求的理念是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相交融以至不可分割,而二三十年代陈西滢、梁实秋等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仅仅是观念、学术式的,并未内化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外在于生命的学理性的存在。
再如鲁迅与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差别,鲁迅在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之后,并未消融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以迁就客观上与自己思想观点存在分歧的左联领导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更多地以政治的组织原则对待自我和政治实践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他们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见解与文学见解来迁就、服从实践政治家的思想和政治组织的意见,这样为解放后的社会悲剧和知识分子自身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在对待外来文化思想的与众不同的立场上,鲁迅更体现了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独异个性,他是将不同的学说融入到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中从而不断深化、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像其他的众多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思考容纳、整合到一种权威的思想学说中并在这种思想学说的掩体下安身立命。鲁迅对中国思想发展的重大意义,正如王富仁所评价的:“他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做的是最基础也最具重要性的工作。他把中国人从各种思想理论的掩体中拖出来,使他们首先感到一种思想和精神的饥寒,正视自己,正视社会人生的矛盾,并进而在自我的真实的人生体验中建立自己真正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精神归位的工作,一种克服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工作;任何真诚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学说都必须有赖于这种需要而创立,也必须有赖于这种需要而接受。”(见《中》第55页)
通过对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对比,作者烛照出鲁迅身上为其他知识分子、包括后来肯定他的研究者、追随者所不具备、所缺失的诸多可贵精神,如批判性、独立性、对受迫害者的感同身受等,这些精神也正是当今我们处于学院内的知识分子所匮乏、所应汲取的可贵品格。鲁迅的精神高度为每一位要走进他的研究者提出了客观的挑战与召唤:只有研究者真正具备自己的独立思想并能与鲁迅的精神相通时,才有可能对他进行理解与阐释。
《中》还对在鲁迅研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有关文化现象、文化格局、文化组合变动趋势等进行提纲挈领的评述,既有历史的总结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如在评价新时期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时,作者积极肯定该派对鲁迅精神复杂性的分析,认为鲁迅的精神复杂性恰恰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带着宗经宣道传统的中国现代多数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也为在一个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所排斥,以至中国出现这样的文化格局和发展趋势:“一种学说因其特定的原因而压倒其他的所有学说成为中统治地位的思想、一时呈现出绝对真理的面貌,但在同时它也压抑了其他所有具有相对性真理的思想文化学说而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相对性。在这时,它越来越把自己的权威性伸展到无法起到认识作用反而足以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文化语境中去,以自己的荒诞性表现而显示其他所有思想文化学说的存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这样,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过多地占领了不适于它表现自己的作用的文化语境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受到压抑的思想却因自己潜在的能量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崇拜,其他所有思想文化学说的发展则又是以绝对排斥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为基本前提的。……那种在排斥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学说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一种思想文化学说便以新的统治思想占领整个中国社会,从而把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学说重新压抑在中国文化的底层,连它们自己原本具有的真理性也不再被人认识、被人接受。但它们又会像其他被压抑的思想文化学说一样等待着现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学说的自行溃灭……”(见《中》第209~210页)作者善于将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加以综合思考,探索出内在的联系。如二十年代末的青年浪漫派开始贬低鲁迅后来推崇鲁迅,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由个人崇拜开始而以反对个人权威告终,都是出于同样的文化心理:中国青年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企图借助于个人崇拜或否定一切权威的方式让社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中国社会这种习惯于按固有的权威衡量青年在新条件下的新追求的文化趋势,“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浪漫派,把青年的旺盛的生命力投入到李逵式的盲目拼杀中去,然后又在反对他们的盲目中否定自我和整个社会的一切形式的生命力表现”。(见《中》第233 页)作者在人们熟知的文化现象的背后敏锐地洞察到不容忽视的文化症结,引人深思。
王富仁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心理的深刻理解,故能驾轻就熟地在约16万字的篇幅中对鲁迅研究作出富有启示性的阐释。作者的出色探讨也为将来的鲁迅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鲁迅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仅仅学理的研究不足以挖掘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内部潜力,甚至也无法真正读懂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研究者真正进入了同鲁迅一样的思想追求过程,我们才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不断变动着的社会体验、思考、研究他的作品。”(见《中》第243页)
《中》是一部思想型的鲁迅研究史,同时也是一部20世纪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命运的剖析史,发掘出迄今为止我们所忽略、所回避的文化思想问题,促使我们与作者一起去思考、去面对。在这个思想贫瘠、缺乏思想家的时代社会,我们或许从王富仁、汪晖等思想型的学人身上看到一丝希望:纵使他们没有成为思想家,但他们至少是孕育、催生思想家的泥土。
标签:鲁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